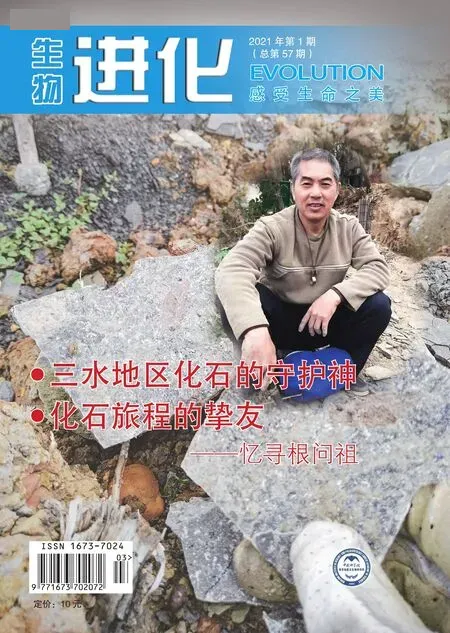春风首度玉门关
——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接待与回访的追忆
2021-06-17廖卓庭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起步,“科学的春风”吹进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大院,学术研究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现转折,从此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作为见证变化过程的过来人,追记当年亲历令人感到既亲切又欣慰。
由于有厚实的研究基础,又有门类齐全的研究骨干,再加上中国南方(东特提斯域)得天独厚的地质条件,南京古生物所研究晚古生界地层古生物的同仁们,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调查晚二叠世含煤地层(响应号召,扭转北煤南运)的实践中,已经注意到二叠、三叠系界线(以下简称“T/P界线”)这项世界级前瞻性研究的价值。赵金科、盛金章老师等也都凭借以往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收到过参加1972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召开的以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研究为主题的会议的通知……然而,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既然不能成行,有关的交流讨论也只能是“空谈”。
1978年,改革开放萌动,国际交流刚刚起步,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的同行专家,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来华科学考察的可能。当年5月,加方向中科院提出了与南京古生物所开展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中国南方 T/P界线地层的要求。由于时机恰当,他们的合理要求立即获得中科院的积极响应,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合作互访协议。以至于加方的这个考察团,竟然成了“文革”之后,中科院接待的第一个外国“大型”学术团体,享受了中科院外事局长全程陪同、受访地副省级首长接见和招待的特殊礼遇。
加方T/P界线考察团共5人,其中4名专家分别来自加拿大地调局、 高校和石油公司,另一名是石油公司的华裔技术员(充当自带的中文翻译)。专家们各有专长,分别研究二叠纪和三叠纪菊石、构造地质和孢粉。在中国考察停留的时间是1978年10月中旬至11月初(共22天)。由北京入境,在院部谈妥合作事宜后,立即由院外事局长苏凤霖和翻译小吴陪同抵达南京古生物所。 此事在当时,不论是所领导,还是与此相关的我们专业研究人员都感到有些“唐突”。好在有院外事局苏局长“统揽全局”,所领导迅即响应,盛金章老师带领的学术接待小组顺理成章“对口”建立。很快,双方之间的学术交流和野外合作考察的具体方案得到落实,次日考察孔山剖面后,双方甚感融洽。
当时接待工作中发生的一件“小事”是需要特别追记的。加方考察团长在做学术报告之前,我所计划科负责接待工作的徐均涛同志,在所布告栏出了一个通知,内容是“欢迎有兴趣听外宾学术报告的同志自由参加”。这个“告示”在当时极为“新颖”,苏局长知悉后深表赞同。这件由我所首开先河的“小事”,在他回京之后,竟然通过院外事局下达专文,鼓励中科院各所仿效——过去听外宾的学术报告,可是有很多禁忌的。
离开南京后,加方在我方专业研究人员陪同下,先后考察了浙江长兴煤山、江西丰城老山和贵州安顺轿子山等地T/P界线地层剖面。良好的自然(或者人工稍加清理的)剖面,丰富的主门类化石,再配以我们接待人员专业的介绍,加方研究人员感到很满意,留下良好印象。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多年前已做过的调查研究。
在华南四省的考察过程中,加方人员一直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入住的都是“国宾”级酒店,如当时的金陵饭店、杭州饭店、云岩宾馆等。各地的宴请也五花八门,名贵高档菜肴不断,仪式从“不知所措”到“盛况空前”,如在轿子山煤矿的那顿午餐,竟然出现省、地、县、区、乡加煤矿领导等百余人的盛宴(十五、六桌)。
总之,对于这次来华的合作考察,加方是十分满意的,特别是在专业研究方面,我们提供的观察剖面和化石资料让加方研究人员感到如愿以偿,用加方团长事后的一句表述:“一切超乎我们原来的想象……”此后,双方的后续合作研究迅速展开。
改革开放之初的这次接待,既是南京古生物所学术研究领域和研究人员面向国际的初次锻炼,也是我国得天独厚的T/P界线地层研究首次向国际的真实展现,特别是自从加拿大考察团来访之后,国际上要求与南京古生物所合作研究并来华考察的请求“纷至沓来”“(不请)自进来,(免费)送出去”的局面迅速打开。改革开放让我国的古生物学研究和南京古生物所的发展受益匪浅。
再说说我们回访加拿大的情况。根据对等原则,中方回访加拿大的T/P界线考察团,成员也是5人,按照院部安排,南京古生物所派出的四名成员分别是菊石、䗴、腕足、孢粉专业研究人员。另一名成员院部分配给北京地质所(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尽管当时地质所沉积室有多位长期从事二叠、三叠纪地层古生物研究的人员,但该所派出的却是沉积室的支部书记(此人学的是金属矿产)。考察团由王义刚任团长,在加停留的时间是,次年(1979)的8月中旬至9月初。
我等都是第一次出国,当年我40岁,是成员中最年轻的。当时出国的物质准备:按规定,由中科院南京分院出具证明,每人先购买高级皮鞋一双(实报实销不超过25元);再凭证明到南京最著名的李顺昌布店做西装一套,由店里最“老牌”的李师傅裁剪制作(报销上限 120元);行李箱由南京古生物所器材科购借;再到北京参加近一周的“出国集训”后,在中科院的地下库房,选借西装一套、领带两条、公文包一只。用这些“道具”武装起来的我们,走到哪里,都显得突兀、扎眼。我们尽管感到别扭难受,却也不得不像龙套演员那样,循规蹈矩,害怕出格!
关于专业研究的回访准备,作为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大原则是清楚的。但具体的出国“目的要求”,所领导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因为他们也还没有出过国),我们也就根据自己当时对“环境”的认识理解,各自行事。就我而言,除了事前参阅可能考察地区(落基山)地层和腕足类资料外,我想好了要利用这次机会,从加方得到一些北极地区标本,带回国内研究比对;另外,我还带上一篇已经完稿,可付梓出版的学术论文。
我们进入加拿大的第一站是温哥华,加方接待者只有一人,就是来华考察团的成员蒙格(Monger)博士。当我们来到他就职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地调所才知道,他是这个地质调查机构(总共14 人)唯一的地质专业人员。他一个人统揽从野外调查填图到室内成图出版的全过程,他的过人能力和效率令我们震惊!因为,一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差不多是我们4、5个江苏省的面积。
我们还在为长途旅行和时差反应的疲劳做调整,温哥华附近的野外考察却已经开始。由蒙格博士掌控的考察安排得非常紧凑,参观访问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系和太平洋海洋研究中心等礼节性成分较重的项目,都被他安排在野外考察的间隙。这让我们很快感受到,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他在为让我们尽量多看一些野外地质地层,珍惜时间和机会,尽心尽力。
特别让我们感觉新鲜和实在的是,宴请我们考察团的“仪式”,是由他夫人协助操持,在他家后院,与他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派对,尽管我国驻温哥华领事馆派了副领事来参加。
数天之后,蒙格博士和他的老师丹纳(Danner)教授,开始带领我们进行总行程约1700公里的野外考察。从温哥华至卡尔加里,我们穿行在峡湾、深谷、高山、泥石流、石漠、冰川和无边的大森林之间,从雾气浓厚的海边到极度干旱、终年无雨的死谷,让我们“走马观花”板块结合部位,考察造山带多样化的地质地貌。每日新鲜而强烈的感观印象,以及似懂非懂(我的外语水平不佳)的理性认识,莫大地激发了我的专业探索兴趣,更明确了地层古生物基础资料在确定造山带构造格局和形成演化中的重大作用……这一系列客观印象,实际上对我后半生20多年承担新疆地层研究都是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尽管这是我后来才觉察到的收获。
幅员辽阔的加拿大,艾伯塔省是最主要的产油区域,而卡尔加里是加拿大石油公司和石油地质研究机构的中心。我们着重参观访问的是沉积岩和石油地质研究所,该所集中了加拿大大部分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在这儿,我第一次有幸观察到来自极地内的二叠纪腕足类标本,还获得数枚(我想要的)赠与标本(后来成为南京古生物所腕足组博士生的研究材料)。同时,当加拿大地球科学杂志主编,友好地主动向我们考察团索要稿件时,我有幸满足了他的要求。那篇《中国南方T/P界线地层腕足动物组合》,也成了改革开放以后,南京古生物所在国外学术刊物上最早刊出的研究论文。
总之,加方接待我们回访考察团是真诚务实的,尽量满足了我们对地层古生物考察等方面的需求,如用直升飞机专程带王义刚考察含菊石的三叠纪地层;让研究孢粉的欧阳舒同志,从西部飞到加拿大东边新斯科舍半岛,考察陆相二叠系,满意地采集了T/P界线层的孢粉标本(后来他与加方同行合作发表了此次研究成果);两年后,加方又从实际需要出发,出资邀请我所䗴类和腕足类研究人员,赴加为石油勘察做标本鉴定,研究北极地区的化石材料。
说说回访过程中的某些令我印象深刻的“花絮”,也许能从另一个侧面对比改革开放40年,国家和知识分子的变化。回访加拿大22天,按当时规定,我们每人有统共14.5加元的出国津贴(当时1加元折合人民币3元多),是一笔不小的“外快”。可是当我们走进超市(我国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超市),尽管各类物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但是我们的这点钱实在买不了什么!我最后选择给夫人买了块“没有比它更低价”的手表——天美时牌(Timex),花费12加元(一年后坏了,后来知道:这是最低档的玩具手表),剩余的两块多钱一直揣在口袋。离开加拿大前的最后一晚(按协议加方的接待到此为止),我们住进我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招待所。当时的领事先生是个满口广东话、年纪60开外的老头,夫人是个珠光宝气、港式打扮的老太(按规定,馆内其他工作人员不得带配偶)。这位领事夫人开办的“小卖部”(说是小卖部,实际货物只装了半个五斗柜),对我们5人进行了专场售卖:全部货物中,尼龙袜5分/双,能显示时间的电子圆珠笔2角/支,缝衣针2分钱一包……相对国内市场价,当然便宜许多(尼龙袜国内当时至少2-3元/双)。我剩的两块多钱买了十支圆珠笔,还买了尼龙袜和针头线脑。剩钱最后派上用场,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回到南京,家里人问起“加元”硬币什么样?我竟拿不出一枚!后来所里不少人开始收集各国钱币,我也有了习惯,每趟从国外回来,总是留一小口袋的硬币,但还常常不够分。
还要记上一笔的是,我们回访加拿大,按那时的规定,每到一个城市,考察团都要向大使馆的科技参赞报告行踪,团长王义刚每每为此“头疼”。因为考察需要,我们的流动性很大,每次他都要请加方人员帮忙,接通大使馆的电话(我们还不会使用),再接过听筒报告:“访问顺利,一切安好。”而电话费(硬币)总是加拿大方面帮忙付。我们出国前,院外事局发给我们考察团只有200加元的应急备用金,发放时严肃告知:“非特殊情况,不得使用。”我们理解:打报告电话并非特殊情况,如果用去几十元,恐怕不能报销?!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已经是南京古生物所的家常便饭,说起这些往事不过一笑而过,但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和国民的自信,足令我辈平生大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