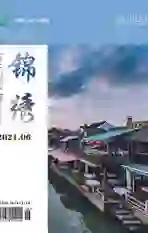我们从未现代过
2021-06-11杜书颖
杜书颖
摘要: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集中于主体议题的争端通常是与特定的历史语境相联系的,但实际上,与其將后人类视为诞生于科技迅猛发展背景下的理论,不如将其看作内在于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固有特征。这种解读也反过来证明后人类特征——破碎的、神经质的、流动的主体对于人文主义而言是原生性的存在。在对莎翁悲剧《李尔王》的解读中,我们会发现类赛博格的概念早已出现,而莎士比亚在“发明”人文主义的同时,也预示了人文主义的衰败。
关键词:后人类主义;人文主义;主体;李尔王
“后”其实并非意味着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与“人文主义”(humanism)是在时间上存在着接续关系的两个概念。就像凯瑟琳说的那样,人与机器的交融以及边界的打破是后人类理论都承认的基本议题,但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键不在于所谓的生物性改造,而在于对主体定义的变化。后人类思想已经跨越了与其绑定的固有“诞生”背景,许多理论家称它是内在于人文主义之中特征,借用拉图尔所称的“我们从未现代过”的说法,后人类理论看似倒错时空的阐释便便具有了合理性。
在这一判断便可以对莎士比亚进行后人类主义的思考。因为后现代性已经在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中(比如哈姆雷特)出现了,这一判断并不是为了说明莎翁的作品具有跨越时空的、直击人类本质的永恒审美价值,而是为了解释其实我们从未现代过。查纳斯解释道“如果拉图尔关于我们从未现代过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哈姆雷特也从来没有现代过,我们也从未后现代过……哈姆雷特不断地向我们诉说,并非因为他是‘永恒的:并不是因为他‘穿越了历史,而是因为我们从未现代过”。[1]
莎士比亚被塑造为人文主义偶像的建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便是“人类情感”,而这正是后人类视野中所不能抛弃的部分。在《李尔王》这部被布鲁姆称为会带来不适和孤独体验的悲剧中,情感与后人类的视角契合着:这部激起“异常情绪”的悲剧让我们开始质疑人性。
以后人类视角解读《李尔王》,可以更好地看出,对人、人性等的关怀在后人文主义话语中是一项重要的介入,即使残破的主体经受着异化情感的折磨,但批判式后人类主义表达的并非是对其刻薄地指责与规避,我们仍然关注着被撕裂的主体。后人类的解读为承载着人性的经典文本打开了新的空间,当科技决定主义吞噬掉一切人类话语,根除一切形式的主体影响后,一种更为‘情绪化的后人文主义变体将会出现——人类的重新出现[2]
安迪·莫斯利认为李尔王代表着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充满着对人性的乐观。作为国王的李尔对人、对人性、对人身份的有着清晰的定位和认同。在他尚未被两个女儿打破其有关亲情的设想之前,他是通过与女儿们的关系确认自己的身份,他有关普世亲情的设想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需要被无条件供养和关照的父亲。作为一个情绪饱满的个体,他在悲剧的最初象征着完满的人文主义理想。
在高纳里尔对他说要削减他的侍从人数时,他第一次对其作为父亲和君主的身份产生质疑。而在身份裂隙逐渐增大的过程中,李尔实际上是一直不肯承认这些破碎和被撕裂的感觉的。在第一幕的第五场他与弄人的对话中:
弄人:你不该在变聪明之前先变老。
李尔:啊!天呀,别令我疯狂!天哪,使我镇定把;我不愿疯狂![3]
李尔此时已经感觉到他所认定的那种真实已经在动摇了,所以这让他觉得快要发疯了。而这种疯狂不断地撕扯着他,在经历了荒野的暴风雨之后,他的神经已然破碎:
肯特:在这儿,大人;可是不要打扰他,他的神经已经错乱了。[4]
而在考狄利娅与其重逢之时,他的理智与辨识力已完全丧失:
考狄利娅:人们的智慧能不能恢复他的丧失的心神……一切神圣的秘密、一切地下潜伏的灵奇,随着我的眼泪一起奔涌出来吧!帮助解除我的善良的父亲的痛苦!快去找他,快去找他,我只怕他在不可控制的疯狂之中会消灭了他的失去主宰的生命。[5]
李尔所构想的秩序至此已全被打碎,他的生命也就不受他的控制了。后人类的精神分裂症附着在李尔的身上,打破了其自恋与膨胀的人文主义式自我想象。李尔在他两个女儿对其父亲身份的认同中确证了自己所想象的一个理想的父亲形象,并定义着理想的亲情。这种自恋式的身份建构其实是对他本来残破的真实的一种补全,格林布拉特认为,李尔王试图通过“唤起他人的焦虑”来弥补自己的焦虑,从而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威,“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体验到为他的慷慨而竞争的焦虑,而不必承受这种竞争的后果。”[6]
有关人性的想象全然破碎,让李尔最后进入难以分辨真实和虚幻的状态。弗洛伊德所说的“物”,那个原初的精神创痛,本质的、异于主体想象的他者被李尔王发现了。他所形容的那些与理想情趣相悖的丑恶现象:啖食儿女的部落,丑恶的海怪,这些异于主体想象的他物实际上存在于主体破碎的身体之中。他的想象所赋予他的秩序和结构被这种异化打碎了。
注释
[1] Stefan Herbrechter. Introduction--Shakespeare ever after//Posthumanist Shakespeares, eds.Stefan Herbrechter, Ivan Callu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3
[2] 同注释1:107
[3] 莎士比亚. 李尔王[M]. 梁实秋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77
[4] 莎士比亚. 李尔王//莎士比亚全集(五)[M].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502
[5] 同上.1994: 517-518
[6] Andy Mousley. Care, Scepticism and Speaking in the Plural: Posthumanisms and Humanisms in King Lear//Posthumanist Shakespeares, eds. Stefan Herbrechter, Ivan Callu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109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