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武器与小鸟
——日本童谣诗的发展与特点
2021-06-11潮洛蒙
潮洛蒙 石 芳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童谣,是以儿童为对象创作的、在儿童中间流行的歌谣或诗歌,是少年儿童认识世界、感悟生命、丰富内心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日本的童谣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三种类型,即“童歌”“唱歌”以及“创作童谣”,三者在时间上前后承接,且各自特征鲜明。
关于日本童谣诗的研究,日本研究者更多是从童谣的内容、音乐性、作家作品解读、教育性等视角进行研究,研究较充分且多元化。例如,高桥美帆(2003)通过将英国女诗人罗塞蒂与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的比较研究,探究了西欧诗人及其作品对日本大正创作童谣发展的影响。若井勋夫(2008)对于童谣诗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做出新的阐释,为童谣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吉本笃子(2015)在《明治、大正时期的艺术教育对于人的培养——围绕唱歌、童谣教育——》中认为,大正时期的童谣对于当时社会的儿童观、教育观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对于个别的童谣诗人的研究同样丰富,比如山内良子(2003)的《窗满雄童谣的表达特点——以童谣集<大象>为中心——》、金井明子(2006)的《从视点的多样性看金子美铃的诗歌表达》、笹本正树(2018)的《北原白秋童谣分析》等。2010年在中国湖南举办的第10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上和田典子发表了《作为综合艺术的童谣集》一文,认为日本童谣集作为文字、音乐、绘画和装帧等的综合艺术品,是日本孩子们以及日本社会的文化财产。总之,可以看出日本研究者对于童谣的研究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重视之高度,但尚缺国外研究者视角下的不同类型童谣的对比分析和面向中国的系统介绍。
相对而言,国内对日本童谣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多的是对个别的童谣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其中,随着近年来金子美铃的童谣译本不断推出,对于金子美铃以及她的作品的研究成为国内对日本童谣研究领域里的热门。比如,吴昊(2013)的《金子美铃的诗情》、刘灿灿(2016)的《论金子美铃诗歌的艺术成就》、秦秘蜜(2017)的《童谣诗人金子美铃的诗法研究》等。另外,宣妍(2009)的《北原白秋的创作童谣研究》以及郭尔雅(2019)《童谣童画童心——<竹久梦二童谣集>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借鉴意义》等,也为国内日本童谣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围绕象征着大正时期创作童谣诞生的儿童杂志《赤鸟》的研究,如王亨良(2012)的《艺术真价值》的追求与落败——以近代日本儿童文学杂志《赤鸟》为例”、牟鑫(2013)的《从大正时代的童谣来看日本童谣文化》等。国内的以上研究,皆是对于日本大正时期创作童谣的相关研究,而缺少对与其在教育目的、创作方法、内容等方面截然不同的传统童歌以及明治唱歌的研究或介绍。
基于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试图从日本童谣诗(不含曲调的文字内容部分)的产生、内容和目的等入手,对日本童谣诗发展过程中的特点进行对比和分析,以期加深对日本童谣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
一、自然传承的传统童歌——隐藏在孩童游戏中的瑰宝
孩子的天性是擅长模仿和想象,日本早期童谣——童歌的形成便是儿童模仿成人歌谣,或在玩耍和游戏中发挥想象力而自我创作的结果。因此,日本早期口口相传的童歌,大多是在孩子玩耍及日常生活中自然产生,也常称为“传承童谣”“自然童谣”等,大部分是作者、创作地点、传达意图等都不明确的童谣。同时在代代传唱的过程中,由于地区和时代的变化,童歌的歌词会发生一些改变,并且受方言的影响较大也是童歌的特点之一。童歌的内容以游戏、传授知识、季节风物、动植物故事、民俗事典等为主,其吟诵的形式几乎都是伴随着游戏进行,比如穿插在拍手游戏、捉迷藏、丢沙包等儿童游戏里完成。例如:

这首童歌是孩童玩游戏时候唱的歌,一个孩子坐在中间闭上眼,其他孩子围成圈,一边唱歌一边绕着圈走,歌曲结束时中间的孩子猜测背后的人是谁。通过最后一行“是谁呀”可以得知这是一个做类似于“猜人”的小团体游戏时候的辅助“玩具”。专业作家的作品往往是个人产物,而童歌则更像是一种群众集体的创作,据柳田国男的《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中的观点,童歌多是孩子们模仿成人进行宗教仪式而产生。[2]虽然后世对于这首童歌有不同的解析和阐述甚至是猜测,比如德川埋藏金子①、阴谋②等等,但正确的解读并没有确定下来。另外,童歌的版本一般有多个,这首童歌最早的文献记录是《竹堂随笔》,由修行僧人行智编著收录在他的童话集里,用词和长短音节奏等都与后世版本有所不同。[1]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在不同地区的传唱,这首童歌被收录于不同书籍中的版本就已达到四种——《返桥背御摄》(1813年)、《月花此友鸟》(1823年)、《幼稚游昔雏形》(1844年)以及《俚谣集拾遗》(1915年)。[3]同时,又因为绝大多数童歌是孩子们玩耍时候的助兴诗歌,注重游戏性而不注重词句意义,以及年代久远,创作者和发祥地不明等等,大部分都很难再寻其歌词真正的含义。
但是,童歌的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作为源远流长的口承文学,它饱含了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日本人民的审美意识等重要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特征。如上述歌词中提到的“鹤”和“龟”两个素材,便是日本传统文化中两个极具象征性的符号,例如小学馆大辞泉中的条目二记载,鹤和龟代表着长寿和吉庆,多出现在一些喜庆的物件或仪式上,比如红包、寿宴、婚礼等。此外,童歌背后扑朔迷离的民间传说,更是展现了日本传统童谣诗的生动、丰满、鲜活的一面,不仅能加深对从江户时代前就存在的古老童谣的了解,也对了解日本民俗、风物以及人文溯源等极具魅力和价值。
总之,日本童歌歌词虽然注重游戏效果而不注重实际含义,是个类似于“玩具”性质的存在,但在释放儿童天性、培养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以及在研究日本传统文化和日本审美意识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文部省唱歌——“德行”的培养
随着明治时期的到来,日本提倡“脱亚入欧”,日本人在诸多方面向欧美学习以求强国富民。日本的教育界也毫不例外地开始探索符合国家发展方向的教育方式和培养国家力量的道路。明治之前口口相传、没有鲜明的创作方向和目标的童歌,已经无法满足日本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因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将欧美音乐学科的教学模式与日本的国家需求相结合的“唱歌”。即日本文部省从明治时期到昭和时期组织编制的或得到文部省认定后编写到小学音乐课教材中的童谣。主要以西洋曲子为基础,配以国文学家或者教师创作或翻译西洋歌词的方式进行。因此,在大正时期的创作童谣运动中“唱歌”也被批判为太过西洋化而忘却了日本固有文化和情感的童谣。正如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唱歌教员青柳善吾所说,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与时代和社会需要相符合的人”[4],当时唱歌打出的口号是为了道德教育。但是只要对当时的日本文部省推送的相关唱歌集内容进行分析,就会明白这里的“教育目的”并不只是为少年儿童身心自由发展而设立的“正向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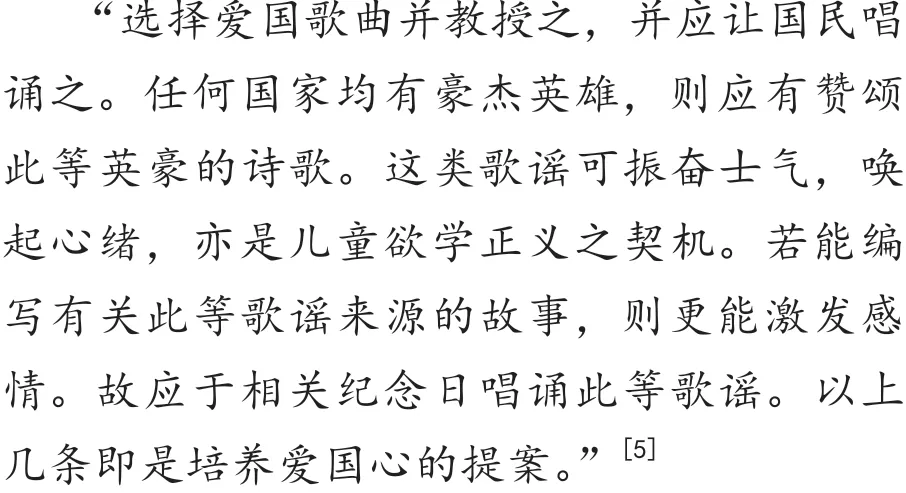
这段文字是日本文部省在1874年欲设立并推行唱歌课程时,在当年的《文部省杂志》第三号上刊登的从德文翻译过来的短文《爱国心的教育》中的一段内容。该文论述了为了培养爱国心而设立爱国主题类儿歌课程的重要性,也正契合了当时日本文部省推出“唱歌”的目的和理念。再看19世纪80年代以此主旨和意图推出的《小学唱歌集》系列教材,其中为了推出更“先进”、更具教化和培养力的唱歌,文部省进行了一系列对欧美音乐和诗歌的考察以及内部人员的调整和部署。以1882年(明治15年)出版发行的《小学唱歌集》第一版为例,其中的第17首“蝴蝶”中唱道:

其中第三行中暗指明治时代的“繁盛的年代(栄ゆる御代に)”的“年代(御代)”是个特殊的日语,在日文中“御代”一词,是对天皇、皇帝、王等治世的敬语说法。这个意义特殊的词传达出了“文明开化的明治时期,在天皇的统治下会更加繁荣”的意思。看似描绘春天樱花盛开一片春意盎然的写景诗句,实则是对天皇统治的歌颂。当时的日本文部省首脑伊泽修二在命人创作此歌时,对这首唱歌做了这样的评价:“将皇室的繁荣比拟为樱花的灿烂,感受着圣恩、生活在国泰民安时代的人民像蝴蝶一般自由飞舞,以此让少年儿童深切感受到国之恩惠,并激起他们为国效力的志气。”[7]可以看出,当时日本文部省所谓的“教育目的”不过是为了借“爱国主义”之名义,宣传和教化忠君报国思想,将一个个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对帝国和天皇甘愿尽忠的一兵一卒。作为面向少年儿童的“唱歌”,为了达到培养为帝国效忠的“国民”的目的,鼓吹“愚忠”,此类童谣不仅会影响少年儿童判断是非黑白的能力,更会遏制少年儿童在天真烂漫的年纪抒发童心和童趣、自我探索和发现世界的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7年,为打压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皇权势力,占领日本的同盟国军队总司令部曾要求将带有明显的歌颂皇室的“在樱花繁盛的(明治)年代”这一句歌词删除。于是同年文部省发行的《一年级音乐》中,对其做了改动,将第三行的“在樱花繁盛的年代”改成了“在花丛间”。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更是产生了不少鼓吹战争、煽动民心的唱歌作品。比如,明治24年(1891年)从山田美妙发表的《战景大和魂》(1886年)节选而成的“成千上万的敌军”[6]这首唱歌中,“敌人虽成千上万/但全都是乌合之众/即使不是乌合之众/我方是正确且有道理的/邪是压不了正义的”来合理化侵略战争,以及“失败逃走的人是国家的耻辱/前进并为国捐躯的人是荣誉之躯”这样的歌词来对侵略战争下的国民进行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绑架,尤其是对于辨别能力还很弱的儿童,更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洗脑。“勇敢的水兵”[6](1895年)中“‘还没有沉没/定远号’/这句话虽然简短/但在心心念念着国家的国民/心里永远长存”这样歌词,从中可以看到甲午海战中清政府派出的定远号战舰的誓死抵抗,而这首唱歌作品则是企图通过描写与定远号的鏖战,来宣扬日本士兵在前线“奋勇”前进,以此昂扬战意、煽动民众。当时文部省为了提高国民战斗意识,鼓励此类唱歌的创作,因此这类在战争期间诞生的战争主题的唱歌不仅在中小学生之间广为传唱,更是作为国民之歌在大众之间流行,不仅污染少年儿童的心灵,更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摇旗呐喊,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来说可谓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综上可以看出日本唱歌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是为了培育符合帝国意志的儿童而诞生的童谣,是对儿童宣传和教化忠君报国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因此,文部省推出的唱歌大多是极具军国主义、国粹主义倾向的童谣,在精心雕琢的语言文字下面往往隐藏着别有用心的目的,借助唱歌这种无形的“思想武器”绑架和改造天真烂漫的童心,通过政府和学校合作的方式将忠君报国的思想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少年儿童,把他们塑造成为侵略战争的先锋和武器。
三、创作童谣——丰富内心感悟生命
创作童谣诞生于日本大正时期开展的“童谣运动”中,是以反对“忘却了日本的风土、传统和童心”[8]的“唱歌”为目的,以创作站在孩子的立场、保留孩子纯真的心灵和美好想象为创作目标的“童心主义”诗歌。当时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符合儿童的读物,市面上更多的是改编或翻译的西欧儿童文学,以及日本传统故事,如桃太郎等,儿童读物亟需新的发展。同时,大正时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整个日本社会弥漫着作为战胜国的自满和骄傲,明治唱歌中的军国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灌输也愈发增强,文部省利用学校唱歌对学生的教化同当时“大正民主”运动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和个人解放相违背。另外,随着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日趋加快,西欧“儿童本位”思想也促进了日本儿童文学对于童真、童心、童趣的再次发掘。1918年(大正7年)日本著名儿童杂志《赤鸟》创刊,创始人铃木三重吉提出了“面向孩子们创作的、具有丰富的艺术性”的新童谣创作理念。这一理念一经推出,便获得了一批有赤子心、有责任感的文学家的支持,如北原白秋、西条八十、金子美铃等,纷纷加入童谣诗的创作。在创作童谣的巅峰时期,类似于《赤鸟》这样的与童谣相关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金色的小船》(1919年创刊)、《童话》(1920年创刊)等,甚至一度出现日本全国上下无作家不写童谣诗的局面。北原白秋认为,“唱歌”这样的童谣让“日本孩子越来越无法天真无邪地歌唱出他们内心的声音”,而“真正的童谣用的是孩子们容易理解的话语,在表达孩子的内心情感的同时,也能引起成年人深刻的感悟和理解。”[8]
正如日本广为传唱的创作童谣之一“红蜻蜓”:
晚霞夕照的山上 从(姐姐的)背上看到的 难道是幻影
采摘山田的桑果 放到小篮子里 又是哪一天
十五岁的姐姐已嫁到远方 别了故乡 杳无音信
只有晚霞夕照中的红蜻蜓 还停歇在那竹竿尖上[9]
诗人三木露风的这首童谣选取的虽只是一些司空见惯的自然界意象,如晚霞、桑果、竹篮、红蜻蜓以及亲人小姐姐等,但是却营造了一种小巧温馨的氛围,加之诗句中对故乡自然流露出的怀恋和亲人的思念——人类共通的感情,充斥着触动读者内心的魔力。
人对于童年时候陪伴过自己的人总是充满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回想起曾经背着自己,披着晚霞的余晖,在夕阳西下的山间田地采摘桑果的小姐姐,诗人的忧伤和不舍溢满字里行间。而故乡,或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或是落叶归根的梦中故土,总之故乡是每个人内心深处不可磨灭的记忆。诗人对于亲人和故乡的怀念之情,这种质朴的感情对于儿童的美育和德育的能量是无限的。尽管儿童身上有着许多的“幼稚”,但是儿童心理渴望着“成熟”,跟儿童谈亲情、谈故乡等问题,将会无限丰富儿童的内心对生命的认识。[10]“动人的作品往往来自深切的感受”[11],三木露风在这首诗里所抒发的对亲人的思念和故乡的热爱,正是人内心深处最本质的构成。这也是一直到今天,这首创作童谣不仅被日本人民喜爱,而且走出了日本,传到中国,被收录于人教版小学四年级音乐课本中的原因所在。那扣人心弦的曲调和优美动人的词语,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对于故乡、亲人以及大自然的淳朴的感情,是其能够超越时空和民族的界限照亮人们心灵的根源所在。
朝霞映红了天边
渔船满载而归喽
大条的沙丁鱼
满载而归喽
海边
像过节一样热闹
海里
几万条
沙丁鱼的葬礼
正要举行[9]
这首广为人知的金子美铃的童谣“大渔”(1924年),将大人们眼中值得庆祝的渔猎大丰收的热闹场景,通过逆转的视角,即透过内心丰富敏感的儿童的眼睛,描绘了一场令人悲痛的大海里的悼念会。儿童总是会将自己作为大自然万物的一员,去感受并擅长和动植物建立“连接”,这不仅是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本能的反应,更是一种作为“自然界的高级动物”的人的善良,因为他们拥有一颗对于“同类”的尊重和爱护的善良的心。孩子常常用和动物平等的视角来看世界,再如蕗谷虹儿的“松叶十字架”(1925年)和“大渔”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孩子的视角传达对动物的同情,“散落在海边的/贝壳,大家以前都是/活的贝壳/大家以前都是/活的贝壳。银色的细螺/樱花贝/象牙般的/蛤蜊/大家以前都是/活的贝壳”“和父母走散了的/小贝壳/和孩子分开了的/贝壳的父母/大家一起哀悼”[9],对和父母走散了的小贝壳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为其母亲和孩子的分离而痛心。
诗人们怀着孩子般柔软善良的心,巧妙地选择了符合孩子内心的主题,创作出充满真挚感情的童谣。而且,这种“万物皆有生命”“敬畏自然”的精神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也非常欠缺,因此这些创作童谣的意义不仅仅是面向儿童的童谣,更是大人的精神补给。人们总是被现代“文明”的发展速度所追赶,而远离自然悬浮于“大地”之上,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真实感,因此,包含着孩子们直接且近乎透明的朴素感情的创作童谣,可以说是治愈心灵的良药。
人在年幼时期对万事万物总是充满好奇,有着更为敏感的洞察力和心得,但却也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和理性的思考。因此,如明治文部省唱歌那样说教、灌输大于引导的形式显然不利于儿童成长,更不必说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和人类的发展的危害,因此正如铃木三重吉所说的,“为孩子创作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来“培育孩子美好的想象力和情感”[12]非常有必要。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身心都需要得到自由的成长,尤其是心灵的成长。那些包含着对于美好、自由、爱的追求以及朴素而美好的情感的创作童谣,正是心灵成长的养料。
承载着人的美好且朴素情感的作品往往拥有着超越个人和时代的生命力,正如创作童谣那样能够像一只小鸟,飞跃时空,历经百年跨越山海来到我们身边,唱着悦耳的歌。
四、结语
如上述分析,日本文学史上的三种童谣诗在时间上前后相继,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众所周知,在一个人成长初期对世界充满幻想和渴望的时候,所接触到的语言或文字以及这些语言或文字带来的感动和留下的印象往往具有启蒙意义,且影响深远。因此,不论是童歌、唱歌还是创作童谣,都会在日本人年幼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另外,文学创作脱离不了母国文化,因此三种童谣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日本的文化、风土、传统等。
而不同之处,首先在语言表达上,童歌在形式上用词简单,大多是便于做游戏互动时候朗诵或歌唱。“唱歌”,作为文部省带有一定目标设置的学校学科,遣词造句多生僻晦涩。创作童谣站在儿童角度进行创作,语言文字表达较口语化,用词通俗易懂且优美清新。
其次体现在内容上,童歌主要是以游戏玩耍、简单的常识、庆典活动等日常题材为内容,大多数是自然发生的口承童谣,因此更具有民风民俗的特色。而“唱歌”由于是通过大人的角度,将大人的思想和感情强压给孩子们,具有功利性,因此不能迎合孩子们的兴趣。创作童谣大多数是考虑到孩童的好奇心和兴趣而创作,有利于开发孩子们的天性与想象力。
再者,体现在思想情感上,儿童阶段是人格发展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培养孩童的美好的想象力和情感才能符合社会和人类发展规律。而“唱歌”更多的是为了宣传为帝国、为天皇效忠,进行思想统一的一种工具,缺乏童歌的质朴和游戏性,更缺乏创作童谣里蕴含的儿童的童心烂漫和天真无邪。创作童谣从1918年到今天历经百年,依旧能照亮我们的心灵,因此创作童谣更有利于儿童心灵的丰富和成长,同时更能呼唤起大人的“童心”,老少皆宜,超越时空。
注释:
①1867年,日本江户末年,江户政府在实行 大正奉还之际秘密地埋藏下金子,用于幕 府复兴的军备资金。有日本民间说法指出, 本首童歌有暗指德川藏金子的地方。
②“竹网眼(かごめ)”还可以写作日语汉字 “籠女”,指腹前怀抱笼子的女人,暗指孕 妇。“笼中鸟(かごの中の鳥)”,指腹中 孩子。民间说法为孕妇家中正在进行继承 人之争,其中有人对继承人候选人增加感 到不快,因此在孕妇预产期即将到来的某个 月夜,将正要下楼梯的孕妇从背后推了下 去,因此说这首童歌是孕妇流产之后的怨 恨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