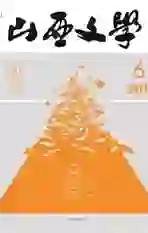再见!心在远方的二湖
2021-06-02张小苏
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同时,二湖的躯体正在这个世界消失。今天,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早上二湖火化。他离世往生已经两天。两天前,他动身移驾启程几小时后,我知道,他走了。这让我两天说不出话来。
一九七七年,拨乱反正头一年,报刊大量刊载悼亡文章。这些文章在补齐了若干历史空缺的同时,作者作为历史亲历者,有成就感。但几乎每篇文章最后都是一个套路,悉有“竟成永诀”一词。那时我和李晓阳一筹莫展,无路可走。他说,咱们也得去结交名人,将来至不济还能写“竟成永诀”。
庚子至今有太多老朋友永诀,我几乎一句不说,尽管有满肚子的话。二湖之死方知竟成永诀这样的文章是不好做的,甚至不能做,尤其无法趁热做。
过去两天中,朋友们关于二湖所说的话,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小群对二湖病因的判断。我们都不是医生,但我同意她的判断。
二湖是断然不想看病也不看病的人。老了,病了,即使看病,浅尝辄止罢了,我身边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处于这种状态。至少在目前,我以为是一种明智。是旷达和智慧,对于注定无解的问题,就由他去吧!
永诀就永诀,招呼都不打,有什么不同吗?我和他已多年不见,如今突然永诀,不是还让我如遭雷击吗?已经铸就了的存在,不会因永诀消失。
我与二湖,曾为街坊,为朋友,为同事,为团伙,为挑担……他是我交谈最多的人之一。
我和他是一个大院的家属,只是大院中有小院,不是邻居,只能叫街坊。那时差两岁就相当远了。我认识广建大姐的时间超过二湖,大姐和我母亲有同事关系,我妈妈相当于她的大姐,但她让我喊她大姐。辈份是全乱了。大姐晚上常来找我母亲谈事。一分公事,九分家常,所以谈二湖和三湖,二湖谈得少,大姐对三湖有担心,说他愣,不知是不是“脑油缺乏”?
后来街上贴出大标语:打倒赵二湖!二湖成为本院家属中第一个也要被打倒的人。这事后来二湖给我备细讲过,而且津津乐道。
我下放回来后,二湖还没回来,其父已去世。一度时期他涉及哲学,找来黑格尔和老庄看,后来他一直对思辨感兴趣。还和朋友搞了个学习的组织,其实就是讨论些问题。这样的团伙当时并不少见,但他们的团伙取了名,一有名就是个事儿!《动物农场》的养鸡婆说过,没起过名的鸡,随便杀,一旦起过名,生命升华了,她们舍不得杀有名字的鸡,二湖们谈事的同好,名之为“鲁迅研究会”,这就麻烦了,成了“活物”。于是被取缔,为首的还进去了。虽然谈的不过是鲁迅。他侥幸得脱,反骨一发成形。同时还有些“老炮”模样,一贯的衣冠不整,来往于太原和临汾之间(那时在临钢当工人)。回到太原就给我们讲插队,讲炼钢,思路与人不同,故有趣。
为了夫妇回太原,搞了个假离婚,毕竟成功了。他说,“我又和法律开了个玩笑”,大人们认为不是正经办法:你和人家法律开的什么玩笑!
一九八四年前,我一直为办刊物跑山西印刷厂,厂里人几乎把我当该厂员工,一日,我从一车间转出,见二湖拉着辆平车在干活儿,于是立在厂区谈了许久。他总算回到太原了。不久就调进省作协。
说赵二湖不喜欢文学,也许有人不信。但他就是这么说的。认认真真,用思辨的、分析的方式嚴肃地说。他相信他有很好的文学感觉,但不愿意干这行,也不当文学青年。说,咱俩反过来了,我喜欢美术,对画画有自信,你生在美术家家庭,却喜欢文学。
他至少不喜欢文学行当中的某些图谋,某些做作,看到类似“强说愁”的酸文立刻上火。他认为当时这一行业中,这样的行为比比皆是。
在一些正经的学术性会议上,他总像憋着口气,幸好他只是服务人员。在某次有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参加的讨论会上,一位鼎鼎大名的专家痛心疾首地讲他在基层的见闻,几乎声泪俱下地说,你们能想到吗?不到乡间底层绝想不到的,富起来的农民居然拿出钱来盖庙,建佛龛!
二湖憋不住,嘟囔了一句:“当然,过去穷,迷信不起嘛!”说完赶紧走,去干他的会务。
他那时对少见多怪,装模作样,虚假的吹捧,七荤八素的这主义那观念十分厌恶。曾一度认真跟我合计,咱俩承包锅炉房吧!你要同意,我今天就去找上边谈。我说你还能抡铁锹,我干不了这活呀!他说,你只要专管软化水就行。我这才知道锅炉里的水要软化。他又凭借着许多化学知识,讲了半天这方面学问。
二湖心胸开阔,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怎么也比窝在那儿看稿子强。人一生得看不少书,但要看好书,你不能把大量时间放在看稿子上!
等不及,于是他“下海”了。郑重告我,他虽下海,但不经商,现在中国捣腾的人多,左手倒右手,流通多而产出少,他要干实业,造产品,他的产品就是扎染的时尚女装。二湖干得很投入,一边跨着美院,一边跨着普罗大众,既要产,又要销。幸好机关给了他部分启动资金,但很快就倒塌了。不过并未烟消云散,那些时尚女装还有不少存货,流通了几年。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党组书记胡正说,二湖就是个二马虎。这事就这么核销了。
许多年后,我俩到阳泉出差,他说他得到一户人家收货款,很快回来。当下约好晚上在王博勤家吃饭。他问好地址,便去了。王博勤没见过二湖,问我二湖有什么特征?让她女儿到外边等。我说,一是气急败坏,二是像老裁缝。博勤嫌我说得不明白。没一会儿,她女儿大笑而来,说我描述得太明白了!
但见,二湖背着个小包袱,急急而入。我问,收货款怎么这么久?欠款的不在?他说在是在,只是刚坐下,就来了个人,和欠他款的人打起来了,问,那你呢?他说炕上有个小孩子在哭,没人管,他就盘腿上炕,一直抱着那孩子,直到人家打完。大家轰笑,又问,你的款收回来没?他解开包袱:都在这儿了!在座的女士一人一件,分了吧!男的也一件,拿去给老婆。
二湖的心肠之软,世上少见,下乡在村里,房东家养着头小猪,来来回回在院里跑,他隔会儿出去看看,晚上悄悄问我,像不像嘟嘟?(那时他儿子嘟嘟不过两三岁)后来实在爱不过,从泥乎乎的猪圈里,抱起小猪亲了一口。
重又回到创联部,其间曾与我一同参加了阳泉文联一次笔会。这次笔会办在盂县一个连路都不通的小村,猫铺。我与他住在村里一位姓梁的老农家。大夏天,我俩在一条大炕上光着膀子,我一侧身就看到他脊背上满是苍蝇,知道我自己也如此。但不以为然,从第一天,二湖就进入一种罕见的激情之中,就算最没事,也在与我联诗作对。那些连珠妙语,是真正永诀了。
他在创联部,平时参加笔会,只代表作协机关,开幕式完了就走,无涉于稿子。跟我一同去,他就休想安生了,我把收上来的稿子和他分了,各看各的。于是他一天比一天激动,白天,我有为作者辅导的任务,得讲话,自然请他也讲,他讲得直率而有趣,由是,他在笔会上越陷越深,往往正午休时,突然跃起,去找某个作者辩论,说必须把对方说服。几次下来,发现并不容易。看到好稿子,我们又一同激动,好像挖得了宝贝。于是我们自己研究,怎么回事?这深山老林怎么会有这样清丽脱俗的文章?恰在此时,雷鸣电闪,电灯也灭了,窗外山的轮廓,在瞬间闪电中,一次次在瞬间展现细节,我和他都懵懵然。一致认为庄子来了。
于是激动,他天天给房东家挑水,房东每天在我俩起床前,煮许多鸡蛋放在炕头上。炕头是条木板,两只大碗,置于枕前,每碗最少五颗鸡蛋,满到不能碰。我们的激情和那两只碗似的,再也盛不下了,溢出来了!二湖说,咱俩一定要为老梁解决问题,老梁自言,解放初期是县中学的老师,请假回家,赶上场大病,恰好遇上改朝换代,回到学校就丢了饭碗。几十年过去,他只想恢复退休待遇。为了让老梁放心,还甩出两张王牌,一是王中青副省长,一是他姐姐赵广建。
二湖忿然不平,那几天他热爱农民的根性大犯。晚上夜夜长谈,这就谈到了文艺政策,文艺路线,山药蛋文学,文学界的宗派,谈着谈着就直呼赵树理了。到后来一发说,赵树理其实是“罪有应得”啊!赵树理想改变什么,改变不了什么,真心服膺的是什么,其他问题也搅在一起,为什么这样的山沟能出“庄子”那样的作者?老梁怎么这么好?这么能忍?那么多煮鸡蛋?幸好我们没酒,平白无故竟大醉。后来他哭了,边哭边说要写首诗,为《父亲》。
于是在山顶,在河边,谈个不住。我们的饭堂在村中心一个戏台上,每日吃饭都有人在台下围观,他又激动。想拉孩子们上来同吃。一日傍晚,暴雨倾盆,洪水恰从台下流过,二湖振臂高呼,喊了几位后生,将台上的作者一个个背了过去。
混了一段,大家知道我和他竟还是连襟,越发有故事了,我们成了作者们“八卦”的对象。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少意识到这回事。太原风俗春节初二必回丈人家。我俩每到这天相遇,都感到奇怪。“你怎么也在这儿?”那时候,我们两位姑爷就找间空房,说我们的话。同院孩子的关系大于连襟关系。后者就被忽略了。
我们从猫铺出来。没有直接回太原,而住到军分区一位老军人家,那天有酒,二湖放声哭了一场,哭痛快了,一举写完《父亲》这首诗。后来我拿给潞潞,刊在当年的《山西文学》。他照样不怎么当回事。
不过那段他爱过几天诗,我们一同翻翻《四个四重奏》,仿佛有所得,有天上午他一口气写了好几首,都很绝。午后,家里来了位诗歌爱好者,看后喜歡得不得了,甚异之:他怎么想得出来?我和二湖都昏头昏脑,写了就忘,今天只记得一首名为《我懒》,有这样的句子:
我懒得结婚
我懒得离婚
我懒得喝酒
我懒得吃饭……
最后一行是:
我懒得懒。
昨天看到朋友文章说二湖生性懒散,不然早成大器。其实二湖生性积极。他只是不热衷于“文章千古事”。
懒得懒的二湖,干脆带一标人马到苏联去了。追逐诗和远方。
几年后,把苏联待成俄罗斯,带了条小狗回来,取名苏改俄。
去俄罗斯前或后,我记不清了,二湖被聘至一家图片社当CEO,他告诉我,他的理想是把这家企业办成一个俱乐部。说,老板的心思是赚了钱还想赚,没完没了,他不,他要适可而止,办成个乐园就是了。有天半夜,跑到我家,让小马弄个小菜,要和我谈事。没一点儿酒量的他,还带了瓶太原高粱白。小马办好就去哄孩子睡觉,二湖和我在窄小的厨房就着小酒,正经谈了一番,他说他要在图片社开办摄影楼,懂光圈速度焦距的人好找,懂艺术的人难寻,他认为我办这事合适。我犹豫了几天,决定放弃。
一段时期,他消失在自家地下室。忽一日,蓬头垢面上来,说实验终获成功!原来,他从俄国带回一些铜浮雕作品,回来研究制成方法,后来知道是电解方式,于是买了各种器皿药水实验,终于做成。后来找到了投资,有了厂房,天天晚上拿个铜物,磨磨擦擦,小马说,我磨磨看?他说我还想磨呢!小马说,让我到你的工厂干活儿吧?他说,你能干什么?小马指着他手上的活计,说,磨呀!他说,磨是我的事,你要干,就当总经理好了!
二湖能钻研,能制造,但不会经营,不会卖。他在这个行当后来搞了不少作品,如大铜板《八十七神仙卷》、小铜匾《正大光明》等。他把这些东西拿到我办公室,各地来客非常喜欢,我也顾头不顾尾,根本不知道被什么人拿了去。
我与他聚聚合合,在一起,总是合计该干点儿什么。其实有什么该干?现成的不就是看稿子吗?但当时觉得,那不算!他积极进取,嫌我太懒,说他近年认下许多大款,那些人求贤若渴,他告诉大款:“我周围有好几个散仙,达到了赤脚大仙的级别,我将把他们煽活起来大用!”
我期望大款来顾我庐。心乱如麻。那几年也有人雇我,给什么部门写书、写电视脚本、策划综艺节目、到电台当嘉宾,乱人心意的同时,也有些风生水起,终于有大款找上门来,我拉二湖同往,他也多次参加了谈判,但当时他的厂子已有了生产能力。便未同往。
之后我与他见面少了,回到太原总要吃喝一场。当时中年往上的职业人,也许因为达到了小康,往往拥有些同好吃吃喝喝。我们这些个吃喝朋友,后来竟办起个网站,名曰《山药蛋文学网》。其实和山药蛋文学什么关系也没有,大家闲了乘车四处拍数码照片。二湖本来就对美术有兴趣,对光影和形体敏感,所以他的照片一起步就不凡。二湖在回答老友李丁问时,归纳过这些人的关系:是文联子弟与图书馆的合流。
二湖崇尚本真也天生本直,喜五湖四海,常能有所发现。有一天很晚了,他来电话,要来我家说件有趣的事,明天不行吗?不行,因为有意思。及至来,说他见到一个奇人,家里有三枪牌的自行车,但挂在墙上,有全套改锥和锯,最袖珍的刨子是极珍贵的木头雕的,不如巴掌大……最厉害的是,这人穿的皮鞋是1940年买的,现在还新新的,只是鞋根鞋底换了,后来帮子也换了,鞋前鞋后全换了,总之,全换了,但鞋本身没换。“那只鞋”的概念没换。
后来我常想起这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大笑,即使是一人在家。这是个标准的二湖式的玩笑。他一生都对“白马非马”这类命题兴趣盎然
厚道、质朴、心灵手巧,天生反感假眉三道,他自己说他心软手黑,多半为吓唬人,看不准人,办糊涂事,荒唐事这都是有的,他不否认,也丁点儿掩饰不住。
估计他干过最假模假式的事就是演电视,扮他爷爷,留下一句对李雪健的话“你演我爹,我演你爹。”透着他的机灵。这事对他太有吸引力了,而且这事办得也不错,他是那部不及格的电视剧里的唯一看点。剧组在北京时,他给我打过个电话,内容忘了,听上去挺眉飞色舞。
十年前,他说他也有点儿脑梗,症状是住在宾馆穿不了拖鞋。挂不住了,一听就不是玩笑,得过这类病的人知道,肌肉群一点点的丧失,就会改变许多。孰料又出现吞咽问题。更料不到他会遽然离世。论性子,他是有点儿急,论旷达,则心地高远。一个自由真实的灵魂飞升而去,在我全天说不出一句话的昨天,莫名其妙看起了《荒原》,诗前的几句话吸引了我:
因为我亲眼见到大名鼎鼎的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只瓶子里,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她回答说:“我要死。”(因为西比尔被阿波罗所爱,被施予预言的能力,然而她忘了问阿波罗要永恒的青春,所以日渐憔悴最后几乎缩成了空躯。)
所以我什么事也做不成,用拙劣的毛笔字抄了一遍《荒原》。
【作者简介】 张小苏,1953年生于北京。在山西太原完成小学和少半个初中教育。之后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努力补足学业。197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此后长期担任编辑工作,先后供职于山西画报社、山西文学月刊社等单位,曾结集出版《老宅流水》、《漂·移》等作品集。201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