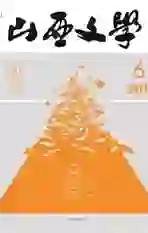何处是高处
2021-06-02李晋瑞
乡村现实
要不是出院门往左边一拐,看到那道很窄的急坡,我还真以为一上午的聊天,我们是坐在村庄的最高处了。进院前,我还曾经驻足留意,前面目及以远的地方,是一叠叠波纹般沿着天际线向两边延展的山脉,背后是一道道深谷,脚底下则是东一处西一处因坡势而建的农家。那个院子建在太行山里某个贫困村的山梁上。村里人叫它大队,也就是村庄一切公共事务的集中所在地。那天上午,我和驻村扶贫队员们坐着板凳在院里聊天。
我们四五个人围成一圈,有山野之风呼呼地刮来。其实我心里并不平静,因为我也是农村里出来的孩子,之前多少次回老家,看着那些人去楼空、破败凋敝的村庄,也曾经产生过梁鸿那样的忧伤: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些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种悲怆欲哭的感觉……我眼前的这个村庄,有着我和梁鸿眼中一样的荒凉与寂寞。第一书记讲,之前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熟悉农村的,可没想真正到村里来,一看,完全让他想象不到。他的想象不到,我也是亲眼目睹了的。我在武乡县分水岭乡的一个村庄就看到过一户人家,昏暗的光线下,绿漆刷过的屋墙已经斑驳不堪,家具用的还是那种如今已经很罕见的扣箱,满屋子看不到一件现代化的电器,炕褥连整个席子都遮不住,两个老人坐在炕上,其中一个耳聋的还听不见,两个六七岁的孩子在地上玩耍,趿拉着少见的塑料凉鞋,她们细瘦的胳膊沾满了灰土,指甲里全是黑泥,尽管知道他们马上就要整村搬到新居了,但这就是他們几十年来的生活实景。
这时,有个中年男人一瘸一拐进来,到村委办公室旁的房子里走了一遭,出来后又一瘸一拐从我们旁边经过,手里多了两盒药。第一书记和他打招呼,他放缓了步子,却没有停下,显得很急。第一书记告诉我,他是村医,当过兵,一条腿没了,裤筒里装的是假腿,这是来取药给村民送去的。他一瘸一拐迎风而去,走出院门,前面便是一片空无一物的蓝色天空。他已经没有一点军人的挺拔与英姿了,他只是村里的一个中年男人,有所不同的是他是村医。
村医还需要亲自给村民去送药?可是,他自己还一瘸一拐走路不利索呢!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去村保健站取药本是一个孩子该干的事,孩子一路小跑来到保健站,站在高高的柜台前,看着医生用药勺将瓶里的药片一勺一勺分到方型草纸上,然后包好,医生一定是会用圆珠笔在纸上标好服用时间和剂量的,那时没有塑料袋,就那么几小包,医生也会抽一根草绳来给你绑上,他一边用牙咬断草绳,一边还会叮嘱你,不要贪玩啊,拿上药直接回家。孩子在乡村里,除了淘气,还是老爷爷老奶奶的腿和拐棍,可是在现在的乡下农村,不要说十五六、十三四,就是五六岁的孩子都很少见了,纵然有那么一半个,也是在哪一位年轻妈妈怀里,因为他还是吃奶的婴儿。既然没有了孩子,就算是这种跑个腿的事,也只能是大人们亲自去解决了。
第一书记讲,前些年在农村还有两个群体,一个是老弱病残,另一个是留守儿童。这几年基本上就只剩老弱病残了。想一想,在昏暗的窑洞里,出不了门的病人蓬头垢面地躺在炕上,眼瞅门外,盼着村医来给自己送药。而那个村医怀抱两盒药,正一瘸一拐,高一脚低一脚紧走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那情景,真的叫人心里发酸。第一书记讲,有多少留在村庄的人,他们的生活不是迫于无奈,就是艰难的硬撑。
那个上午,我们本来是聊脱贫攻坚的。快晌午时,又来了一位老人。老人拄着木棍,颤颤巍巍,他坐到我对面的圆凳上,两手紧紧抓住怀里的木棍,也只有那样他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他人瘦,黑,皮肤粗糙,两腮塌陷,一身深蓝色衣裤,光脚穿鞋。老人七十九岁了,还有癌病在身,是一个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天的人。他是来找第一书记的,为自己的“心病”那处未盖成的新房而来。他说自己的新房,国家该补的钱补了,自己要交的钱也交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停工好几年了,现在四边的墙都垒起来了,就剩屋顶没有盖上。他拖着一副行将离世的身体来谈新房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要财”还是“要命”的问题。不过我知道,在一些人心里,尤其是一些农村老人心里,人命最贱,在他们那里,财就是命,命可不一定是财。但我还是一再劝他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却不搭我的话。他还在有气无力地跟第一书记讲,不知道自己死前能不能看到新房子建成。我还想,就算老人看不到,至少还有他的儿子吧。结果第一书记讲,老人的儿子去年刚死,儿媳妇也带着两个孙子去省城太原了。
那我就更加疑惑了,老人如此遭际,怎么还有心情惦记一处对他来说已毫无用处的房子呢?既然一心惦记着新房,怎么又让儿媳妇带着两孙子去了太原呢?
我不知道老人的儿媳妇带着两孙子到太原是去上学,还是讨生活。但我知道,这也是他们的必然选择。因为在农村人心里,离开农村就是希望。看病、购物先不说,最为现实的是孩子上学问题。现在的很多乡村,不要说偏远的山庄窝铺,就是靠近公路有二三百户人家的村庄,很多也没有学校了。纵然孩子们将来成不了龙成不了凤,就算想让孩子有点文化也得上学,相比乡里的学校,城里的教学资源当然要好很多,因此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下,大部分农村家长,哪怕是借钱、租房,也要一步到位往县城挤。农村里不要说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人,就算四五十岁的人不多见也就见怪不怪了。
这也是许多乡村的现实。人们纠结、无力、逃离、心不甘情不愿,但又必须随从大流。
我们还是回到老人的故事上来。我当然无法知道老人在得知儿媳妇要带孙子去太原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他一定知道儿媳妇和两个孙子走后,留下他和老伴儿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是,他决然不会因此就流露出半点“挽留”之意。村庄白雾蒙蒙中凌空绽放的桃花,枝节零乱的杮树丛中展翅腾飞的喜鹊,还有夜色笼罩下悬挂在村庄高空的明月,这些东西在城里人看来是美,是景,但老人早已司空见惯,无美可言了。尤其是儿子死后,我相信他无论是坐在炕上隔着窗户向外望,还是站在院里的树下透过树叶罅隙往外看,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不再有一点实物感了。儿媳妇和孙子要走了,在内心深处,他也希望他们离开。哪位老人不希望自己的孙子有出息呢,他也希望将来,哪怕是自己入土多年,也能听到孙子们传回来在北京、天津上学,或在太原、西安,上班的消息。
放儿孙出去,是农村老人不得已的心愿。儿孙们走得越远越好,因为远方代表未来,代表见识,更代表前途。作家梁鸿在答凤凰网记者时就说,出梁庄是他们(离开村庄的人)唯一的出路,是他们唯一可以获得一些金钱,获得一些更好的可能的一条路。在当代社会,乡村整个是一种被抛弃的状态,我们的所有资源把它抽空了,人力资源没有了,河流的资源、沙没有了——沙被拿来盖房子,泥也没有了,路也没有了,树也被砍了,整个乡村是一种空虚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废墟的状态。尤其是北方的村庄,它很早就被抽空了。
我面前的这位老人,总结不出这样的话,但不等于他没有如此的感受。面对现实,他也只能选择低头。可他又是心有不甘的,他相信一种不随时间流逝,也不因岁月而改变的亘古的东西,那是一种祖祖辈辈一脉相传继承下来的东西。那是些什么东西呢?从经济意义讲,可能不值钱,但从精神意义上,又被视作无价之宝,那就是“根”,一个人的来处。中国人不能没有根,老人坚信“根”的想法迟早会在儿孙们的心里生发。因此,他必须得拼尽全力给儿孙们留住一处归处。
农村人总是将自己视为草民。他们中很少有人有勇气一出村就剪断与故乡间血脉相连的那根脐带。多少人出门的目的,是暂时的,只是为了打拼几个钱,从他们离开的时候就会叮嘱自己背后的家才是躲避风雨的港湾。儿孙是不是这样想我不知道,但老人一准会这么认为。草民胆小,经不起风浪,更让他们无法从容的是,离开土地后的悬置感让他们产生的恐慌。但是留在家乡,无论土地有多厚实,无论他们怎样在春节时将“土中生白玉,地里出黄金”的对联,端端正正贴到土地爷的神龛上,他们能把土地深刨五米,也还是刨不出白玉,挖不出黄金来。他们只能选择走,去城市、去工厂、去那些只要付出时间和体力就是金钱的地方。因为你在农村,可以靠一把锄头两只箩筐花十几年在山里掏出两眼窑洞,但你却无法不出钱买到一部手机、一台电视机、一台农用车,更不可能娶到一个女人。
这样的事实,老人太知道了。
但是,老人有老人的理想,他不想在百年之后,给两个孙子留下的只是一堆毫无牵挂的废墟。至于孙子要不要那是孙子的事,至于孙子将来回不回来那是将来的事。自己能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必须得给两个孙子留一攒院子,得为他们的将来准备一处归处。
灵魂深处
作家梁鸿曾说,乡村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但是又有哪一个事物不是矛盾的存在呢?矛盾恰恰是万物发展前行的动力和常态。乡村在这些年里,因为缺乏有规划的开发,成了粗犷、旧有、落魄的代名词。当然,也正是因为它逃过了过度的开发,又成了青山绿水、花繁叶茂、泥土香郁,田园风光的象征。乡村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肉体的栖身之地,还是灵魂的寄托之所。乡村偏陋,但也有高雅,因为乡村有旺盛和长久的情感;城市繁华,同时也孤独,因为城市里到处是铁条般冰冰冷冷的建筑和秩序。
这不是孰高孰低、谁优谁劣的问题。城市的快速发展是城市的需要,乡村风貌的保留有乡村的理由。世界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平面的,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内心需要,自然也应该是多方位、多角度、多种可能的。
我们说乡村是安静的,那是因为在乡村自然是大部分,是主体,人只是小部分。而在城市里,到处是人,到处是喧嚣与杂味纷陈,那是城市本该有的特征。钱钟书的《围城》是个很好的哲学命题,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我们都有着同样的心理,拼命想进入,又拼命想逃离。其实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城市与乡村并不对立。城市便捷、高效、光怪陆离,乡村宁静、散漫、自然而然,各有美处,也各有妙处。上文中的老人兴许想不到这些,但他心里明白,儿媳妇带孙子去大城市的选择是对的,那里有一个人成长中所需要的更多营养和挫折,几十年后的将来……将来,是个沉重的话题,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各地城镇化进程加快,留在村里的人真的越来越少了。在我的家乡,我记忆中人口有千人之多的村庄,现在人口不过二百,百分之八十外迁,大部分还是年轻一代,还带走了自己的子女。我們似乎陷入一种悖论,村里人说,现在村里学上不成,病看不了,连买瓶酱油都没有地方买。但是反过来,一个村不到十人,除了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多岁的,孩子没有一个,村里还怎么再有学校、商店、卫生所呢?
在我粗浅的认识里,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或者说,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最大的区别,看似是因为科技,但背后实则是金钱观的差异。在农村你种一亩地和我种一亩地,一年下来收成差不多,但在城市里因为掌握技术或拥有某种资源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就可能天差地别。因此在农村与城市,人们发奋努力的动力与成因,其实本质上是不同的。
费孝通在谈到社会时就讲,社会的本质不是“共同”,而是“一致”。我理解“共同”的基础是“合作”,而“一致”的背后是“竞争”。这样说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乡村,“社会”就要浅表了一些,而城市里,“社会”就要深刻许多。我们喜欢用“机器”来形容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每个组件不停地高速运转,每个轴承、每个齿轮、哪怕罅隙间那层薄薄的润滑油,都有自己的作用和使命。只有大家都拼出自己的本职之力,让这台机器输出最大功率,社会才会快速发展。当然,大家为之拼搏的目的是——为了向前进,或各自所得的幸福。可是怎么来定义“向前进”与“各自所得的幸福”呢?向前进要好解释一些,但幸福就难了。
我们在城市一提到社会,很容易就联想到一台隆隆作响的机器。可是回到乡村,你就很难将社会与一台机器联系在一起。当你回到乡村,或坐或站在屋顶的高处,去瞭望那一层层绿色的梯田,那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你可以看到成群的蜻蜓在身边飞来飞去,远处和近处山野上的树,也因为不再有人砍伐而茂密了。在那时,你似乎才会真切地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它的内涵上还包括了自然与人文。
两个月前,我回了一趟老家。我老家在太行山里,一个小山村,同样是贫困村。正好是农历六月初九,再过四天就是村里一年一度圣母龙王的庙会。到那天,在外的人都会尽可能回去,我母亲几乎年年都回去,尤其是村里唱戏的年份,台上唱戏,台下各种买卖生意,四邻五舍的亲朋好友都来,场景好不热闹。后来,村集体没钱,唱不起戏,就有村干部登门入户找人捐,再后来也有村里跑运输的年轻人自发出钱请剧团。理论上,剧团唱戏是给圣母龙王看的,但看戏的还是本村和上下邻村的老百姓,说是庙会,其实就是一次乡村聚积人气沟通有无的机会。
自从有一年建在南边的戏台被暴雨冲垮后,村里就再没唱戏了。六月十三回村的人,也就少了。可我母亲还是坚持回,之前说是为了回去打看打看房子,毕竟六月份雨水就开始多了,水渠通不通,修修补补的事总是会有的,今年她另加一条,说要回去看看家里的厕所改成啥样子了。
不知道是不是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还是脱贫攻坚里的一项具体内容,但说要把厕所改成水冲式的,我还是震惊的。我们村至今没有通自来水,高高低低的窑洞多建在石头山上,地下根本没有管网,之前的厕所都很简陋,院门外垒起一人高的墙,上面用干草搭个顶,下面挖出一个坑再在上面垫两块石头就是了。差不多家家如此。因此每到一户人家,没进大门前,总会让你先闻到茅坑的臭味。
这次回村,感觉确实大变样。也就两年时间,它的变化已经超出我十七岁离开村庄到现在三十年的总和。那种变化远远不是村容村貌的变化;不是之前我上学时翻山越岭步行七八公里却依然是一条羊肠小道,变成了现在黑油油平坦宽阔的公路,路旁竖起护栏种上柏树的变化;不是村委大院外在广场上,竖起黄底红字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巨幅宣传牌的变化;不是村东村西中间那条河上架起了新桥的变化;不是村中的那棵千年古槐、村南一座抗战时期有四五位区领导惨死在那里的古庙旁立起了漂亮的石碑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我的内心,是一种由绝望或失望,到充满希望的变化。
我们家的厕所确实改了,换成了坐便式,旁边墙角的砖台上摆放着一个白色塑料桶,冲洗时只要用力摁几下桶盖上的液压装置,冲力很足,操作简便。所有的厕所都上了天蓝色的铁皮门。进门用了一次后的母亲非常满意。但她还没来得及看的是村里其他的变化,村里所有的街街巷巷都做了整修,磨坊前原本破破烂烂的猪圈和粪坑,也做了清理,平整的水泥路上垒起高台,台上鹅卵石铺地,中央恢复了一盘石磨,和旁边的古槐、旧院交相呼应,倒成了一景。
于是我想到,前几年网上的一则新闻,说一对年轻的北京夫妇放弃了北京的工作,用积蓄在大理买了一处院子住下来,一边搞民宿,一边过起了自己舒适轻松的生活。还有另外一则说,一对美院毕业的小夫妻到郊区租了一个农家小院做起了陶艺,男的做陶,女的金缮,日子似神仙。类似的新闻其实不少,生活舒不舒适轻不轻松,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知晓,日子似不似神仙,也只有过日子的人明了。可我相信,两对夫妻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生活。不过最近《新京报》报道,河南省新县的西河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让这个原本只剩下三十九名老人的村庄有二百多名村民重新回到了村里,却是人们重新选择生活方式的又一例证。
也是在今年夏天,我去山西省武乡县分水岭乡的泉之头村采访。那个村,村东有眼泉井,泉水四季不息、冬温夏凉、清冽可口,村庄周边森林密布,水源丰富,山水配合形似展翅之凤。村庄不仅风光优美,出村不远就是云竹湖水库景区,更主要是文化积淀深厚。村里的民居,多数坐北朝南,布局为前庭房,后楼院,既有两进院落,又有辕门院的五进楼院。大约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陈氏宅院,土、木、石、砖混合,檐升斗飞,雕梁画栋,是武乡境内不可多见的著名传统院落。那个村曾经出过不少高官大贾,在晋商辉煌时期,村里的陈家就是其中一支,他们的足迹遍布广东、山西、北京、内蒙古,甚至俄罗斯。走在泉之头的街巷,明清建筑随处可见,因此也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从县城方向沿公路而来,右手边是泉之头要整村搬迁的新居,雏形已形成,左边是旧村,一条护坝已经整修一新的小河将其一分为二。旧村里那些老房子,很多已经久不住人了,有的已经颤颤巍巍,眼看就要坍塌,但在村民们眼里却成了宝贝,在过去他们看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承载历史的旧物,现在却成了村庄迎接未来的新希望。
这让我突然想起关于我和姥娘的一幕:我离开老家,尤其到太原生活后,就很少回老家了。因为厕所、洗澡、用水等诸多的不方便,每次回去,基本上也只是送个脚踪打个照面,匆匆地回,又匆匆地离开。我是姥娘唯一的外甥,小时候在她身边生活多年,每次回乡自然必去看她。有一次,我离开时,她送我到村口,那时她已经八十六岁了,站立对她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她坐在路旁的石头上,扬着满是白发的头看我,她紧紧地拽住我的手,问我,孩子,你真看咱这里不亲了?我木讷地站在她面前,却无法回答,因为我怕一回答就会惹她伤心。就在这时,有个中年男人路过,他笑我姥娘的问话天真。他说,咱这地方穷山恶水,要啥没啥,有什么好亲的呢,你快让孩们走哇,要是再年轻几岁我也走了。要知道,那个说话的中年人是村干部。后来我上车,加油,摁喇叭,像往常一样一溜烟快速离开。那种快速是一种决绝,是一种斩断,因为我不想让姥娘在村口望我太久,更不想受这种亲情牵绊。
姥娘下世后,我每次回老家总会想到这一幕,我却没有回味过姥娘之前跟我说的另外一句话,她曾和我说,孩儿啊,山不亲水亲,水不亲人亲,人不亲还土亲了呀……姥娘始终没有说出下半句话。后来我才体会到,姥娘是在提醒我,人不该忘本。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觉醒,因为从小到大“人往高处走”的想法,牢牢占据了我灵魂中最为中心的位置,在村里,我眼中的高处是乡镇;到乡中学上学,我心里的高处是县城;到了县城,这个高处又变成了太原、上海、北京。那么,如果再到了上海、北京呢?飞机、高铁、四百多米的高楼、一个接一个的会议,我们每天都在为“幸福”这个高处而拼命挣钱,钱是挣到了,可是,我们幸福了吗?
我不知道如何作答。
可能与年龄有关?尤其今年回了一次老家后,我突然想问自己,难道生活在乡村的人就远离了幸福?这几年农村大搞乡村振兴,更进一步讲,一场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还在进行,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或者说汲取了前些年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这几年农村的发展更加尊崇自然、尊重人文,更加因地制宜、强调以人为本,乡村已经或者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它也越来越成为追求自然恬淡之人所希望的样子了。
记得有一次与作家张锐锋先生聊天,他说,乡村的问题不是经济上的贫穷,而是希望问题,人们之前对乡村失去了希望才是根本。这么多年来,我们似乎也感同身受,当人们听到上海、北京那样的繁华城市时,眼神里流露出来的那种情不自禁是闪闪发光的,似乎只要置身乡村,就在低处,只要抬脚迈步,就是攀向高处。那么,当他们有朝一日去上海、去北京设身处地打拼,他们坐在几百米高的大厦楼顶,再往哪里张望呢?
要我说,如果人类必须要有一个奋斗的高处的话,那就是“幸福”,可是,通往幸福高处的道路有千万条,城市,或者乡村,只不过是其中的两条罢了。我还想说,能够照亮前行之路的光,应该来自希望。那么,无论是留在乡村里的人,还是对乡村寄有乡愁的人,会不会重新审视乡村,重新定义幸福呢?
兴许,我对乡村的未来太过乐观,兴许这种乐观充满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但我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因为时间这条大河比大地更低,比大地有着更大的包容,也终将会给我们提供出最有力的实证。这也让我进一步觉得,一直以来我们自以为看清了前路,一直在大地上撒欢、恣意,以幸福的名义狂奔,但是到头来,我们很可能走反了方向。
人往高处走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自然规律,甚至可以说是天道。但是,“何处是高处”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
【作者简介】 李晋瑞,山西平定人。著有長篇小说《爱上薇拉》《中国丈夫》《原地》以及中短篇小说集《陌生人的玩笑》等多部。曾获赵树理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