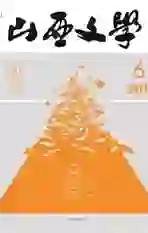无极之命 (创作谈)
2021-06-02梁豪
梁豪
“极命”是某个地方的人的口头禅,相当于一种感叹。这个地方是我的马桥或说哈扎尔,我在小说里称之永安,那是它的曾用名,我以为挪来虚构挺合适。这词什么意思呢?用小说里的话讲:“不妨理解为生命当中的某些极限状态。”而“在這种状态底下,人很难正常行事,容易冒失,旁人看了,半是唏嘘,半觉荒唐”。永安还有很多颇值得玩味的惯用语。比如“事闻多”,是形容一个人难搞,毕竟只有不好对付的人才“事闻多”,一般百姓理应众志成城默默无闻。还有像“画鬼画出肠”。韩非讲,画犬马最难,画鬼魅最易。道理不难理解,至于画出肠来,是又从“人皆未见之”的抽象拐回不难想象的具象,而且那画笔俨然成了解剖刀,令里外虚实不分,实在多此一举、画蛇添足,糊涂常因反被聪明误。此外,形容将老之人眼眶凹陷叫“落里”,而身骨缩窄称为“落格”或“落架”,里子格子架子回落,正是一个人日暮黄昏的景象,有多生动就有多凄凉,因为毫无元气复盈的办法。
故事发生在这样的永安,主人公林明,在外是防疫站的办公室主任,在住家附近,他是所在街巷的小组长。在不大的南国永安,他无疑是有头有脸的一号角色。这篇小说有些像传,我在意的是他的人生。儿子林玺的种种变故,无疑是让林明和林家发生重大转折的根源。所以我感兴趣的似乎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是如何变得灰头土脸的,以及,在这么一个把人瞧得分外仔细的社群里,他又将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这么看,好像是我蓄意要逼出主人公骨子里的韧劲,而坚韧的前提是,他得认,认他的极命,之后,靠自己,将时间轴拉长,过好接下去的命途。
但最开始,我不过是想笑。我试图让这笑不那么简易、浅白。其实今天我们并不缺笑,如火如荼的脱口秀、喜剧类舞台剧、相声社,还有大量真人秀节目,都在竭力让我们发笑并从中套取商机。不妨回想咱们十几二十年前稍早的综艺节目,《开心辞典》《幸运52》《曲苑杂坛》,甚至《相声大赛》,都脱不开“正襟危坐”的底里。于是,那些零零星星的笑,是春回大地艳阳朗照丹桂飘香瑞雪丰年的笑,是循序渐进点到即止的笑,又或始终戴着精致的假面,端庄有余,优雅过剩,美中不足在,电视外面的人并不觉得十分好笑,或者说,嫌它没法狠狠挠到痛处和痒处。彼时娱乐要么阳春白雪,要么下里巴人,短缺的是阔大的中间带,因此,幽默权基本专属来自“大城市”铁岭的“小农民”赵本山。现在,我们大体摸爬出相对常态化的释放渠道和幽默节奏,少有人再去指摘全民娱乐,因为木已成舟,这是苦闷得以悬置乃至和解的巨大刚需,存之已久。
那么,小说能为这个笑的时代做什么?将段子串成一个同心圆一株幸运草?将玩世不恭进行到底?还是乐极生悲,或者悲欣交集?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小说无妨让笑更深刻一点,且把这份深刻埋得更深一点,就埋向生活的内部,然后,看它笑出个什么样子。
林明绝非一个懂笑的人,我们却常能从他煞有介事的言行中俘获笑料。在专论笑与滑稽的《笑》里,柏格森指出:“如果一个人有孤立的感觉,他就不会体会滑稽。”即,“笑需要一种回声”——当然,我同样常在这类回声里感到透顶的无聊,这是题外话。总之,是这样一个与“笑的回声”绝缘的人,突然没收了我们同频共振的笑意。因为他,因为这个三口之家,陡然让我们体会到孤立无援的汹涌的压抑。那一刻,我们离“命”更近了。这是人物带领我历经的峰回路转。
好一个全民学习幽默、寻找幽默、掌握幽默的时代,我爱这个“笑林”时代。若说还有期待,我愿斗胆扫扫大伙的兴——别忘了还有大量的时刻我们无从发笑。正视这些瞬间,或许我们才能更为持恒、更加坦然地笑对人生,笑迎未来。正因为,人先是孤立的,担待它,渡过它,享受它,正如享受群体阵阵的狂欢。
命本无极,生生不息。这是最大的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