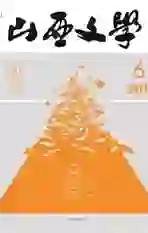极命
2021-06-02梁豪
林明,人如其名,不够出挑,但却好记,因为下巴歪长着一颗痣。鸦青色,凸起,豆豉大,痣上葱茏着一绺毛,日光下是飘飘的绯红。老太太说了,不能剪,更不能点,害了命水。林明觉得有碍观瞻,总可以修吧,不问意见,偷偷裁了几刀,感觉日子照旧风调雨顺。
林明在防疫站高就,县里不兴跳槽,安逸为大,干了一辈子,风浪里颠簸过几下,感觉不成人精,也绝不会捅出什么大娄子。这一世要就这么耗光,林明也觉得不枉此行,很对得住下巴这颗风雨不动的宝痣。
因为嘴里生了两颗龋齿,当年林明报名参军体检遇挫,在家哭了两天半,心底很有些埋怨在百货大楼上班的母亲。罪状有二,其一,以前母亲总把几颗大白兔藏兜里,带回家让他吃;其二,监督自己刷牙不力。是不得已,林明被父母怂恿去了县防疫站。家里人倒是高兴的,说只要不犯大戒,这辈子高枕无忧了。林明面目清冷没搭话。
林明参加工作早,工龄长。以前的登革热、天花、肺结核、疟疾和麻风病,都让他给赶了趟儿。林明手巧,打针不疼人,不管是三角肌、大臀肉,还是手背上藏蓝的静脉,笑谈间,一针筒的药水就空了。县里人没少称奇,在更年轻的女护士进站前,林明在防疫站很吃香,人人都嚷着,让小林医生给我扎针。
但小林医生正值事事敢为人先的年纪,并不总黏在防疫站里头。上街道跑乡镇,接种牛痘,发放脊髓灰质炎糖丸,有样学样地跟一脸鼻涕的孩子们合照,再往前,还跟过卫生局的人一起落村落户,宣传卫生教育,推广避孕套,让妇女把月经带换成卫生巾,不要随地大小便。永安县辖六镇三乡,林明捏着指头算了算,自己在各处地方,挖了不下二十口粪坑。
县城小得亲切,大家低头抬脸,总能碰上几个熟眼的。一有事,都张罗。当年人防办往山里挖洞,林明去撂过几次铲。植树节,单位大门跟前的桂树苗,有一抔土就是林明培的,如今树已赛楼高。九八年的大水,他也陪着武警战士守过夜,喘着大气扛沙袋。更别说政府办的五一表彰会,领奖的领掌的,林明都露过脸面。怎么说呢,全县一盘棋。
林明的主心自然還是祖国的防疫事业。谁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冷链运输出了状况,扎针就相当于注水,水痘照长。也不排除有些批次在源头出了问题,打了两针狂犬疫苗,狗是好狗,倒把人的眼睛打瞎了。最让老林揪心的,到底还是孩子。注射了疫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或者大脑受了损,一辈子就这么交代了。和解不了,家属便带人来闹。防疫站所有人这时都往里缩,边退边拨110。就他林明挺着一身瘦肉出去,向家属耐心解释。药不是我们审的,更不是我们造的,平日里兢兢业业,打针连带说学逗唱,要讲委屈,谁比得上我们?厂商弄虚作假,远在东北那旮旯呢,咱鞭长莫及啊,再说,也得听国家的发落。现在,我陪你们一起骂娘,日他先人。
人家也不是不懂得抓弱点挠。平日注射大厅里,免费疫苗便散漫,自费的就勤快些,都是见钱眼开的货色,不要把自己撇得那么干净。还有,给我们外人打国产的,给自己亲戚家孩子就打法国的五联,别以为我们没有小道。
实在没招了,林明也只好跟着退回去,顺带把门用U型锁扣死,等待警方来救急。好在这样的事件屈指可数,林明把它们当作一种阅历。人生一世,谁还能处处都得意的。
林明心里不是没有芥蒂。他最看不惯那些没遮没拦的造谣者。有人搜刮了一些信息,急急放出风声,说什么林明夫妇搞黑心一条龙,净赚病人弱者的血汗钱。林明倒没生大气,更多是哭笑不得。林明的妻子黄琪,在县第三人民医院上班,不过是给病人打针吃药的护士。平常,永安县人更喜欢把第三人民医院喊为精神病院。
而今,小林熬成了老林,不坐窗口了,底下管着一批疫情员,堂堂的办公室主任。那回单位组织去了趟灵渠,林明跟带字的石头和匾额都拍了合影。什么年纪干什么样的事,林明没觉得不妥。他喜欢到此一游,爱拍照,还爱大团结,指挥座次排序,总是最后一个入镜。对此领导应该很满意,会上常说林明懂政治、讲政治。林明的心思就更活络了。
眼下的流行病似乎比从前来得少,也来得温和。防疫站的核心业务,转为发放餐饮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很多人卡在采集大便的环节,心里有些打紧,半天屙不出,光腚占着茅坑,内急的工作人员的脸,比大便还臭。林明见了,骂这帮小年轻没有服务意识,连带说了很多遥想当年的话。我跟你们一般大的时候,一天从白到黑,去了张村到李村,早忘了自己拉撒的事儿,相反,是在全心全意解决群众的拉撒问题。我这辈子挖了不下二十口粪坑,解决了多少人的排泄问题,你们可以算算的。现在生活宽裕了,看把你们个个给憋的。男男女女的只赔笑,一声不吭,林明就嗟一口气,背过手,踱回办公室吹二十六度的空调,看看人机斗地主的手气换了没。
过些日子,林明自己去放水的时候,感觉管道紧得难受,到后头,不放水也疼得两脚发软。黄琪搀着他去医院的泌尿科,做了检查,确诊为肾结石。黄琪抖着片子说,结了十好几颗呢,葡萄似的,你瞧瞧,都比当年送我的钻戒肥。
从那以后,林明去哪里都提溜着一个保温杯,间隔约莫一小时就跑去解一次小手。防疫站的大楼是六十年代的苏式老房子,卫生间没装小便池,大小问题一处解决,所以人都在门口排队守着。大伙见林主任来了,纷纷让道,说您先请。有次实在憋急了,林明猛拍门板,喊道,同志啊,不脱裤衩,在外头蹲着酝酿,不也一个卵样?后边一个后生把持不住,浅浅笑了一声,大伙紧接着一起哄笑。
卡介苗、水痘、百白破,防疫站里预防针也照打,只是现在大医院都有疫苗,所以防疫站就显得门庭冷落。但只要阿猫阿狗在,就还得给阿猫阿狗打疫苗,同时给被阿猫阿狗咬到的人打疫苗。县里到今天,也没开出一家专门的宠物医院。公安局组织过几次打狗行动,打了疫苗的狗耳朵上,都得串起一颗白纽扣,没有的,就等着吃棒子。那期间,来的人和狗都特别多,防疫站的护士就得累一下,林明若是心情澄明,也会间断性重出江湖。狗听不懂人话,所以疼得该叫的时候照管叫,林明就觉得,人真是高级动物。
防疫站有个水泥篮球场,林明偶尔喜欢露几招。很多放学的初高中生,还有附近的居民,会来这里凑几局,排排汗,下班时间门卫一般不阻拦。有时候肢体动作幅度大,火气上来了,林明就把这些初高中生给轰走,闩上铁门,不怕人嘘,自己在场地单练三步上篮和三分球。心态不稳定,篮子屡投不进,林明面上强装镇定,其实心里很生着自己的气。
总体上,防疫站的日子水波不兴,晚到早退,理解万岁。下午太阳不旺的时候,林明就捏着下巴痣上的毛,到菜市场吹一曲哨,跟人抱怨几句物价的涨幅,照例杀杀价,回家洗菜做饭去。因此,林家揭锅通常比别家快几手,饭后散步也比别人早上一个小时左右。邻人见了,问,林村长这是退休啦?这边回,远着呢,再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那边改为哼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林明跟着和那最后五个字。
在防疫站,别人喊林明医生或大夫,在住家一带,大伙都喊他村长。县城早撤了村,最小的地理坐标是巷。可巷里住着的人,很多上半辈子还在乡下劈柴插秧,晚近才在县城混出了身份。所以到选街巷小组长的时候,还是喜欢叫村民小组长,到最后,把小组长也换成了村长,到底顺口至上。林明是在县城长大的少数派,不管是父辈的意见,还是自己的经验,这档事不提也罢。三年一届的小组长选举,无需候选人,大家都能使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记名投票,选一块平整的空地,有专人唱票,另一人拿著粉笔头画正字。这时候的林明多少有些紧张,躲得有点远,单念白一句,还是不当了吧,换换将也好。
过程是紧张的,结局是满意的。林明再度连任,邻里统一鼓掌,喊他林村长。林明就笑,作揖说,不辱使命,不辱使命。
戴着头衔好办事,指挥起人来,林明有时候不大分长幼。公共的路面起坑了,到各家张罗款项,水泥地熨得比衣柜里的衬衫还平滑。谁跟谁家闹了纠纷,他林村长也会出面调停,脸色铁黑,有几分神似金超群扮演的包大人。上头来了方针政策,他赶紧召集大伙开小会,以家庭为单位,谁家不来代表,他就当众点名批评。远远地听到有人喊,来啦来啦,刚上着大号呢,总得擦擦吧?文件他是一字一句地念,越念越有些磕绊,两眼瞟瞟聊起小天的听众,说,还是讲方言吧,大家都容易懂。念完了,让诸位回去再好好学习巩固。每逢公益活动,比如人口日、禁毒日的文艺晚会,他也不忘跑到各家窗户边上吆喝一声,得空去看看啊,不然观众席太空,电视台拍起来不热闹。
有说他官僚做派的,也有夸他称职肯干的。来年再选举,还是他林某。黄琪总说他好管闲事。林明捻着痣毛说,能耐大,怨我咯?
倒有过一回,林明落选了,差了第一位三张票,估计是大伙看腻了他下巴的大肉痣。为此,林明不跟邻里吭声了个把月。大家后头把这当故事说,最后来一句,极命啊,真是极命。极命是永安县的方言,非要搬弄字面的意思,不妨理解为生命当中的某些极限状态。在这种状态底下,人很难正常行事,容易冒失,旁人看了,半是唏嘘,半觉荒唐。那届的小组长,主动放弃了连任,开天辟地只干了一届,私下里笑说,再不让贤,怕林明往我孙子的屁股蛋里打石灰水。
林明晚婚,主要是给前一任女人耽误的。到谈婚论嫁时,女人突然跟了一个做糕点的温州佬。温州佬的西装头总是香而湿亮,费了不少啫喱水,脸颊陷着,皮肤很白,林明见过,到底君子,不事声张,也不做欺负外来人口的事。女人的说法是,林明太大男子,不懂换位思考,嘴巴也不够甜腻,于是就做了糕点师傅的太太。林明认识黄琪的时候,特地问了人家,你喜欢甜口还是咸口?黄琪人机灵,说我喜欢你这口。林明就笑了,是他要的女人。
林明顺带着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四十岁才尝到当爹的喜悦。黄琪大龄产妇,孩子装肚里沉得吃紧,还多动,想说这小子踹得那么狠,将来铁定随他爹,十足的猴性。性别早就验过,但探出脑袋哇哇哭的时候,林明还是泪雨如注,在产科的楼道里喊,带着秤砣的,带着秤砣的!林明鼓足干劲,誓把优生优育也给做到位。
当年林明查了半天《康熙字典》,翻到某页的时候,眼睛亮了几道光。玺者,信也,古者尊共之,秦汉以来唯至尊以为称。多么霸气外露,当儿子的名字正合适。
林明对林玺,打小管得严,《增广贤文》里讲得在理,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林明让黄琪也记着,底屋教儿上屋精。每周一到周五,不许出门玩,必须在房间写作业、练习题。近年来吻戏多,电视禁看。周末有两小时的放风时间,林玺喜欢到家附近的竹林里待着,挖些蚯蚓,弄成几段。黄琪问,怎么不跟小伙伴闹?吸一把鼻涕,不答。板起脸再问,说不亲,都不跟我玩。其余的时候,林明给儿子报了书法班和国画班,后来还报了英语和奥数。儿子既不反对,自然也不支持,背上书包就出门,踩点到家。
林明统管大节,黄琪负责小节。每小时去一次小解,不然尿囊易结垢,别学你爹给堵上。每天必上一次大号,否则等于吸包烟。管喝水,一天八杯水,早上第一杯是黄琪泡好的蜂蜜水,利尿利便。一口饭至少嚼十五下,一餐饭不得少于四十五分钟,当心长胖,对肠胃也不厚道。林玺嗡头嗡脑,很是乖巧。
散步的时候,黄琪说,我看儿子不随咱俩,一点也不够活泼。林明说,文静一点不好吗,非得闯出祸来,你才有戏,看了高兴?黄琪怼回一句,接着说,将来倒是可以考虑学医,沉得住气。林明摸着越来越秃的脑勺,咧嘴笑道,真给你蒙对了一句话。
那回林玺主动到卧室里找黄琪,黄琪将《知音》撇下,半边脸上写着欢喜,半边脸蛋挂着讶异,问说咋啦玺?林玺脸蛋红透,支吾了小半晌才冒字,说我按着书上的方法,给自己检查了一下,发现左睾丸上,长着一块肿瘤,估计得了睾丸癌。黄琪吓得从床上蹬起。人已经发育,又不好意思翻下裤头查看,黄琪赶紧打电话给林明。事关重大,两人当即约好到医院会合,就找上次打结石的黄大夫。一通检测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林玺自己躲到卫生间里,掏来掏去,回来说,现在又好了。黄琪回去路上开始教育儿子,少疑神疑鬼,书没读透,先成了神经质,想我给你打几针地西泮?
黄琪如今做到护士长,两口子饭后无事,偶尔切磋辖人之道,边交流,边偷着乐。评上职称的时候,林明负责安排,跟医院的领导吃了一桌上好的。领导喝高了,开始大夸黄琪是第三医院的定海神针,缺了她,病人就开始整宿整宿地闹情绪。黄琪嗔怪道,敢情我也神经病。众人的眼窝于是笑出几线热辣的泪来。
论资历,黄琪也到了这份上。当年还是黄毛丫头的时候,抑郁、精神分裂、精神发育迟滞、癫痫,全混在一块,断无医疗区和康复区之别,也没有轻重症之分。眼下这身胆量,就是这么硬生生磨出来的,晚上走夜路,哼起《敖包相会》,不降调,不破音,一个半拍都不赶,心都不多跳两下。这一路过来,杀妻的、自戕的,见得多了,也就有些以怪为常。有时得上手腕,黄琪也不含糊,练出了两截好臂力。要掰手腕,林明还真未必是老婆对手。
现在条件自然比以前好太多,病人们可以打牌下棋看电视,药也不敢上猛了。不久前还装了中央空调,把他们一个个给逍遥的。眼下难就难在床位不足,共计一百零八张床,也就能躺下一百单八位好汉。有医好了的,家里人不敢签字,生怕放出来再祸害人间,把出院健康指导手册当废纸卖。看形势,唯有走扩建一条路,只得老老实实巴望着上头批钱批地。
林玺学业不赖,开家长会的时候,班主任对林明说,就是不爱笑,也不够合群。林明不以为意,搓搓黑色素越发亏空的痣毛,说这小子跟我一样,小时候腼腆,将来出了社会,经人一点拨,早晚彻底疯开了。
林玺高考考了个二本,在永安县算喜事。那时还是估分,填报志愿的时候,林明和黄琪四处打探消息,查了两天两宿的报考指南。林明很久以来都没这么用功地吃下一本大部头了。最后四个志愿,都给报了医科院校。提交的前一刻,夫妻俩问林玺,你有啥意见或建议吗?林玺拱了拱溢出镜框的镜片子,摇了摇头。放榜出来,最后一个捡的漏。他们不知道还有大小年一说。
两口子都称得上医护人员,但看牌面,到底算不得大中至正。他们希望儿子可以成为正经八百的医师,将来救死扶伤,胜造七级浮屠。他们私下里也不否认,当医生,收益那个好哦。
从第一步来看,儿子走得有惊无险,学的是口腔,专业是个好专业。林明闲来到镜子前,翻起嘴唇,照照里头几颗糟心的龋齿。真是奇迹,越瞅还越顺眼了,似乎天生这般。想来不剪痣毛是对的。
上大学后很长时间,林玺都没用手机。林明说,我得联系你,不能总打座机吧?十个电话,九个无人接听,还有一个是舍友,总听不懂林明的普通话。儿子并未吱声,林明于是给他买了一个山寨机,铃音很响,无关音量键,里头说话,五十平米内都能感受到当中的语气。
那回放假,趁林玺去洗澡,林明翻了翻他的手机。没有一个口气暧昧的联系人,应该说,都没什么人跟他联络,手机干净得像个新机。林明下意识冒出一句,怎么跟木头桩似的。黄琪说,奇怪,医学院照说女娃娃多得数不过,挑花眼了?林明在手机的一个子文件夹里,翻见了三个视频,都是赤发白面的洋人,行着苟且之事。林明赶紧把手机按灭。待儿子出来,林明笑嘻嘻地说,玺啊,学校里有感興趣的女生,可以交交朋友,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留学生也可以的。儿子立在那里,发丝渗着豆粒大的水滴,脸一路红到胸口的肋骨。
那天,负责教务管理的老师忽然打来电话,说林玺在学校,不爱吱声,也不结交朋友,感觉活得太自我了,担心将来不好适应社会。林明用他那不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们在家也没少劝他,别活成一个焖锅。可老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大学生,文弱一点问题不大,又不是考的武状元。要真改不掉,就由着他吧,胡杨三千年,可不是躁出来的。那头的老师说,现在的问题是,舍友都有些怕他。倒不惹事,就是整天对着电脑打游戏,不跟人讲话,舍友打呼噜,他睡不着,就坐在床板上,打坐似的盯着对方,看得别床的心里发瘆。几个舍友都申请搬到其他寝室,担心他是第二个马加爵。林明倒笑了,说我的儿子,能是杀人犯?那边的老师忙解释,林明打断说,老师您别解释了,道理我懂,只是山高皇帝远的,打电话的疗效有限,还得您跟他多谈谈心,叫他少玩游戏,有这工夫,不如去实验室多解剖几只小白鼠。
过不了一个月,学校那边再度来电。估计上回没说通,这回打给的是黄琪。去电话的人也改了,是学校心理咨询的老师。黄琪报了自己的职业,说咱俩算半个同行。听那人的口气有些凝重,黄琪说,不会吧?那边的老师让黄琪别紧张,跟林玺谈了谈,经初步分析,可能患了抑郁症,同时还有轻度的焦虑症,也不算顶棘手的问题。黄琪突然感觉自己的大脑有几个洞,风声在洞里闯着叫。到底是心理老师,语速一点没变,说了一些关于林玺的情况。一到黄昏心情就低落,学术上通常称为黄昏恐惧症。自我评价低,极度自卑。厌食,一天经常一碗泡面解决。多疑,总觉得自己得了睾丸癌。缺乏快乐,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有成就感。懒。严重失眠。
黄琪提着胆说,老师,叫林玺的人应该也不少吧,您确定没打错?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他从没跟我反映过。除了睾丸的事,我以为他相信医学,不会再生疑虑了。懒倒是真的,稍不留神就跑床上歇着,好在听话,念几句日精于勤荒于嬉,就老老实实去削笔了。那边老师补充道,这就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实话说,林玺现在的状况,恐怕跟原生家庭脱不开关系。
黄琪很纳闷,说我们县里的精神病人,全不长他这样的啊。心理老师很官方地笑了一下,说,咱说的不是一层意思,心理问题不等同于精神疾病。但总之,你们家长得对他上心点,多体谅他的难处,站在他的立场思考问题,学会倾听。黄琪捏着油腻腻的拳头说,我们对他还不够上心?还不够体谅?还不够倾听?感觉再多说两句,就要哭出调子来。那头的老师说,当然,也不排除是天生的,咱们共同努力。黄琪哭得更悲切了。
晚上两口子商量来去,也不知如何是好,饭吃不下,也不去散步了,天黑了一个时辰都忘了开灯。林明咬着烟嘴说,这都养出的什么富贵病,我们那会儿,有罪就受,有劫就躲,躲不过硬扛。先是不饿死,再是吃好的,有肉,不管肥瘦,哪怕是带壳的呢,嘴就咧开了花。哪来那么多愁情别绪,又不是演《红楼》。一顿唠叨完了,感觉心思更为混乱。
打这以后,林明电话里跟儿子联络感情,处处都赔着小心。语调刻意弄尖,显轻快,像是爷孙在对话。那头的林玺闷闷地说,爸,最近咽喉还好吧?
林玺大四那年的夏天,林明终于发现了一些异常。暑假回家,林玺老躲房间里,窗帘拉得严实。三楼朝南的房,暗得像地窖。林明来了气,说好端端的,学什么林彪?一把将整面窗帘哗啦扯落。林玺也不搭理他,回头自己再安上,改棉质的了,照例暗无天日地窝着。原以为在被窝里扎寨,进去一摸,早没了踪影。两边的年纪都长了,林玺的底气跟着有些足,不像从前那么听教。林明早没了杀手锏,总不至于打吧,打不过岂不更难看。
林玺也不嫌热,天天穿着长袖格子衬衫配直筒牛仔。林明闪过一个念想,不敢深思,悬着又万分难受。回学校的前两天,林明一把将儿子的上身薅了个干脆。他高估了儿子的身板和力道。其实只要他愿意,把这小子海揍一顿都不会出大汗。林明真的把他海揍了一顿。他之前从没揍过儿子。林明那时抽出肚腩下的仿真牛皮带,狠命地抽。林玺疼得在地上打滚,哀号。
林明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密麻麻的针孔。天塌了。天塌了就是这样的感觉,针扎的感觉,打滚的感觉,行尸走肉的感觉。
林玺那次屈打成招,说了很多,比他此前跟林明所讲的话码起来还要多。
找不到出口,加了一个名为抑郁症患者自救会的群组,想说可以产生共鸣,得到些许慰藉。成员背景相似,不被人理解,把自己闭合起来,像蚌。一来二去,互相成了不亲不疏的朋友。后来有个小伙私加了林玺,介绍他吃一种类似跳跳糖的东西,说是可以纾解压力。林玺说,毒品吧。那人说,跳跳糖,要不要吧。要了一次,就再也脱不开了。
林玺一年前就辍学了,在外头混迹,缺钱,逼着他兼了两份工,替人游戏练级算一份,偷鸡摸狗算一份。离校前,林玺提早篡改了父母的联络方式。林明后来打去学校和学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破口大骂。他扬言,回头腾出时间来,有你们花红柳绿的。每通电话,最后都成了林明的独角戏。
后来,林明必须服用降压药,不然就得搬医院住。每天早晨,林家总会传来血压仪的嗡嗡声。邻居有起早的,都爱冲门口喊着招呼,林村长,打豆浆呢?林明的声音,比从前弱了几个音阶,自己也不知道捋出了个什么字句。
熟人社会,消息散得快,又以这类消息最让人津津乐道。有人看笑话,有人跟着唏嘘。但凡记住林明长相的,见着了,总会例行公事般交头接耳,跟电视里群演演的一模一样。林明老来余光贼,心里就苦笑,艺术源于生活啊。
林明没能再往上蹬,主任位置退的休,哪儿也不去,不想去,在家里陪着孩子。骑上摩托车,按时送林玺到街道办领取美沙酮,在工作人员闪烁的注目下,一口气吞服干净。街道办的人都认得林明,报一声林大夫,嘴上扯些本是天气预报该关注的事。林明心里五味杂陈,从此更不愿出门了。
如今再进行小组长选举,人堆里就找不见林明。大伙很识趣,从此以后,林村长就再也不是林村长了。想想也是,儿子都没管好,哪来的资格对人指手画脚?
终归不能白白饿死,林明出门买菜,见人都赔着微弱的笑。总不至于哭吧,愤怒不对,冷脸也不对,都不对。说到底,笑也不对的,是一个红钩上点着一捺,错得不过分。
林玺到底没能戒掉,接着糟蹋,更甚了。林明把着钱,林玺没本事,开始以贩养吸。林明听到过几回电话里的交易,就在家不远的那片竹林。那次他恨得亲手报了警,让人赶紧过来一锅端掉,自己后头住了一回医院。当时黄琪把自己摆成大字,拦住警用面包的去路。她哭得浑身湿透,像浑身在哭,说让他再抽一斗吧,就一斗,不然进去以后,怎么受得住啊?很多邻居扒着自家的窗框,在阴影里叹气说,真是极命。
不多时候,儿子又给放了出来。警察说,缺点证据,到底是心魔,心魔难除啊。那片竹林,邻里都警告自己的儿孙不准去,说里头到处是用过的针头,怕不怕?那以后,林明就把儿子锁在家里,装修队来镶了铁窗,房间当戒毒所用。瘾上头,林玺在里头疯叫,黄琪红着眼说,如今上班下班,没了分别。
再不是人也得吃喝拉撒。林玺趁吃饭的空当,逃了出去。林明心底骂了声孙子,彻底寒了心,当从没养过这么个儿子。他的头发愁成了烟灰色,头顶光得彻底,亮堂堂的,照得人心里发虚。他痣上的毛也呈烟灰色,硬得刺手。
黄琪每晚睡前,都给自己服用一粒半艾司唑仑,还是一眼瞪到天亮。谁都可以把林玺当成如假包换的疯子、糟粕,就她黄琪不能。到底共用过一条脐带的母子,黄琪私下里偷偷联系着儿子,塞钱,当年寻思留个洋,回不回来另说,现在都可以打发掉了。多半是给拿去买了解口的。
那年除夕夜,黄琪牵着林玺进得家门。先把他领到供桌旁,给列祖列宗敬茶酒,又拜了三拜。父子俩对视良久。林玺的皮肤泛着绿光,关节看起来有些肿大。林明点了点头,说吃饭吧。自己先动筷子,嚼得脆亮,快要盖过外头的炮竹。
晚上一家人从头到尾看完了春节联欢晚会,都觉得这届小品还挺可乐。黄琪和林玺喜欢大兵,林明还是偏爱赵本山。
林玺又搬回了家里住,窗帘一半遮着,一半漏光。
林玺现在的生活逐渐滋润起来。闲暇时,他喜欢跟几个朋友到池塘钓鱼,总能捎回几条甩得起劲的鲤鱼草鱼。林玺底子还是属静的。林明不大喜欢他的那些朋友,刻满文身,凶煞,但他乐见儿子交朋友。
当年肾结石的一大后遗症,就是养成了起夜的习惯,每次放完水,林明都会顺带拐到林玺的房门前。最近夜里,林玺不爱睡觉,靠在床上看电影,不时哈哈大笑。林明忍了忍,默默把门关上,退了出去,走到阳台抽烟。月光撒遍全身,不暖,也一点都不寒。
来年孟春,下过几场软雨,天氣逐渐明朗了起来。在一个春光乍泄的日子,林玺倒在了一小圈白色的粉末里,白色的粉末洒在房间不见天日的暗影部分。
他是笑着走的。
林家上下送了黑发人。
林明其实很想知道,当时出现在儿子眼前的,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世界。林明不信那里有美味的鲜肉,出挑的衣衫,还有敞亮的独栋小楼。
那天家里来了一名便衣,嘴上捂着口罩。给林明出示了警官证,说自己是缉毒大队的。林明问,为何戴口罩,需要保密?警察挥挥手,说操,那么大岁数,还得了腮腺炎,队里放了几天假,顺便让我来这儿一趟。林明说,小时候没打麻腮风吧?警察终于咳出两声笑,说,那时候,人都自生自灭。林明这下也笑了,笑得很拘谨,他说,是我们工作不到位,惭愧,惭愧。回去拿仙人掌切片,敷一敷,好得利落。
警察后来似乎还说了很多话,但林明到现在,只记住了这么两句。这位警察说,你儿子是我们的线人,有年头了。他之前跟我们说,哪天要是走得匆忙,让我们给你带个话,他这辈子,也是为社会出过力的,没算白活。
当天入夜,林明迟迟不着床。他从厨房里搬出一把多年弃置的镰刀,走了出去。月色凛然。吭哧吭哧,那片离家不远的竹林,被他砍了个干干净净。
第二天醒来,黄琪总感觉林明的脸看着不舒服,却又揪不出错。过了小半天,突然抢到林明跟前,大惊道,痣,痣,痣跑了!
【作者简介】梁豪,1992年生。北师大文学硕士。小说见《人民文学》 《十月》 《上海文学》 《山花》 《天涯》等杂志。有小说被 《小说选刊》 《小说月报》 《中华文学选刊》 《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刊和年选转载。另有诗歌和评论文章见《诗刊》《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等报刊。著有小说集《人间》。有评论文章获《南方文坛》年度奖。现为文学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