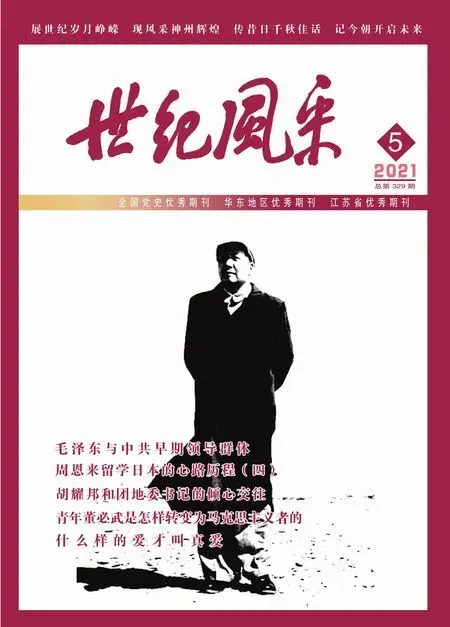油山烽火铸丰碑
2021-05-16庄春贤
庄春贤

1938 年1 月,闽北、闽东、闽西、闽浙赣等游击区领导人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合影,左起:张云逸、叶飞、陈毅、项英、黄道、涂振农;后左起:顾玉良、沈冠国、温仰春、曾昭铭、李步新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央苏区浴血坚持的一段峥嵘岁月,“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1935 年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项英、陈毅到达以信丰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项英、陈毅和红军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与敌人展开了传奇般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一个极其宝贵的胜利”,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凯歌。红军游击队用忠诚、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英雄风采,犹如一座巍巍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心间。
临危受命 勇扛重担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几个独立团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计3 万余人,指示他们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坚守苏区斗争,并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领导机构。
关于留下的人员,后来朱德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采访时说道:
我们把各部队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召集到瑞金,通知撤退的计划。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央委员会委员项英从东线来到。我们通知他留在中央苏区任司令员兼所有留下来继续战斗的部队的政治委员。在兴国前线率军作战的陈毅也留了下来,负责军事……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有一人是中华总工会主席,七个月后被国民党抓到砍了头。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
在主力红军即将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却在8 月28 日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弹片打伤右腿盘骨。陈毅受伤后,先是在兴国,后到博生(今宁都)县江西军区医院疗伤,后来根据朱德、周恩来的指示,由担架员将其抬到瑞金国家医院治疗。
这天,天空碧朗,万里无云,然而陈毅心头却罩着一层阴云。他从《红色中华》上的重要文章及医务人员捆绑器械的匆忙行动中,估摸出主力红军有可能会转移。于是他想方设法让人把他抬到瑞金梅岩背村,找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请求随主力红军转移。
这时,朱德心潮起伏。按理来说,陈毅这样的高级干部,完全可以和主力红军一起转移,可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高级干部的去留名单,都由“中央三人团”决定。他作为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竟然插不上话。他只好抱歉地说:“仲弘,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歇梢,啥子事都不要管,先把伤养好。至于你提出的请求,我会转告博古、恩来他们,你就等通知吧。”
听到朱德的四川乡音,陈毅感到格外亲切,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总司令,十分感谢您的关心,我回去等通知。”
几天后,陈毅伤势变得更为严重。于是他只好写信向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求助。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0 月9 日接陈毅报告自己的伤情和要求做手术的来信后,当即和朱德令卫生部长贺诚取出已装箱的医疗器械,派两名医生为陈毅进行手术治疗。并在次日赶到医院看望,说:中央决定留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秋风吹动着残枝败叶,吹动着身穿单衣的红军战士。陈毅不顾自己伤口未愈,毅然从医院搬到瑞金马道口中央政府办事处办公。他和项英共同筹划,想尽各种办法,组织留守苏区军民支援中央红军长征。
10 月10 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8.6 万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伟大征程。10 月16 日晚至18 日晚,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在茫茫的夜色中开始渡河,向安远、信丰、赣县等挺进。国民党粤军以信丰桃江为天险构筑第一道封锁线,这条封锁线南北长约120 公里,东西宽约50 公里。因周恩来、朱德派出的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的代表在寻乌罗塘镇达成的“可以互相借道”等5 项秘密协议来不及传达到粤军驻赣部队。粤军重兵拦截,红军只有强行突破封锁线,双方打得非常激烈。10 月21 日上午10 时起,红军先后取得信丰百石战斗、金鸡圩战斗、新田圩战斗、石背圩战斗、古陂战斗、安息战斗等六战六捷的胜利。不幸的是,在长征第一胜仗——百石战斗中,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中,壮烈牺牲。25 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发出感慨:“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油山革命纪念碑
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向西突围后,虽然项英、陈毅指挥留守苏区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是敌强我弱,苏区多地被国民党军陆续侵占。敌人对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地主豪绅回来后也进行反攻倒算,很多地方变成“血洗村”“无人村”。朱德回忆:“敌军用二十个师的兵力占领苏区的重要城镇。他们从来没有将武装起来的农村征服,倒是杀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大批妇女、姑娘被抓起来,以五块钱一个人的代价卖给士兵、军官、地主和妓院老鸨……白军占领苏区的行动很迟缓,但很残酷。”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陈毅认为要及时调整策略,“旧的局势完结了,新的局势已经来了。要适应新的局势,就要把领导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转变过来。新旧衔接,事先就要有准备,要掌握这个转折点。新局势来了,我准备好了,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就能保存力量,不会灭亡”。他果断地向中央分局建议:面临强敌压境,我们要赶快做好准备,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争。
1934 年11 月中下旬,宁都、长汀、瑞金等县城相继失守,“赤都”失陷,形势变得非常严峻。项英采纳了陈毅的一些建议,逐步分散干部,同时向中央请示留守部队是否可以突围到苏区近邻开展游击战争。12 月上旬,中央分局和中共赣南省委决定在于都小溪成立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后改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任副书记、刘新潮任少共特委书记,并组编了一个独立营,约700 人,配备了干部。在一个北风呼啸、天空漆黑的夜晚,李乐天和杨尚奎率领部队从于都小溪出发,开赴赣粤边。这支队伍在大田与大埠之间西渡桃江,经峰山、王富圩、大龙、龙回、东西角、茶沿坳、上乐抵达信丰油山槽里村,与中共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中共长安区委书记朱赞珍、中共长安区委组织委员李绪龙等党政干部和武装人员会合,随后转入南雄。他们在油山隐蔽,开始了艰苦的游击生活。
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央苏区的斗争,专题研究并提出转变斗争策略。1935 年2 月中旬,在于都南部地区收到党中央发来“部队应分散突围出去开展游击战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指示后,项英、陈毅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中央军区指挥的所有红军部队分成9 路向四周突围。分局和军区领导除项英、陈毅和分局委员贺昌留下外,其余干部都分配到各突围部队,到邻近地区去开展游击战争。9 路部队陆续突围。2 月25 日,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1200 余人,从于都南部突围,途经信丰铁石口、小河、万隆到油山,作短暂休整后,转移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3 月4 日,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率独立第六团等部1800 余人,分三路从于都上坪向三南(龙南、全南、定南)突围。在信康县唐村(今属安远)遭粤军第一师第一团阻击,刘伯坚负伤在鸭婆坑被俘,21 日在大余英勇就义,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诠释了“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荡气回肠的诤诤誓言。阮啸仙在信丰安息(今属信丰安西镇)地区枫树庵上小埂与粤军第二师教导团遭遇,他被一颗子弹击中,高呼“为革命战斗到底”壮烈牺牲。
3 月中旬,项英、陈毅、贺昌率红七十团分3 个梯队向会昌突围。到会昌县归庄时遭敌阻击,贺昌受伤后高呼“红军万岁”用手枪里的子弹射向自己,英勇牺牲。项英、陈毅率部由天心返回于都上坪,巧遇原信丰县委书记曾纪财,遂决定由曾纪财带路,向赣粤边油山突围。项英、陈毅等人,化装成农民和商人,从赣县立濑巧渡桃江抵达信丰牛颈,几经周折找到了牛颈地下党组织。在交通员带领下,项英、陈毅来到中共信康赣县委所在地雉山(又称蛤蟆岭)。3 月底,项英、陈毅吃尽苦头、几经周折到达油山,与李乐天等会合。陈毅热情而自豪地对李乐天说:“国民党吹嘘说他们要在仁凤把我们消灭,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油山聊天。”陈毅诙谐的话语,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蔡会文、陈丕显等率80 多人到达油山。聚集在油山的红军游击队有300 多人。项英、陈毅在南雄大岭下和大余长岭分别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把聚集在油山的部队进一步分散出去打游击,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改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从此,油山游击战争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艰苦卓绝 浴血坚守
油山是一座脚踏赣粤、绵延百里的大山。山里是山脉连绵起伏,松竹青翠茂密,古树参天;山外却是水陆交通成网。朝东通往赣州至瑞金,往南通往韶关至广州;北通上犹、崇义至湖南,向东南通往安远、寻乌至闽西。登上油山主峰远眺,章江、桃江汇成赣江碧水,北江千里直向南海湖,山河风光秀丽。油山有“万宝山”之美称,这里不但物产丰富,盛产杉木、松杂木、竹子、药材、茶叶、油茶树、山果野菜等,而且中草药很多。这些野生的草药,对症下药,疗效显著,能医治一些疑难杂症。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员缺医少药,许多伤病员受伤,就地取材,挖几棵草药,有效地治愈了伤口。油山的群众基础好,大都是客家人,热情好客,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帮助下,在这里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和红军,一心跟共产党走。
获悉项英、陈毅等到达油山的情报后,国民党军队迫不及待地采取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恶毒手段,对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区,沿渡口、圩镇、公路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同时又用听响声、看烟火、跟足迹的办法,跟踪游击队,妄图在3 个月内全歼红军游击队。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清剿”,游击队员几乎成了被追捕的野兽,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陈丕显回忆说:“搭棚子最好用杉树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窝棚,我们就用树枝把它们伪装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露宿过夜,睡在树下或草上。有时也支个布帐篷,但是没有床,甚至连块板都没有。”陈毅在《赣南游击词》描述了当时的艰辛:“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浸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
冬季北风狂啸,寒风扑面刺骨,树叶发出“哗哗”的声响。跟随陈毅打游击的警卫员宋生发回忆:“一到十月,严冬过早地给山石草木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满山的树枝,挂上尺把长的冰棱,冷风吹来,相互撞击,发出‘吱吱喳喳’的响声;到了来年二月,山下已是风和日暖,春到人间,而山上却仍是严冬的天下,满山满岭冰雪铺地;直到四月,冰化雪消,草木发芽,油山才换上了绿色的新装。”项英、陈毅他们先是搭人字形棚子住。由于棚子目标大,后来只好买纸伞或油布凑合生活,再后来只好住山洞或露天宿营。1935 年冬天,由于敌人“清剿”,陈丕显的背包和衣服弄丢了。在油山,他身穿夹背心和短裤,住在森林或石洞里,晚上他和杨尚奎合盖一床薄薄的毯子,冰雪和寒风冻得他们整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里所写:“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天放晴,对月设野营。拂拂清风催睡意。森森万树若云屯。梦中念敌情。”

向苏南敌后挺进的新四军第一支队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陈毅利用昼伏夜出、袭击、伏击等灵活游击战术,打击敌人。1935 年11 月上旬,信丰游击队陈芳兰、刘崇发、郭祖庭、肖泰志、刘礼鸿、康举洋等6 人,化装成当地农民,身藏武器,从莲花坞出发,经太平围、谷山、游州、水南坝、长岗嵊、大塘埠、坪石圩、力迳圩、月岭圩抵达乌洋游击区,返回油山。他们用火屎炭在沿途的茶亭、庙宇墙壁上,涂写革命标语,署上许多游击队的假番号,向白区群众宣传,扩大影响,迷惑敌人。信丰游击队政委吴汉财,率一个班乘夜到信康交界的犀牛、牛颈、龙回、三益、大龙一带放冷枪、贴标语。标语落款有的写游击队第三支队,有的写第五支队或八支队。然后让老百姓去报告国民党驻军,吓得敌人惶惶不安,赶快撤回。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一诗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
敌人实行移民并村后,红军游击队生活更加艰苦。项英、陈毅和游击队员春天扯来“糯米草”,夏天摘杨梅,秋天采集野山果,冬天挖掘冬笋充饥。条件变好时还会猎取野猪、捉蛇改善生活。陈毅有时也会去掏马蜂蛹。有一次,陈毅带警卫员宋生发、给养员何庆生掏了一大窝马蜂蛹。他亲自动手炒,个个蜂蛹都炒得像花生米一样,吃起来又香又脆。正如在《赣南游击词》所说:“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1936 年2 月,国民党粤军用“篦梳”式的办法对油山发动大规模“清剿”,强迫信丰、南康、大余等县群众,分8 路抄山。敌人夸下海口,用8 天时间全部“肃清”游击队。但是,进到山里只有4 天,群众以“没有带足口粮”“天气十分冷,我们要回家”等各种理由,只抄了3 天,敌人就草率收兵了。此时,大雪封山一个多月,树枝、茅草挂着一串串冰棱,呼呼的北风吹拂,发出“叮当”声音。此时正值春节,躲藏在信丰油山上乐钟鼓岩山洞里的项英、陈毅,连米、菜都没有,上乐的群众就将过年的年货让交通员送给他们。项英、陈毅在信丰油山秘密据点吃着群众送来的食品,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依靠群众 凯旋出山
陈毅回忆说:“敌人的致命伤,就是我们与群众相结合。敌人采用种种办法来对付我们,都是白搭。因此,就对我们采取分区‘清剿’。而我们也采取分区活动。南雄北山是一区,油山是一区,信丰、南康、坑口是一区,长安是一区,三南(龙南、定南、全南)是一区。我们的全部地区就是这几个‘岛子’。”
信丰油山上乐村群众革命积极性非常高,他们自愿组成了游击小组,除站岗、放哨、运送物资外,还直接参加政治、军事斗争。上乐有一个邓坑娘娘,游击队员到她家里,她总是笑脸相迎,热情地炒些好菜请大家吃,还为游击队员缝补浆洗。有一次,刘新潮住在她家里。邓坑娘娘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看待,刘新潮的衣服被雨淋湿了,邓坑娘娘拿出自家的衣服替他换洗,连夜烘干,好让他天亮前穿上赶路。
1935 年夏,油山游击队李绍炳率两名队员在信丰油山上乐村传达项英、陈毅关于反“清剿”指示精神。长安“铲共团”团总林新球率领一支队伍偷袭。革命群众朱叶妹身背3 岁的难妹子,肩挑一担水桶前往菜地浇菜时,突然发现敌人,她不顾自己的安危,转身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高声叫喊:“白狗子来了!”正在村里的3名游击队员听见呼叫,立即离开村子转入深山丛林。敌人恼羞成怒,恫吓威胁村里群众交出呼喊的人。为了不连累其他群众,朱叶妹挺身而出,英勇牺牲。1959 年杨尚奎在《红色赣粤边》满怀深情地讲述了朱叶妹勇救红军的壮举:
两个反动派士兵向朱叶妹扑过来,吓得难妹子哇哇哭叫。朱叶妹两手一挡,说了声:“不要吓我女儿!”转身把背上的难妹子抱下来,交给婆婆,霍地跪倒地上,叩了个头,婆婆一边扯她起来,一边泣不成声。朱叶妹却还是很坦然。
“婆婆!对不起你老人家,我先走了,不能给你养老送终了。”说完,朱叶妹随着反动派走向屋场后面。片刻间,响了两枪,子弹像在每一个人的心上穿过。
勇敢坚强的朱叶妹被反动派枪杀了!
上乐村邓坑娘娘的儿子郭洪传是一名朴实、忠诚、机智、勇敢的农民。1935 年冬天,项英到上乐村指导工作,召集刘符节、刘新潮、郭洪传等人开会。项英分析说:粤军将山区群众赶出山外,企图断绝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为此,项英决定在油山坑口村滴水垄设立交通总站,由李绪龙担任交通总站站长,负责赣粤边特委主要活动区域的交通联络工作;在上乐村上乐塔设一个赣粤边特委交通站接头处和赣粤边特委油印处,由刘新潮负责。特委油印处有三个人:郭洪传担任交通员,经常为游击队传递情报,油印员谭延年,炊事员黄老伯。项英、陈毅起草的各种政治声明、宣言、宣传大纲及红军游击队识字课本等,都是在这里印好后,由交通员送往各游击区。李绪龙、郭洪传等交通员,依靠群众帮助,闯过一道道难关,及时把项英、陈毅的指示传达到信康赣游击区、北山游击区、南山游击区、油山游击区和上犹崇义游击区。上乐塔下的游击小组,利用赴圩和晚上去大余新城看戏的机会,把特委油印处印制的标语传单,秘密散发到新城敌人的据点。
在油山奋斗的峥嵘岁月,是陈毅一生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反“清剿”斗争中,许多干部和战士英勇牺牲。1935 年冬,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与敌激战中在崇义赤水仙牺牲;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在信丰上塘村受伤后,为掩护战友突围,连续击毙几个敌人,最后从容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曾纪财突围到了油山后,项英、陈毅任命他为中共大龙中心区委书记,他骁勇善战,屡建奇功,1936 年2 月被敌包围,不幸被俘,坚贞不屈,在信丰牛颈英勇就义。陈毅在信丰油山滴水垄经常找干部和战士谈心谈话,告诫他们:“南方游击斗争已经到了很难忍受的程度,打死饿死病死是家常便饭……如果怕困难怕牺牲的,只要你们愿意回去,你们可以离队,但回去落到敌人手里,不要翻面无情,以免将来不好见面。我们只要保存几百武装,并坚持到底,前途是光明的。”在项英、陈毅领导下,油山上空革命红旗高高飘扬。
1937 年2 月,国民党军派部队到油山潭塘坑“清剿”时,群众及时把驻军一营的征粮数字通报给项英,从而使项英准确地推算出敌军“清剿”的时间有多长,于是决定带领队伍转移。项英、陈毅在油山阅读的国民党报纸,也是群众提供的。朱赞珍想方设法到白区收集一些国民党报纸送给项英、陈毅。项英、陈毅从报纸上得知华北事变、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他们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为“两广事变”告民众书》《为日本侵占华北告民众书》等,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政治攻势。朱赞珍十分敬佩地说:“真没想到,报纸里面也可以出枪炮!”信丰油山锡坑的李桂花也是一位机智勇敢的青年妇女,1930 年她就参加油山革命活动。项英、陈毅率红军游击队在油山打游击时,她经常为红军游击队采购物资,打探消息,掩护裁缝师傅为游击队缝制衣服。信丰油山坑口革命群众李绍仁把竹杠打通一端,把米、花生、番薯、芋头、海带、辣椒干、小鱼干等藏在里面,或者挑一担水,水桶里面做个夹层藏东西,送给红军游击队。他还每年夏天做粽子、冬天做豆腐乳送给项英吃,一再得到项英的表扬。信丰黄泥排有个名叫黄垂基的屠户,以卖猪肉为掩护,经常给红军游击队提供情报。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他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所说:“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项英、陈毅和红军游击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共患难、心连心,终于战胜一切困难,迎来了光明前景。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的炮声,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在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被迫于7 月11 日停止了对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
项英、陈毅获悉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又从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看到毛泽东于1937 年5 月8 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摘要,立即在油山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精神,准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
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全权代表,从油山下山,先后赴南雄钟鼓岭、池江、大余、赣州等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陈毅对党绝对忠诚,他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等协议。9 月下旬,项英到达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南方其他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等协议。谈判成功之后,项英回到赣粤边,立即召开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讨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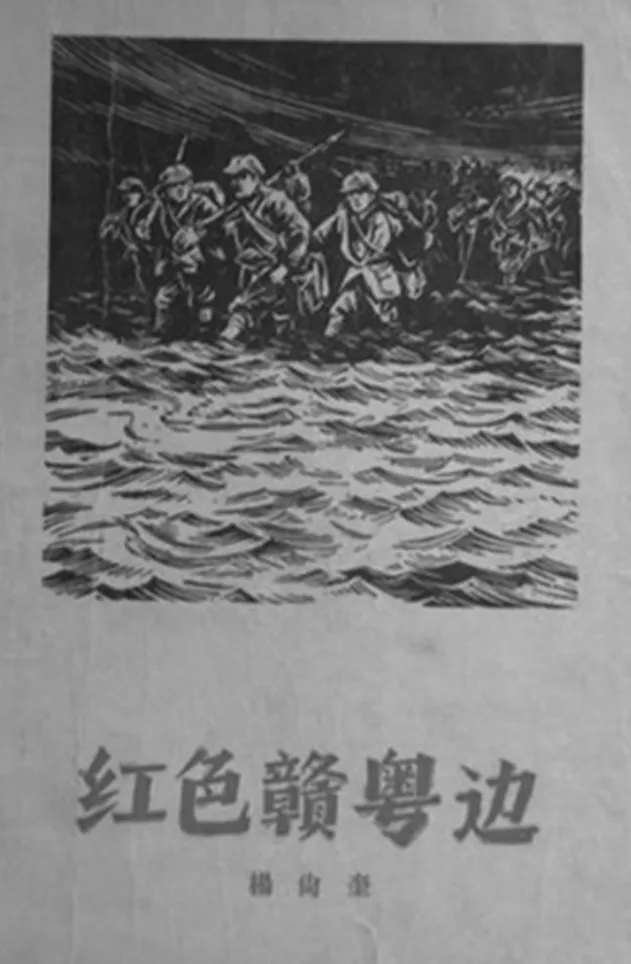
杨尚奎著《红色赣粤边》
1937 年10 月,南方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赣粤边特委命令各地游击队集中整训,等待下山抗日。在信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赣县大龙、南康等地的红军游击队接到命令后,陆续集中在信丰油山潭塘坑整训。经过3 个月的整训,补充扩大了队伍,由原来200 多人扩大到近400 人。随后开赴大余板棚下整训一个月后又开赴池江。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下山改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陈毅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高举抗日大旗,驰骋在大江南北,成为抗日前线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后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