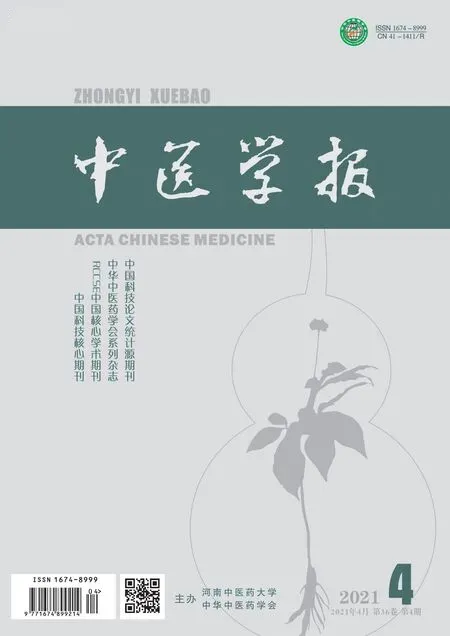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探讨*
2021-04-17张怀亮
张怀亮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45000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的暴发及流行震惊了世界,中医药参与防治,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即使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也再次证明了中医药参与重大疾病防治的不可或缺性。余经常关注疫情的发展与变化,通过不断学习新冠肺炎防治方案,了解中医药防治信息,与一线人员沟通探讨以及参与会诊防治,对新冠肺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总结如下。
1 病名
此次新冠肺炎属于中医学“温病”范畴,细分之为瘟疫也。《黄帝内经》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说文解字》曰:“疫,民皆疾也。”新冠肺炎传染性强,无论老幼,触之即病,有致死性的特点,且流行性甚广,符合瘟疫的特征,系感受疫疠之气所致。“天以阴阳而运六气”,岁月变更,运气流转,瘟疫发病的性质与证候也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瘟疫有温热疫、湿热疫、寒疫、寒湿疫等。如《伤寒温疫条辨》云:“肇于乾隆九年甲子,犹及谢事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纵有火毒之证,亦属强弩之末。自兹已后,而阳火之证渐多矣。”
新冠肺炎患者多数舌苔厚腻[1]、发热不甚,或伴全身酸痛,具有湿的临床特点;其病程缠绵,甚至治愈后出现复阳[2],符合湿性黏滞特性;根据目前的尸检和穿刺组织病理观察,肺脏、脾脏、心脏、肾脏、脑组织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病理损伤[3],符合湿性弥漫的特点。
《素问·刺法论》云:“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在中医学中,“毒”的概念有二:热之甚谓之毒;邪之甚谓之毒。新冠肺炎传染性强、流行性广、有致死性,邪气炽盛,符合中医学“毒”的特性。
新冠肺炎患者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恶寒并不多见,极期又可见疫毒闭肺和气营两燔证,因此用“寒湿疫”不能概括其全貌。据资料显示,仅有半数患者发热,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故用“湿热疫”命名也不能显示其特征。
综上所述,用“湿毒疫”命名相对符合新冠肺炎之特点,也可阐释其从阴化寒、从阳化热之转变。
2 病因
吴又可云:“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时疫温病气运徵验论》云:“瘟疫,天火也,由天之五运六气而生,谓之标病。”新冠肺炎发生于2019年12月,处于己亥年终之气。《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终之气,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任何一种病原微生物皆有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且多属条件致病。2019年下半年武汉地区气候变化剧烈,冬季应寒反温,又出现连绵阴雨,客观上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及传播提供了条件。《伤寒指掌》亦云:“天久阴雨,湿寒流行,脾土受伤,故多寒疫寒湿。”
3 病机
叶天士指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吴鞠通认为:“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疫疠之气,除可兼秽湿浊毒,也可夹杂四时之常气,若夹风夹寒,侵犯卫表,表气郁闭,则见发热、恶寒、鼻塞、流涕、身体酸痛等症。肺主气司呼吸,通于外界,湿毒疫邪,由口鼻而内侵入肺,湿郁于肺,宣肃失职,则见干咳。《黄帝内经》云:“五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肺气不展,鼻窍失司,可见嗅觉减退或丧失。湿毒阻遏胸阳,轻则胸闷,甚则短气,更甚者张口抬肩,出现喘促之征。
胸闷、短气、喘促,此为新冠肺炎病情进展过程中3个不同的病理阶段。初期表现为胸闷等症或发热、乏力、干咳,经过治疗发热等症缓解,经过6~10 d后患者突然病情加重,表现胸闷、气短、乏力,动则更甚,若病情未得到遏制,呼吸困难加重,表现为喘促难续,因肺居上焦,为清肃之脏,且为水之上源,有宣降肺气,布散津液,通调水道之功,今湿毒阻滞上焦,郁遏肺气,布津无能,宣降不力,通调失职,水液结聚,秽浊内侵,病日重一日。尤其是初病发热,经药物治疗发热缓解,貌似病情稳定,体内病势仍在潜移默化的进展。数日后,“炎症风暴”作矣,患者表现或胸闷,或短气,或喘促,仍可用上述机理以阐释。
疫疠之气,虽曰外感,但多有内伤相合,病延日久,随患者体质而发生从化,或从阴化寒,表现寒湿郁肺证、寒湿阻肺证;或从阳化热,表现湿热内蕴证,大致可分为湿重于热、湿热并重、热重于湿。湿毒阻肺日久,可致邪毒闭肺,肺与大肠相表里,脏病传腑,可出现阳明腑实之证。还可从气分而深入营分,在高热烦渴的同时伴见心烦躁扰、斑疹隐隐,呈现气营两燔之证;甚则进入血分,热甚动血,出现吐血、衄血、便血、尿血,即西医学中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叶天士有“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之说。肺为水之上源,主通调水道,又主一身之气。而三焦“通行诸气,运行水液”。新冠肺炎之秽湿浊毒,首犯于太阴,肺气郁遏,津液不归正化,变为水湿痰饮,壅滞三焦决渎之官,气、水、火不能正常通调、敷布,三焦通道郁阻,气滞血瘀,湿阻化热化火,甚至产生种种变证,导致多脏器损伤。
湿邪缠绵,在一经不移,“肺主太阴湿土之气,肺病湿则气不得化,有霜雾之象[4]”,加之疠气暴烈,故新冠肺炎进展迅速,肺部呈现“白肺”改变,可发展为呼吸衰竭。五行火本制金,若湿毒郁肺,寒化太过,反侮心阳矣。且(2019年)己亥年终之气主气为太阳寒水,亦伤心阳[5],故肺病而心亦病也,部分患者出现心力衰竭,甚至心阳暴脱,而致阴阳离决。
脾为太阴湿土,同气相求,加之己亥年为土运不及之岁,故平素脾运不健者,湿毒易自上焦传入中焦,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湿在上焦,若中阳不虚者,必始终在上焦,断不内陷;或因中阳本虚,或因内伤于药,其势必致内陷……湿邪自表传来……由肺而至于脾胃。”湿毒困遏脾胃,纳运无能,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味觉减退或丧失等症。也有患者初病即现脾胃症状,此属“秽浊归于中焦”。且脾主地气,肺主天气,地气上蒸,天气不化,常使肺失其轻清之性,加剧肺部病变。脾肺俱病,又可使宗气生成无源,易致大气下陷,出现喘促之症。
“湿之为物也,其在人身也,上焦与肺合,中焦与脾合,其流于下焦也,与少阴癸水合”。若上中不治,其势必流于下焦,湿毒郁于下焦,邪水旺一分,正水反亏一分,肾精不足,肾不纳气,肺肾俱虚,则出现胸闷、气短、乏力,较病之早期,湿郁胸阳所致之胸闷、气短,一虚一实也。湿毒太过,流于下焦,郁遏肝肾,肝木失其疏泄之任,肾虚不能主水,气化不行,湿毒更甚,病深胶固。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道,新冠肺炎可致男性生殖障碍,睾丸易受攻击。此为湿毒疫邪伤及下焦之佐证。
经过积极治疗,其恢复期多表现为正虚邪恋,临床以脾肺气虚、气阴两虚多见[6],可兼夹痰湿、湿热、瘀血之邪,此时应积极使用中药治疗,以修复脏器损伤,防止肺纤维化的发生。
基于上述认识,新冠肺炎的基本传变规律为:疫疠之气兼秽湿浊毒,或夹风夹寒,侵犯肺系;或首入中焦,或由中阳亏虚,传至中焦。其病位主要在太阴肺、脾,初期或偏于肺之表,或偏于肺之里,或独见于足太阴,或肺脾合邪。其最主要的病理因素是湿毒。随体质从化,可从阳化火、从阴化寒。随病情进展,湿毒蕴结,若病势仍未得到遏制,则可传变少阴心肾,或湿毒弥漫,直损厥阴,五脏皆伤,其病危矣。
4 治疗方法
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中医药的早期干预是改善疾病预后的重要环节。本病初期:疫毒初犯,正气尚可,以祛邪为主;中期:邪正交争,宜祛邪扶正;极期:易出现内闭外脱,扶正兼祛邪;后期:邪势已缓,正气耗伤,以扶正为主,若余毒未尽,正虚邪恋者,少佐祛邪之药。基于新冠肺炎病因病机的认识,提出注重清解湿毒、重视宣畅少阳三焦、注重补气药使用、三因制宜等原则。
4.1 注重清除湿毒治湿不治气,非其治也。湿毒为病,易郁阻气机,调畅气机可使气行则湿行。如温病学中宣上、畅中之法,可用质地轻清之品,开宣肺气,“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药如杏仁;可用芳香化湿或燥湿理气之品,调畅中焦气机,如白豆蔻、厚朴。
治湿不治脾,非其治也。脾虚失健,运化失常,湿毒内蕴者,宜健脾化湿,药如薏苡仁、炒白术;湿毒困脾,气化遏阻者,宜运脾化湿,药如苍术、藿香;若脾气亏虚者,需补脾益气,强健中州,药如人参、党参。因此,临证需以脾与湿的相关病情,酌选补脾、健脾、运脾之法。
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此即温病学中“渗下”之法,给邪以出路,使湿毒从小便而出。
4.2 重视宣畅少阳三焦“少阳为枢”“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少阳的功能是转枢气机,使人体之气升降出入,通畅无碍。“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三焦者,元气之别使也”。三焦有通行诸气、运行水液之功。此次新冠肺炎之湿毒疫邪易于弥漫三焦、壅遏气机,因此在治疗上应重视宣畅少阳,通利三焦。余临证常以柴胡剂合温胆汤加减治疗肺系疾病,包括部分“白肺”的患者,取得较好疗效。新冠肺炎中医诊疗方案中清肺排毒汤也合用小柴胡汤加枳实等理气药,有枢转气机,调畅三焦,散津除湿,扶正达邪之义。
4.3 注意补气药的使用外邪侵袭人体,决定最终结局的是正邪斗争,其中元气的存亡尤为关键。余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10余年,发现HIV感染后往往迅速消耗正气。疫毒暴戾,攻伐元气尤为剧烈。有报告表明,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在短时间内发生免疫功能破坏,患者表现为气短、乏力等症,化验检查早期可见白细胞总数、淋巴细胞计数减少。感邪早期,若元气充沛则抗邪有力,使疫疠之邪不致内陷,可防止轻症转为重症,故有医家推荐早期使用人参败毒散治疗。发展至危重阶段,有一分元气,便有一分生机,及早使用补气温阳或补气滋阴药,可防止元气暴脱之患。张伯礼院士曾讲述很多患者氧合水平低、血氧饱和度波动,注射生脉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口服独参汤后,患者血氧饱和度稳定,氧合水平上升。
4.4 三因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域不同,寒湿燥火不均,故武汉早期病例与各地输入性病例特点不同,治疗当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新冠肺炎发生于2019年12月,此时的五运六气,主气为太阳寒水,时当冬季,需防寒伤心阳,在重症肺炎治疗时尤当留意;2020年初之气,主气为厥阴风木,客气为太阳寒水,时值春季,治疗时应兼顾疏散外寒,助肝木升发。自3月20日后进入庚子年二之气,主气为少阴君火,客气为厥阴风木,木火相生,则患者火热症状可能更为明显,治疗时兼顾疏风散热。
因人制宜:体质有强弱,禀赋有厚薄,用药当有别。《灵枢·寿夭刚柔》云:“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对老人、虚人新冠肺炎患者,当及早合用补益之药。
5 预后与复发
《时疫温病气运徵验论》云:“瘟疫,天火也,由天之五运六气而生,谓之标病;出现有时,过期若失,由外而至,又谓之客病也。”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疫情乃自然界气候变化之产物,根据既往瘟疫类疾病的一般发展规律,随着五运六气的变化,新冠疫情极有可能自然消亡,这是瘟疫的最终预后!(例如,2003年夏季天气转暖后,SARS疫情消失,之后虽有零星病例,但没有再次演变为疫潮)。当然,由于新冠肺炎已经引起世界大流行,各国由于地域环境以及防控措施的差异,其最终结束时间也不同。
至于新冠肺炎个体患者的预后则和体质强弱、治疗措施是否得当密切相关。中医学认为疾病的预后与邪正交争的态势有关。虽同样感受新型冠状病毒,但不同人群表现多样。正气充沛者,甚至可无明显临床症状。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资料,截至2020年9月15日,国内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尚有361例。由于正气强弱不均,感邪多寡不同,其潜伏期为1~14 d。发病有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不同。病轻者可仅表现为胸闷、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年老体弱,或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或未得到及时救治,病情可迅速进展,甚至死亡。
据报道,武汉江夏方舱医院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无1例转为重症,无1例复阳,说明中医的深入干预确能减少复阳。中医虽不直接杀灭新型冠状病毒,但能破坏其生存环境,降低其活力,又可益气扶正,增强免疫能力,修复组织损伤,在扶正、祛邪两方面同时发挥作用。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虽重点在肺,但实际上肝脏、心脏、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都广泛受累,故不能仅根据肺部情况及核酸检测就定义患者是否痊愈,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还要注意湿邪是否退净,脉象是否转常,脾胃纳运功能是否恢复,元气是否充沛,否则,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6 讨论
疫疠之气是否有阴阳属性?中医学认为任何疾病的产生都应该有阴阳属性。《黄帝内经》云:“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疫疠之气也应该有阴阳属性,寒热从化,历代医家多认为疫病非四时之气所为,但其临床表现无非是表里虚实寒热,其辨证多选用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其治疗或祛邪为主,或祛邪扶正,或扶正为主,其运用的方药与治疗常病无异,不过是常用方药的加减组合或剂量的大小变化。所谓疫毒并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换言之,治疗伤寒、温病的药物与治疗瘟疫的药物没有不同。因此,所谓的疫疠之气也是六气所化生,六气之常者,则为四时之常气,染病而为伤寒、温病(或称为常见病、多发病);寒温错时,六气之变者,过甚而为毒,则为疫疠之气,具有较强传染性与致病性,即所谓的异气、杂气,而发为瘟疫。
新型冠状病毒直径60~140 nm,在电子显微镜下方能看到,中医在微观层面对该病原微生物没有深入认识,为何能治疗新冠肺炎?张仲景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清初医家钱潢曰:“外邪之感,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中医学是审症求因,辨证论治,即根据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体后引发的症状推求病因,根据感邪后机体所处的病理状态来制定治疗方案,所以中医治疗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顺应机体所处的病理状态,因势利导,辨证施治,恢复阴阳平衡,才是最大的“特效药”,也是中医一以贯之的理念。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瘟疫流行,在中医学的庇护下,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昌盛不绝。明末吴又可根据自己治疗瘟疫的体会,撰成《温疫论》一书,每一代中医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虽然新冠肺炎在国内已经得到有效遏制,但我辈中医人也应当力同心,或总结其临床经验,或探讨其中医理论,以供同道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