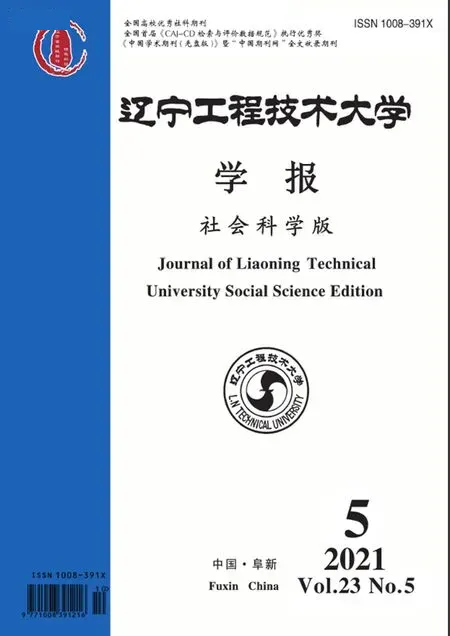《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孝道思想的 差异分析
2021-04-17赖思宇
赖思宇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0 引言
查阅中国知网数据库,研究《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中孝道思想的相关论文共计17篇,研究《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草堂》)中孝道思想的相关论文共计16篇,但有关两者孝道思想对比的研究仅有2篇。目前,学界对二者的孝道思想持有不同的观点:一是从封建伦理道德层面来看,认为《聊斋》中的孝道思想先进,《阅微草堂》中的孝道思想保守;二是从反理学层面来看,认为《阅微草堂》举着反理学、反封建的大旗,有动摇封建伦理根本思想的倾向,而《聊斋》未涉及这一层面。这两种说法都未免过于绝对、刻板,其中,《阅微草堂》中的孝道思想呈现出既保守又革新的分裂状态。因此,试图通过回归文本,进行客观地比较、梳理。
1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对传统孝道思想的承袭与发展
由于清朝廷的推崇,清朝孝文化日趋广泛化、平民化,以孝行列名于《清史稿·孝义传》的人物有二百余人,以社会下层民众居多。在此时代背景下,两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展现平民的孝道故事。此外,纪昀对创作历来有劝惩之志,又将其儿子的死归咎于《聊斋》,对《聊斋》明确表现出否定与不满,并在具体写作中针对《聊斋》里青凤、林三娘等狐鬼故事故作反语。据此,可以推测《聊斋》中大量平民孝道故事对《阅微草堂》题材选择有一定影响,如侯忠义先生说:“《聊斋志异》出现一百多年后,袁枚(《子不语》)、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先后打起反《聊斋》旗子……但他们的作品,明显看出题材、写法与《聊斋志异》中志怪作品的相通之处,可以说《阅微草堂笔记》既是反《聊斋》又是摹拟《聊斋》的产物”[1]。
对两书的孝道故事进行统计,相似孝道题材确实不少,可以归为4类:为尽孝而自残,为尽孝而复仇,为尽孝而寻父,因尽孝而得神佑等,都承袭于传统经典孝道故事题材。前3类题材的极端孝行故事,在清代社会存在着众多的原型,而最后一类题材看似虚幻但也蕴含现实性,因为孝行本身无法带来直接的物质回报,有时反而需要献出生命。虽然孝子尽孝不图回报,但小说作者在文本世界里,在财富、寿命、仕途甚至姻缘方面给予孝子奖励,以此来增强孝子故事的感染力,有利于以儒家伦理观为基础的家族的和睦长久。这也反映在《阅微草堂》中的一则故事里,某妇人起初对婆婆只是唯命是从,但当她偷听到神灵会庇护孝妇后,便受到“感动”,侍奉婆婆体贴周到、无微不至,妇人孝心的转变展现了此类题材的现实功效。蒲松龄、纪昀多记载因果报应之事,但并不意味着两人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们认为鬼神故事多属虚妄,却仍然有意虚构,最终目的是淳民风、正人伦,从而达到小说的劝世效应。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中相似的孝道题材均承袭于传统孝道故事,但两部作品都对传统题材进行了创新。《聊斋》侧重讲述尽孝与修仙的矛盾,如《罗刹海市》《翩翩》《仙人岛》《龁石》《白于玉》《青娥》《粉蝶》《西湖主》等8篇故事都有涉及。在此类题材中,男主人公偶入仙境,尽管富贵长寿、美女相伴,仍不忘回人世尽孝。小说化解矛盾的方法不一,但都秉承了尽孝高于修仙的原则,强调孝的绝对地位。如《罗刹海市》《翩翩》《仙人岛》《青娥》《粉蝶》等,其中的主人公最后都选择离开仙境,而《龁石》和《白于玉》的主人公则选择为母亲养老送终后再入仙境。《西湖主》的主人公则干脆用仙术造了一个分身,回人世尽孝,自己则在仙境享受荣华富贵,尽孝与修仙的矛盾在这个故事里得到了最理想化处理。孝虽为人伦,但对于鬼神,尽孝高于修仙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为成全丈夫尽孝,《罗刹海市》《翩翩》中的仙女忍痛与丈夫分离,《仙人岛》《粉蝶》《青娥》等里面的仙女则放弃自由的仙境生活,到人世奉养公婆。人世中的孝甚至能约束人世外的鬼神,凸显孝在天地伦理中的至高地位。与蒲松龄对这一题材的热衷不同,纪昀对此着墨甚少,这一差异也是情有可原的。蒲松龄深尝寒门学子之辛酸,壮志在胸,却报国无门,蹉跎半生却一事无成,问道修仙成为他苦闷精神生活的唯一出口,在仙乐飘飘的幻想中逃避现实,得到了王侯将相也求之不来的美人、珍宝乃至寿年,以此作为精神慰藉。蒲松龄还赋予书中人物尽孝这一优良道德品质,弥补他们在经世致用上的无用,为了尽孝宁愿暂别仙境,更反衬出人格的完美。尽孝与修仙两难选择的设置,蒲松龄实际上是为了自我美化,以达到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而身为高官大儒的纪昀,现实生活的富足使他无需寄情于道,况且对于儒家而言,问道修仙属于逃避社会责任的做法,《阅微草堂》自然不会涉猎此类情形。
纪昀也有偏爱的特殊题材,他热衷于设置礼教与人情水火不相容的极端情境,让封建伦理道德的不同层面发生内部冲突,探析尽孝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以此揭露尽孝在理学严苛要求下难以自洽的困境,《阅微草堂》里有7则故事探讨孝与节的矛盾:一是取孝舍节,如媳妇为赡养公婆卖淫,少年为父脱罪献身于县令,寡妇为抚养丈夫子嗣而改嫁,妻子为全家生计忍痛离婚改做富绅之妾等。二是取节舍孝,如父母为了活命令女儿委身于盗贼,而女儿为了贞节违抗父母,导致全家丧命等。三是节孝折衷,如媳妇为赡养公公而守寡数年,给公公养老送终后才改嫁。但就连最后一种折衷做法,基于当时的价值判断来看,也不完全是节孝两全。对此,纪昀借神灵之口讨论“妇至孝而至淫,何以处之”[2]130的难题并提出了5种意见,却始终难以服众,因此,这些面对节孝困境所做出的种种抉择,连纪昀都难以进行道德评价。此外,《阅微草堂》还探讨了孝的内部矛盾,如弃儿救姑与孝子杀人这两则故事,前者讲述寡妇为背婆婆渡河而抛弃独子,被婆婆斥责不孝而悔恨至死。在只能保全一人的极端困境下,寡妇舍弃婆婆自是不孝,舍弃儿子断绝夫家子嗣也是不孝,这个孝道困境难以打破,最后逼死寡妇。后者则讲述孝子为父复仇,不为父复仇本是不孝,但报仇杀人招致死刑,则又变相自绝宗祀,孝子又陷入新的不孝困境。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并非完美无缺,引发了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陷入困境。纪昀采用社会研究的方法,以学者的眼光设置尽孝的极端困境,放大、激化并曝光这些伦理矛盾,而这些刻意设置的极端困境极少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因此,以现实笔调抒发孤愤的蒲松龄当然不会涉猎此类小说题材。
2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孝道思想的差异
在《阅微草堂》中,媳妇私下偷偷抱怨婆婆就会立即遭雷劈致死。而在《聊斋》中,《菱角》《陈锡九》《连城》《青凤》《长亭》《宫梦弼》《阿宝》等故事中,子女都有违拗父母的情况,《仇大娘》《小翠》《青蛙神》《凤仙》《镜听》甚至出现子女直言顶撞父母的情况。但这些“不孝”行为并未招致报应,蒲松龄对此的态度是包容乃至赞许的,他不吝于给这些“不孝子孙”美好的结局,两位作者的孝道思想无疑有很大差异。
2.1 追求内在的孝心与追求外在的孝行
学界一般认为《聊斋》和《阅微草堂》所强调的孝皆为发自内心的真情。正如蒲松龄所说:“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犹在天壤”[3]20。又如纪昀所说:“事亲无失礼,然文至而情不至”[2]190。尤其是孝子遵从父命、以不合礼数的博具为父陪葬的故事,被认为体现出纪昀重真情而不重形式的超脱。然而主流解读并不一定正确,因为真正的孝心应是使父母了解沉溺赌博的危害,而不是明知有害还一味盲从。就像《聊斋》里的仇大娘“辄忤父母”,但并不影响她被作为孝女歌颂。蒲松龄认为子女的行为是否顺从并不能证明其有无孝心,同一结论放在《阅微草堂》中却令人生疑,媳妇被婆婆活活虐待致死也无权伸冤,十岁的童养媳为求活命能否逃跑的议题,连神灵都难以决断。这说明在《阅微草堂》的语境里,孝甚至剥夺了子女的生命权利,而事实上,纪昀对于孝的认知,并非他所声称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而只是孝的外在形式,即言行的顺从,并不是出于真心。如《丐妇尽孝》《狐避雷击》这两则故事,百依百顺的孝行都是出于为求神灵庇佑等现实的功利目的,因此,纪昀对孝的态度显得极为苛刻,要求子女摒弃自我意识完全顺从。蒲松龄则相反,他重视真情实感,允许子女在一定程度内违抗,态度较为宽容。
2.2 孝与义的不同取舍
《聊斋》里的父母半数以上都有不义的负面品格,如《镜听》《凤仙》里的长辈势利又偏心,《菱角》《陈锡九》《连城》《宫梦弼》《封三娘》等中的父母嫌贫爱富、失信于人,《珊瑚》里婆婆则凌虐媳妇,《小翠》里的公公不知感恩而求全责备,《鸦头》《柳氏子》里的长辈品行败坏等。这些文章中,为信守婚约而违抗父母的女性最终都得以圆满,不义的父母则都遭到了报应,甚至出现父母祈求子女原谅的情节。这种因果设置体现了蒲松龄的道德判断标准,即义高于孝。此外,不少父母往往被设定成恶人,而子女为了守义不惜付出“不孝”的代价,借孝反衬出更高层次的义。如《鸦头》中,母亲强迫女儿卖淫,孙儿便杀掉祖母、姨母,实际上救母无需杀死长辈,这种泄愤行为只有出于道义考虑才能得到理解,在伦理层面上却是大逆不道的兽行,但最终并未招致报应,反而全家团圆,日益富贵,因为道义层面的“义行”对伦理层面的“兽行”做出了更高层次阐释。与之相反,《阅微草堂》中只要求子女对父母单向付出,却不对父母做相应要求。媳妇私下偷偷抱怨婆婆便遭天谴,而婆婆虐待媳妇致死,这种不义之举却未遭到任何报应,因为作者认为孝高于义,明确表示婆婆虽不义,但也要求媳妇不得反抗。孝高于义这一原则贯穿全文,如富翁为夺人妻以重金许其公婆,公婆便逼儿休妻,导致儿子忧伤而死。死后鬼魂缠绵妻子不愿离去,富翁又献金,父母便怒斥鬼魂,鬼魂虽为亲生父母所害,且极不情愿离开妻子,但在孝道面前仍得听从父母。父母品行再低劣,子女生前死后都必须顺从,再度凸显纪昀心中孝的至高无上。蒲松龄允许取义舍孝,义为孝开拓出折衷的空间,子女有权拒绝父母的不义行为。而纪昀则坚持取孝舍义的原则,不论父母之命是否不义,子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抗,进一步表现出其对于孝的严苛态度。
2.3 社会角色中的性别分工差异
《聊斋》中有不孝行为的角色,男女数量约各占一半,而《阅微草堂》里有不孝行为的角色,女性占比高达80%。由此可见,关于违孝,《聊斋》中的性别设置较为均衡。此外,不同于《聊斋》,22位不孝女性中仅有6位是媳妇,《阅微草堂》中,13位不孝女性中有12位是媳妇,同时《阅微草堂》里女性尽孝的对象也几乎都是婆婆,可见纪昀特别重视婆媳关系,认为构建家族孝文化的关键便在于此。在《阅微草堂》的语境里,维持婆媳关系是单向的,即要求媳妇无条件地顺从婆婆,婆婆却无需对这种关系负责,反映出在纪昀心中,维持家族和睦的责任都落在媳妇一个人身上,丈夫的责任被淡化。与之相反的是,《聊斋》中不仅在违孝行为的性别设置上较为均衡,在68则尽孝故事里女性仅占28例,男性承担尽孝的主要职责,并且维持家族和睦的性别分工较为平等,儿子、女儿、媳妇都参与其中。蒲松龄在《大商》的结尾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与纪昀不同,他认为维护家族和睦的职责不仅应由女性承担,男性也应当承担。对于尽孝性别分工的不同认知,使得在面对女性行孝这一主题时,蒲松龄展现出了宽厚温情的一面,而纪昀则表现得格外苛刻。
2.4 复杂宽泛与统一深刻
蒲松龄生长于农村,深知在生存压力下,尽孝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做出折衷与妥协,因此,他的孝道思想有着复杂的形态特征。如《鸦头》中的女主角,表面上显得很愚孝,不仅不反抗母亲的凌虐,还嘱咐儿子念及骨肉之情不要伤害母亲。但她明知儿子身上存在杀戮欲,却只字不提,这种放纵的态度表明儿子的杀戮欲正是她本人弑母欲望的延续,体现了主人公愚孝与弑母的双重矛盾思想。与之相反,纪昀并不熟悉平民的家庭生活,不能遇见尽孝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境,因此,难以相应做出变通与妥协,孝道思想显得较为简单和理想化。蒲松龄的“孤愤”是在宣泄对社会环境与个人遭遇的不满,这些情绪真实、生动,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但却只是碎片化的浮光掠影,虽然极具感染力,却没有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读者的注意力很快就被艳丽的词藻与曲折的剧情吸引,难以达到批判所需的深度。
《阅微草堂》中孝道思想的深刻性正是《聊斋》所缺乏的,纪昀用三言两语概述情节,其写作并非像蒲松龄那样真实地反映社会现象,而是让读者直面封建伦理道德自身逻辑难以圆通的矛盾,虽然缺乏生动地描写与真实的生活细节,但有利于引导读者专心进行深层次思辨。纪昀常常设置极端情节,使封建伦理道德的不同层面发生内部冲突,把孝置于矛盾的困境,使故事内涵颇具丰富性与延展力。为了探讨孝与节的矛盾,
纪昀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父母为了活命令女儿委身于盗贼,而女儿为了贞节违抗父母,导致全家丧命。“节孝并重也,节孝又不能两全也。此事非圣贤不能断,吾不敢置一词也”[2]12。封建伦理道德要求女子顺从父母,同时贞操又是封建伦理道德对女子最基本的要求,纪昀的评价反映了他本人感到封建礼教实难自圆其说,但是这些探究并不代表他反对礼教,纪昀的创作目的是在礼教与人情的伦理范畴中寻找通往稳固社会关系的坦途。关于寡妇为抚养丈夫子嗣而改嫁这则故事,纪昀评论说:“程子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诚千古之正理,然为一身言之耳。此妇甘辱一身,以延宗祀,所全者大,似又当别论矣”[2]145。可见,纪昀对于程朱理学是认同的,但与理学家动辄以礼责人的严苛相比,他能从具体情境出发,权衡利弊,对失节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正如他所说:“是皆堕节之妇,原不足称。然不忘旧恩,亦足励薄俗。君子与人为善,固应不没其寸长。讲学家持论务严,遂使一时失足者,无路自赎,仅甘心于自弃,非教人补过之道也”[2]145。纪昀并不是反对理学本身,而是反对理学家曲高和寡之论,把一度偏离封建伦理道德的人推得更远,逼得失足一时之人失足一世,难以重返礼教正轨,不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纪昀不迷信、不盲从传统的伦理道德,对其中的问题大胆提出质疑,虽然显得迷惘彷徨,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但他敢于直面正统思想内部存在千年痼疾的勇气和对当事人的宽容态度是可贵的。鲁迅曾评价纪昀:“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是很有魄力之人”[4]。他强调纪昀思想的深刻性,认为当时的人们以劝惩之佳作来称赞《阅微草堂》,其实是“不能了解他攻击社会的精神”[5]。
3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孝道思想差异的成因分析
3.1 作者个人际遇的不同
叶嘉莹在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时,提到觉悟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于观他人之痛苦而觉悟的,一种是觉自己之痛苦而觉悟的[6],这也是造成蒲松龄与纪昀孝道思想差异的主要原因。
蒲松龄身处乡间,对于平民百姓真实、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深有体会。蒲松龄曾对好友纵容妻子虐待老父,使其客死他乡一事极为愤慨,并以此为底本创作了《马介甫》。蒲松龄的个人际遇也使他感触良多,自己严格遵守儒家家庭伦理道德,妻子也深得蒲松龄母亲的喜爱,但这份喜爱使妯娌心生嫉妒,纷争四起,终至分家。蒲松龄与妻子不争不抢,剩得家产寥寥无几,而这个结局正是他秉承孝悌思想所导致的,这一切对他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强烈震动,使其孝道思想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复杂包容的特征。《曾友于》的故事便体现了蒲松龄内心隐秘地动摇,庶子常年受嫡子欺凌,奉行孝道一味退让,骄横的嫡子们反而变本加厉,在庶母的葬礼上击节而歌,甚至不让她与父亲合葬,直到威猛刚烈的长兄暴力制服了嫡子,庶母才得以安葬,“由此兄弟相安”[3]168。隐忍与反抗换来的结局截然不同,因此蒲松龄内心其实明白,在具体实践中,遵守孝悌思想、一味顺从对现实并无益处,不过小说最后,嫡子等人幡然悔悟,家族重归和睦,这种理想化的情节体现了蒲松龄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对孝道的执着坚守。另一个极为写实的孝道故事是《仇大娘》,在继母和异母弟妹遭难之时,早已远嫁的仇大娘挺身而出,不求任何回报扛起家庭的重任。这种无私孝行与她此前“性刚猛,每归宁,馈赠不满其志,辄忤父母,往往以愤去”[3]254的不孝行为似乎矛盾,一个孝女竟会因为一点钱财忤逆父母,但正是这一点才生动刻画出仇大娘的真实与重情。在《青蛙神》的婆媳冲突中,神女十娘养尊处优,但“朝侍食,暮问寝”[3]278,不至于不孝。她们的矛盾只是因为婆婆出身小户习惯勤俭,看不惯媳妇娇生惯养,两人生活观念不合。若是在《阅微草堂》里,十娘的忤逆肯定会被责以不孝,招致报应丧命,但蒲松龄对十娘却十分宽容,只把她塑造成一个娇养的大小姐,因为他深知在现实家庭生活中,这类因观念不合导致的婆媳冲突相当普遍。
《阅微草堂》中动辄严惩的道德评判看似极具威慑力,实则并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对于家庭和谐并无益处,人与人之间互相妥协包容才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正如袁世硕、徐仲伟先生在《蒲松龄评传》对《聊斋志异》思想价值的评价一样,“蒲松龄对于人伦关系的理解虽然仍不离传统的道德框架,但却没有像宋明的道学家那样,将上下尊卑推向极端。他歌颂孝顺勤劳的媳妇,这种表现和追求无疑更富有人情味,从而也更能为世人接受和理解”[7]。与之相反,纪昀在朝廷中身居高位,又是文坛学术领袖,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会像蒲松龄那样深切地体会平民家庭伦理关系的复杂,而是站在理学的立场上,以居高的姿态俯察社会百态,他与他笔下的创作内容是有距离的。纪昀有一妻六妾照顾家庭,因此,他特别强调在尽孝上女性责任的重大。妻子是大家闺秀,妾的地位低下,宦门衣食无忧远离生存压力,她们自然对婆婆、丈夫温柔顺从。纪昀对于女性孝道的标准脱胎于士大夫生活,但用同一标准要求平民家庭中忙于生计的女性,稍有不顺从便致死,显得尤为严苛且理想化,而普通百姓有时候连生存都极为艰难,拿什么来要求他们恪守伦理道德呢?
3.2 作者写作目的不同
蒲松龄潦倒半生,郁积一腔愤懑无处倾诉,只能在文学创作中抒发“孤愤”。纪昀则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创作上持有一种教化者的姿态。创作《阅微草堂》时,半生功名已定,他既没有抒愤的心理需求,也无需露才扬己,以此获得文坛认可。纪昀在首卷《滦阳消夏录》问世后,便知道这部作品将有广大的受众群,在序言中写道,“盖是书之作,姑以弄笔怯睡而己。境过既忘,己不复省视,乃好事者辗转传抄,竟入书贾之手,有两本刊”[8]。纪昀在创作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作品会被众人争相传抄、被书商广为刊行,因此下笔切忌随意,必须重视文章的社会影响。他行文严谨,因事说理,不同于蒲松龄以笔抒愤反映社会现实,纪昀写作的出发点是试图重构不完美的儒学伦理,因而他的孝道思想与蒲松龄的孝道思想相比较,显得更为统一,对于孝的态度也更为严格。此外,纪昀还对照《聊斋》的狐鬼故事故作反语,因此,两部作品孝道题材虽相近,却在孝道思想阐述上有很大差异。
3.3 社会时代背景的变迁
蒲松龄和纪昀对于孝道的态度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乾隆帝重修《大清律例》,相比于蒲松龄所处的顺治、康熙年间法律制度更为严酷成熟。在乾隆年间,《阅微草堂》里那些看似严苛的要求都有真实的法律依据,如由田涛,郑秦点校的《大清律例》中规定:“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杖一百”。又规定“凡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绞。须亲告乃坐”。这无疑是《阅微草堂》里要求子女绝对顺从的法律依据。
《阅微草堂》极为重视对理学的反思,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乾隆年间汉学与理学的矛盾更为尖锐,而纪昀本人在学术上更接近汉学,因此“反理”是势在必行的。乾嘉学派重考据,理性精神深深根植于纪昀的脑海,因此,他对于理学要求下,孝的逻辑困境极为敏感。另一方面,清朝廷对于理学的复杂态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理学有利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因此,清朝统治者鼓吹理学,但又不满于党同伐异等有碍于君权巩固的行为,认为“足为太平盛世之累”[9], 于是“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9]。清朝统 治者对理学采取的这种双面态度,必然会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身为宠臣的纪昀在创作中自然与其保持同一步调,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攻击道学先生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9]。
4 结语
清朝统治者特别重视推行孝道,因为通过提倡父母权力的绝对化,能够培养子女对权威的顺从心理,这样子女在进入社会后,会自然地将臣服心理转移到封建君主身上,王权便更加稳固。清朝社会的重孝风气使两部作品的孝道故事虽有许多共同点,但因个人际遇、写作目的、时代背景的不同,也造成了两者孝道思想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