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丝路酒香”
2021-04-16王子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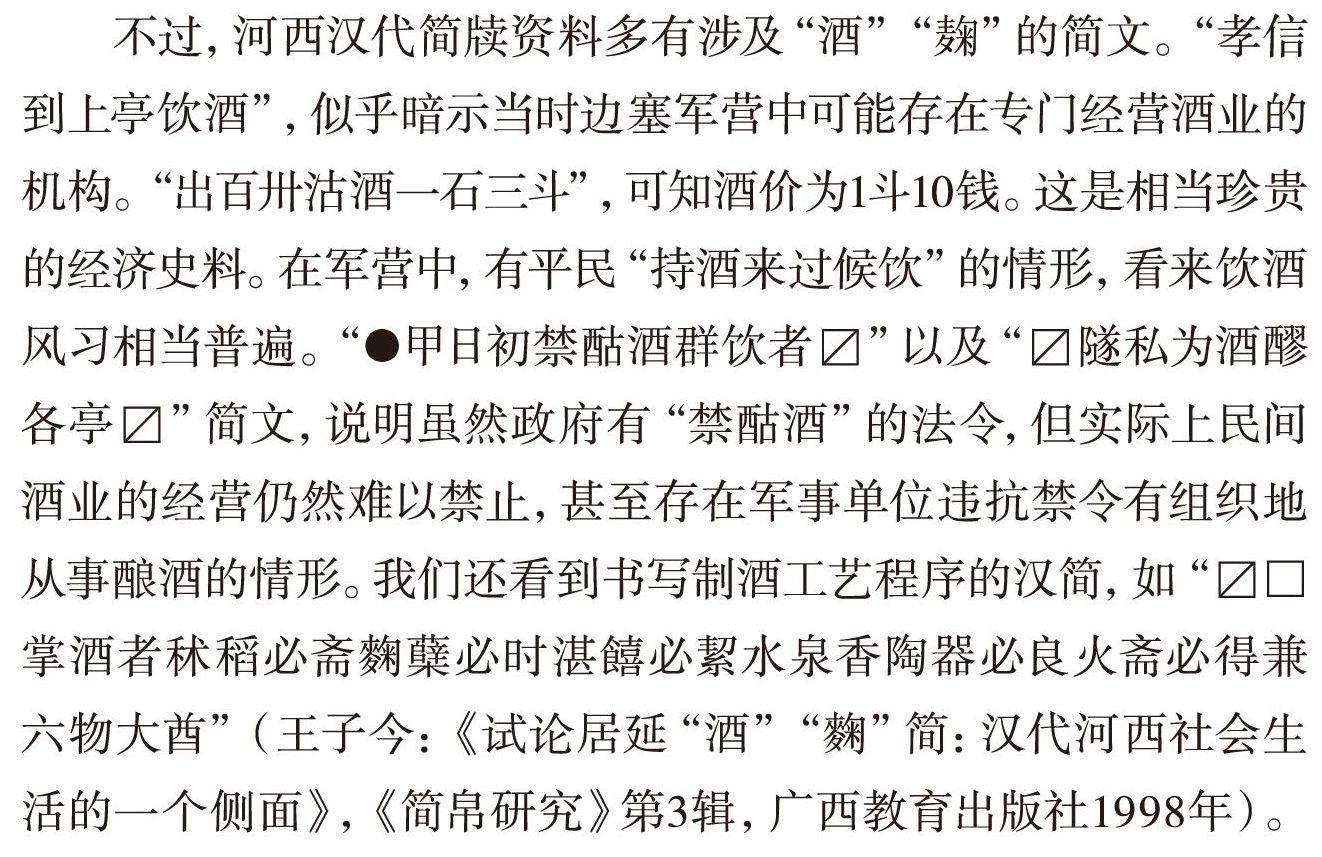
司马迁予以突出记载的“张骞凿空”(《史记·大宛列传》),成为丝绸之路史富有纪念意义的符号标志。其实,在前张骞时代,中原文化与中亚、西亚地方文化之间,已经通过草原、绿洲、沙漠、戈壁实现了长久的联系。但是,汉武帝时代由张骞出使西域开创的汉王朝与西北方向诸多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之间正式与密集的外交往来、经济沟通和文化融汇,使世界交往史的意义得以明朗显现。
《史记》对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通行的过程和意义有着生动具体的记述。其情节,为军事史、外交史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而涉及“酒”的内容,则反映了丝绸之路交通线上,在战争和经济竞争的另一面,也有休闲生活的雅趣、情感体验的温馨、精神意境的陶醉。丝绸之路沿途美好的文化风景,可以在体味酒香的同时加以欣赏。丝路的酒,丰富了当时人们饮食生活的消费内容,也沁入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较深层次。丝绸之路美酒的醇厚和热烈,正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宽宏、豪迈、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
一、大宛、安息的“蒲陶酒"
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西行见闻,包括沿途考察西域国家地理、人文、物产等多方面的信息。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张骞的西域考察报告分两个层次,一是“身所至者”诸国,二是“传闻其旁大国”。
关于“大宛”国情,张骞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大宛的地理形势,“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扦罙、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张骞关于大宛自然条件、经济生活、军事实力及外交关系的报告,在陈述其生产方式后,明确说到其国“有蒲陶酒”。
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蒲陶酒”的最早记载。
汉武帝对大宛国最为关注,甚至不惜派遣数以十万计的大军远征,夺取的是“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在司马迁笔下,大宛“有蒲陶酒”的记载,竟然在“多善马”之前。可知太史公对于这一信息的高度重视。
关于安息的介绍,《史记·大宛列传》写道:“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司马迁又说到安息国情的其他方面,“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史记》记述大宛国情所谓“有蒲陶酒”,是“(张)骞身所至者”的直接体会。关于安息的“蒲陶酒”,则应当来自“传闻”。
安息國有稳定的货币体系。所谓“有市”,说明商品经济比较成熟。而所谓“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则体现了商运的发达。“蒲陶酒”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意义,应当是重要的,可能仅次于“稻麦”。商贾“行旁国或数千里”的交通条件,无疑可以保障“蒲陶酒”的远销。
二、西域:“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蒲陶酒”是西域多个地方的特产。而当地民俗传统中,“嗜酒”是显著标志。司马迁写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这里所谓“宛左右”,《汉书-西域传上》“大宛国”条写作“大宛左右”。据《史记·大宛列传》,大宛民间礼俗传统是“嗜酒”。所谓“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说明“蒲陶酒”储藏技术的成熟,也说明“蒲陶酒”经济价值的重要。
“蒲陶”,是西域普遍栽培的、主要因可以酿酒而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藤本植物。《汉书·西域传上》“难兜国”条和“罽宾国”条都说,当地“种五谷、蒲陶诸果”。《晋书·四夷传》“康居国”条也说,其国“地和暖,饶桐柳蒲陶”。“以蒲陶为酒”,很可能是种“蒲陶”的主要经营目的。
“蒲陶酒”应当是中原上层社会喜爱的饮品。《后汉书·宦者传-张让》记录了官场腐败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常侍张让“交通货赂,威形喧赫”。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赡”,与张让奴“朋结”,愿求一拜。“时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佗时诣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遂共舆车入门。”于是,“宾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李贤注引《三辅决录注》的记述涉及“蒲陶酒”:“(孟佗)以蒲陶酒一斗遗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可知当时洛阳地方对“蒲陶酒”的看重。这一故事,又见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三辅决录注》:“……(孟)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他”即“孟佗”。“蒲桃酒”就是“蒲陶酒”。“蒲陶酒一斗”和“蒲桃酒一斛”的差异,应是传闻失真。《晋书·山遐传》中也可以看到对这一政治腐恶现象的批评:“自东京丧乱,吏曹湮灭,西园有三公之钱,蒲陶有一州之任,贪饕方驾,寺署斯满。”以“蒲陶酒一斗”贿赂当权宦官,竟然可以换得“凉州刺史”的官位,即所谓“一州之任”。
三、中土肥饶地始种“蒲陶”及“蒲陶宫”之名义
在丝绸之路物种引入史中,“蒲陶”是众所周知的引种对象。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录了汉王朝引种西域经济作物的情形:“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丝路交通的繁荣,使得这两种经济作物的栽植有了更大的规模。“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司马迁所谓“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是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后,物种引入的著名记录。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录司马相如歌颂极端“巨丽”的“天子之上林”的赋作,有这样的文句:“于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燃柿,椁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褡棵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可知上林苑中栽植了“蒲陶”。关于“蒲陶”,裴驷《集解》引郭璞的解释:“蒲陶似燕薁,可作酒也。”大概宫苑中“蒲陶”的栽培,主要目的应当是用以“作酒”。大概长安宫苑管理者已经能够学习“宛左右”地方的酿酒技术,“以蒲陶为酒”了。
西汉长安上林苑有“蒲陶宫”。《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匈奴单于“来朝”,汉哀帝出于“以太岁厌胜所在”的考虑,安排停宿于“上林苑蒲陶宫”。《资治通鉴》卷三五“汉哀帝元寿二年”记述此事。关于“太岁厌胜所在”,胡三省注:“是年太岁在申。”关于“蒲陶宫”,胡三省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种植之离宫。宫由此得名。”我们这里不讨论“厌胜”的巫术意识背景,以及“太岁在申”的神秘内涵,只是提示大家注意“蒲陶宫”的营造。“蒲陶宫”,可能是最初“采蒲陶种植之离宫”所在,或者是栽植“蒲陶”比较集中的地方。
前引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说:“(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家使节于是引入,“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史记》记载,一说“苜蓿、蒲陶”,一说“蒲陶、苜蓿”,《汉书·西域传上》“大宛国”条则都写作“蒲陶、目宿”,“蒲陶”均列名于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河西汉简资料中,“苜蓿”都作“目宿”。“目宿”,可能体现了汉代文字的书写习惯。“蒲陶、苜蓿”是同时引入的富有经济价值的物种,但是河西汉简仅见“目宿”而不见“蒲陶”。《汉书·西域传下》与《史记·大宛列传》同样的记载,写作“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颜师古注:“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指出唐代丝绸之路沿线苜蓿的种植沿承了“汉时所种”的植被形势。
有可能“蒲陶”的移种,其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离宫别观旁”,即前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谓“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对于汉武帝时代的开放、开拓与开发,《汉书·西域传下》篇末的“赞日”这样总结道:“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由于继承了文景时代的经济成就,所以能够有多方面的进取,“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群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而宫苑生活因此具有外来文明的色彩。“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所谓“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指出西域进取致使直接的物种引入。应当注意到,汉武帝时代以积极的态度促进汉文化的外扩,以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其意义绝不限于“天子”个人物质生活等级的提升,而有更大的文化意义,更长久的历史影响。
四、置郡“酒泉”的象征意义
东周时期,已经有“酒泉”的地名。《史记·周本纪》记载:周襄王十三年(前639),“郑文公怨惠王之入不与厉公爵,……”张守节《正义》引录《左传》的记载:“庄公二十一年,王巡虢狩,虢公为王宫于蚌,王与之酒泉,郑伯之享王,王以后之肇鉴与之。虢公请器,王与之爵。郑伯由是怨王也。”又引杜预的解说:“酒泉,周邑。”这里所说的“酒泉”是“周邑”。汉武帝时设置的“酒泉郡”,则远在西北。
郭声波《史记地名族名词典》有“酒泉”条:“酒泉,郡都名。”又有“酒泉郡”条:“酒泉郡,郡都名。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一说元鼎六年),取匈奴浑(一作昆)邪王、休屠王地置酒泉郡,治酒泉县(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因以为名,境域约当今甘肃省河西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西部一带。元鼎六年(前111),析东境置张掖郡,西境置敦煌郡。”(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13页)
《穆天子传》前卷记载周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的事迹。周穆王乘造父所驾八骏之车从镐京出发进入犬戎地区,又溯黄河登昆仑,抵达西王母之邦。西王母所居,有说在青藏高原,有说在帕米尔高原,有人还考证远至中亚地区甚至在波斯或欧洲(参看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国书店1990年;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这部书虽多浪漫色彩,然而又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周穆王曾“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史记·秦本纪》说,“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駵、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周穆王见西王母的传说,《史记》注家的解说与“酒泉”相联系。裴骃《集解》:“郭璞曰:‘《纪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丘,见西王母。”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十六国春秋》云前凉张骏酒泉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丘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按:肃州在京西北二千九百六十里,即小昆侖也,非河源出处者。”“酒泉”是中原前往西北远国通行道路上的重要地理坐标,因此与“周穆王见西王母”的神话相联系。
酒泉,应当是汉王朝得到河西地方之后最早设置的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说:“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张守节《正义》:“河谓陇右兰州之西河也。酒泉谓凉、肃等州。《汉书·西域传》云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后分置武威、张掖、燉煌等郡。”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酒泉置郡,是汉武帝强化北边军事的重要战略行动。
《史记·大宛列传》说:“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又有“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的说法。汉武帝举兵伐宛,“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裴驷《集解》引如淳的解释:“立二县以卫边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卫酒泉。”《史记》原文明确说“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当然,“卫酒泉”也就是“卫边”。“酒泉”在河西地方东西往来主要通道上“通西北国”的重要交通枢纽与西境边防关钥的地位明朗地显现出来。《史记·河渠书》记述边地水利开发成就:“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酒泉”竟然与“河西”并列。也可能“河西、酒泉”不宜分断,应当读作“河西酒泉”,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所谓“遂开河西酒泉之地”。无论怎样,“酒泉”曾在“河西”地方居于首要地位,这是明显的事实。
“酒泉”地名,自然与“酒”有关。《汉书·地理志下》:“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颜师古注:“应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师古曰:‘旧俗传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太平御览》卷七0引应劭《汉官仪》曰:“酒泉城,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郡。”又引《三秦记》曰:“酒泉郡中有井,味如酒也。”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这与前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的说法相合。然而《汉书·武帝纪》说:“(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如果说武威、酒泉同时置郡,则“酒泉”郡名与“武威”完全不同,它体现出一种温和美好的气氛,这与丝绸之路史长时段和平友好交往关系的主流相一致。
五、河西的“清酒”“浓酒”
虽然《史记》最初记载“酒泉”郡名洋溢着浓重的酒香,但关于汉代河西地方“酒”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信息,则不见于《史记》。仅有与霍去病军旅饮食生活相关的一则记录,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批评其不恤士卒,未得基本军粮供应,竟然“重车余弃粱肉”。但是并没有说到“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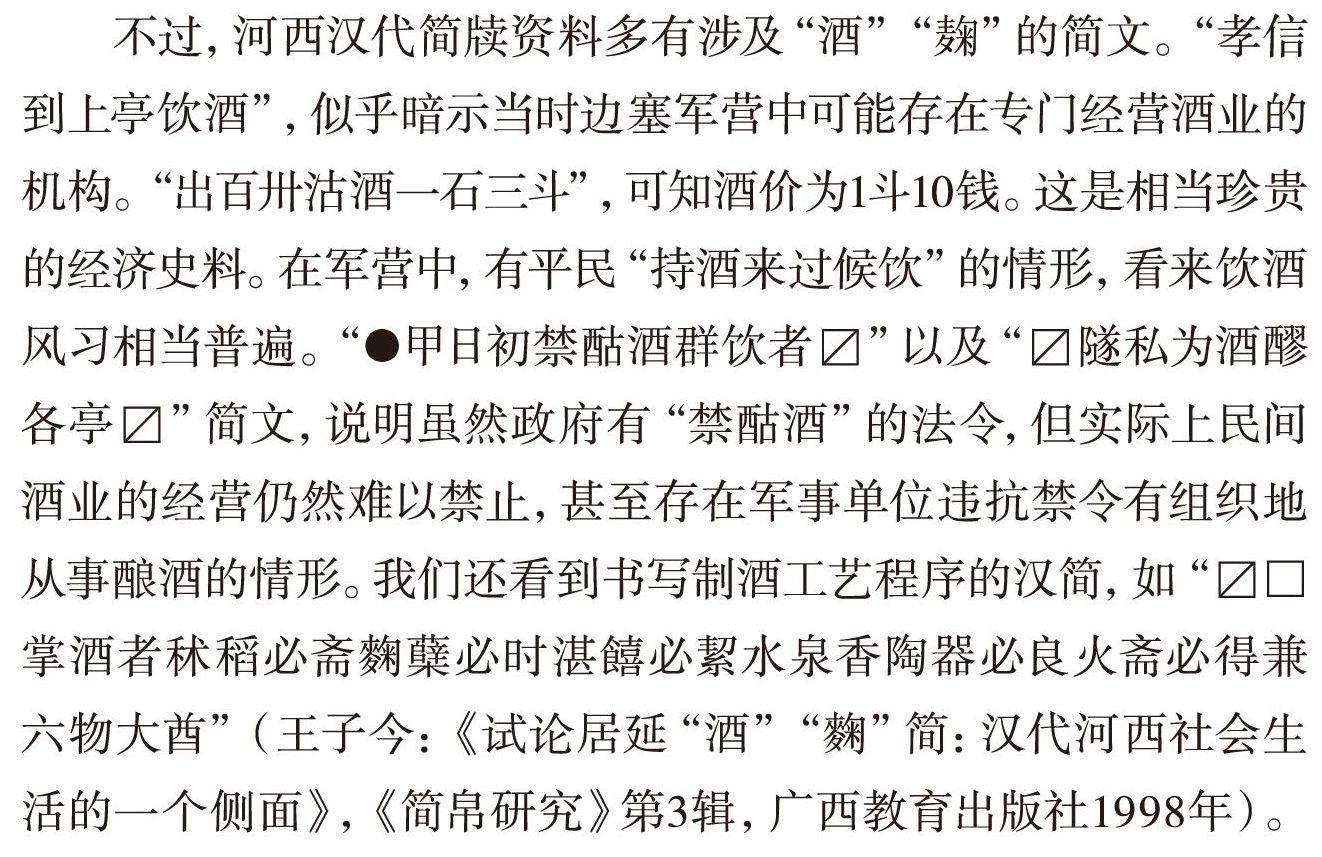
肩水金关汉简出现了“清酒”的简文。彭卫曾经在关于秦汉饮食史的专门论著中讨论了汉代的酒,指出:“文獻和文物数据所记录的汉代酒类有如下18种:……”即(1)酎酒。(2)酝酒。(3)助酒或肋酒。(4)米酒。(5)白酒。(6)黍酒。(7)稻酒。(8)秫酒。(9)稗米酒。(10)金浆。(11)青酒。(12)菊花酒。(13)桂酒。(14)百末旨酒。(15)椒酒。(16)柏叶酒。(17)马酒。(18)葡萄酒。论说时涉及汉代文献所录酒的名号,还有温酒、盎酒、醪、醴、醇醪、甘醪酒、酇白酒、缥酒等。他指出,出自《西京杂记》,未可确认是汉代信息的还有恬酒、甘醴、旨酒、香酒等。彭卫说:“汉代酒的类型大致根据三个原则命名:其一,酿酒的原料,如黍酒、稻酒、柏酒等;其二,酿酒的时间和方法,如酎酒、酝酒等;其三,酒的色味,如白酒、旨酒等。”(彭卫:《秦汉时期的饮食》,《中国饮食史》卷二第六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466—469页)说到“青酒”而未言“清酒”。关于“蒲陶”和“蒲陶酒”,在河西简牍资料中都没有发现。居延汉简可见“醇酒”。关于酒的质量,居延汉简有“薄酒”,肩水金关简文“薄酒五钱浓酒十……”涉及“薄酒”和“浓酒”的对应关系,两者的价格或许相差一倍(王子今:《说肩水金关“清酒”简文》,《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
悬泉置出土汉简《过长罗侯费用簿》中记录接待长罗侯常惠的饮食消费,有“羊”“罩(羔)”“鱼”“鸡”“牛肉”“粟”“米”“豉”等,另外还有“酒”:“入酒二石,受县。”“出酒十八石,以过军吏年,斥候五人,凡七十人。”“凡酒廿。其二石受县,十八石置所自治酒。”“凡出酒廿石。”(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汉王朝与草原民族和亲,有“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史记·匈奴列传》)的传统。悬泉置汉简可见接待“沙车使者一人、厨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沽酒一石六升”的记录(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3日第11版)。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从汉简资料看,接待外国使者和朝廷出使西域(广义的西域包括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的官员,除了米、粟、麦等日常饭食外,还必须要有酒肉。而每饭提供酒肉,这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是一种特殊的礼遇。”这当然也是对“俗嗜酒”风习的一种迁就。具体的简例有:“出米四升,肉二斤,酒半升,以食乌孙贵姑代一食西”,“疏勒肉少四百廿七斤直千……酒少十三石直……□(A)且末酒少一石直……(B)”,“使者廿三人再食,用米石八斗四升,用肉百一十五斤,用酒四石六斗”等(张德芳:《从出土汉简看敦煌太守在两汉丝绸之路上的特殊作用》,《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
在河西“酒泉”,军民们对“酒”的深切热爱,是对得起这个地名的。可能司马迁对河西地理人文稍显生疏,致使相关文化信息在《史记》中少有记录。司马迁没有到过河西,成为丝路沿线地方史研究的遗憾。正如王国维所说:“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观堂集林》卷一一,第4页)
六、丝路草原宴饮
《史记·匈奴列传》关于匈奴的礼俗制度,有“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的说法。“赐一卮酒”,是对军功的嘉奖形式。草原民族“俗嗜酒”的史例,还有《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裴驷《集解》:“韦昭曰:‘饮器,棹樯也。单于以月氏王头为饮器。晋灼曰:‘饮器,虎子之属也。或曰饮酒器也。”这件“饮器”在汉元帝时韩昌、张猛与匈奴盟会中曾经使用。张守节《正义》:“《汉书·匈奴传》云:‘元帝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与匈奴盟,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此“饮器”就是“饮酒器”。
汉与匈奴的战争中,曾经有这样的战例。汉武帝任命卫青为大将军,统率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军俘虏右贤王部众男女万五千人以及“裨小王十余人”(《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右贤王“饮酒醉”导致大败的战事,在司马迁笔下成为酒史与军事史的生动记录。
上文说到汉与匈奴和亲,“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史记·匈奴列传》还说:匈奴喜好汉地出产的“缯絮食物”,也就是物质生活资料中最基本的衣物饮食。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警告说,匈奴人口不能与汉之一郡相当,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与中原衣食不同,“无仰于汉也”。现今匈奴领袖改变传统习俗而喜好“汉物”,则汉地物资不过付出十分之二,“则匈奴盡归于汉矣”。他建议:“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湮酪之便美也。”匈奴所“好”汉地“食物”,推想应当包括“酒米食物”中的“酒”。中行说所谓“汉物”中的“汉食物”,与“湮酪”相对应,可知“汉食物”应当有“酒”类饮品。中行说对“汉使”说:“(匈奴)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说到“肥美饮食”,无疑应当包括饮品。司马迁记载,汉文帝派遣使者送给匈奴的书信中说:“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蘖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提供给匈奴的所谓“秫蘖”,一般理解为制酒用的糯黍和曲,即前引居延简文所谓“秫稻”“麴蘖”。明人王立道《泉释》写道:“夫嘉宾良燕,非酒弗交。于是酌清流之芳澜,汲深涧之春涛。酝以秫蘖,醇酎清缥。仪狄奏盎,杜康挫糟。”(《具茨文集》卷六《杂著》)所谓“酝以秫蘖”,语意是非常明白的。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少孙补述说到傅介子出使外国,刺杀楼兰王,以功封侯之事。傅介子杀楼兰王的具体场景,是在宴饮中。其具体情节见于《汉书·傅介子传》:“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账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后来汉元帝建昭年间,陈汤、甘延寿出西域击匈奴郅支单于,也就是此后发表“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壮言的那次战役,是与康居结为军事同盟然后取得胜绩的。《汉书·陈汤传》记载:“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康居人的配合,使得陈汤军“具知郅支情”。而郅支单于“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已接近绝望。“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楣,并入土城中。”战役进程体现了康居人与汉军的全面配合,而这种合作关系的结成,是以“酒”为媒介的“与饮盟”。
这些史例的发生,都在《史记》成书之后,或许可以看作司马迁有关草原民族“好酒”“俗嗜酒”之记述的历史余音。
我们增进关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认识,通过阅读文献和考古发现,可以获得多方面的感受。丝绸实物遗存有悦目的绚丽色彩,而读《史记》的相关文字,可以体味沁人心脾的芬郁酒香。因此,我们应当感谢丝路上往来的各民族使者、商旅、征人和辛苦屯戍劳作的男女,也应当感谢真实记录社会历史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