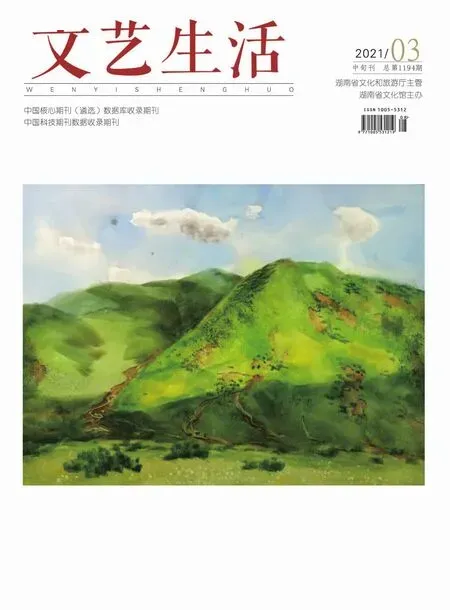以创作者的人物画像透视当代电子舞曲行业发展中的弊病
2021-04-08潘哲煜
潘哲煜
(杭州昊美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324100)
电子舞曲(Electronic Dance Music,简称EDM)是通过电子音乐的技术来进行创作的一种舞曲流派,重点在电音节、夜店和派对等各种场合通过DJ(即Discs Jockey,中文:唱片骑士)来进行播放。下文会把对电子舞曲的创作群体进行细分,简析各自的特点,并对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探讨。
一、混合型创作者
混合型创作者是指,涵盖了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并集其他职业身份于一身的创作者群体。这是一支支撑创作者规模、奠定其基础的庞大“舰队”。而这支“舰队”还衍生出了三小类。
(一)DJ/制作人型创作者
该类创作者在融入到电子音乐的制作领域之前,一般都是职业DJ。他们在表演的同时既能掌握音乐的节奏,又能够收到现场的反映,这给他们奠定了创作的基础。
欧洲的电子舞曲引领了潮流,其中尤属“荷兰帮”House 音乐高歌猛进。[1]House 自80 年代发展于DISCO,起源于芝加哥的俱乐部。它发展很快,衍生出了各种亚风格,比如Electro House,Deep House,Progressive House 以及big room 等。“荷兰帮”是荷兰电子音乐人组成的团队代名词,代表音乐人有Tiesto、Hardwell、Martin Garixx 等。这部分人通常都有唱片骑士和舞曲制作人双重身份,通过以老带新或强强联手来构建合作关系,比如Tiesto 提携Hardwell 和Martin Garixx;W&W、Sick Individuals DJ/制作人双人组。
最近几年,电子音乐人具备实力后会选择独立建立电音厂牌,并吸纳优秀作品和艺人。比如音乐制作人Tiesto 建立了电子音乐厂牌Musical Freedom,还成就了Hardwell 以及Martin Garixx 两位世界级的DJ/音乐制作人(之后,他们二人也建立了各自的厂牌Revealed Recording 和STMPD RCRDS。)当下,欧美的电子音乐人很青睐这种厂牌、作品和制作人三者协同的模式。不过该模式需在完善的音乐著作权保护法、成熟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及受众健康的音乐审美等各种高标准条件的加持下才能够运转。
另外,虽然“荷兰帮”的团队作战可以保持荷兰电子舞曲的领先地位,不过还是给音乐产业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其他国家音乐人的发展空间被压缩了。“荷兰帮”拥有在创作生产环节的权威话语权。他们不断被世界各地的俱乐部和电子音乐节争先预定演出来获利,这就造成了“马太效应”,使得其吸纳了行业过多的注意力和资源。其次,阻碍了电子舞曲创作手法多样性发展。虽然,“荷兰帮”一直在融合不同的音乐元素,创新舞曲风格,不过权威性使得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带领了潮流,其他音乐制作人便会以他们的风格为标杆,进而丧失自己的独创性。
(二)卧室制作人
卧室制作人(Bedroom producer)狭义上是指创作过程不被时间和空间约束的非职业音乐人,有着创作主动性和个体主导型。广义上指涵盖狭义在内的各种独立职业制作人,这里只是讨论狭义的卧室制作人。
基于互联网技术和音乐科技的快速发展诞生的各种数字音频工作站(Digital Audio Workshop)、虚拟工作室技术(Virtual Studio Technology)和各式音频软硬件给普罗大众提供了音乐制作的工具,如YouTube 以及各大音乐论坛等拥有各式音乐制作教程,给出了专业训练上的新出路。卧室制作人群体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和兴起了。他们在音乐平台上发布作品后可以得到与唱片公司和厂牌签约的机会,从而开启社会化、职业化的音乐生产之路。不过荷兰电子音乐制作人Mesto 和挪威电子音乐制作人Alan Walker 的发展历程指出,这种方式有利有弊。
Alan Walker 代表了新生代卧室电子音乐制作人,2014 年通过作品《fade》出道,跟索尼音乐旗下的MER Musikk 签约。随后还推出了单曲《Faded,并有《Alone》、《All Falls Down》、《On My Way》等众多热单,不过其标志性的音色和midtempo 的主打风格导致的风格单一性和创新匮乏性渐渐被资深的电子音乐人排斥,且其曾被证实了作品的不真实。虽然本人被质疑,不过他跟唱片公司的高契合度使得音乐的商业价值得以最大化。
新生代电子音乐制作人Mesto 是荷兰电子音乐人,也是卧室制作人的代表,早年基于YouTube 上公开作品而被大牌电子音乐人Martin.Garixx 关注,并协作推出了《Bouncy bob》、《WIEE》等知名单曲,并陆续在荷兰著名的电子音乐厂牌Musical Freedom 和Spinnin’Records 发行单曲,并转型DJ/制作人型艺人。他一直坚持商业化作品中的艺术性,而资本的加持又优化了他的创作环境。他后续还推出了《Chances》、《Wait for Another Day》等高质量单曲。
此外,当卧室制作人得不到知名度后会转型单一型制作人—Ghost producer,即影子制作人,通过做枪手来获得收入以及锻炼自己技能的机会。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当下行业的浮躁之风和作假之风。该现象会在下文的“影子制作人”部分进行分析。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商业和艺术的联系异常紧密。[2]商业面向社会人类的经济活动,跟艺术进行互动融合从而互相推进。商业融入到艺术中可以扩展艺术的影响力,同时带来经济上的支持,帮助艺术家探索艺术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支持亦会产生副作用。
当下,卧室制作人群体需要做到的是即使面对音乐商品化和资本的无限逐利,仍要保持初心,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做权衡,需要在日益浮泛化的电子音乐的审美需求“压迫”之下来不断精进自己的创作技法。
(三)跨界型制作人
跨界型制作人主要指在音乐制作领域以外的娱乐界或者艺术领域同样拥有职业身份的创作者群体。他(她)们具备一定艺术素养和人脉资源,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音乐资源。澳大利亚DJ/制作人双人组NERVO 正是其典型代表。
NERVO 由一对孪生姐妹Miriam.Nervo 与Olivia.Nervo 组成。他们16 岁时被模特公司选中。18 岁跟索尼音乐签约,曾参与制作了中国台湾歌手蔡依林的《MR.Q》和瑞典已故著名电子音乐人Avicii 的《Enough is Enough》等,凭借和法国著名音乐制作人David Guetta 等人合作的单曲《When Love Takes Over》而走红。之后在世界最大的电子音乐节Tomorrowland 登台,并与荷兰知名电子音乐制作人Armin.Van.Buuren 的音乐厂牌签约,重塑了乐坛和大众对女性DJ/制作人的看法。
当前,由于艺人跨界的趋势日渐凸显,这种形式的创作者群体也正逐渐壮大,慢慢走入音乐受众的视野,但是他(她)们的影响也待业界更多的观察。
二、单一型创作者
单一型创作者是指创作人只拥有音乐制作人一种身份。他们有着更加专一的职业发展目标。所以,该群体往往比混合型创作者有着更高的制作能力和专业素养。单一型创作者群体还可以依照其自身意愿,划分成匿名的影子制作人和公开身份的制作人群体。下面将对两类群体进行简析。
(一)影子制作人
影子制作人(Ghost producer),是一个匿名性的、为雇主创作特定作品或出售自己艺术作品的创作人。他们会同时出卖自己的作品包括署名权、修改权在内的所有著作版权以换取以经济利益。[3]
在这里,我们基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相关理论来对影子制作人群体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布迪厄曾经把资本划分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资本形式。文化资本指借助各种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用品。文化资本分别基于身体化和制度化两种形态得以存在。布迪厄觉得,经济资本、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和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三者基于一定条件,能够发生转化。
市场目前更加青睐那些具备音乐素养、能够创造价值点和噱头的群体。因此,DJ/制作人双重身份的制作人逐渐成为业内的“摇钱树”和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择偶”标准。不过,很多DJ 和制作人缺少专业的训练,短时间内无法获得身体化的文化资本。这就促使他们付出经济资本去雇佣具有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却通常缺乏经济资本的枪手。
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矛盾便催生了灰色产业链。比如,荷兰DJ/制作人R3hab 雇佣影子制作人团队来承载创作压力,从而名利双收。虽然这种现象已遭到了业内外的抵制,不过这是根植于商品经济的“顽疾”,代表了当下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的矛盾性,一时难以根治。
(二)公开身份的制作人
公开身份的制作人群体会在社交媒体和公共场合公开自己制作人的身份和作品。该群体一般是职业的音乐人,把生产高质而非高量的音乐作品当作职业目标,较好地融合了创作者和受众对于作品的商业需求和审美需求,是两者之间的润滑剂。
三、结论
自21 世纪10 年代以后,电子舞曲产业开始迅猛发展,一跃成为发达国家音乐产业的重要支柱。其创作者的专业技能、职业发展和审美倾向都会对创作生产带来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产业中的消费、营销等环节。
在本文中,当代的电子舞曲创作者被分成了混合型创作者、单一型创作者两类,从而又进一步细分成了DJ/制作人型创作者、卧室制作人、跨界型制作人、影子制作人以及公开身份的制作人5 个子群体。对各个群体的分析暴露了当下电子舞曲界的弊病,比如在DJ/制作人型的创作者会为了商业利益而雇佣“枪手”。艺术商业化进程在不断加快,音乐作品浮泛化和艺术从业者的逐利行为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结果。
商业和艺术在加速融合,过度强调艺术本体性,会让艺术脱离现实生活难以发展,而过度强调商业,又会使艺术创作失去本真。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维持艺术性和商业性动态平衡的同时,保护艺术在商业的加持下更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