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面面观
2021-04-06林继中
林继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林语堂这个人。我想凡是看过电视剧《京华烟云》的人,大体上都知道林语堂是一个小说家。如果没看过这片的人就不一定知道。
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林语堂是很著名的,特别是在欧美,他的知名度甚至比鲁迅还高,这是我们现在想象不来的。我不久前看过我们福建省著名的散文家章武的一篇散文,叫《蕉海中的林语堂》。他里面一段话讲得很绝,他说:古往今来中国可敬的作家很多,但可爱的作家只有两个,哪两个呢?一个就是苏东坡。这个大家可能都会赞同。另一个呢?他说是林语堂。我没问章武先生什么理由这么说。但我推测大概就因为这两个人特别有人情味,感情也特别丰富。苏东坡的感情丰富大家是知道的,他具有的人情味大家可能也是很熟悉,他自己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乞丐老百姓,他就是这么一个乐观的多面的人。林语堂在他的著作《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的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你看这杂七杂八的,因为他就想表现出苏东坡是这么一个多面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综合体,苏东坡的性格确实可爱。
他有很多的侧面,这些侧面虽然是矛盾的却相反相成交相辉映,没人比他更复杂,也没人比他更单纯。我想,大凡一个伟大又可爱的人,这样的人,总是单纯而不单调的,他就好比一粒水晶,大家都看过水晶,有很多的侧面,每个侧面都能够折射出一种光彩,那合起来就显得有很多的异彩,但是它又通体透明,非常单纯,所以水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既复杂又单纯的物体。苏东坡也是这样,虽然他看起来人格上有很多面,甚至互相矛盾,他给人总体的感觉就是很单纯,在现代作家里能够跟苏东坡比较相近的,我看林语堂的确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林语堂也像苏东坡一样,是一个多才能的多产的乐天派的作家,他一辈子写了60多本书,1000多篇文章,而且英文的、中文的成果是很多,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翻译家、小说家。他也很乐天,小时候的名字就叫和乐。他一直是脸上挂着笑意,甚至到后来他提醒自己说不要老那么傻笑,所以他在某些地方确实很像苏东坡,而且更要紧的是,他是一个多面体,性格上充满很多矛盾。人家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自己想了想说,我是一捆矛盾。一捆,不是一把,一捆的矛盾,充满了矛盾,这么一个人。
我们如果仿造林语堂写苏东坡的那种笔调来写他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林语堂是一个快乐风趣的老头儿,一个自由主义者,大翻译家,小说家,想逃离政治而不能的绅士,美食家,基督教徒,尊崇老式婚姻的洋博士,“明快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人,爱胡思乱想的人,是一个老顽童。他也是这么杂七杂八各种性格都揉和在一起的人,他的自相矛盾我举几个例子。他是基督教徒,但是却很讨厌神学,他年轻的时候读神学院;回家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个牧师,就很以自己的儿子为骄傲,这样呢,他就叫他的儿子给村民来布道,结果他在讲坛上面不是讲神学而是大讲进化论,说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大酋长,结果把他的老父亲差点儿吓得昏过去。他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就是在情感的处理上面也充满矛盾,他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叫锦端的姑娘,结果锦端的父亲看不起这个穷小子,就不答应把女儿嫁给林语堂,而且还亲自替他介绍了一个钱庄老板的女儿廖翠凤。林语堂看自己没希望当他的女婿,便同意跟廖翠凤结婚。结果锦端本人从美国留学回来一直没结婚,到32岁才结婚,而林语堂却早早就结婚了。那是不是结了婚就忘掉了锦端呢?也没有,他心里还老惦记着她,一直没放弃,到了晚年生命即将结束时,80岁了,他还想坐着轮椅去看鼓浪屿的梦中情人——锦端。你看他感情也是这样充满矛盾。
更深刻的矛盾是反映在他思想上,他这个人有点像左手拿了个中国秤,右手又托着个西方的天平,量过来量过去,两个标准,结果造成了很多困惑,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中国心”和“西洋脑”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会成为一捆矛盾的人呢?这跟他特殊的身份有关,他是一个边缘人,什么叫边缘人呢?就是游走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他自己说两脚踏两种文化——中西文化,那留学生、移民,算不算边缘人呢?不一定能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边缘人要对两种文化都像土生土长的人那样去理解这两种文化,这才能算边缘人。有一个人类学家讲的比较好,容易理解,他说这种边缘人不但自己要会穿中国鞋走路,还要会知道美国人如果穿上中国鞋,将会怎么走路。这才能算边缘人,对两种文化都把握得很准确。
我们从林语堂的一篇小杂文里可以看到一些影子,他的一篇杂文叫做《记纽约的钓鱼》。在纽约钓鱼,里面说七八月的时候,在星期日,海面上三五里之内都是小渔船、渔艇、钓鱼的。当晚上渔火星星点点的时候,那是很好看的,也很壮观。那么多的人在钓鱼,但这里面就没有什么中国人。那是不是纽约的中国人少了?不是。当时在纽约的寓公是相当多的。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差别,他认为中国的诗画家写诗啊,画画啊,总是喜欢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渔樵”,打渔的,砍柴的,经常出现在诗歌里面。中国画的画面上,山水画喜欢画一个人在挑柴,或者是写诗的时候,写着一个钓鱼的、打渔的人,这是经常出现的,可是这些画家、士大夫,一般不会自己真的去打柴,真的自己去打渔,他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欣赏渔樵,而不是亲自去参与打渔,或者是砍柴。不是这样的。而外国人就比较不一样,他喜欢参与。所以你看跳舞,中国皇帝最喜欢看跳舞,但没有看到哪个中国皇帝下到舞池里面亲自去跟舞女一起跳。但是你看俄国的沙皇,英国的女皇,他们就会到舞池里面跟大家一起跳,这个观念是不一样。
林语堂讲了一个李鸿章的逸事。李鸿章有一次和一些英国的绅士朋友在一起,绅士朋友就跟他讲,请你来看我们的足球比赛,他就去看了。他这些朋友就在场上踢,天气非常热,李鸿章看了半天感到很诧异,就说:这么大热天,为什么不雇些人去踢,还要亲自下去踢呢?他认为踢球,你雇些人去踢给我看就好了,所以这两个思路方向是不一样的。他们乐在其中,我们是看着好看。那我们现在思想慢慢转变,现在大家都经常说“贵在参与”,这恐怕就是进口货了。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对两种文化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不然他就不会发现这样一个题材,而且,这种理解往往都是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我们讲《水浒传》,历来讲《水浒传》都讲官逼民反,《水浒传》最著名的一句话叫“逼上梁山”。谁逼的呢?官逼的,官逼民反,但林语堂讲《水浒传》就跟人家不一样,他是从国民性这边切入,从老百姓这个“民”自身切入,这个角度就跟人家不一样。他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梁山好汉”呢?特别喜欢侠义小说呢?他说原因就在没法治,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个人的利益都没有一个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而自己又不敢去抗争,挺身而出,所以第一要靠清官,青天大老爷,第二靠那些侠客出来打抱不平,替自己解决问题,总之,等别的人来解放自己。这是他认为国民性里面的劣根性,那好了,你喜欢侠客也很好,但是侠客本身会惹是非,“侠以武犯禁”,侠客往往使用他的武力,结果触犯了王法,那会连累家人。我们大家知道,过去有“连坐法”,一个人犯了罪,要“株连九族”,甚至连同一个街道的邻里都要受到牵连,“保甲连坐”,所以大家虽然喜欢侠客,反而很怕这个侠客就生在我们家里,因为这个侠客肯定要惹事生非,去打抱不平,触犯了王法,那就会连累到家里。一方面爱,一方面又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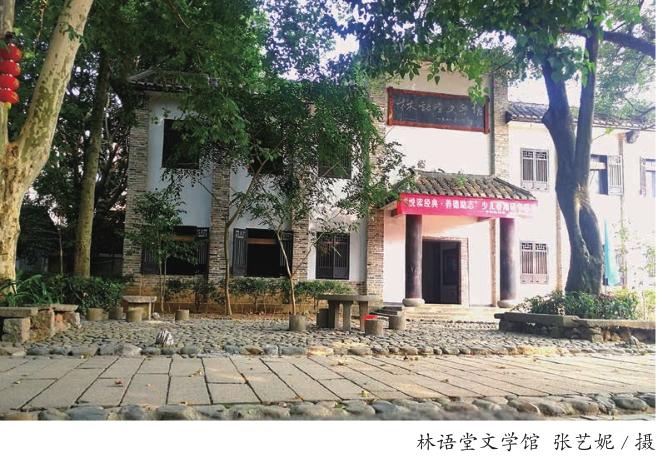
《水浒传》里面大家都知道宋江,呼保义、及时雨,是一个侠客式的人。但他父亲宋太公怎么做呢?他早早就到衙门去告他,跟他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就是怕宋江惹事连累了他。宋太公的心理就是当时比较普遍,整个社会都是这样,这些好汉们、侠客们走光了——每一家都不喜欢侠客好汉出在家里面,就你推我搡地把他给推出去了。他们往哪去呢?就流落到江湖,就要上梁山,就要入绿林,那社会上剩下来的就是怕惹事的,庸庸碌碌的平庸之辈,那再等到不平事,有什么事情又不平了,这时候,他们才记起那些被赶走的好汉。那怎么办呢?那就开始羡慕之,景仰之,编戏、写小说来崇拜之,然后想从这些侠义小说里面找回顺民世界所失去的英雄。这群人往往是自己病怏怏的,躺在床上看《水浒传》赞李逵,羡武松,归根到底还只是精神上的向往,实际行动上,还是不敢挺身而出,不敢为自己争权益。但林语堂还进一步指出来,他说这种国民性,不是天生的,是因为长期的文化环境养成的,这怎么培养出国民性呢?他认为宗法伦理社会,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他对家族很在意。他认为家族是专门培养劣根性的东西,可见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可谓不深。对西方文化他也有他独特的理解,比如说,他认为西洋人有这么一个毛病,不近情理,喜欢创立一种学说,然后就用这种学说解释一切的事实。比如说基督教,他举出一个例子,基督教有一个理论叫“赎罪说”: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一辈子要去赎罪,但是这个学说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他说是建立在一个苹果上。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写亚当偷吃伊甸园的一个苹果,结果被上帝赶出去了,赶出伊甸园,人类从此就带着一种罪,所以生下来就有罪,一辈子都去赎罪。他说:这就不近情理,全人类就因为我们的祖先偷吃了一个苹果,所以就要赎罪,他就认为,西方这个人或这个文化里面,不近情理,其实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选择。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的解放是西方思潮里很重要的问题,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对立,焦点就在于人是不是有罪,是不是生下来就有罪。因为人有罪,就是束缚,要解放人类自身,那就要从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个东西做起。所以,他这个故事里其实后面隐藏着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批判。
再比如说,美国的工业社会创造一种机械的文明,物质生活非常发达,但是人也异化得很厉害,人跟着机器转。大家有没有看过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我记得电影一开头一大群的绵羊涌出来,挨挨挤挤的往前走,“蒙太奇”,剪辑下来是大工厂的门一开,一大群的工人也拥拥挤挤的往前走……他用这个来比喻人失去了个性,在工厂机器的控制下,人失去了个性,异化,人们只能拼命地工作,拼命地竞争,结果,人被物所控制。所以他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在上一个世纪他就发现这么一个问题。他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他就针对西方人异化的现象来写这本书,人忘记了个人的尊严,成了服从物质的人,成为这部大机器里面的小小的齿轮,失去了个性。
他曾经这么说: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他对自己的人格下这么一个定义,我敢于做我自己。正因為他有对中西文化的这种双边,感性的理解,所以我们称他为边缘人。
从水浒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林语堂对中国社会有比较深的了解,对西方,刚才那个例子(同样)也是说明这个。如果你看了他的全部著作,那你的印象会更深刻。问题是:他怎么会成为边缘人?我们都不会成为边缘人。因为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生长环境,有一个很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叫林志诚,是漳州平和山村里的一个牧师,这几个字很关键,他是一个“山村里”的“牧师”。首先他是牧师,所以,林语堂在这种家庭就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而且有机会受到西式教育:教会有学堂,牧师的孩子受教育在这种学校里,会受到资助,所以有这么一个机会,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这种教育,对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能够提前接受。因为他父亲是“山村里”的牧师,他父亲原来是个小贩,是个农民,后来虽然当了牧师,但他毕竟还是在“山村里”,他骨子里还是农民,林至诚就有两面性。这两面性就对林语堂起了很大、很深刻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在那么一百年前,八十年前,本来漳州就不是繁华的地方,又是山区里的一个小村子,那边人居然能够关心第一架飞机试飞是不是成功,而林至诚很早就知道了最近西方在实验飞机,试飞成功,这个信息他很早就得到了。而且,他能把所有当时有关报道的书拿来看,但他心里说,没亲自看过,我还不太相信。
他有一个同事,叫范礼文也是一个牧师,经常向林至诚介绍一些新书,一些新学。像满清末代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以后西学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到,所以他经常把一些新的翻译的作品,介绍给他看,而且有一份油印的报纸,一年一块钱的《教会消息》,是油印的,大家可能没看过,过去不像现在有复印机,这么容易复印。这种报纸虽然是油印的,但里面有很多西方的信息,除了教会的内容,还有很多像刚才说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这一类的信息。所以,他们家有这么一份报纸,使林语堂很早就接触西方新的东西,但由于林至诚自己没上过学,又是当过小贩、务过农,所以他本质上是农民,他很关心农民,很同情农民,经常为农民排忧解难。有一次看到一个挑柴的人,挑了一担柴去卖,结果当地的税务官就跟他征税,说:你这一担柴要交很多的税。林至诚看到了就打抱不平,就跟那个税务官几乎打起来,先是吵起来,差一点打起来,可见这个牧师对农民还是很关心的,而且他讲道、布道,跟人家不一样,这个牧师讲上帝,林语堂说他父亲讲上帝和中国人讲佛祖差不多,他说基督教和佛教没什么区别。在他那里,上帝就像菩萨一样不但可以治病,赐福,还可以像送子观音一样给你送个小男孩儿。这是基督教里所没有的东西,这是他中国化的理解。所以,他在教孩子的时候,教学生的时候,教他们《四书》《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同时也给他看林琴南当时翻译的西方的作品,包括《福尔摩斯》《天方夜谈》《茶花女》,在当时是很新潮的东西。
林语堂两样同时受教育,就像我们现在的双语教育,两种文明的教育,所以,林语堂从小就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氛围里面。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农民,家庭妇女,叫杨顺命,顺着命运走,认命,也很善良,也很勤劳。她经常邀请一些过路打柴的农夫在她那边歇歇腿,甚至在那边吃午饭。
林语堂还有一个二姐,中学时书读得很好,成绩很好,她也很想读大学,但是他们家比较穷,他父亲一心想培养林语堂去上大学,不可能一家里面有那么多人读大学。他二姐虽然很羡慕他,但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就出嫁了,牺牲自己的机会,出嫁,以便保证林语堂有读大学的机会。在她出嫁的时候,和林语堂坐同一条船,她弟弟要去上海读书,坐同一条船,到那边上岸了,嫁人了。临走之前,从袋子里掏出四毛钱,带着体温的四毛钱,给她弟弟,对他讲:我们是穷人家,二姐只有这四角钱给你,你不要糟蹋了上学的机会,从上海回来时再来看我。结果他回来时,二姐已经死了,生病死了。再比如说,他谈恋爱的对象也是很朴实的农民,叫赖伯英,是他初恋的姑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这个农家女儿,住在半山上,自己弄了一个果园,他们家在那边,林至诚一家大热天去那边避暑,他们在一起。赖伯英是个孝女,她说她要留下来侍奉他的爷爷,所以林语堂要到上海读书,后来要到外国去,她都不能和他一起去,决心要留在山村。所以他们分手了。不管怎样,她也给他很深刻的影响,整个山村淳朴的民风,给幼小的少年时代的林语堂深刻、深远的影响。
林语堂说,影响于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母,我的父親;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州西溪的山水。在《赖伯英》一文中,他说:人若是在高山里长大,高山会使他的观点改变,溶入他的血液中。他说:假如你住在山里面,你用高山作为参照系来衡量一切,那时侯你看到一座摩天大楼,你的参照系就是高山。在高山面前,一百层的摩天大楼也没什么。所以他认为人生观也有两种。一种叫低地的人生观,一种叫高山的人生观。低地的人生观是平的,从来不抬头看,平平的平地。高山的人生观总是以高山为标准,和它相比,做参照系,繁华都市的摩天楼,也显得低矮。
人,商业,政治,经济,金钱,无不如此。这是他所说的高山的人生观。
其实山的形象大家都知道,它是象征山村淳朴和谐的人文环境。我们的传统有两种,一是大传统,比如儒家、道家,是大传统。民间的东西就叫小传统,比如民俗、民风。研究林语堂的人,一般都注意到大传统对他的影响,其实更应该注意到小传统,民俗民风对他的影响。
林语堂的童年所接受的其实主要就是小传统的影响,积极的影响。所以后来林语堂一个倾向就是经常接受非正统的文化。所谓的“异端”对他特别起作用,他就喜欢这个,跟他小时候的开头有关系。林语堂自称说:“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简朴的农家子弟的眼睛来看人生。”他一直保持用“农家子弟的眼睛来看人生”。用简朴的农家子来看人生,那就是用山村淳朴和谐的人文作为参照。有没这个参照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有句话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人只是埋头走路,开头有点分叉,那就会越走越远,甚至走到你原来不想去的地方。反过来,我们经常以原点作为参照,回头看看,如果有偏差纠正一下,那就好多了。
林语堂一辈子有70多年在城市里,真正在农村的时间其实很少,而且又是那么年轻就走出去了。但他年轻时,山村的影响对他异常的深刻。就是这个原因——因他经常以这个所谓的“高山人生观”作为参照系,经常回到原点上来。他在国外的都市生活长达三十几年,上海、巴黎、纽约,国内国外,他都住了很久。但他能保留心灵的一方净土。这就得力于他的高山人生观,能够用农家子弟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生。这只要看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红牡丹》《奇岛》,这些里面都有体现。
有一张照片,很宝贵的照片,叫《三个小孩》,其实是把林语堂小时侯的照片剪下来,贴在两个孙子的旁边,贴在一起,巧妙的组合起来,叫《三个小孩》。他和他的孙子都是小孩,那已经是晚年时的“作品”,他的杰作。这表明他到老的时候童心未泯。说实在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林语堂那样,深深的怀恋自己的童年,童年那些东西才对他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刚才讲林语堂的小名叫“和乐”,他一直保持这种性格,常看到人性善的一面。所以他女儿说,我父亲写《京华烟云》,八十多个人物,没一个坏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就是看到人性善的一面多。如果我们不了解林语堂的性格,不了解他的童心,不了解他的乡情,我们就很难理解作为“边缘人”的林语堂。这颗心,富有一种包容性,能够包容中西双方的文化,所以他是一个“一捆矛盾”的人,却又能像水晶一样,在很多不同的侧面通体透明。这是我们上面说的他和苏东坡很神似的一点,既复杂又单纯。
林语堂到晚年的时候,从美国回来,定居在台北。为什么定居在台北?台北这个地方,整个台湾,闽南人很多,保留乡音,保留民风,保留民俗。我到过台北,就像我们的旧厦门。所以到那边,你就觉得像我们闽南一样,有亲切感。所以他就认台北作为他的“故乡”。今天用林语堂晚年在台北用闽南方言写的一首诗来作为结束语。因为我也是漳州人,所以我就用漳州的本地话来念,以乡音来表达林语堂的乡情。我用方言念,那边有个提示:
乡情宰(怎)样好,让我说给你,
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如此)。
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
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
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
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
新笋园中剥,早起(上)食谙糜(粥)。
胪脍莼羹好,呒值(不比)水(田)鸡低(甜)。
查母(女人)真正水,郎郎(人)都秀媚。
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
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
(黄)昏倒的困(睡),击壤可吟诗。
今天就聊到这里。下一回我们再来聊一聊《林语堂的中国心和西洋脑》。
观众朋友,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