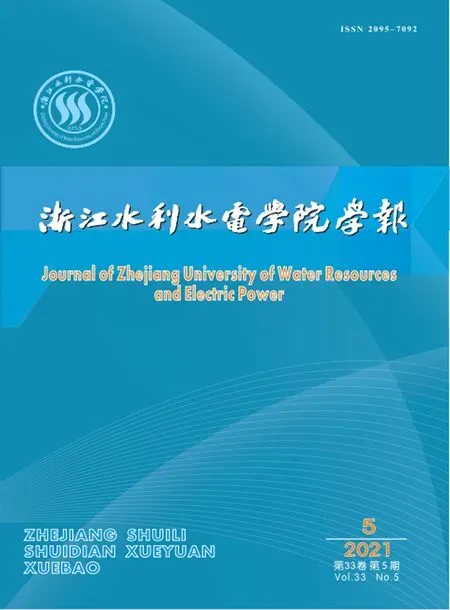日本遣明使眼中的明代浙东运河
——基于策彦周良《入明记》文本研究的视角
2021-04-02胡梦飞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策彦周良(1501—1579年),号怡斋,后称谦斋,日本室町幕府后期临济宗高僧,五山文学后期代表诗人。他博学多才,通晓汉文,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分别作为副使、正使率领日本遣明贸易使团入明,并将其在入明期间的见闻用日记体的形式写成《入明记》一书。《入明记》由《初渡集》和《再渡集》两部分组成,其中《初渡集》是日本天文七年(1538年)策彦周良以遣明使团副使身份首次赴明所写的日记,全文约有十五万字,详细记录了策彦周良首次出使明朝的经历;另一本《再渡集》是日本天文十六年(1547年)策彦周良以正使身份第二次出使明朝时所写的日记,仅有三万余字,而且由北京南下的回程记录只记到济宁便辍笔。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可以低估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这是日本十九次遣明出使中国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之一,是了解明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明代中日关系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学界有关的策彦周良及《入明记》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现有成果以宏观、整体性研究居多,区域性、微观性的考察仍有待深入。
浙东运河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浙东运河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谓连篇累牍,但从域外视角探讨其运河交通状况和城市风情的成果尚不太多。策彦周良曾先后四次往返于浙江境内,留下了众多有关浙东运河交通状况、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的记载,对了解明代浙东运河区域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策彦周良《入明记》为视角,结合地方志等史料,从运河交通状况、运河城镇风貌和运河名胜古迹三个方面,对策彦周良眼中的明代浙东运河风物进行分析和考证。
1 策彦周良《入明记》中的运河交通状况
浙东运河,又名杭甬运河,西起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跨曹娥江,经过绍兴市,东至宁波市甬江入海口,全长239 km。明代浙东运河沿岸设有众多驿站,由北向南分别为萧山县西兴驿、山阴县蓬莱驿、会稽县东关驿、上虞县曹娥驿、余姚县姚江驿、慈溪县车厩驿等。自杭州武林门出发,往南25里至浙江水驿,渡浙江9 km至西兴驿,经25 km至钱清驿,再25 km到绍兴府蓬莱驿,又40 km达东关驿,渡曹娥江5 km至曹娥驿,经45 km到姚江驿,再30 km至车厩驿,又30 km达宁波府四明驿。《寰宇通衢》记载:“武林驿十五里至浙江驿,三十里至西兴驿,五十里至钱清驿,五十里至本府蓬莱驿;蓬莱驿一百里至东关驿,十里至曹娥驿,九十里至姚江驿,六十里至车厩驿,六十里至本府四明驿。”[1]
嘉靖十八年(1539年)十月十九日,策彦周良一行自宁波北门出发,前往北京,舟泊于宁波西坝。《初渡集》记载:“予问水夫以处名并舟行之程,请笔书云。盐仓门至西坝四十里,慈溪县打口粮柴米人夫。”[2]西坝,又名大西坝、西渡堰,在余姚江西岸,在宁波城西北12.5 km,水道通宁波西门。明正统年间,宁波知府郑珞移建于浦口,两岸砌石塘、植柳,是旧时官船民舶进出宁波的必经之处。开庆《四明续志》卷三《水利》记载西渡堰东距望京门二十里,西入慈溪江,舳舻相衔,上下堰无虚日,“盖明、越往来者必经由之地”。[3]至正《四明续志》卷四《山川》记载西渡堰在县西二十里。[4]成化《宁波郡志》卷三《河防考》记载西渡坝在县治西二十五里,明正统年间,郡守郑珞移置浦口,两岸甃石为塘,植柳于上,以便往来,民称“郑公柳”。[5]策彦周良提到的“盐仓门”指的是宁波城东北的“和义门”。《宁波简要志》卷一《城镇志·城池》记载宁波城东北门曰“和义门”,抵姚江,内有盐仓,俗呼“盐仓门”。[6]
嘉靖十八年(1539年)10月20日,策彦周良一行抵达慈溪县车厩驿。“二十日黎明,著车厩驿之岸,舟行四十里。”[2]成化《宁波郡志》卷五《廨舍考》记载,车厩驿在府城西六十里慈溪县之石台乡。[5]嘉靖《宁波府志》卷八《公署》记载,车厩驿在县西南四十里,中为厅事,后为正堂,左右为使客房,东为官廨,西为囚舍,官廨后为庖舍。[7]策彦周良等人在此上岸参观。《初渡集》记载:“(十月)二十一日午刻,同三英、三正、仁叔上岸,徐步极目,有小山,号车厩,越王勾践憩车马地也。……戌刻,著姚江驿,舟行六十里。”[2]天启《慈溪县志》卷二《山岭》记载,车厩山在县西南四十里,“越王勾践停车秣马之所”。[8]由车厩驿前行六十里为姚江驿。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六《建置志四》记载姚江驿在县东一里,滨临姚江,嘉靖三年(1524年),知县丘养浩重建并撰写碑记。[9]万历《绍兴府志》卷三《署廨志》记载,姚江驿在县城东门外姚江北岸。[10]
嘉靖十八年(1539年)10月22日,在第一次出使由宁波至北京途中,策彦周良还详细记载了余姚过坝情景:“未刻,自龙泉寺前拨舟,酉刻,至下坝,舟行四十里,候潮泊于此。戌刻,潮满了,力士将辘轳索卷越坝。夜半,舟竖拏舟,丑刻,至中坝,舟行十八里,又如前坝。同刻,拨舟,寅刻,著上虞县岸,舟行十里,临岸有一门,揭‘便民仓’。”[2]嘉靖十九年(1540年)九月十日,由北京返回宁波途中,再次经过余姚中坝、下坝:“辰刻,打廪粮,即开船,船路十里而巳刻超中坝,十八里而午时超下坝,其险可畏。酉刻,著姚江驿,舟行四十里。”[2]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月六日,第二次出使,由宁波起程。八日,抵达姚江驿。“九日,辰刻,著登瀛门,以鹿索卷越船。午后,过中坝,又如前度卷越船。”[2]
记文中提到的“余姚中坝”,又名“郑监山堰”。明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水利志二》记载中坝在县东十里,又名通明北堰。明洪武初年,鄞县人郏度将其移建于郑监山下,故又名“郑监山堰”;嘉靖初,有奸民私置幽洼泄水,知县杨绍芳知之,遂对其进行重新加固。[10]余姚下坝,又名江口坝、大江口坝或新坝,在余姚县境,距中坝9 km,东北距余姚县城20 km(一说17.5 km),为十八里河的东端,左江右河,运河高于余姚江5 m。明代为绍兴至宁波舟船必经之路,坝太高不能急上,往往候夜潮通行。[11]明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水利志二》记载余姚下坝:“一名新坝,亦石甃,西去中坝十八里,东至县四十里,左江右河,河高于江丈有五尺,明、越舟航往来所必经;然坝高舟难猝上,又候夜潮乃行,率夜半,始群至坝下,至则各登涯争先绁缆,每相持或竟夜不车一舟;遇雨雪之夕,衣服濡湿,饥寒僵缩,股栗不禁,尽死力争之,尝有斗而死者。”[10]
嘉靖十八年(1539年)10月23日,策彦周良一行抵达曹娥驿。“二十三日午刻,至曹娥驿,舟行三十里,……驿楼门揭‘曹娥驿’三大字。”[2]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10月11日,第二次出使,由宁波至北京途中,再次经过曹娥驿。“十一日,晴,辰刻,发曹娥驿,而前进者三里许,持越行李,又经北渡,各转运行李于船。予、副使以下先到者,次第驾轿子至东关驿前乘船。即刻,下廪给口粮,少焉,开船。武官出应,外卫打挽夫。夜雨,夜半到蓬莱驿。”[2]记文中提到了曹娥驿、东关驿、蓬莱驿三处驿站。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六记载曹娥驿在兰山下、曹娥江滨,元大德中,圮于怒涛,徙县西;洪武初,迁移至今所。[9]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三《署廨志》记载东关驿在曹娥江西岸,旧名“东城驿”。[10]蓬莱驿在迎恩门外,唐代曰“西亭驿”,宋曰“仁风驿”。[10]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10月28日,策彦周良由宁波至北京途中第一次抵达萧山县西兴驿。《初渡集》记载:“二十八日,三里许而有西兴驿,廪给如右。驿门横揭‘西兴驿’三大字。”[2]“西兴驿”位于浙东运河南岸,今西兴街仓桥和屋子桥之间,旧时为邮政、公文传递和官员中转的驿站。吴越争霸时称“固陵驿”,唐时称“樟亭”或“庄亭”,五代后名“西陵驿”,宋代曰“边驿”,明代萧山知县邹鲁题“庄亭古迹”于其上。嘉靖《萧山县志》卷二《建置志·邮铺》西兴驿在西兴镇运河南岸,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主簿海牙公重建。[12]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三《署廨志》记载,萧山西兴驿在西兴镇运河南岸,唐代称“庄亭驿”,宋代曰“边驿”。[10]
明代驿站有专门为走水路官员而设的“站船”。明人王圻《三才图会·器用四·站船》记载:“此官府所坐之船,谓之站者,就驿中之程言耳。”[13]作为外国使节,策彦周良等人亦享受乘坐站船的待遇。嘉靖十九年(1540年)九月九日,因站船不足,导致前行受阻。《初渡集》记载:“午时,著曹娥驿。即上船,自东关至本驿总计一十里路,站船不足,故不前进。酉刻,打廪粮,戌刻,乘月拨船。子刻,著上虞县便民仓下。”[2]
策彦周良第二次出使由北京返回宁波时也应到过浙东运河,但是现存的《策彦和尚再渡集》为残本,只记载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9月30日使团一行抵达济宁,对于济宁以南的行程未见记载,故第二次出使回程途中有关浙东运河的记载我们无从得知。
2 策彦周良《入明记》中的运河城镇风貌
浙东运河依次流经萧山、绍兴(山阴)、会稽、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城市,对这些城市的景观面貌和市井风情,策彦周良在《入明记》中都做了详细记载和描述。
嘉靖十八年(1539年)10月22日,策彦周良上岸赴余姚城中参观游览。《初渡集》对此做了详细记载:“二十二日,解缆于姚江驿前,辰刻,提举司驾楼船,护贡物来。船头挂牌,牌朱漆,中书‘进贡’二金字。又黄旗二竿,一书‘进贡’二大字,一画麒麟。姚江乃绍兴府附庸也,系船之所有布政司华第,外头有石门,上镌云物,横书‘进士及第’四大字,又左右分‘元’‘魁’二大字书之。又书云:‘弘治十四年辛酉’‘顺天乡试第一名’。……城里乃余姚县也,同刻,进舟者少许,过余姚石桥,天下第二桥云云。泊舟龙泉寺前。龙泉寺侧有旧祠堂,不知何人,揭‘忠烈祠’三大字,又揭‘文正祠’三大字,横又有门,揭‘完全名节’四大字。又所经历,及第门多多,或颜‘榜眼’二大字,或揭‘登瀛’二大字。”[2]从策彦周良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余姚科举之兴盛。
嘉靖十八年(1539年)10月25日,策彦周良等人抵达上虞县,对上虞县城之景观和风貌,策彦周良也做了详细描述:“二十五日,寅刻,拨舟,所历过傍北山有宇,门揭‘瓜山铺’三大字。自东关舟行四十里有陶家堰铺,又傍有石门,横揭‘秋官里’三大字,又其次有堂宇,横揭‘赏元宵’三大字,盖正月十五聚会于此乎?又十里许,有樊江寺,门前有市,市中帘铭,或有‘佳酿’二字,或有‘酒海’二字。……又有堂宇,门揭‘织女铺’三大字,又临河有小亭,榜‘泗水亭’。”[2]
嘉靖十八年(1539年)10月25日,策彦周良一行抵达绍兴府。“午时,至绍兴府。自陶家铺至本府,舟行四十里。外头总构有石筑地,又有楼门,横揭‘迎春亭’三大字。……申刻,著蓬莱驿。驿口有楼门,横揭‘迎恩’二大字,自迎春亭下至蓬莱驿,舟行十里。绍兴府左方有会稽山。”[2]对绍兴府城市井面貌,策彦周良在其《入明记》中亦做了详细记载:“二十六日,天气快晴,辰刻,自迎恩门下开船,船路少许而有青田铺。又次有石桥,横刻‘灵芝桥’三字,船过其下,又有帘铭,书‘时新清酒’四字,又有及第门,横揭‘父子进士’四大字。又舟行里许,而渠口有石桥之尖头者,横刻‘露头桥’三字,又舟行四五里许,而有铺门,额上横书‘山阴县’三小字,下竖书‘梅氏铺’三大字。又二里许而有石桥,横刻‘通济桥’三大字。又有寺,有二重楼门,不榜额。余指以水夫,答以‘柯桥寺’。寺外有铺门,书‘柯桥铺’三大字。”[2]记文中提到了“灵芝桥”“露头桥”“通济桥”等桥梁名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绍兴城内桥梁之多。这里的“柯桥寺”即南宋时期的“柯桥接待院”,后改名“灵秘院”;明代称“柯桥融光寺”,简称“柯桥寺”。[14]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一记载融光寺:“在府城西三十里,旧传‘柯亭’即其地也;宋时‘接待院’,明正统十二年,诏从侍郎王佑言,赐经一藏,构重屋贮之,赐今额,俗呼为‘柯桥寺’。”[10]
嘉靖十八年(1539年)10月27日,策彦周良一行抵达萧山县城,对萧山县城之风貌及城内店铺帘铭,策彦周良亦做了详细记载:“二十七日,辰刻,上岸,同列方轿子至半途,缺行李转运人夫,故借黎家一宿。所历有帘铭,或书以‘洞庭春色’,或以‘时新美酒’。又有卖果店,铭云:‘发卖诸般果品。’又有卖帽家,书以‘任氏帽铺’。又山侧有旧祠,揭‘祷雨’二字,盖旱年祈雨之堂也。”[2]出使途中,沿途经过运河沿线城市时,策彦周良对店铺帘铭颇为留意,故在其《入明记》中记载颇多。
3 策彦周良《入明记》中的运河名胜古迹
浙东运河沿岸地区名胜古迹众多,尤其是各种寺观祠庙更是星罗棋布,策彦周良对此亦颇为留意,并在《入明记》中做了详细记载,为我们了解相关文物古迹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史料。
曹娥庙,全称“曹娥孝女庙”,位于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孝女庙村,早年又叫灵孝庙、孝女庙,是为祭祀东汉时期上虞孝女曹娥的祠庙。据历史记载,东汉汉安二年(143年)5月5日,上虞人曹盱坠江溺水而死,其女曹娥,年方十四,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寻找父尸,十七日不得,投江而死,时人以为孝女。东汉元嘉元年(151年),时任上虞县令度尚为孝女曹娥造墓建庙,并立石碑,由其弟子邯郸淳撰写碑文。嘉靖十八年(1539年)10月24日,策彦周良一行抵达上虞县城。上虞县城内有曹娥庙,策彦周良虽然早有耳闻,但却遍寻无果,《初渡集》对此亦做了记载:“二十四日,辰刻拨舟,二里而上岸,正使及予方轿子,行二丁许又换舟,各转运行李,涉小渡。又驾轿里许,而至东关驿,换别船,日亭午。武官之称首二员,马上而率诸卒,护送至渡口。或奏乐,或击钲。自曹娥驿门回舟,少许有石桥,舟过其下,绝渡少许,有祠堂,疑是曹娥庙乎。又其次有楼门,颜‘曹娥场’三大字。余问水夫曰:‘是处有曹娥碑乎?’水夫不晓。今为公程忽忽,故欲见其碑不得。”[2]文中提到的“曹娥场”,即“曹娥盐场”。明清时期,曹娥江北部沿海的滩涂地,有的农户以煮盐为生,后发展为盐场,原曹娥盐仓桥下,曾设有“盐课司”衙门,由“曹娥场大使”管辖盐务。
嘉靖十九年(1540年)9月6日,策彦周良第一次出使由北京返回宁波,由杭州渡钱塘江进入浙东运河。9月8日,“巳刻,开船,所历过河之右方,有敕赐兴善将军之庙,横揭‘越岭遐观’四大字。……酉刻,著东关驿,舟行八十里”。[2]明万历《会稽县志》卷十四《祠祀下》记载,兴善将军庙在县东四十里白塔,吴越忠懿王钱俶建。[15]
嘉靖十九年(1540年)9月11日,策彦周良在由北京返回宁波途中,在余姚上岸参观游览龙泉寺、严子陵祠等古迹。“十一日,昧早雨,须臾而歇。卯刻,打廪粮。辰刻,携三英游龙泉寺。寺在山麓,寺门无额,佛殿按三世如来像,左右有十六罗汉,哑钟在殿里,塔头荒废,一个僧亦无,恰如‘无僧寒殿开’之句。古人云:‘龙泉寺绝顶有井’,予今指点问居民,居民不知其处。此行忽忽,不果其志。”[2]文中提到的“龙泉寺”位于余姚市龙泉山南麓,是余姚市区的著名古迹,始建于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至今已有1 700余年的历史,与杭州灵隐寺年代相仿,与宁波天童寺同为浙东名刹。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寺庙毁于火,元贞元年(1295年)重建。当时寺内除天王殿、大雄宝殿外,有弥陀阁、千佛阁、蟠龙阁、罗汉院、中天院、东禅院、镇国院、唤仙亭、更好亭、龙泉亭等,层楼叠阁,蔚为壮观。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曾组诗社于寺内,后又在中天阁讲学授徒。宋僖、谢迁、黄韶、钱德洪都曾莅寺赏鉴,并留下诗章传世。地方志中对其历史沿革记载较细,但对其形制和内观却鲜有涉及,策彦周良对龙泉寺的记载无疑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严子陵祠”是祭祀东汉隐士严光的祠庙。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市)人,东汉著名隐士。严光少有高名,与东汉光武帝刘秀同学,亦为好友。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后卒于家,享年八十岁,葬于余姚的客星山。万历《新修余姚县志》卷八《建置三·祠祀上》记载:“严公庙在云柯乡之严公山,征士光二十三世孙唐绛州刺史某请于玄宗,得立庙专祀。今云柯白云峰,平石可坐数十人,有‘严公山’三大字刻其上,虽苔藓侵蚀而披拂可观,后徙祠客星山,庙遂废。”[16]明代弘治年间,参政周本立严子陵祠于灵绪山巅,以便瞻谒;明正德八年(1513年),同知屈铨重修;明嘉靖三年(1524年),知县邱养浩移建于千佛阁左,规模相较之前更为宏敞;不久,又迁于龙泉山龙泉寺东,知县顾存仁林仰成重修;明万历三十二年,浙江巡抚尹应元再次重修。
策彦周良在其《初渡集》中对严子陵祠做了详细记载:“山腰有严子陵庙,有小楼门,恰如小亭。檐端横揭‘汉严先生祠’五大字,门里横颜‘高风亮节’四大字。上头有庙,庙里无像,惟按木牌。牌上书以‘汉征士严先生’六字,木主左右,又立牌,左书云,‘辞劳庶职,甘烟雨于桐江’,右书云,‘抵足故人,动征符于帝座’。又左右壁间挂牌,左书云,‘尚一代高节’,右书云,‘播千古清风’。”[2]地方志中对严子陵祠的历史沿革记载较详,对其形制和匾联则鲜有提及,策彦周良的记文对于研究严子陵祠的历史发展变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4 结 语
浙东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浙东运河作为对外交往重要通道形成于唐代,繁荣于宋元时期,明清成为稳定期。”[17]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曾经作为王朝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将瓷器等出口产品经宁波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海外。同时,日本、越南、高丽等地的产品也通过浙东运河运往京城。外国使节也往往从宁波登岸,再经由浙东运河前往南宋都城临安等地。明代,宁波成为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港口,贡品通过浙东运河前往京师,故在历代外国使节留下的相关史料中,以日本朝贡使团对浙东运河记载得最为翔实。
“有明一代,日本派遣使者入明,永享(元年为公元1429年)以后先后共有11批,然而多数寂寂无声,而最后两批,因为策彦周良留下了其详细日程记录《入明记》,即《初渡集》和《再渡集》,成为日本入明使者的绝响,在中日交流史的载籍中占有极为重要乃至不可替代的地位。”[18]策彦周良一行先后四次经过浙东运河,留下了众多有关运河风物的记载,从其言谈举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高深的汉学水平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浙东运河沿岸交通状况、城镇风貌和名胜古迹的记载,现在看来,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明代中后期浙东运河区域社会风情,也为研究浙东运河史和城市史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