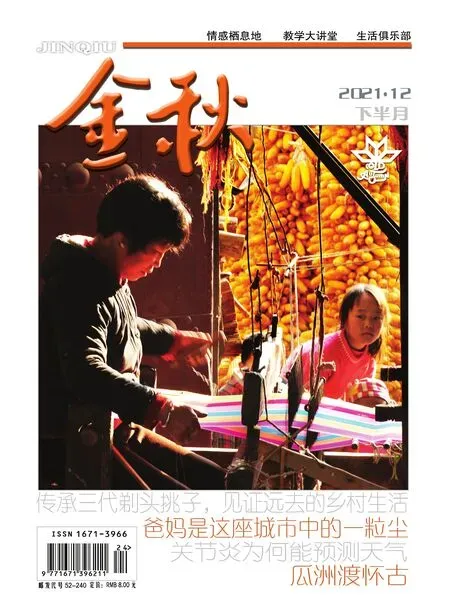六十年,我们牵手走过
2021-04-01肖素霞
◎文/肖素霞
我和我的夫君赵明,大学读书期间相识;1967年春节结婚,至今已经携手走过54个年头,步入金婚的殿堂。回首往事,历历在目;蹉跎岁月,感慨万千。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的“不幸”,是两个“病号”,在别人的怀疑、惊讶与不容乐观中走到一起来了。
我于1960年9月入学陕西师大汉语言文学系学习。开学后,全年级同学开赴灞河农场,参加为期一学期的劳动锻炼。除荒草,深翻地,夺红旗,搞竞赛。秋雨连绵,泥里水里,干得热火朝天。夜里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八面透风,与蚊虫为伴。不到两个月我就病倒了——浑身关节疼痛,下肢冰凉,走路要扶着墙,只好回校就医。校医说:“风湿病,重度贫血,下次检查如果指标没有好转,那你就准备休学吧!”于是,我只好请假回家看病、休养,直到1961年2月下旬才回校上课。
3月初的一天,赵明以插班生的身份来到我们班。他高挑,瘦弱,白皙,头发像干草一样没有光泽,一看就是一个病人。不久得知,赵明果然是得过大病的人。他比我们高一级,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当我们在灞河农场劳动的时候,他在医院做了心脏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当年此手术属于“尖端”,危险性极高,可以说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本该休学一年的他,却提前一学期回到了学校,与我同班。很快同学们就发现,赵明上课的笔记记得条理清晰,内容详实,成为全班同学争相传抄的“范本”。我自然也会经常借用他的笔记,加之一起负责办班上的板报,接触就慢慢多了。后来又听到一些有关赵明的消息:他是他们原来班上的“学霸”,即使因病耽误一两个月的课,一年级期末考试依然获得全优的好成绩。
5月的一天晚自习,突然班上骚动起来,说是赵明下午晕倒在医院,被抬回来了,同学们陆续去宿舍看望。快下晚自习的时候,我一个人悄悄走出教室,急匆匆来到男生宿舍,正在走廊上张望,赵明已经看到我了,就冲我喊了一声“在这儿”!走进宿舍,看见他躺在床上,不自然地笑了笑。我们彼此相视良久,什么话也没说。坐了一会儿,下晚自习的铃声一响,我就离开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相处,虽然短暂,却是另一个“开始”。
慢慢地,我们有了默契,早晨会在同一个地方读外语,晚自习会在图书馆多占一个位子……但同学们并不看好,普遍的看法是:两个风都能吹倒的病人,将来谁照顾谁呀?我的发小严肃地警告我:“你胆子真不小!你知道那是什么病?”她坚决反对我和赵明在一起。父母亲虽然有顾虑,但对赵明还是比较喜欢的,所以就尊重我的选择,没有多说什么。就这样,经过学校里四年的“热恋”和工作后一年半的“异地恋”,在“文化大革命”最深入、不放假的1967年春节,在红卫兵警惕的目光里,在“大批判”“拼刺刀”的间隙里,在双方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在26岁的时候结婚了。
我周六下午坐火车赶到赵明工作的学校,晚饭后有几位同事朋友先后来到宿舍表示祝贺,我们用一包奶糖做招待,收到的唯一贺礼是正在接受批斗的教研组长杨老师送的一幅木质边框的毛主席诗词刺绣。
第二天下午,我又匆匆回到自己的学校,悄悄给住在单身宿舍的几位老师的枕头下塞了一包奶糖,以这种方式告知大家我结婚了。
家里原本给我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后来都被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抄家抄走了。赵明的父亲是大学教授、系主任,原本就不同意我们在那种情况下办婚事,什么准备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婚礼,除了一张结婚证,没有一件新衣服,没有新被褥,没有仪式,更没有蜜月。现在回想起来,虽不无遗憾,却留下别样的甜蜜。一年之后,孩子出生。两地分居,他在宝鸡,我在西安,困难重重。“文化大革命”渐渐缓和,我开始跑调动,抱上孩子两地奔波。1973年,赵明终于调回西安。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赵明的身体比预料的要好得多。修补术后的心脏很对得起他,竟然没有惹过一次麻烦。
2013年是赵明的本命年,他已经72岁了。春节去给表哥拜年。闲谈中表哥说:“你身体不错啊!都72岁了,当年大夫说你的预期寿命只有40岁。”这就印证了我的发小对我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她的说法和大夫的寿命预期都是有医学根据的。庆幸的是,赵明打破了医学的定论,如今已经“超期服役”,“多活了”40年。
而我,却大小病痛不断,还有几次是要命的大病。一次是生小孩得了“子痫”,因抢救及时而捡回一条命;一次是胰腺炎被误诊为胃痛,最后关头被一位老大夫发现并纠正;一次是胆囊炎,做手术切掉了半个胆;一次是“极高危”高血压被大夫强制住院治疗;一次是冠心病发作,搭了五个支架。每当这个时候,赵明都是我的靠山和支柱。他沉着冷静,不慌不乱,该拿主意时当机立断。记得那一次搭支架,是在他要去山东主持召开一个全国性课题会议的前一天。他把我送进介入治疗室,第二天又把我从重症监护室接出来,安顿到病房后,就赶去机场了。
就这样,两个病恹恹的人,相互搀扶,彼此照顾,平平安安度过几十个春秋,现在已是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了,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几次同学聚会,我们都得到了同学们的夸赞:“赵明和肖素霞原来是同学当中身体最差的,现在人家比谁都好!”还被誉为“同学中最幸福的一对儿”。如今,许多同学都已经过世了,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岂不更是一种福运了。
一路走来,感悟颇多,归纳了一下,主要有两点值得与大家分享:

一是不把自己当病人看。有病的人,如果老是记着自己的病,生怕别人不把自己当病人看,得不到家人的照顾,那反而会影响心情。作为病人,要善于调养自身的正气,甚至忘掉自己的病痛,像健康人一样生活着,居然会真的健康起来。人老了,各种老年病的到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必在意,不必惊慌,更不必大把大把地吃保健品。赵明不动烟酒,但有喝茶的习惯,每天喝一点蜂蜜水,此外再没吃任何保健品。我呢,为了控制住血压和血糖,会找一些中药制剂,或用手疗、足疗、穴位按摩来做治疗。我搭了支架之后,大夫让长期坚持吃的药,我吃了两个疗程,各项指标基本正常之后就停掉了。随身携带救心丸,心慌气短时含服一两粒,也蛮管用。至于日常饮食,则粗茶淡饭,可口而已。
二是坚持劳作。人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感受是“生命在于劳作”,包括体力劳作与脑力劳作。记得当年结束两地分居,虽然有了家,但家徒四壁,一切得从头开始。赵明买了一本木工书,干起了木工活,小椅子,小饭桌,以至床头柜、写字台,都是自己打出来的,都是卯榫结构,有的到现在还在用着。油漆活,泥瓦匠,都干过,还干过“大厨”。我弟弟结婚时,赵明竟然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在家里摆出了五六桌丰盛的饭菜。对于教学及行政工作,更是兢兢业业,全身心地投入。在繁忙的校长岗位上,还给高三学生开设课程,课外讲授文学史知识。在赵明当了教导主任、校长之后,有学生考上大学,终于使学校扭转了多年“剃光头”的局面。到教学研究机构之后,更是如鱼得水,为指导西安市中学语文教学和培养青年教师,竭尽全力,成绩突出。2001年退休,转向中国教育学会工作,连续20年主持三个国家级研究课题,使得全国两千多所学校上万名教师获益。同时笔耕不辍,撰写并发表论文及散文作品,出版150万字的四卷文集《落叶满长安》。直到现在,他依然文思敏捷,不断有新作品问世。在各地作培训报告,两三个小时下来也不觉太累。赵明上学时体育活动不是他的长项,但依然爱好。同学们打篮球,他吹起哨子当裁判,吹得有模有样。上下班能骑自行车就不坐车,退休后能步行就不坐车,走路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但不追求什么指标,随心而已。
我早年笨手笨脚,什么都不会做,但生活所迫,也买了一本服装剪裁书,学会了给孩子裁剪、缝制衣服。修整住房时,我像小工一样,拉车、搬砖、和泥。学校的班主任及教学工作,更是毫不马虎,曾获得过西安市教学评优一等奖。所带职教班有许多学生考上技术学校,其中几位后来很有出息,干成了大事。我给工厂职工夜校上课,帮助年轻工人考大专文凭。我又是赵明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判者。我所提出的意见,他都乐于接受,认真修改。到现在,我还保持读书、学习、锻炼的好习惯,在西安市文慧文化书院听课,并指导教学工作。打太极拳也坚持二十多年了。
两个人走到一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相濡以沫应该是不变的选择。珍惜当下的一切,所有的机遇都不是你应该得到的,而是偶尔遇到的。顺境是你的好运,逆境是你的财富。感恩人生,人生就既有意义,又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