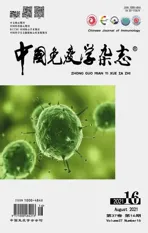儿童特应性皮炎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关联性及其潜在机制的研究进展①
2021-03-29任文静徐阳春
任文静 徐阳春 黎 萍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发育儿科,长春130041)
特应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AD)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皮肤病,全球范围内儿童AD的发病率15%~20%,多在2岁以内起病,部分患儿发病持续到成年时期[1]。AD的发病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尘螨、蟑螂、动物毛、牛奶、鸡蛋、虾蟹类、金属制品、甲醛等都可能是诱发AD患儿发病的重要过敏原[2]。研究证实,在AD人群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抑郁和焦虑以及压力相关障碍的发病率显著增加,其中ADHD最受关注[3]。ADHD是儿童及青少年期最常见的神经行为障碍,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冲动和多动。全世界约7.1%的儿童和青少年患ADHD[4]。AD和ADH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AD与ADHD存在流行病学关联和发病机制的联系,本文综述了相关研究进展,以期为两种疾病的防治提供潜在思路。
1 儿童AD与ADHD的流行病学关联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儿童AD与ADHD有较高的共患检出率。与正常对照组(非AD儿童)相比,AD患儿患有ADHD的相对危险度显著升高[5]。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884例ADHD患儿中,约44.3%患儿共患过敏性疾病,其中8.1%为AD[6]。美国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AD患儿较非AD患儿ADHD患病率明显增加(9.4% vs 7.1%),如合并睡眠障碍、贫血、肥胖或家族特应性疾病史,ADHD的患病风险进一步升高[5]。这提示儿童AD与ADHD存在共病的流行病学基础;但是二者关联的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前有学者认为AD是特应性疾病进展的特殊症状移行的表现,可能发展成为过敏性鼻炎、结膜炎和支气管哮喘等特应性疾病,而这些疾病可能使ADHD的患病率增加[7]。
2 儿童AD与ADHD关联的潜在机制
目前研究表明,AD和ADHD关联的潜在机制包括基因-神经递质、神经-免疫、肠-脑轴、心理应激、共患睡眠加重等,以上机制可能存在相互协同作用。
2.1 基因-神经递质机制 AD及ADHD均有高度遗传性,二者可能共有的发病机制首先表现在基因遗传层面。MOORE等[8]研究发现6个月内婴儿AD的累积发病率达17.1%,若双亲中一方患病,则子女发病风险增加2倍,若双亲均患病,则子女发病风险增加3倍。AD的易感基因主要包括参与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因子,以及调节角质形成细胞终末分化的分子[9]。ADHD是神经发育异常的多基因遗传病,遗传度高达76%[10];ADHD相关的基因主要有多巴胺受体基因、5-羟色胺代谢基因、去甲肾上腺素运转基因等[11]。Th2细胞因子免疫反应的关键调控元件STAT6编码基因的遗传变异与AD发病密切相关[12];而STAT6在中枢神经系统高表达,在ADHD的发病机制中起着主要作用[13]。另外有学者提出,食物、吸入物等环境刺激与ADHD的发生有关,AD‐HD并非由过敏反应引起,其本身可能是一种过敏性疾病[14]。目前,AD与ADHD可能共有的遗传基因与信号通路尚处于推测阶段,有待更多临床和基础研究进一步阐明。
2.2 神经-免疫机制 在AD病程中,Th2相关炎症反应占主导,IL-4、IL-33等细胞因子释放增加[15]。ADHD患儿神经系统存在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功能低下,5-羟色胺功能下降,而这些脑内神经递质失衡在AD等过敏性疾病中同样存在。研究表明,AD患儿过度分泌的Th2相关细胞因子可通过血脑屏障,激活与ADHD相关的行为和情感回路的神经免疫机制[16]。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PFC)区域的变化与认知障碍、不恰当的运动输出、决策障碍和注意力控制减弱等ADHD的特征有关[17]。功能核磁共振的研究表明,AD等发生过敏反应时与AD‐HD密切相关的PFC区域激活,可能会影响神经行为发育[18]。
AD病程中炎症细胞因子分泌增多,其影响认知功能和PFC区域的可能机制包括:①炎症状态下,血脑屏障可直接分泌细胞因子、前列腺素和NO等与神经免疫系统相关的物质,这些物质可通过血脑屏障分泌到中枢神经腔室或血液中,从而间接促进涉及小胶质细胞或血液屏障相关内皮细胞产生新的神经递质,进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3];②外周血液循环释放较大的炎症细胞因子可影响大脑和所有相关的病理生理区域,其无法轻易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往往通过脑室周器官等血脑屏障的漏区,或激活迷走神经传入纤维传输细胞因子信号到孤束核等特定脑核,然后作为中继站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19];③炎症细胞因子会对大脑的神经内分泌产生一系列影响,也可导致某些关键的神经递质代谢发生改变[20]。综上所述,可推测AD患者炎症细胞因子水平的升高可能间接或直接影响ADHD相关的PFC区域等大脑部位。因此,AD患儿炎症因子可激活大脑的免疫细胞,后者激活后可产生更多的炎症因子,促进更多的大脑免疫细胞的激活,继而导致ADHD神经系统的病理生理变化[21]。
最新研究发现,硬脑膜窦内存在功能淋巴管,这些结构表达了淋巴管内皮细胞的所有分子特征,能够携带脑脊液中的液体和免疫细胞,并连接到颈部深层淋巴结;中枢神经系统脑膜淋巴管作为脑脊液引流的新途径,改写了神经免疫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这为ADHD的已知免疫学机制提出了新的可能[22]。因此,对于伴免疫功能改变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脑膜淋巴管功能失调可能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为后续研究AD与ADHD的共病机制提出了新的启示和方向。
2.3 肠-脑轴机制 肠道微生物群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双向信号传导受肠道黏膜免疫、神经内分泌、肠道迷走神经的调节,这种结构称为肠-脑轴,对维持体内平衡至关重要[23]。研究表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在菌门水平,AD患儿拟杆菌门及梭杆菌门群落丰度降低,在菌属水平,拟杆菌属群落丰度降低;而菌种水平,在丰度排名前15的菌种中,两组间分布无明显差异[24]。SONG等[25]采用SrRNA基因检测技术发现,AD患儿粪便中F梭菌内部失衡,推测肠道菌群失调可能与AD发病和皮损症状加重有关。LEE等[26]研究发现,AD患者肠道菌群中免疫发育相关的功能基因与健康儿童存在差异。
失调的肠道菌群可通过调控宿主对致病微生物的免疫反应以及自身免疫应答,影响中枢神经系统[27]。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可改变血循环细胞因子的水平,导致免疫功能失调,对大脑功能产生显著影响;胃肠道微环境变化可通过改变迷走神经激活状态与相关大脑区域,调节多种复杂行为[28]。此外,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会对肠道炎症和肠道屏障功能产生有害影响,导致代谢性内毒素血症,直接或间接地改变迷走神经传入神经元等神经功能,进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29]。有研究表明,ADHD发病机制可能与5-羟色胺、多巴胺及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失调相关[11,30]。AD可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异常,使神经递质分泌增加;此外,人体中存在通过复杂的神经-内分泌通路完成的肠-脑轴的双向调节机制[31]。因此,AD患儿异常的肠道菌群可能会导致体内神经递质水平失调,促进ADHD的发生发展。
2.4 心理应激机制 AD影响了患儿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患儿社会敏感性和自我意识加强,暴露部位的皮损以及剧烈的瘙痒常使患儿感觉尴尬甚至羞耻,导致情绪改变、社交障碍和认知障碍等精神心理问题[32]。研究发现,慢性心理应激过程中,糖皮质激素发挥重要作用[33]。AD患儿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可能会干扰与ADHD相关大脑部位的发育和成熟,尤其是影响PFC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这些功能和结构的改变很可能导致认知障碍,从而导致ADHD[7]。
2.5 睡眠加重机制 AD与ADHD均存在睡眠问题。ROMANOS等[34]研究发现,与无睡眠障碍AD患儿相比,同时存在睡眠障碍的AD患儿ADHD的患病率高出2.5倍,而在没有睡眠障碍的儿童中,AD和ADHD无显著的关联性。AD患儿夜间剧烈的皮肤瘙痒、频繁搔抓可导致入睡困难、夜间睡眠不足、早醒等,使患儿产生行为改变、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一系列ADHD相关表现[35]。此外,睡眠障碍也可与炎症因子协同影响大脑的发育,影响与ADHD相关的大脑PFC区域的功能发育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系统的成熟,导致前额叶和前扣带皮质等对唤醒调节和睡眠剥夺的敏感性也下降,产生AD‐HD的病理生理改变[36]。睡眠问题在AD共患ADHD中可能发挥着桥接、协同作用。
综上所述,大量的流行病学关联研究以及相关的机制研究表明,AD可能通过神经免疫机制、肠道菌群和心理应激、共患睡眠障碍疾病等方面促进ADHD的发生和发展。针对这两种疾病潜在的关联,临床医生应对AD以及ADHD患儿进行全面医学管理;针对其潜在发病机制可开发缓解AD和AD‐HD共病的新药物,对有效改善AD、ADHD患儿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