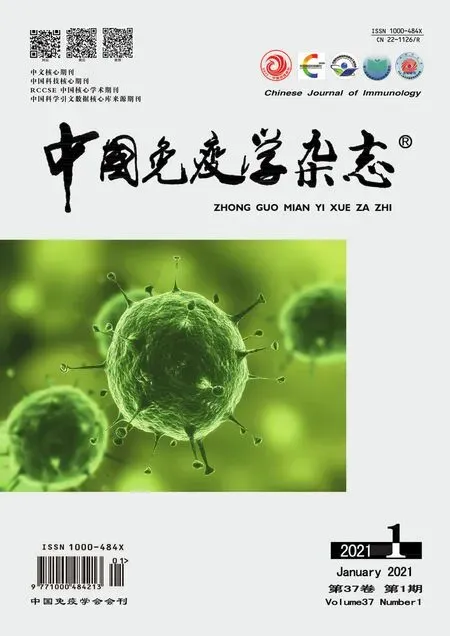肠道微生物在类风湿关节炎机制中的作用及对心血管风险的影响
2021-03-29杨金萍
杨金萍 桂 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肾病风湿科,长沙 410013)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慢性系统性的自身免疫疾病,患病率在0.24%-1%之间[1]。RA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遗传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2]。最近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通过影响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和辅助性T细胞(helper T cell,Th)之间的平衡来调控促炎和抗炎反应,增加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从而影响RA的发生发展[3-5]。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是导致RA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RA患者的CVD的病理生理学涉及免疫失调和慢性炎症,近期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和其代谢产物的改变参与CVD的发生发展[6]。本文将介绍肠道微生物在RA机制中的作用并探讨其对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的影响。
1 肠道微生物
1.1肠道微生物概述 人体肠道(200~300 m2的黏膜)是10万亿个不同共生体(50个细菌门和约100~1 000个细菌物种)的“秘密花园”,统称为“微生物群”,其编码的基因被称为“微生物组”,比人类基因组多150倍[7]。人体大多数微生物存在于肠道中,它们在合成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营养素、保护宿主免受病原体的入侵及调节免疫宿主反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8]。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与宿主及外部环境保持动态平衡[9]。研究表明,新生儿的肠道几乎是无菌的,出生后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包括年龄、分娩方式、母体微生物组成、早期是否使用抗生素和喂养方案等[10]。每个个体都有独特的相对稳定的肠道微生物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抗生素和病原体的干扰[11]。近期的研究表明,人类微生物群分为三种,包括:拟杆菌型、普氏菌型、瘤胃球菌型,人类肠道微生物组的个体差异大,平均遗传率仅为1.9%~8.1%,而肠道微生物组20%以上的差异与环境因素有关[12]。
1.2肠道微生物与免疫应答 文献报道,个体肠道微生物群数量占体内总微生物量的80%以上,与免疫系统的联系最密切[13]。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ut-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GALT)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约占人体免疫系统总表面积的70%,所有产生分泌型IgA的浆细胞约有80%驻留在肠道固有层中[14]。肠道微生物在宿主免疫系统的发育和成熟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无菌小鼠的GALT的发育存在明显的缺陷,若将无菌小鼠重新暴露于肠道微生物分离出来的肽聚糖中,受损的淋巴组织结构能够正常发育成熟[15]。
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在人类3岁左右时趋于稳定并维持其多样性,与宿主免疫系统共同进化,协同完成机体必需的生理过程,从而达到共生状态。有学者指出,肠道共生菌群的组成和相对丰度影响宿主的免疫应答[16]。在人体健康的生理情况下,肠道共生菌群维持体内Th17/Treg细胞的平衡,可以有效防止自身免疫反应的发生[17]。研究表明,分段丝状细菌(segmented filamentous bacteria,SFB),一种常见的肠道共生菌,它可以促进肠道中Th17细胞的增殖和活化,增加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从而增强宿主的黏膜免疫应答[10]。脆弱拟杆菌是另一种肠道共生菌,通过与Toll样受体-2(Toll-like receptor,TLR2)结合,增加Treg细胞的比例,抑制Th17细胞的产生,从而维持免疫稳态[18]。
2 肠道微生物与RA
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的改变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与宿主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免疫调节失调,从而导致RA发病[19]。肠道微生物和免疫系统之间双向调控,共同维持免疫稳态。然而,肠道微生物和RA间的因果关系的确立仍有待进一步研究[20]。
2.1RA肠道微生物的变化 研究表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RA患者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降低,其中放线杆菌属和拟杆菌属的丰度增加[21]。此外有研究发现,早期RA患者肠道中的拟杆菌和双歧杆菌的分布显著下降,而普氏菌分布呈增多趋势[22]。有学者提出,RA患者肠道微生物中的乳酸杆菌的多样性增加[23]。值得一提的是,蠕虫状阑尾,作为一个富含Treg细胞的免疫器官,其黏膜周围存在的最丰富的共生细菌门包括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变形菌门、梭杆菌门。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既往有阑尾切除术病史的病人患RA的风险明显增加,研究者认为阑尾可能有助于在肠道菌群紊乱后重新接种肠道内的微生物,参与维持RA的肠道微生物群稳态[24]。
2.2肠道微生物参与RA发病 RA是基因、环境因素和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是RA发病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环境因素[25]。在20世纪提出的“毒性因子”假说认为肠道革兰氏阴性细菌会增加循环内“有毒代谢产物”的产生,促进关节炎症的发展[26]。KIM等[25]通过建立具有遗传易感性的实验性RA模型,证实了肠道微生物在RA发病中的关键作用。近期的研究结果显示,RA患者的滑膜中提取出的肠道菌群DNA以及RA患者肠道共生菌群的异常,进一步验证了肠道微生物在RA的发病机制中的重要性[27]。
肠道微生物参与RA发病的机制包括分子模拟、外膜囊泡、T细胞分化、表观遗传修饰、免疫启动以及免疫衰老,其中涉及分子模拟的机制被广泛接受[28]。研究表明,外源性细菌抗原和自身抗原之间的分子模拟可以促进T细胞和B细胞的分化和成熟,T细胞的表位模拟可能构成黏膜免疫与关节免疫之间的潜在联系,特别是普氏菌属可能与关节内高表达蛋白的自身表位发生交叉免疫反应,从而激活黏膜表面的T细胞,促进关节炎症的发生[29]。类似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可通过自身抗原的分子模拟促进RA的发病[23],例如,有学者提出[30],SFB通过分子模拟的机制选择性地扩增Th17细胞表达的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TCR),识别SFB表位和自身抗原,从而增强宿主体内的自身免疫反应。同样地,肠道微生物的代谢产物也可以发挥分子模拟的作用,包括小分子有机酸、胆汁酸、维生素、胆碱代谢物和脂质[31]。
2.3肠道微生物影响RA的免疫应答 在健康人的生理情况下,正常的肠道微生物群维持免疫稳态。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RA患者外周血中的Treg细胞比例减少,Th17细胞比例升高,提示RA患者的Th17/Treg细胞失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通过调控Th17/Treg细胞的平衡状态来影响RA的免疫应答[32-33]。研究表明,Treg/Th17细胞的分化和扩增由厌氧细菌的特定成员独立控制[34];普氏菌通过介导Th细胞的分化影响Th1细胞和Th17细胞的比例[35];脆弱类杆菌通过其表达的多糖A与TLR2相互作用,增强Treg细胞的抗炎作用[18]。此外,肠道代谢产物(如丁酸盐)与RA的免疫应答密切相关。研究表明,丁酸盐通过调节Treg/IL-10/Th17轴抑制了胶原诱导性关节炎(CIA)小鼠模型关节炎的进展[36]。近期的研究发现,RA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和功能发生改变,并且与临床指标相关,经过抗风湿药物治疗后,RA患者异常的肠道微生物部分恢复,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肠道微生物参与调节RA的免疫应答[37]。
肠道微生物群与GALT之间互相影响,共同控制RA的发生发展[38]。研究表明,普氏菌通过激活表达TLR的细胞,增加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促进了Th17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中性粒细胞的募集[39];此外,普氏菌还可以通过刺激RA小鼠模型的B细胞,调控Th17细胞的促炎反应,促进抗瓜氨酸化蛋白抗体的形成[40]。另有研究表明,SFB通过诱导肠滤泡辅助性T细胞向全身淋巴组织部位分化和迁移,促进自身抗体的产生,从而加重关节炎的症状[30]。
2.4RA的免疫应答及其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文献报道,人体胃肠道黏膜表面由一层肠上皮细胞(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IECS)组成,IECS表达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负责识别肠道的病原体相关模式分子(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41]。在RA中,肠道微生物通过调控位于GALT上的抗原提呈细胞和PRRs激活免疫应答[42],TLR参与维持Th17/Treg细胞的平衡,其中Th17细胞通过产生促炎性细胞因子以及招募中性粒细胞促进自身免疫反应,而Treg细胞通过增加Th细胞的比例影响肠道炎症反应[14]。研究表明,RA患者位于GALT的免疫细胞处于免疫失调状态。例如,RA患者外周血和淋巴结中的CD4+IL-10+T细胞表达减少,而外周血中的CD4+IL-17A+T细胞表达增多,这与关节炎发病密切相关[43]。
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了肠道微生物群在RA发病中的作用,但目前仍不清楚肠道微生物的改变是RA的致病因素,还是RA自身的炎症反应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44]。以前的研究表明,宿主的免疫系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的分布[4]。有研究表明,IECS的自噬功能的破坏可以改变小鼠肠道微生物的组成,降低小鼠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45]。另有研究表明,TLR基因型参与调控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缺乏TLR5的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群发生改变[4]。更重要的是,有学者提出,RA的基因型决定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研究结果显示,与携带具有遗传抗性基因HLA DRB*0402的小鼠相比,携带关节炎易感基因HLA DRB*0401的小鼠具有不同的肠道微生物群,他们认为这与肠道黏膜免疫功能的改变相关[44]。最近的研究表明,RA中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至少部分是由于HLA-B27和HLA-DRB1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所致[46]。除此之外,免疫功能上的缺陷也可能影响微生物群的组成,有研究发现,RA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剂后,体内的肠道微生物群随之发生变化[47]。
3 肠道微生物参与RA心血管风险的调控
文献报道,与健康人群相比,RA患者的CVD发生率增加了两倍,动脉粥样硬化(arteriosclerosis,AS)是CVD中最常见的病理改变[48]。AS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病变,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异常激活可以加速疾病进展,研究表明,T淋巴细胞存在于AS病变的各个阶段[49]。有学者提出,Treg细胞主要通过阻断Th1细胞的分化调节局部炎症反应,发挥抗AS的作用,效应T细胞与Treg细胞比值升高可以促进AS的进展[50]。许多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和其代谢产物的改变通过调控宿主的慢性炎症反应,影响CVD的发生[51]。例如,KOREN等[52]利用16S rRNA基因测序的方法在AS斑块中检测到细菌DNA,证实了肠道微生物可能参与AS斑块的形成;氧化三甲胺(Trimetlylamine oxide,TMAO)作为一种常见的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已有研究证实TMAO可能影响斑块和血栓的形成,与AS的形成密切相关[53]。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与RA疾病进展间存在关联。益生菌作为一种活的“肠道微生物”,它主要通过增强Treg细胞的功能,减少Th17细胞的产生,从而影响宿主的免疫系统功能。研究表明,补充益生菌可以降低CIA小鼠模型中RA的发生率[54]。更重要的是,有学者发现,补充益生菌可以改变TMAO的产生,以此来达到预防AS的目的[55]。此外,近期的研究表明,普氏菌比例的增加可以导致血浆TMAO水平的增加、TLR4过度活化、C反应蛋白增加等。在RA患者中,普氏菌通过其表达的脂多糖与TLR4结合,可能导致血小板聚集、T细胞异常激活和蛋白尿的增加,从而增加心血管风险[56]。由此可见,肠道菌群的调节或许可以成为改善RA患者心血管风险的潜在治疗手段。
4 小结与展望
肠道微生物群与宿主免疫系统共同维持内环境的稳态,肠道微生物对自身免疫反应的调控有重要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RA患者肠道微生物发生特异性改变,肠道微生物是RA发病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环境因素,而且肠道微生物是体内炎症分子的来源,其多种代谢产物已经被证明与心血管风险相关。对于RA患者而言,肠道菌群的调控或许可以为RA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