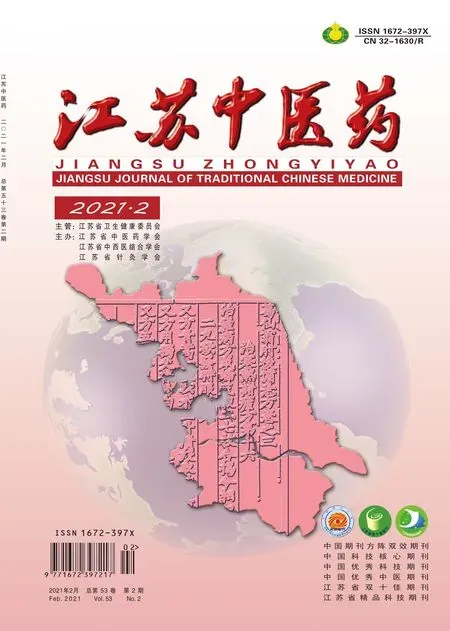从寒热错杂论治慢性腹泻
2021-03-28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慢性腹泻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病程较长,缠绵难愈,临床多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便质稀薄不成形,甚至泻出如水样便,并伴有腹痛、腹胀或肠鸣音、排便不爽或黏滞臭秽等症状,多由急性腹泻发展而来。我们认为慢性腹泻病基本病机为寒热错杂、虚实夹杂,属本虚标实,以脾肾阳虚为本,湿热内盛为标,从寒热错杂论治慢性腹泻常取得良好疗效。
1 慢性腹泻存在寒热错杂病机
慢性腹泻可归属于中医学“久泻”范畴,一般认为其发病原因主要有外邪所伤、饮食内伤、湿热内蕴、脾胃虚弱等,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异常,肠道分清泌浊、传导功能失司[1]。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慢性腹泻大多迁延难愈,存在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等复杂情况,提出寒热错杂是慢性腹泻的基本病机。其形成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因虚致实形成虚实夹杂(虚寒兼湿热),二是由实转虚致实中夹虚(湿热兼阳虚)。这两种病理机转以脾肾阳虚为内在基础,以湿久化热为重要条件。
1.1 脾肾阳虚 《景岳全书·泄泻》:“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脾弱者,因虚所以泻,因泻所以愈虚,盖关门不固,则气随泻去,气去则阳衰,阳衰则寒从中生,固不必外受风寒而始谓之寒也。且阴寒性降,下必及肾,故泻多必亡阴。”脾气虚运化失司,水谷不能正常运化,湿邪内生,阻滞中焦,下趋肠道,发为泄泻;泄泻日久,气随泻去,气衰日久导致脾阳虚,其主要表现为脘腹冷痛、泄泻、完谷不化、纳呆、稍进寒凉食物则加重、舌淡、苔白、脉濡细等。脾阳虚日久累及肾,肾失温煦,脾肾阳虚,水湿内停,日久化热,最终形成以脾肾阳虚为本,湿热阻滞为标的复杂情况。肾阳虚主要表现为在脾阳虚基础上兼见四肢不温、五更泻、右尺脉弱等。或因苦寒太过,伤及脾胃阳气,日久生湿生热,即因虚致实形成虚实夹杂、寒热错杂,很多慢性腹泻均存在这种病理机转。就湿而言,主要表现为舌苔白腻或水滑、大便溏薄而黏、排便不爽、稍进油腻食物则加重;就热而言,主要表现为舌红、口苦、大便臭秽、苔黄等。这种寒热错杂病理机转的形成是以脾气虚为前提,脾气虚主要表现为乏力倦怠、食少腹胀、便溏等。临证时应四诊合参,全面认识疾病的动态变化过程,整体精微辨证,才能有效施治。
1.2 湿久化热 现代人慢性腹泻寒热错杂证的形成与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外界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加快,饮食多肥甘厚味,加上缺少运动锻炼,导致内生湿邪,脾为湿困,运化失司,则湿浊内停,湿蕴化热,内伤脾阳,日久及肾,形成寒热错杂泄泻,故寒热错杂为现代人慢性腹泻的常见证型。或因素体阳虚,复感湿热之邪;或外感湿邪,伤及脾阳,内生湿邪,湿浊内停,郁久化热,湿热又反伤脾肾阳气,加重腹泻发生;或寒湿侵袭,从阳化热,日久导致脾肾阳虚。上述病机变化形成了因实转虚的、实中夹虚的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的复杂情况。
2 针对寒热错杂的治则治法——健脾温肾,清热化湿
脾肾阳虚兼湿热是慢性腹泻的病理基础,故临证时应健脾温肾、清热化湿。健脾温脾常用干姜、桂枝、高良姜、白术等;温肾阳多用补骨脂、吴茱萸、肉豆蔻等;化湿止泻多用扁豆、薏苡仁、山药等;清热化湿多用黄芩、黄连、葛根、苍术等。马淑然教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治疗寒热错杂型腹泻的基本方:党参10 g,茯苓10 g,白术10 g,补骨脂10 g,吴茱萸5 g,砂仁10 g(后下),扁豆30 g,山药30 g,薏苡仁30 g,黄连10 g,黄芩10 g,葛根30 g,桔梗10 g,陈皮10 g。该方为参苓白术散、葛根芩连汤、四神丸加减。方中党参、白术、山药补脾肾之气;桔梗、茯苓、扁豆、陈皮、薏苡仁、砂仁健脾理气化湿;补骨脂、吴茱萸温肾;黄连、黄芩、葛根清热。偏脾阳虚者加理中汤,偏肾阳虚者加四神丸,兼肝郁者加痛泻要方,兼气滞者加木香、槟榔,泻下无度者加煅牡蛎、石榴皮。
清·程国彭认为,引起泄泻的病理因素主要有脾虚、肾虚、湿热、寒湿以及饮食积滞等,宜分而治之(《医学心悟·泄泻》)。现代医家治疗慢性腹泻多从单一病理因素入手,治疗效果欠佳。慢性腹泻病机复杂,在疾病演变过程中,往往出现寒热错杂病机,因此,分清寒热虚实轻重缓急,攻补兼施,寒温并用,才能药到病除。
3 临证注意
3.1 健脾祛湿清热法贯穿寒热错杂慢性腹泻治疗的始终 寒热错杂型慢性腹泻,虽然其根本原因归于脾肾阳虚兼湿热,温脾肾、祛湿清热为基本法则。但须知,脾阳虚和肾阳虚均是在脾气虚基础上发展而来,而脾气虚生湿,湿郁久化热,或湿热日久伤脾肾阳气是慢性腹泻的前提。因此,临床治疗寒热错杂型慢性腹泻皆是在参苓白术散和葛根芩连汤基础上加减用药,随着疾病动态变化,脾阳虚为主者加理中汤,肾阳虚为主者加四神丸等,如此来应对寒热错杂型慢性腹泻的全过程。可见,健脾祛湿清热应贯穿治疗过程始终。有研究表明参苓白术散有助于胃肠道黏膜修复,维持其屏障,起到止泻作用[2],葛根芩连汤加味治疗湿热型腹泻效果明显优于诺氟沙星[3]。
3.2 年老久泻应注意补肾阳 泄泻日久累及肾阳,正如《医方集解》[4]谓:“久泄皆由命门火衰,不能专责脾胃。”故在治疗病程较长者或老年人腹泻时,应注意使用温肾阳补肾气的药物,如肉豆蔻、吴茱萸、补骨脂、煅龙骨、煅牡蛎等,且适当加重用量。
3.3 不可过早使用收涩之药 久泻多表现为本虚标实证候,脾肾阳虚运水无力,水停为湿,湿蕴化热,湿热内停,此时不可过早使用收涩之药,特别是病人兼有泻而不爽或大便黏滞者,切不可用罂粟壳等收涩之品再事收涩。若过早使用收涩之药可将湿热留滞体内,造成“关门留寇”。
3.4 临证注意肠道气机升降问题 寒热错杂型腹泻由于存在湿热、肠道气机不畅,易导致泻而不爽或大便黏滞,而脾肾阳虚又容易导致泄泻无度。因此权衡风药、收涩药与通因通用药的比例和用药先后成为处方用药的难点。若肠中有湿热积滞,湿热阻滞气机,泻而不爽或大便黏滞,此时可加入木香、焦槟榔等“通因通用”药;当脾肾阳虚为主,泄泻无度时可以使用“逆流挽舟”的风药,如葛根、防风、羌活等,或收涩之品,如煅龙骨、石榴皮等。若既有泻下清稀,又有臭秽不爽,则二者同用,视其轻重而调整用药剂量。
4 验案举隅
4.1 脾阳虚兼湿热证
刘某,男,34岁。2018年3月25日初诊。
腹泻半年余,时好时坏。经肠镜检查诊断为慢性结肠炎,其余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现大便日行4~5 次,溏黏不爽,稍进油腻或寒凉食物即泻,遇寒加重,食欲不振,偶发恶心干呕及胃痛,喜凉饮,口干苦。舌淡苔白微黄腻,脉沉细弱。自述早年常食冰棍冷饮。诊断:泄泻。辨证:脾阳虚兼湿热证。处方:
党参10 g,清半夏9 g,茯苓10 g,炒山药30 g,炒白术10 g,焦槟榔10 g,炒薏苡仁30 g,炒白扁豆30 g,砂仁10 g(后下),桔梗10 g,黄芩10 g,黄连10 g,葛根30 g,高良姜10 g,生甘草10 g,香附10 g,木香10 g,干姜6 g,补骨脂10 g,吴茱萸5 g。7剂。水煎,每日1剂,早晚分服。
4月2日二诊:服上方7剂后,胃胀痛减轻,腹泻次数减少,日3行,大便仍不成形,口苦减,舌苔薄白,脉细。上方将生甘草改为炙甘草10 g,黄连减至6 g。煎服法同前,共14剂。
4月16日三诊:服上方14剂后诸证大减,大便日2次,已成形,腹胀恶心消失,食欲增,舌苔薄白,脉细滑。嘱服参苓白术丸善后。电话随访3个月,未再复发。
按:患者正值年轻气盛,气血充盈,腹泻半年,自述早年嗜食冰棍冷饮,损伤脾胃,故食欲不振,遇冷加重,皆是脾虚伤阳的表现。脾虚清阳不升,水湿内盛,水谷夹杂而下,故发泄泻;湿停中焦,郁而化热,脾胃失和,胃气上逆,故恶心干呕;湿热停滞,不通则痛,则发胃痛;湿热停滞中焦,津液不能上承于口,故口干;浊气不降则口苦;大便黏滞不爽为湿热阻滞,肠道气机不通的表现;舌淡、苔白、微黄腻、脉沉细弱为脾阳虚兼湿热征象。故初诊在基本方基础上加理中汤加减,补气健脾温阳,除湿热,寒热兼顾。方中含理中汤温脾散寒,参苓白术散化裁健脾祛湿止泻,葛根芩连汤清湿热,加高良姜、吴茱萸加强温脾胃阳气的作用,木香、焦槟榔除肠中积滞、湿热气滞。其中葛根之用,既能升脾胃之阳,又能止泻。现代研究表明,葛根中所含的葛根素和大豆苷元具有止泻作用[5]。全方祛邪不伤正,扶正不碍邪,寒热平调,标本兼治。二诊时,腹泻次数减少,故将生甘草改为炙甘草以加强健脾益气之功,口苦减,湿热仍在,故黄连减量。三诊后患者阳虚和热证已愈,仅余脾气虚兼湿证,故用参苓白术丸健脾善后。
4.2 脾肾阳虚兼湿热证
赵某,女,40岁。2017年9月20日初诊。
五更泻18 年。医院检查肠镜未见明显异常。现每日大便3~4 次,泻前腹痛,大便粘马桶,不成形,或夹杂不消化食物,平素畏寒,四肢不温,自诉腹泻与情绪相关,自觉经常口干,少腹发凉,月经量少,有血块,舌质淡、苔白腻微黄,右脉数、尺脉弱,左脉沉细弱。诊断:泄泻。辨证:脾肾阳虚兼湿热证。处方:
党参10 g,炒白术10 g,生薏苡仁30 g,诃子肉10 g,炒白扁豆30 g,砂仁10 g(后下),桔梗10 g,炒山药10 g,陈皮10 g,防风10 g,生甘草10 g,黄芩10 g,黄连10 g,茯苓10 g,葛根30 g,炒白芍30 g,煅牡蛎30 g(先煎),盐补骨脂10 g,制吴茱萸5 g,煨肉豆蔻10 g,醋五味子10 g。7剂。日1剂,水煎,早晚饭后分服。
9月27日二诊:药后腹泻好转,自诉每日腹泻次数减少,饭后易泻,右脉沉细弱,左脉寸弱关尺细滑,舌质淡黯,边齿痕,苔白黄腻。上方将生甘草改为炙甘草10 g,炒白术加量至20 g,肉豆蔻加至15 g。14剂,日1剂,水煎,早晚饭后分服。
10月11日三诊:服上方14剂后效果明显,腹泻次数明显减少,晨起腹泻次数减少,自觉手足转温。上方再进7剂,后嘱饮食清淡多食青菜热粥养胃,忌辛辣寒凉。大便已正常,无腹部不适,服用参苓白术丸和四神丸巩固。随访半年,未再复发。
按:本例患者证属脾肾阳虚兼湿热。患者五更泻18年,脾肾阳虚必见,其平素畏寒、四肢不温、舌质淡、右脉尺弱为明证。然其大便粘马桶、口干、舌苔白腻微黄、右脉数为兼湿热气滞、津液不上承之象。泻前腹痛,腹泻跟情绪相关,则为脾虚木乘之象。综合舌脉,四诊合参诊为脾肾阳虚兼湿热证,又累及肝乘脾之象。故在温补脾肾阳气、祛湿清热中加疏肝之品。在经验方基础上加痛泻要方和四神丸加减。其中,参苓白术散健脾祛湿,四神丸温肾,痛泻要方调和肝脾,葛根芩连汤清热除湿。二诊时腹泻次数减少,将生甘草改为炙甘草,炒白术、肉豆蔻加量以增强温脾胃益气之功。袁子民等[6]研究发现,炮制后的肉豆蔻止泻与抗炎作用明显增强。三诊时大便次数基本恢复正常,嘱服中成药善后及饮食调养,以恢复脾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