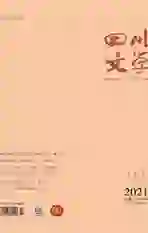读贾札记十四则
2021-03-25杨辉
杨辉
一、粗算起来,我读贾平凹,少说也有二十余年,潜心研读,也已越十年矣。此番培浩兄邀约,原以为早有“成竹”在胸,可以随意挥洒。孰料交稿之期日近,虽辗转思索多时,仍未得一妥当题目。这一日偶翻浦起龙《读杜心解》,见他有言:“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合乎百氏之言十三,离乎百氏之言十七。合乎合,不合乎不合,有数存焉于其间。吾还杜以诗,吾还杜之诗以心,吾敢谓信心之非师心与,第悬吾解焉,请自今与天下万世之心乎杜者洁齐相见。命曰《读杜心解》,别为发凡以系之。”这差不多是在说杜诗的“读法”。读法有次第,有进路,以心证之,为其要义所在。我读贾平凹作品,初时仅关注人物、故事的展开,及至因缘际会,要做些研究文章,便着意于在思想史、文学和文化史的视野中,去做作品意义的探讨。对贾平凹研究史略作考察,可知此类文章所在多有,已远较贾平凹作品为多。后个人年齿渐长,有些个人的不得已处,便常想如贾平凹处此境况,当作何论。有此想法,再去读贾,心境既已不同,所见自然也异。贾平凹创作已有四十余年,作品已逾千万字,但无论小说、散文、诗歌,还是书法、绘画,皆是在处理“我”与“物”之关系。夫人生于天地之间,死生、荣辱、得失、进退,莫之能御,亦无从逃遁。如贾平凹般出众人物如此,庸碌如我辈,亦复如是。本乎此,以我心读贾,虽有些六经注我的意思,但用意仍在于别出一路,以开读贾之新面目。是为这一略显生僻题目的来由。
二、自其四十余年创作的整体观之,贾平凹的写作,凡有三变。一变在1970-1980年代之交。其此前的创作,多受其时观念、文风的影响,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作品所敞开之世界也略显简单,乃彼时潮流之所趋,无须多论。此一变,乃是重新返归作为审美之“文学”一路,与其时文坛整体之变革,亦可谓互为表里。一变在1993年。此前虽在1982年《“卧虎”说》中,申明其有心以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方法,表现当代中国人的情绪,嗣后亦有《古堡》等作的尝试,《浮躁》中亦不乏于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新境界的展开,但迟至《废都》写就,方可论其“中年变法”。《废都》核心所述,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知识人之精神和生活情状,但其境界与笔法,得自《金瓶梅》《红楼梦》处颇多。庄之蝶之恍兮惚兮,有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慨,约略近乎贾宝玉之精神顿悟。李敬泽对此有极为深入之阐发,此不赘述。不宁唯是,此书所敞开之世纪末的西京城,绝类《红楼梦》之世界。此境如何得之?仍可以李敬泽《〈红楼梦〉影响纵横谈》做参照,或再读些余国藩论《红楼》文,其意庶几可得。《废都》虽有意于古典,也做了现代转换的尝试,启发后学之处不止一二。但真正标志贾平凹于古典思想及审美传统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进而慧心妙悟且发之于个人创作实践的,却在《古炉》之创生。此后《老生》《山本》沿此道路有不同程度之推进。贾平凹写作之三变亦渐次阶段性完成。是否会再有一变,殊难预料,但依此三变,可为解读其作之整体进路。若论古典传统之现代转换,贾平凹之尝试不可忽视。其意义亦不限于当代文学七十余年,可上溯至“五四”,自“现代性”以降之语境中作整体探讨,于思想史、文学和文化史之革故鼎新处论之,为基本进路。非此,则所论虽多,难免褊狭,且易陈陈相因,难有进境,不可不察。
三、前述三变,仅为初论,可再作细致阐发,尤以古典传统现代转换之经验最为紧要。《废都》之前,《浮躁》《古堡》及《商州初录》诸作,古典意象已所在多有。汪曾祺欣赏贾平凹,原因或也在此处。但贾平凹于古典传统之悉心实践且渐入堂奥,却应以《废都》为重要节点。《废都》之尝试,亦不仅止于文章作法,其间人物之观念,已颇多古人意趣。且看庄之蝶与数位女性之情与性的纠缠,如是《红楼》,取法或亦在《金瓶梅》。庄之蝶应世之无能和无力,他在无可如何之境的若干了悟,约略也有些来头,不全是现代人的思虑。兼以文白夹杂,气韵生动之文法从容写来,古典气息自然氤氲其间,不胜枚举,触目皆是。于古典传统之赓续论,《废都》虽好,却未“尽善”,至《古炉》乃有新境界的开拓。《古炉》所述之特殊阶段之史事,被纳入“四时”叙述作整体考量,其间人物亦历兴废成败,荣辱进退之境,不一而足,端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也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如是荣辱、进退、成败、离合、悲欢所在多有,堪称繁复,然无论人事物事,皆可納入四时之中统一视之。会此,则可知贾平凹之观念与古典思想之关联,亦可得读解该作之法。依此思维,可再读《老生》,读《山本》,历史人事之起落、成败,都付“闲话”,似为“笑谈”,但有根底,有来由,为古典史观阅世经验之一种。浪花淘尽,人事褪去,唯余一声长叹。此境近乎《三国演义》卷首杨慎一阙《临江仙》所示,乃古典观念现代转换路径之一,无论得失,皆可作细致发挥。此为读贾进路之一。
四、如以为读贾当以古典传统当代赓续之经验种种为唯一路径,不二法门,实大谬不然!如前所述,贾平凹的写作,起步于1970年代初中期,与彼时文学潮流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作品,得柳青及陕西现实主义传统影响处甚多。1980年代转型之后,此一传统之影响仍在,《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小月前本》《浮躁》等等,皆有极为浓重之现实关切。如“浮躁”“妊娠”“废都”等,也着意于以某一意象所示之精神,总括一时代之精神状态,并作细致之文本演绎。故此讨论贾平凹与古典传统之关系,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在当下,乃是以古喻今,非为以今证古。虽用心于古典,也未必就要做个白衣胜雪、羽扇纶巾的“古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照此理解,可知贾平凹作品,扎实细密之现实书写为其基础,其于“实境”之上常有意于“虚境”的开拓,实为返本开新之举,乃《红楼》所持存之古典审美表达方式使然,不可胶柱鼓瑟,做抱残守缺解。考察1970年代初迄今贾平凹作品与四十余年中国社会世态人情、世道人心之变,亦是一路,其义自具。即便论贾平凹作品与古典传统之关系,此亦为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维。故此,“虚”“实”相生,“古”“今”融通,为又一读贾路径,与前述路径并无高下、先后、优劣之别,亦无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式单向度选择之弊,如能统合融汇,相互印证,互相发明,则更为妥当。
五、自世界文学之整体视域观之,可知不仅“古”“今”融通,“中”“外”汇聚,亦属贾平凹作品进路之一,可稍做阐发。若无川端康成融通本土传统与域外经验之适时启发,或如《“卧虎”说》所言之赓续传统之独特了悟,推后数年也未可知。当然,走精神和审美返归的路径,观念资源也不局限于川端康成、马尔克斯诸人。在贾平凹,与孙犁、汪曾祺,甚至沈从文的启发皆不无关系。照此思索,可做大文章,此不赘述。此后《废都》之不设章节,漫笔而来,如水而逝,得自苏东坡自然成文说之启发甚多,此亦不赘述,但或也有乔伊斯等人意识流观念及笔法的影响。《废都》仅作初探,至《秦腔》,此种“仿日子”结构得到了可谓淋漓尽致的发挥。《秦腔》之难读难解,此亦为原因之一。此书如何去写,如是笔法根源何处,皆可再作深入论述,亦属一大文章之论题也。二者间之关联,贾平凹于古今中外笔法的融通与再造,此间大有文章可做。晚近数年,贾平凹反复论及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甚至在写作《山本》时,将这九字写成条幅,悬于书房,以时时自省。就中用意,并非不言自明。贾平凹被视作最具古典意识的现代文人,缘何反复申论现代性,他如何理解现代性之意蕴?这一问题,如强以理论观念读解,仍属胶柱鼓瑟,失之简单。贾平凹所言之现代性,亦被其换作人类意识。也就是说,一时期人类整体思考之精神要义何在,此即现代性、现代意识,抑或人类意识之谓也。故此,如何扎根本土经验,开出朝向更为复杂之总体经验之境,融贯古今、会通中西,便是读贾重要路径之一。
六、去岁李敬泽有文章论作家批评家之“文学故土”,以为有此意识,也调适得当,作品或可开阔大境界。既有意奠基于“精微”,也便可得致“广大”之境,“广大”与“精微”,也不可强为二分,乃一体两面。沈从文、萧红、汪曾祺,甚至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等与其具体生活世界之内在关系,皆可作如是解。贾平凹之“血地”为商州。此处属“秦头楚尾”,故贾平凹自谓因此血地所蕴之复杂能量,其既可赓续明清世情小说传统,做如《废都》《秦腔》般细腻文章;亦可效法两汉史家笔法,做如《带灯》等粗犷文字。前者为阴为柔;后者属阳属刚。照此思維读解其作,可以类如儒家所谓之内外感通之路径说明。即以“我”为基础,向内为“内圣”,向外为“外王”,即自我精神之修成与其所生长之地域特点、独特之风土人情、时代风气等皆有关系。如能沿此思路贯通之,不独可以与时与世推移,亦可深得因革损益之妙处。内外感通、物我一贯,天地万物也别开生面。可以此读解贾平凹作品。
七、贾平凹以诗开启创作,亦曾尝试剧本写作,后专事小说、散文,于后两者,皆有新的开拓。其在1990年代初创办《美文》杂志,标举“大散文”,力主散文不拘抒情一路,有更为阔大之境界展开。举凡自然万物,天地万象,皆可纳入其间。且看他如何读解归有光。归氏以抒情散文(此说亦为现代“建构”)《项脊轩志》等知名,殊不知其《全集》所载,抒情散文不足十一。谈天地,观万物,明人事等等十九。此足以说明由“抒情散文”至中国古典之杂文学观之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写《读稿人语》,写《江浙日记》,皆有些宗法古人笔记的意思,可与《东坡志林》对读。且看他《读稿人语》首则:
读老作家文章如进寺遇长老,想近前又不敢近前。不敢近前,怕他早看穿了我的肠肠兜兜,不近前又不知那是一双什么佛眼,如何看我几多忙人?
读《五十心境》,说尽了不惑,到底还惑。想起一友人游杭州归来,极力夸赞某一公园门口的对联怎么怎么地好,问对联内容,说:“上联是□□□□□□□,下联是□□□□□□春。”只记得最后一个字。
王中朝淡,《雾村》懒,一个是老僧吃茶,吃茶是禅,一个是黑中求白,乖人说憨。周涛善冰山崩塌,与之可论天下英雄,何立伟独坐听香,你只能意会他却能言传。同是女人写女事,《我与董小宛》人为狐变,《小黑》狐为人变,《我开餐馆》华而不实,却有独立之姿。
此间古今融汇、文白夹杂、诗文互现,非为游戏笔墨,要在多种尝试。要去写小说了,这些个古意古语逐渐褪去,化入作品之中,几如羚羊挂角,踪迹难觅。是为由生至熟,再进阶为自熟返生。此为书画家马河声论书语,照此亦可论贾平凹之文学观。
八、不过数年前,王德威在陕西师大开讲“抒情传统”,以屈原始,以贾平凹终,其间所涉之理论及文学人物,皆可统摄入“抒情传统”一路作贯通解。再看他《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所论,可知“史诗”与“抒情”并不可简单二分,或偏于诗和史,或用心在个人情感之感发,其中足可融通之处不止一二。如贾平凹1990年代标举“诗人”与“现实主义”之分,后又论两汉史家笔法与明清世情小说传统,且将二者归入“刚健”与“柔婉”,“秦头”与“楚尾”,“水”与“火”之观念中理解,至《山本》则有以《水浒传》笔法写《红楼梦》故事之尝试,足见其融通“水”“火”,“刚健”与“柔婉”之深层用心。此一路向,《带灯》是也,《山本》是也,新作《酱豆》亦是也。此亦为读贾路径之一。如细加阐发,可以“抒情传统”观之,可以“史传传统”观之,更可以“抒情传统”与“史传传统”融通之视域观之。小叩小鸣,大叩大鸣,良有以也。
九、贾平凹晚近二十年间作品中之典范人物,或偏儒,或近道,或有禅家意趣,不一而足。此或属有意为之,在写沧桑世变中各色人物之文化应对。如是作法,以《山本》最具代表性。其间有精进人物,如井宗秀、陆菊人、井宗丞、夜线子、周一山,甚至那个反复无定的阮天保亦在此列;亦有任性逍遥,却也做些个用世的事情,如陈先生、麻县长;还有那个130庙和宽展师傅,则是佛家代表无疑。上述三类,亦是古典观念核心之三种。贾平凹用意或不在阐发不同思想于世变中之不同反应,而在写个人身在人间世,面临世相种种,如何选择,如何合理应对。当然,何为合理,自是言人人殊,不可一概而论。读者读此,心之不同,所见自然也异。其大用心处,也是纬度多端。但照此思路,可梳理贾平凹作品中人物,得其自具之结构谱系,向内可以深入理解贾平凹人物塑造之用心用力处,向外则可知当代文学人物之不同面向及其意义。此亦属读贾路径之一。
十、贾平凹书中所写人物,虽属小说家言,不可照实看去,但若干重要形象,大抵也有些来历。《山本》中之井宗丞、井宗秀、陆菊人等等虽与历史人物关联甚深,皆有本事可循,且不去说他,单论陈先生。陈先生早年从军,后拜师道门,学得些救人的方法,其命运转折,约略与庄书所论无用以得全生之说相通。他在涡镇,虽用草药医病,但仰观俯察,于世态人情、世道人心看得更为通透,所以他也说病,说天地,说万物,说历史,说现实,说兴废,说生灭,说世道家道人道,如是《古炉》中那个善人。沿此思路推衍开去,亦可得读贾之又一路径,不独可用之于《山本》。《古炉》《老生》《秦腔》,甚至《带灯》《暂坐》《酱豆》,亦是一理。
十一、读1990年代后贾平凹作品,人常惑于何以往昔清纯之世界渐次退去,繁复芜杂甚或污浊之人事物事几乎随处可见。如屎溺如其他种种分泌物之略显细致之描画教人不适甚至于厌恶了。人世间之日常生活种种最为普通也最为真实之面相本是如此,贾平凹不过照实写去,不做些去粗取精的工夫,此为一解。郜元宝以为《白鹿原》中污秽之物形成之原因,与道教若干观念颇有些相类,并援引鲁迅致许寿裳语“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说明之,亦是一解。照此思索,亦可得读贾之又一路径。
十二、贾平凹好写也善写物,散文自不必论,小说中所描绘之物象亦堪称繁复,晚近十余年间,以繁复庞杂之自然物色“入”小说,属其作品重要特征之一。且看《暂坐》中对海若为活佛准备之禅堂绘画之细致描述,对那个神秘的作家兼书画家弈光书房物事的详细铺陈。此细致笔墨非为炫技,亦不可作闲笔轻易放过。其间用心,或可呈现贾平凹文学、文化及世界观念之紧要处。其与“现代”观念“不合”处,或恰为其价值和意义所在。何出此言?《周易》“复卦”曰:“复,见天地之心”。天地有大德曰生。此“生”或属某一事物之“永劫回归”,属已逝之物的再临。马克思所论之历史的“相似性”,柄谷行人所言之“历史”的“反复”,大用心即在此处。再如写陆菊人娘家纸坊沟云舒云卷,写云寺梁山川地貌、飞禽走兽、花鸟虫鱼,写人与诸般物象和谐共处之自然状态。还有那个似乎一事无成的麻县长,端坐于公堂之上形同虚设,对衙门外世事风起云涌全无半分能力,卻发愿要写一部《秦岭植物志》,写一部《秦岭动物志》,为后世留下一份当世的记录。所处之历史境遇相当,其缘何未如《白鹿原》中朱先生,用心于史志,寄托于后世。此间亦大有文章可做。历史人事化烟化灰之后,唯物事更为长久,青山老过青史,物事老过人事。此间所蕴含之历史人事之浩叹,亦非《三国演义》书前杨慎一阙《临江仙》所能涵盖,也非倪云林历史、人事观察之“小”(拘)“大”(达)之辨所能简单说明。延此可申论贾平凹之自然观念。此观念不限于世界观念,亦可落实于审美方式章法布局,其源头在《周易》,显发在《史记》在田锡在苏东坡在赓续苏门文章学观念之诸公,流变在沈从文、汪曾祺,再变在贾平凹。此亦属读贾重要路径之一。
十三、贾平凹的文学语言,有韵味,有意趣,有张力和表现力,有独特规矩,自家法度。与两汉史家笔法对应,则有骨气和质感,如树如石如山,具刚健气象;对应明清世情小说传统,则有韵味和气息,如花如风如云如水,得柔婉之趣。贾平凹自谓其早年于语言之韵味及表现力用心颇多,用力也深,曾于五线谱上调适体味文字之节奏、气息、韵律等等,后又悟得文风与世风与地域风土与个人之心性和才情统一之意义。他用心于炼字,遣词造句章法布局上皆有些心思,却不愿沦为“小道”,有贾岛气或孟郊气。并非贾岛、孟郊不好,而是以此推敲工夫,写诗或散文可以,用来做长篇小说,则难矣哉!故此,自刘熙载论庄子文中,贾平凹悟得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子里却尽有分数。汪洋恣肆、随意挥洒,却无不“合道”。彼固自谓猖狂妄行以蹈乎大方,学者当自大方处求之。会心于此,贾平凹《废都》而后的语言,便有意漫笔写去如流水之逝,苍茫而来,浑然而去,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如是而已。此虽偏于章法布局,却也是语言妙处。且看他在《好的文学语言》中谈搭配,谈闲话(闲笔),谈简省,谈成语原初语义之“还原”,谈学习古典及民间传统,谈如何追求语意之混沌。他还曾谈文章中虚词与实词之搭配一如阴阳、刚柔之相济之于语言运用之意义。照此可梳理其在语言上所作之复杂功夫,以及由此功夫所彰显之语言之个人特点。或可言之,贾平凹四十余年所以写作源源不断,且呈生生不息之象,才华与积累自然是核心,语言之才能亦不可忽视。试看《暂坐》,定然是挥洒自如,一气写来,韵味贯通,无间断,无枯涩,无窒碍,如水遇山石曲折能随物赋形,如云自然出岫变化无端。再看《山本》《古炉》《秦腔》,皆五十万字上下,主体故事算不得繁复,然而读者去读,却深感人世之庞杂,物象之细密。如人目力所及,山川地貌人事等等可以素描勾勒,亦可工笔详绘。要详细绘去,则即便一种景观,例如远观涡镇种种,人、事、物简略描绘,是一种笔墨,一种情状,而细腻、繁复写去,万千语言或亦不能尽述。一册《山本》,大略言之,天地自然诸般物象描绘十之二三,历史人事之叙述十之七八。而就局部论,亦有人事描绘十之一二,物象叙述十之七八。此间正是考校作者语言之韵味之表现力的重要时刻,若无如云出岫、随意挥洒之语言能力,怕也不能做成如《古炉》如《山本》般文章。以语言之节奏之韵味之气息等等为法门,亦可得读贾之重要进路。
十四、或问:贾平凹写作已逾四十年,在不同时期,皆有重要作品之创生,且呈不断“上出”之象,此境如何得之?对此,笔者思考经年,以下试简论之。如以《废都》为界,既可上溯,亦可下延,为读解贾平凹作品之要津。但若以其新作《暂坐》《酱豆》为“起点”,以追根溯源的方式整体理解贾平凹作品,不难知晓,其融合古今、中西,会通文学与书画艺术等等努力意义皆有可观处。这一种融通,绝非于种种不同观念及写作路向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晚出作品,融通其之前作品,而有新境界的开拓。此种思维如论者谈苏东坡时所言,乃是一种圆融通观,此通观意义并不单一。既包括思想观念之多元融通,亦包含文章作法之汇通,要义更在自我之“圆成”。无论有意与否,贾平凹的写作路径,其所敞开之世界与个人之关系,可以儒家所论之修养功夫解。修养既为功夫,当然有次第,有进路,有境界。照此思路,可得读贾根本。参之以古典思想,如二程如朱熹如王阳明,此间义理,或可窥知一二。
责任编辑 崔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