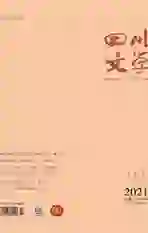在医院
2021-03-25李存刚
李存刚
2005年那年,我从门诊部调到住院部工作刚满六个年头,但我做医生已经十年了。在这个偏僻的县城,这份工作还是可以的,有不错的收入,还能够救死扶伤。这话听起来有些冠冕堂皇,但能为一些人解除伤痛,总是令人心安的。可就在这一年,我突然有了离开医院,即医生岗位的念头。也不知是什么时间冒出来的,它像一根铁钉,深扎在我的意识和念想里。
是一则来自宣传部门的消息。消息是小道的、非正式的,但确定无疑。因为它来自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的朋友,由于位置和个人秉性等原因,他总是能够提前获取一些我无从知道的信息。朋友说,我的文学创作成绩引起了有关部门有关人士的注意,准备把我调过去。
我很诧异。这消息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个人穿着白大褂,一边为人疗治伤病,一边从事着写作的“勾当”,无论怎么说,也有些不务正业的嫌疑,更不要说写作这事在当下年代里,人所共知的尴尬性质。因此,一直以来,我只是一个人埋头默默地写,从来不敢声张,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得足够私密足够低调,足够小心谨慎,却没想到还是被人知道了。
那一瞬间,我承认我是真的动了心,而且是那种突然间豁然开朗的动心,仿佛茫茫无际的迷途之中瞥见头顶依稀闪现的天光。但我又觉得犹豫。我不知道,如果真的离开了医院,到了另外的行业,我是否能够如愿获得自己想要的?如继续坚持我多年来羞于启齿的文学写作。
1999年,先生将我调到住院部工作的时候,医院还在北城街。现在的这里,即医院所在地,刚刚开始破土修建,医院后面的宿舍楼却是早先就建成了的,我在县城里没有单独的住所,因此迫不及待地成了最早的入住者之一,因此得以目睹医院办公楼一天天拔地而起,直到医院整个地从北城街搬迁过来,我不再每天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于宿舍楼和北城街之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像熟悉自己的五个手指一样熟悉走廊上的一切,包括走廊的天花板上悬挂的带箭头的“安全出口”指示牌、走廊两侧的墙上张贴的一些历代中医药大家的画像和他们的经典语录。
那些画像和语录,都出自先生的手笔。先生自幼学医,同时也习书法和绘画。我曾若干次听人说,如果先生不是一名医生,也一定是一位画家或者书法家。在我看来,这其实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无须任何假设,单凭走廊上的那些画像和书法,先生就完全配得上书法家和画家的称谓了。
但先生从不在意这些,打走廊匆匆而过的人们更不会在意这些。先生不只一次对我说过,写字和画画就是人的另外一张脸、另外一双手;没有它们,人是可以照样活着,但这样的活和那样的活,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在意的则是如何顺利地、尽可能快速地经过走廊,去到他们想去的地方。相对于路,路边的风景永远只是风景,它存在的意义全在于路,在于赶路的人是否存有稍事观瞻的心境。医院的走廊显然不在此列。
先门诊部后住院部,这与绝大多数医院、绝大部分医生同行的成长之路完全不同。但实实在在的,这就是我的经历。在我看来,这也是我的幸运之旅。
也许是注定的,但我更相信是先生有意为之:我所以能到这里工作(当年我们同时有八个相同专业的医学生毕业回到县里,先生独独挑中了我),就是因为医院门诊部工作极度紧张,急缺人手;到医院工作的最初几年里,我名义上是在门诊部工作,先生每天先住院部再门诊部,而我除了作息时间上没法跟上先生的节奏(先生总是每天不到六点就上班,中午两点以后才下班,晚上一直到干完当天的所有工作)。我的上班时间基本都跟着先生,是先生实质上的学生(尽管先生总不承认我是他的学生,我叫他老师,从没听他应承过),我实际上是门诊部和住院部的工作都涉猎了。涉猎便是经历和积累,便是营养和财富。如果真要说出原因,这也便是我在这里坚持下来,一直待到今天的动力和源泉。
我工作的病区一直在住院大楼的一层。起初,医院的基本构成也很简单:我工作的病区隶属的住院大楼、门诊部、门诊楼左侧的急诊楼、门诊樓右前方的康复楼。急诊楼和康复楼都是独立的大楼,建成使用的时间也晚,这可能就是它们独立出来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功能所属,尽管都和治疗有关,但前者是专事危急重症,后者则大多收治生命无恙的恢复期患者,差别显而易见。门诊部和住院大楼,从最初开始修建的时候起就是一个整体,若从平面上看来,俨然一个大写的“工”字:上一横是门诊部,下一横是我所在的住院大楼,两者之间连着的一竖,便是我日日经过的走廊。
说是住院大楼,却只有五层高。我曾有好几次爬到楼顶天台上去,看医院周围鳞次栉比的楼宇和县城四周围栏似的绿水青山,或者仰望高高在上的天际。有时候什么也不看,就站在那里,微闭着双眼,聆听耳旁呼呼的风声,烈烈夏日里浑身透着凉意,寒冬时节像是有无数把刀子刺向身体。
从医院外面进到住院大楼,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廊拐角的楼梯,二是走廊口正对着的电梯。我的办公室就在电梯背面的第一间屋子。从走廊进来,一抬眼就能看见办公室高高的玻璃窗户,看见玻璃门上写着的绿色大字:医生办公室。字体呈竖形排列,差不多占满了整个玻璃门框。为了让那些习惯了只看门牌的人看见,玻璃门框上方同时支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同样颜色和内容的五个大字。但凡视力正常的人,一抬眼即可看清。
住院部和门诊部之间,有一道双扇对开的玻璃门。门外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栽了两排楠木,树下砌了花台,种了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草。院子属于住院部楼前花园的一个部分。楠木树枝上一年四季挂满了碧绿的叶片,树下的阴影因此显得宽大而且幽深。阳光炽热的夏日从树下的小路上走过,丝丝凉意从阴影里横溢过来,让人禁不住抬起头来,仰望楠木树高大茂盛的枝干;双眼也会冷不丁撞上枝叶间投射下来的太阳光线,眼前顿时一片漆黑,世界瞬间旋转成了一整片巨大的阴影。树下的花台差不多齐膝高,天气晴好的日子,好多病人拄着拐杖来到花园里,坐在花台上,享受楠木树制造的阴凉,呼吸花香。
玻璃门出口正对着的地方,以前是一块缺口。缺口的玻璃窗外,便是住院大楼与门诊部之间的后花园,同样栽种了楠木树和更多的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有一天,一位新到医院工作不久的同事发现花园里有一株兰草,开了粉白靓丽的花,在门诊办公室很兴奋地说给先生听。年轻同事刚到医院工作不久,他自然不知道,那株兰花是医院搬迁过来时先生亲手种下的,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开花。年轻同事是无意间和先生说起的,却不知被那时候正在门诊就诊的哪个爱兰之人听到了。等下午下了班,年轻同事和先生相约去后花园,那株兰花早已不翼而飞。花台里,裸露着一块不大不小的新鲜泥坑,仿佛一只小小的空洞的眼眶。
后来,缺口沿着走廊的一面装上了木制墙壁,被隔成了一间小屋。朝向走廊开着的门和墙壁都是木质的,涂上了朱红色的油漆,透着浓浓的古典气息。木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不知道的人打走廊经过,根本不会注意到,那是医院新近投入使用的煎药室;木门打开,耳边便响起煎药机哔哔剥剥的响声,不大,但规律而整齐,使得空气里便弥漫着浓郁的中药香气。好多打走廊经过的人,会不由得停下步子,大约是想弄清楚香气来源于何处,少部分人则是紧捂口鼻,脚下的步子迈得似乎更快了。
站在“工”字那一竖的任何一个点上,都能清楚地看见走廊两侧靠墙摆放的淡蓝色塑料座椅,在廊道灯的映照下,泛着亮汪汪的光。座椅之间,左侧断开了两个缺口,开着两扇宽大的金属门,那是普通X光片摄片室。右侧也断开了两个缺口,靠里一个装着同样宽大的金属大门,那是CT检查室。金属大门都是由多层特殊材料制作而成的,表面是防火层,中心装着厚厚的铅板,既防火又防辐射。金属大门上下都装着滑轮,被固定在坚固的不锈钢轨道上,尽管厚重如墙,只需轻轻一推或一拉,即可打开或者关上。右侧的第二个缺口正对着左侧靠前的那道金属大门,拐过去,可直通到医院的楼前花园。那是走廊上的第二个出口。出口左侧是放射科的办公窗口,右侧靠墙也放了一排同样颜色的座椅。因为享有更多的光照,座椅上的油光要亮眼许多。
此外,只要稍稍抬一下眼,也能清楚地看到天花板上横挂着的警示牌。警示牌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面是一个黑色三角形,框内是三片呈放射状排列的黑色扇面,下面是一行黑色的粗体大字:当心电离辐射。警示牌其余部分被涂成了黄色,在明亮的灯光映照下,黑和黄,两种颜色同时呈现在视野中,沉甸甸的,直戳人眼。
白天,走廊上总是挤满了人。那些可以走动的患者或者家属,早早地把座椅坐得满满当当的,其余的人只能与轮椅、平板车站在一起。轮椅上、平板车上坐着或者躺着的,基本都是新近受伤的人,一些人嘴里不断发出嗯嗯啊啊的呻吟声,另一些人则紧闭着双唇,满脸阴郁。不时有人从座椅上站起身,隔着长长的队列,向办公室窗口探着头,大声询问还要等多久才能拿到检查结果,再转过身去时,刚刚空出的座位早已被人占去,有时候刚直起身,便赶巧听到办公窗口里唤自己或者家属的名字,焦急难耐的脸上马上露出一丝欣喜之色。
医院里的工作不分昼夜。不同点仅仅在于,成倍减少的病人和穿白大褂的数量。黄昏来临,门诊部的工作都差不多进入尾声,尤其是骨伤门诊,那些远远近近赶来就医的患者,大多已经回到了他们来的地方,少部分成了住院大楼里的临时房客。走廊空了,放射科医生办公窗口外空了,淡蓝色的座椅上空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在打走廊经过时,才有机会一眼瞥见办公室里的医生,他们坐着或者站着,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明晃晃的电脑屏幕和读片灯上。那是他们在回顾总结一天的工作。电脑屏幕和读片灯上正显示的,是当天早些时候拍摄自某个疑难病人的片子。
大牛和我同一年进到医院工作。一天晚间,放射科只有大牛一个医生值班,同时来拍片的有好几个病人,其中一个男子刚一来,就把申请单塞给大牛,要大牛赶紧给他拍片。大牛要他排队,男子不作声,直接插到队列的最前面,但大牛早已把一切看着眼里记在心里,按照顺序,直接叫先到的病人进了摄片室。等大牛又一次推开厚重如墙的防护门,从摄片室的门缝里探出头,准备叫第三个病人进去拍片的时候,男子便再也忍不住了,而他表达忍无可忍的方式,就是在大牛刚刚叫出第三个病人的名字时,身体腾空,飞起一条腿,狠狠地踹向了大牛探在摄片室门外的头。
因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大牛的头被飞踹过后,飞速地撞向摄片室厚重如墙的金属大门,又被弹回门框。咚咚两声闷响,大牛像一个突然泄气的皮球,歪歪扭扭地瘫倒在地。可男子似乎还觉得不过瘾,冲撞着想要再次冲上去,但同时来拍片检查的人们突起的惊叫声引来了医院保安,医院保安紧接着叫来了公安。
瞬间完成了由医生到病人的角色转换之后,大牛第一时间被送到急诊科,很快苏醒过来。看着周围紧张忙碌的同事,大牛眨巴着双眼,好半天才适应了这样的角色转换。他想说话,嘴刚张开就又闭上了——痛得快要爆炸的头让他没了力气。他挣扎着想要从床上坐起来,双肘刚刚将上身支起一点点,就又无可奈何地躺下去,因为右侧的肩膀怎么也使不上劲——他尚不知,他右侧的锁骨在倒地时摔骨折了。
同事们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好些人急匆匆地跑去病房看大牛,也想顺便看看那个竟然在医院动手打人的男子。同事们心里都带着怒气,一个个摩拳擦掌,如果不是男子已经被公安控制,说不定就对他拳脚相加了。
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大牛人高马大,说话却轻言细语的,脸上一天到晚堆著笑。有一回,我们几个老同事一起在外聚会,邻桌有几个黄头发青年嫌大牛喝酒猜拳的声音太大,借故冲过来找碴,我们起先都没注意到,等几个青年围拢到身边时,大牛突然腾起身,微笑着抓起身下的小凳,二话不说就拍向闹得最凶的那个黄头发青年。几个青年见状,像受惊的鸟雀般,纷纷四下里逃散开了。
我问大牛,为什么对那个男子毫无抵抗?大牛咧着嘴,笑着对我说:“你叫他换个地方试试?!”我听出了大牛话语间满满的不甘和无奈。有一点毫无疑问,如果真的换到别的地方让大牛遇上那个酒后滋事的男子,甚或大牛不是医生,结局定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外面的人进到医院,首先是门诊大厅,再就是依次排开的挂号收费处、导医台、出入院处、中西药房、医保结算处……门诊大厅还有两处楼梯和四个出入口。左侧的楼梯就在走廊口边,转身而上,就是医院行政办公区,往后可去住院大楼二楼。右侧的楼梯在靠近大门的角落,蜿蜒向后,上去就是医院心电、彩超室,再往后,同样可以去到住院大楼二楼。包括走廊口在内的四个出入口,分置于大厅的四个方向,随便从哪个出口又都是去往另一个地方的入口。
每天天一亮,门诊大厅里便排起了长龙。开始的时候,长龙还短而直,渐渐地,就蜿蜒扭结在一起。到处都是人影,到处都是说话声。我打大厅路过,冷不丁地听到人丛之中有人唤我的名字,扭过头去,却不清楚唤我的声音响自何方,唤我的人身在何处。
一天夜里,大厅里突然挤满了人。人们先是胡乱堆积在一起,随着一拨人垂着头从住院大楼三楼下来,沿着走廊,慢腾腾地步出大厅,没有谁指挥,人们便自发地一分为二,排成了两条相互对视的长龙。长龙一头沿着走廊,直通向住院大楼一楼的电梯口,另一头通向医院大门。
长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医院里年轻力壮的医护人员,他们都穿着日常的衣服,表情恶狠狠的,空空如也的双手紧握在一起,不断地揉搓着,有的则无声地垂在身体两侧,五指不断快速地张开又快速地握紧成拳头,仿佛随时准备挥击而出的拳手。另外一部分是大街上闻讯赶来的县城居民、三轮车夫和医院四周的商铺摊主。很多人的面孔似曾相识,有的似乎从来就没见过面。他们手里握着棍棒、钢筋、菜刀、小铁铲,相互认识的那些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几个早已禁不住破口大骂,诅咒这个世道一低再低的坏风气,诅咒某些人不可理喻的无耻和贪婪。呆立在人群中,跟着人群哗啦一下散开,又无声地让出一条道,我胆战心惊,无所适从,又心如刀割。
从住院大楼三楼走出来的,是一位老人的儿女和兄弟。一天多前,老人走路时不小心跌了一跤,摔断了大腿,送来医院时,只有老人的女儿一个人。对于老人而言,断腿只是其一,更要命的是老人罹患多年的肺心病。我问老人的女儿,她的哥哥或者弟弟呢,她说没有。我告诉她,因为严重的肺心病,老人家随时都有可能去世,所有的治疗可能都是徒劳,她说没事,反正都八十多岁了,来都来了,就在医院里住一下再弄回去。我建议她直接入住内科,以更好地治疗老人肺部和心脏的毛病,她说不,她送老人来就是医治断腿的。
一切都像是早就设计安排好了的。老人入住一楼的病房里,我紧接着就去到他的病房,再次更系统地检查老人的心、肺和腿,却发现,老人根本无法平躺在床,喉间呼啦呼啦的,像放大了若干倍的猫喘,断掉的那只腿肿,没断的那只腿也肿。我说骨折暂时没法治疗,必须转内科。病人在医院里,当然听医生的,老人的女儿说……从内科医生那里听到老人去世消息,老人的女儿第一时间掏出电话,步出了病房。一两个小时以后,老人的大儿子、二儿子和兄弟,便带着一拨人出现在医院。老人的女儿说过她没有哥哥和弟弟,现在,老人去世了,她的哥哥弟弟却突然从天而降了。
“送进医院的时候都还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医死了?”这是老人的两个儿子和兄弟发出的第一个疑问。
“既然你们都说是肺心病,为什么不直接收到内科治疗,要转来转去的?”这是老人的两个儿子和兄弟发出的第二个疑问。
一拨人最先出现在三楼内科医生办公室,随后又下到了一楼我的办公室,最后去了位于门诊大厅二楼的医院行政办公区,后来索性一分为二。一拨人由老人的两个儿子带领,盘踞在医院行政办公区,要医院领导给一个明确的说法。医院领导找到我,又找到為老人诊治的内科医生,很快就向老人的两个儿子和兄弟给出了说法,但自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另一拨人由老人的兄弟率领,一个个叼着烟,在内科办公室里横冲直撞,每进去一个医生,就有人迎上前去,指着医生的鼻梁,厉声质问:为什么把人医死了?旁边的人跟着帮腔:为什么医死了?进到办公室的医生,进去了便没能出来,因为没有任何机会和可能出来,因为老人的兄弟和几个家属把门严严实实地堵住了。
不知道老人的两个儿子是否从走廊上大厅里越聚越多越来越嘈杂的人群,觉出了事态出乎意料的发展变化,和可能出现且无法准确把控的严重后果。在医院行政办公区盘桓到深夜,却依然没见医院领导有一丝松口的迹象,他们开始动摇了,有人借上厕所之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医院行政办公区,最后,只剩下老人的大儿子、二儿子。两个人面面相觑,无声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也先后离开了医院行政办公区,撤退到了住院大楼三楼。到了住院大楼三楼他们才发现,从家乡一起来的人,连同他们的妹妹,都聚在一起。然后,他们便从三楼的病房里搬上老人的遗体,垂着头,经过人声鼎沸的走廊,经过门诊大厅,一步步离开医院。
我站在汹涌的人群里,看着担架上白色布帘包裹着的老人,听着人群里发出此起彼伏的咒骂声、混乱的脚步声、粗重的呼吸声、棍棒敲击地面的声音,被海潮般涌动的人群裹挟着,机械似的快速移动,只感觉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仿佛即刻就要飘飞起来。
那是医院有史以来发生的第一起医闹未遂事件。
我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听医院的领导和同事们这样说。言辞间,洋溢着大功告成的激越和豪迈。我理解同事们的激动心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医生乃至整个医疗行业,越来越多地成为各种媒体社会新闻版所关注的对象;医院,越来越多地被一些人当成了发泄桶、取款机、疗养院、祭祀场……只要人们觉得有必要,觉得它应该是什么,它就可以即刻变成人们想象的样子。
有人将患者定位为弱势群体,这个观点至今仍被很多人真理一样信奉,却不知,它武断地把患者和医生划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同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便真有强、弱之别,两者也都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有时候,两者之间会完全地互换成彼此。正常(也是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医生和患者互为一体,共同面对疾病——这个可能强大可能弱小的敌人。
这么些年里,我总是时不时想起2005年秋天的那个午后:得知有关部门要调我去的消息,我跑去门诊部找到先生。先生对我说:那也是一条路,但那条路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你要想好了……我明白先生是希望我留下来,但如果我真的决定离开,先生也不会阻拦。先生十多岁时便辍了学,跟着父辈学医;我到医院工作的时候,先生是医院的院长,但他就把自己当医生,每天早上六点上班,午后两点下班,晚上六点上班,九点以后下班;现在,先生已经退休,但在门诊工作的作息时间依然如故。时间日复一日,一秒接一秒,对于先生而言,这样的重复,便是面对一个又一个病人。我望着先生,我的决定已暗暗在心底里形成。
这么些年里,数目巨大到没法计数的病人来了又走了。他们当中极少数的人,若干时日之后的某个时刻,会猛然在医院里再次遇见,或者冷不丁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听他们叫我李医生的时候,我总是刹那间呆住。片刻过后,我就彻底原谅了自己。漫长的时光里,需要记取的人和事委实太多,而忘却似乎是一件更加容易的事情。
这么些年里,也有好些同事来了又离开了,有几个像大牛一样,是我很要好的一位朋友。他们离开之后,有的偶尔还会回来走走看看,更多的人一旦离去,便杳无音信。他们一旦回来,我照例会约上三五个要好的同事喝酒,海阔天空地闲聊。只是,每每在目送着他们起身离开时,心底里便会生出一种时光不再的无奈和失落。还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来,我依旧在医院,是一个医生。天天和这样那样的病人打交道。从他们各种各样的伤势、病情和呻吟声中,以及他们个人以及亲人的各种表现里,我通常能够觉得出人世间某一些隐秘而又宏阔的东西。作为医生,我愿意长此以往,更愿意尽己所能,把这一份职业做到精湛和问心无愧。
责任编辑 杨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