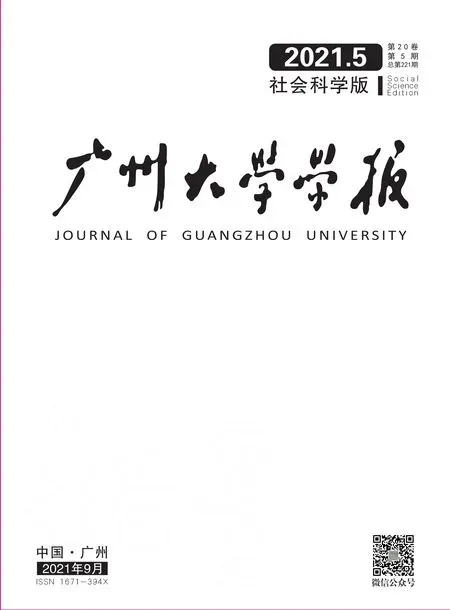城市参与式艺术的“在地实践”与“场域感知”
2021-03-25张意
张 意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今日,“在地性”或“现场性”(site-specificity)无疑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论题之一,此论题的聚焦、确立,与当代艺术在时代语境中做出的探索性回应相关联。千姿百态的艺术“现场”并非只与在时间中呈现的物质“现场”有关,还包括以事件、项目、表演等形式,在物质、行为、话语、数字等媒介领域展开的形形色色的情境。在《绵延不断的地点》中,权美媛精当地指出,当代艺术对“在地性”“现场性”的强调,使连绵不断的地点、空间不再是作品被动的容器或载体,而是一个个在具体情境中展开的“地方”,同时也是具有时间性的作品本身:“让每一个观看主体通过对亲临现场,对空间拓展和事件延续的感官即时性进行此时此刻、独来独往的体验,而不是靠脱离躯体的眼睛和视觉顿悟,即刻获取感知。”[1]
中国当代艺术最初是全球化时代的舶来品,其历史并不悠久、土壤也不丰厚,因而须得启用“在地性”钥匙,“自下而下”地打开其历史、记忆和现实。当艺术家与一个个“现场”相遇,试图去理解和感知一个个作为“地方”的情境时,他才能成为新型感知和意义的开启者,成为新的“场域”和“情境”的建筑师。
一、城市参与式艺术的在地实践:以实验性艺术个案为例
近年来,笔者观察或参与了一些艺术家在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实验性参与式艺术实践,他们的工作引发了笔者持续的思考。笔者所关注的成都,地处长江上游的西南内陆,不像一线城市那样具备丰富的当代艺术资源或艺术话语权,不能提供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中心视野,然而这正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当代艺术发展的现实处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地区当代艺术的转型与该区域的城市化运动有很多交集和重叠。成都这座生活闲逸散淡、历史上有名的移民城市,不断吸引着艺术家来居住或工作,至今,这里仍拥有一批活跃在国内或国际当代艺术领域的不同代际的艺术家,和这座城市中诸多艺术机构、大学、民间组织一道,在艰难但充满活力地探索当代艺术的生根、生成和美育养成之道。
实验性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家,正试图通过在地实践与城市生活建立新型关系,同时探索新的艺术语言和新型感知机制。譬如,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从2010年前后开始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其作品如《昆山在造》(2010—2012)、《梁山路径》(2012)、《顶楼之眼》(2014)以及延续至今的“水系计划”项目(2015—),持续关注当代都市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居间关系。“水系计划”项目起源于他们对2008年汶川地震的思考。经由成都到都江堰水域的长期在地调查后,他们注意到都江堰水利工程自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已成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水系景观。然而经过实地寻访,他们发现了都江堰周边水系中常被忽视的内容。例如,坐落在都江堰上游的苏联援建大坝(1958),曾因技术原因被炸毁,目前仅留废墟;始于2001年修建的紫坪铺水库,引进了现代水利技术和水文管理,但却持续地改变了岷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汶川震后羌族定居点重建工程中,存在现代技术对古老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对传统建筑智慧的忽视等问题。经过查询资料、访谈专家和沿岸居民,他们以作品《水系博物馆》(2015)作为对这段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的呈现。来自新津广滩村造船坊的一条闲置木船,被挪用来作为作品和现场的连接,沿岸居民受邀在废船木构建的“水系博物馆”上书写有关水的记忆,木船后来从陆路被运至都江堰玉垒公园展出。作为研究性参与式艺术项目,该作品关注与都江堰上下游的岷江水系有关的记忆、历史、权力话语,对“水系”进行了反复交错的叙述。艺术家强调,在他们关于山水的研究性探访中,由长期往返于山水现场和交流访谈建立起的身体感知,形成了他们关于水系的特殊“知识”,从而绕开被权威机构、科学话语抽象为数字或概念的现成知识,重建并开启富含地方空间潜能的感知知识。
在2018年“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中,策展人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余位艺术家的作品连缀成关于“全球都市”的叙事,从不同侧面回应城市与艺术、艺术与人、艺术与自然等主题。当观众来到展厅,一幅立面的屏幕播放着曹明浩的影像作品《东郊以东》,旁边是《一段河流的再注解之后》系列作品。观众最初会觉得相较其他展厅,这里缺少视觉冲击,整个空间显得比较素朴:
在整个空间的中心放置着一张“长满腿”的桌子,看上去旧旧的,参差不齐,桌上的玻璃罩中放着一本已经泛黄的歌谱。在桌子两边的墙壁上,一幅长达19.87米的黑白铅笔画整齐铺开,旁边还贴有两张艺术家走访时的照片。[2]
驻足观看墙上的长卷铅笔画,画面上那些吊脚楼、茶铺子、小吃店、说书人、买卖人,活生生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成都九眼桥一带的水码头场景。这是水井坊的前居民,也是清音艺术家龚素清凭记忆绘出的成都合江亭周边的街景。笔者低头发现展厅中央那个看似普通的桌子下,有许多颜色样式不同、形态各异的旧桌腿。艺术家说这一百根桌腿,有的是在地调查中居民送的,有的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通过这些有年代感的物件和白墙上艺术家在城市中寻访的照片,艺术家似乎在暗示他们对城市急剧变迁中那些飞逝的城市记忆的关切和寻找。他们在展厅内举办了八场主题工作坊,其中包括请新津广滩村的造船师傅程文忠为观众现场制作和讲解如何造船;请建筑师薛亮讨论传统建筑的智慧;请生态科学家张雪华博士分享南极科研中对生态和垃圾的思考。艺术家说,成都曾经河道密布,但随着城市发展和空间改造,一些河道消失,船只和造船技术也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他们希望通过作品和现场工作坊,邀请更多的人思考城市与水、城市与传统的关系,促使作品的生产与讨论成为一个流动的过程。[3]
曹明浩和陈建军说,2010年他们刚到成都不久,除了要深度、细致感知这座城市外,还需要探索新的艺术方法和语言。他们觉得应走出工作室,到生活现场去感受和学习。曹明浩认为,“学习”对他们很重要,从最初在成都城郊的昆山村金桥镇,到后来在大朗堰、都江堰、汶川和广州的城中村等,每一个富含信息的现场都带给他们很多冲击,原有的知识、理解方式,包括一般的媒体信息都很难解释这些现场,所以他们只能耐心地、长期地向当地人、不同学科的专家学习和咨询,学会去理解这些现场。(1)笔者跟两位艺术家有过多次访谈,这里采自访谈记录。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源于对时代问题的直觉和敏感,然而在美术馆的展场中,他们的视觉呈现是含蓄、留白的,因此他们更倾心于用工作坊的形式来呈现在不同现场获得的关于“地方”的感知,他们也更注重在工作坊的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中作品意义的生成和流动。2020年他们以作品《水系避难所》,参加了2020—2021年的上海双年展,继续讨论生态、栖居和人类纪等问题。
近年来在中国的城乡涌现出不少出色的参与式艺术项目,如北京皮村的新工人剧团、上海的定海桥互助社、广州的阳台聊聊、深圳的握手302、安徽的碧山计划、山西的许村计划、甘肃的石节子美术馆、贵州的羊蹬合作社等等。在成都,有一批青年艺术家,以“身体地理学”的方式,进入各种社会和生活场所,将“地方”转换为作品或项目呈现。这些作品或艺术项目不再以强烈的视觉呈现为目的,而是以长期性、研究性的方式浸润并生根于一个个“地方”或“现场”,以艺术之名参与到巨变中的中国当下生活,让不可见、不被听闻的被看见和被感知。
二、城市艺术机构的在地实践与“艺术驻地”
除了艺术家个体的参与式艺术实践,城市艺术机构也在悄然改变着与公众生活隔绝的姿态。有着新颖外观与复活功能的新型美术馆、博物馆,在国内城市中呈不断增长之势。新型美术馆受全球化和艺术“在地化”浪潮的影响,逐渐摆脱传统美术馆作为文化展示和知识呈现空间的文化观念,不再强调宏大叙事、文化权威感,而试图以关系为中心,成为担当公共美育功能的场所,建构邀请观众、启发现场体验的流动美术馆。[4]国内的美术馆、博物馆,在借鉴西方美术馆、博物馆体系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其空间需要生根于在地文化和历史中,需要变成一个文化发生场,即将一个物理空间激活为一个艺术的“现象”“思潮”“群体”“事件”发生的文化发生场,实现从物理到文化、从空间到场域的转换。[5]这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艺术的在地实践和场域感知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在成都,以当代艺术展为中心的这类场所影响最大的则是麓湖A4美术馆和成都当代影像馆。位于城南生态湖区的麓湖A4美术馆,自2008年成立以来,历经十多年耕耘,已成长为非一线城市中具有较强生长力与影响力的美术馆。2019年,笔者作为学术观察员,参与到麓湖A4美术馆的“国际艺术驻地项目”中。该项目与美术馆的“青年策展人计划”“istart儿童艺术节”一道,成为美术馆激活城市新区、推动公共美育、赋能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驻地项目的策划人蔡丽媛女士,已持续推动项目近十年,至2019年达到高峰,一年内有23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与驻地。笔者感兴趣的是在短暂的驻地期间(一至三个月不等),艺术家如何感知一个新的“地方”,如何将丰富的在地场域转译、投射到自己的作品中,如何通过驻地与在地城市发生关联。
当代艺术的驻地机制,源于战后全球化时代艺术中心(如纽约、伦敦、柏林)之外的城市艺术机构,通过吸引、招募来自异域的艺术家到具体的“地方”体验在地日常生活并将异质性的艺术创作带到在地,一定程度地刺激和影响了在地艺术文化生态。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并不长,需要长期多元、异质化的艺术生产,使之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中真正生根:一方面,需要深入“地方”进行在地性探索;另一面,需要与域外艺术家和艺术机构搭建长期交流、合作关系。而艺术驻地机制正是一种较灵活的方法,可以辅助艺术机构和艺术家探索在地实践和场域感知的可能路径。
2019年下半年,笔者所属的学术团队与驻地艺术家一道开展问卷初访、采访对谈、跟踪观察等相关活动,使驻地艺术家和在地学者、助理、学生在持续交流中获取更多的在地信息,生动体验在地人关心的问题,加深对“地方”的理解,这同驻地艺术家之前对在地城市的模糊认知有很多出入。可以说在交流、行走、访谈和观察的过程中,驻地艺术家与访谈者获得了彼此视域的融合。学术团队进一步引入与驻地艺术家工作方式相似或有交集的在地艺术家,有些在地艺术家还与驻地艺术家一道完成驻地创作。比如来自波兰的艺术家耶利克(Jarek Lustych),初到成都一周后在问卷中说:“我对远东的异国情调和浪漫主义有一种定型观念,在阅读了霍尔的《隐藏的维度》后,有所弥补和丰富。起初,我对中国人向我展示的那种轻巧的优势,感到有点恼火,我不习惯被当作孩子/野蛮人。我也知道这与我的不诚恳的期望有关。但是过了几天,我开始理解代表4000年文明的人们有这样做的权利。”在他和助理多次外出和交流后,他表现出对社区居民参与创作的兴趣。他和我们及在地艺术家有过几次对谈,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关注的问题,并提出三个作品方案:想与社区居民交换家中的小物件,然后教会大家为这些旧物件镀银,用这样的方式保存一段记忆;用在地的语言在城市的树上贴字;在不同的国家通过自制的录音设备采集河流的声音,并将其制作成影像作品。在驻地项目负责人蔡丽媛的协调下,常常关注文字的弦外之音并用多媒介方式讨论词与物之间关联的在地艺术家马锟,对耶利克的镀银和文字方案很感兴趣。此后两位艺术家不断讨论并联手居民共同完成了两件作品去参加了此后的年度展。在不断交流和协商的过程中,耶利克的驻地工作给美术馆、社区居民、在地艺术家、学者、学生和观展的观众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当然,驻地经历也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在艺术驻地项目中,类似的案例还不少。异质文化通过艺术驻地的在地实践,在相互协商、碰撞中获得沟通和再生长的契机,为艺术生产和城市空间吹送出新鲜空气。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艺术家、艺术机构、驻地城市和辐射的人群来说,艺术驻地是一件礼物,它带来多元和混杂的丰富性;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它通过行走、考察、体验、记录、策展、创作等,成为一种艺术空间的生产模式和日常工作方式。[6]关于艺术驻地的问题和机制还有很多可探讨之处,限于篇幅,本文仅聚焦于艺术驻地通过陌生化眼光,为在地场域祛蔽,以新的感知方式重启一个个熟视而无睹的“现场”。
三、当代艺术感知机制的变迁:从凝视到场域感知
在观察和描述了艺术家个体与城市艺术机构的在地实践个案后,本文试图转入对在地艺术实践的美学机制的分析。首先拟将参与式艺术的在地实践置于艺术机制的变迁中,考察这类艺术实践对参与性、在地性的强调与艺术感知机制变迁的内在关联。社会参与式艺术(Social engaged art, Social participatory art)或“在地艺术”(Site-Specific art),自20世纪50年代萌芽。20世纪60年代,欧美等国的城市公共空间出现了参与性公共艺术作品,艺术生产突破美术馆和画廊的“白盒子”,作品嵌入或参与到城市公共空间中,强调从作品的物理空间到文化、心理空间的多重生成,重新开启公众对历史事件和公共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战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和消费社会的壮大,促使艺术的社会转向(Social turn)发生,艺术参与公共空间,以事件、活动、过程、表演等方式呈现和展开。[7]在艺术的社会转向、跨领域联动与消费社会中,文化向日常生活沉降几乎同步发生,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社会生活的解域化和重组潮流的文化症候。20世纪90年代,兰茜(Suzzanne Lancy)提出基于社会参与的“新型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ic art),重新命名的新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区别于那些被安置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纪念性雕塑或装置,更注重建构社会关系,注重邀请公众在时间延异中参与的过程,并借用多媒介形式,以跨界、多元的形式与公众互动,促成在互动、协商或对抗状态中共同生成作品意义。[8]
新型公共艺术在创作、接受方面都极大地区别于传统艺术。在具体场所中不断发生的艺术事件,要求艺术家和观众在创作与接受环节都需要持续地在地感知、场域感知,这种美学趣味的转向或悄然的革命,与当代艺术从现代主义的“凝视”转向“场域感知”直接相关。“场域感知”作为新的观看方式,可溯源至极简主义艺术对“剧场性”的开启。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E.Krauss)认为,极简主义雕塑超越传统雕塑就在于其“场域性”,譬如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无题:L形横梁》、贾斯帕·约翰斯(Jasper Johns)的《无题》、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一吨支柱(纸牌屋)》以及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的《死》《黑盒子》等系列。[9]这些悍然立于公共空间中的体积巨大的物,拒绝在视觉上取悦观众,其意义生成有别于传统雕塑对再现、支架、构成等观念的依赖。如何理解这些物体呢?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曾敏锐地指出极简主义对物性的凸显,这些排斥寻常符号性、象征性意义的物,所要召唤的经验特质正是某种“剧场性”。弗雷德站在捍卫现代主义媒介的纯粹性视角,含讥带讽地批评极简主义(他称其为实在主义)对“物”和物性的关注,是受大众化的“剧场性”侵袭,因而受制于非艺术的、溢出于画框和雕塑基座的外部因素。[10]
其实,被弗雷德讥讽的“剧场性”,恰恰道出了新的艺术感知机制的实质。[11]如果说以往艺术的意义注重作品的内部要素,如色彩、光线、构图、媒介,那么极简主义艺术却要将这些相关性带到艺术外部,即极简主义作品的物性的在场,让作品意义除去源自艺术家的创作外,还依赖于一个置身于公共空间中观者的观看,依赖于具体的观看行为发生时的空间关系(如光线、地板、墙面、湿度、温度等)对观看的影响,依赖于观看主体的现场解码和身体感知。也就是说,极简主义召唤一个情境中的观众身体的参与,强调对难以一眼给予意义的奇异物及其物性的身体感知、在场体验,从而重构物性、媒介和观看的关系。
事实上,弗雷德所指出的“剧场性”,正是当代艺术“场域感知”转向的缘起。不过,新的感知机制是一种不追求戏剧性叙述、连贯情节的情境性感知,我们不妨更准确地称其为“后剧场性”。沉默不语、意识无法穿透的物,借助“后剧场性”的展示空间,打碎了观看主体习以为常的对象式感知体验,即静态“凝视”的观看机制,从而使观看者在游走中与沉默物遭遇、照面,物的实在性在观看的打量中忽隐忽现,观看行为使得不在场与在场在时间的延异中相互映照。时至今日,由“后剧场性”牵引出的观看方式,已沉淀为诸多艺术实践所共同呼唤、邀请的艺术参与方式,一种身体在场的“在地感知”方式。
克莱儿·毕莎普(Claire Bishop)在《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中,从艺术脉络和视觉观看的视角,富有启发性地梳理了当代参与式艺术与现代主义历史先锋派的关联,如与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的激进剧场化实验,与国际情境主义、视觉艺术研究会等的都市情境建构实践的关联和异同。[12]80-13420世纪60年代,居伊·德波(Guy Debord)及其同仁的艺术实验遭到众多质疑,其实践仅被视为当代参与式艺术的史前史,然而这些实践对被动观看和积极观看的讨论,对艺术与城市关系的参与,对此后的实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艺术家和观众的身体在场、参与式“在地”观看,一道成为当代艺术意义生成的核心要素。国际情境主义者与超现实主义者对艺术在情境性现场中偶发、相遇经验的强调,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激进批判姿态有关,这一立场从一开始就蕴藏在形形色色的情境展演中。
与之呼应的是相继发生的当代实验艺术,如美国黑山学院的艺术实验,音乐家约翰·凯奇(John Milton Cage)、编舞家默斯·坎宁汉(Merce Gunningham)、偶发艺术创始人艾伦·卡普罗(Allan Kaprow)的不断创新。20世纪60年代,“荒诞剧”“残酷戏剧”成为焦点,而新的大地艺术、环境艺术、波普艺术与之遥相呼应,新先锋派将造型艺术、舞蹈、电影、摄影、文学、设计等艺术门类形成跨媒介的艺术共同体,使传统的剧场艺术成为古董。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布莱希特式的戏剧观念受到跨门类艺术家的青睐,各种现场表演、展演日益挣脱情节、悬念、模仿等经典戏剧观的束缚,相继形成不同形式的后戏剧剧场。[13]54-55跨门类的现场展演呼唤新的“观看机制”,这种艺术机制追问对事件过程的呈现和感知。与好莱坞等娱乐工业制作的景观化、戏剧化叙事不同,后戏剧抵制暗藏悬念、连续性、有内部逻辑的叙述故事。“叙事的断片化、风格的异质性、高度的自然主义、怪诞和表现主义等”[13]18,是后戏剧剧场的典型特征。那些被传统剧场所过滤和筛除的日常生活瞬间进入舞台,观众成为作品的重要元素,直接与表演者发生身体接触。而当代艺术创作中益发凸显的展演性,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后戏剧剧场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欧美及亚、非、拉美涌现出不少社会参与式艺术项目或作品,新兴前卫艺术溢出传统美学和艺术史框架,日益强调“现场性”“在地性”,向批评话语提出挑战。回望艺术家创作的现场作品,无一不以独特方式打开现场空间——后戏剧剧场,将作品转变为事件,让未被预料、未经考虑、无法计划的偶然因素卷入到事件,观众刹那间的身体领会、情感体验也卷入到现场感知中,每一次作品展演都与具体形态、场所情状相关。因而,展演性的事件空间将日常生活经验与艺术展演涵纳在一起,使不同时间层面的观众经验被缝合到作品纹理中。
四、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审美”与“伦理”之维
就国内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而言,其目前仍处于当代艺术的实验和边缘位置。然而,无论是艺术家个体实践还是艺术机构的策展计划、驻地项目,都越发重视跨领域研究性实践、非现成状态的作品呈现等。我们在这些艺术实践中发现,艺术的在地实践常常出现艺术与社会、审美与伦理不断冲突、协商与混融的状态,这与强调审美与伦理拉开距离的自律艺术,与重视视觉呈现的媒介艺术都非常不同。那么,如何看待参与式艺术在艺术现场中的艺术与社会、审美和伦理的冲突?更进一步说,参与式艺术中的两个维度之间的张力、互渗与感知机制的变迁有怎样的内在关联?
对此,国外这几部较有影响力的批评著作,如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的《关系美学》(1998,法文版)、毕莎普的《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1998,英文版)以及格兰特·凯斯特(Grant H. Kester)的《对话创作:现代艺术中的社群与沟通》(2004,英文版),能给我们的思考提供不少借鉴。2004年,毕莎普撰文与《关系美学》的作者伯瑞奥德和主张“对话美学”的凯斯特商讨:参与式艺术的宗旨或要义究竟是建立协商关系还是对抗式歧感?究竟是伦理关系覆盖或颠覆审美关系,还是在艺术的社会关怀、参与事件中,蕴含着审美政治对可感性的重新分配(此处援引雅克·朗西埃的审美歧感论)?以上几本批评论著及其作者的论争,在国内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界受到较多关注,也在艺术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14-15]
伯瑞奥德在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都市中一系列新型参与式公共艺术作品时发现,原有的艺术概念和艺术史讨论不能应对新兴前卫艺术的生成。如果说,艺术作为一种不断变动的游戏,总会朝向自己的时代做出自己的回应,而新兴艺术在小众化、原子化的后现代社会,试图重启探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我等居间性关系的可能。受路易斯·阿尔都塞“相遇唯物主义”和茨维坦·托多洛夫对“共在经验”强调的影响,伯瑞奥德提出了“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的概念,来回应这类首先在后现代都市中兴起的前卫艺术的核心要义:“关系艺术是一种将人类互动及其社会脉络所构成的世界当做理论水平面的艺术,而不限于只是宣称某种自治或私密的象征空间,这种艺术证实了对于现代艺术所操弄的美学、文化与政治目标进行彻底颠覆的可能性。”[16]关系艺术试图促成“交互主体性”的达成,作品更注重现场“体验时间”的交汇性,而非静态的凝视性空间关系,即艺术项目或作品成为一个生成社会关系、发生交互性意义协商的场所,就像城市作为集结“相遇状态”的社会空间一样。
而更早关注新型公共艺术的凯斯特则认为,自艾兰·卡普罗以来的后格林伯格派离经叛道的艺术实践,与欧洲的社群艺术,如瑞士的“闭关周,参与帮助吸毒妇女”计划(1995—1996),以及美国的在地性公共艺术,譬如塞拉的《倾斜之弧》 (TiledArc,1981),有着内在的关联,即这些前卫艺术更强调超越美术馆画廊的隔离之墙,面向现实世界建立主体间互动、协商与合作,艺术作品或项目不再强调一个现成、已完成的作品形式,而是注重其临时性、现场性和互动性的实施过程。凯斯特用“对话性创作”来命名这些前卫艺术,为了讨论这种新型艺术所促成的新感知和审美经验,他援引康德、席勒等启蒙时代学者的美学著作对审美与共通感的本然关联的讨论,来重建被现代派艺术及其美学因强调震惊、自律而隔断的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公众的关系。如果说现代派艺术通过攻击、错置等策略来维护艺术的自律,抵抗工具化日常所导致的庸俗眼光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中,重建主体间的对话性关系,取消景观和符号化媚俗文化对关系的瓦解,使艺术重新回应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则呈现出历史和逻辑的必要性。[17]49凯斯特还以哈贝马斯的“对话性交往行为理论”来支撑他对对话性美学的讨论,他认为哈贝马斯的对话性交往行为理论是一种主体间哲学,而康德和休谟等对审美经验的讨论仍囿于主体哲学的框架,强调需要建立一种一致性的客观基础,如“共通感”“理性”来取代上帝缺席后的空位,对话性美学则主张主体间的交流互动能促成具有约束力的共同知识、判断和观念的生成。此外,在对话性美学中,主体性可以通过言说与跨主体间的交流达成,主体间的言说不仅是主体间传递内容的工具,更是塑造主体间性的场所。凯斯特以艺术家维列兹(Stephen Willats)的作品为例,讨论艺术跟观赏者的关系,重新定义艺术的内涵,譬如在《你可以一起来恰恰恰吗?》(AreYouGoodEnoughfortheChaChaCha?, 1982)和《在夏维巷的人》(ThePeopleofCharvilleLane,1983)中,艺术家进入社区与居民合作,促使他们透过艺术,与生活经验建立一定距离,从而重新打量他们自己的世界。[17]151凯斯特还将列维纳斯的“他者”,巴赫金的“表演性身份认同”以及南希的“共通体”思想都带入到对话性美学实践的讨论中,用以分析对话与协商是作品意义生产的必要基础。
与伯瑞奥德和凯斯特不同的是,毕莎普则更看重参与式艺术对矛盾和歧感的曝露。毕莎普极力批评凯斯特和伯瑞奥德一味从协商、对话和共在关系中分析参与式艺术的意义和审美机制,且过度仰赖参与式艺术中的伦理维度。毕莎普认为,参与式艺术是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的产物,艺术家为了抵制艺术与市场暗通款曲而将这种协商、对话的伦理发展到极端,反对作品以既定形态出现,甚至忽视作品的审美维度,譬如土耳其艺术家小组的《失败 # 更好》(Fall#Better, 2004)就是这一趋势的表征。艺术家们为社区搭建起一个公共交流空间,关注官僚化、组织化社会中的空白和缝隙,不关心美学问题,而聚焦于社区中动态而持续的关系。[12]45-54毕莎普质疑这类以“关系”为名而忽视审美距离的艺术,她肯定另一些强调社会矛盾、冲突并以艺术形式使其被看见、被感知的作品,譬如英国艺术家杰瑞米·戴勒(Jeremy Deller)的《欧格里夫抗争事件》(TheBattleofOgreave, 2001),作品以邀请“重演协会”集体展演的方式,重现1984年矿工和骑警的暴力冲突:当年撒切尔新政推行产业改革,重创煤矿业,致使约克郡的欧格里夫村近八千警察和约五千名矿工发生激烈对抗。作品中,戴勒作为发起人和导演,邀请当年的警察和矿工互换角色,重演冲突事件,使得历史创伤被重新打量。此外该展演作品还以影像作品、口述史和文献档案等多媒介形式被纪录和呈现。
毕莎普坚持一种拉康式的伦理,即直面象征裂缝后的真实。暴露矛盾和冲突的参与式艺术,不仅仅因抵抗社会压迫和控制而具有政治意涵,更因其呈现被主流观念和媒体所遮蔽的声音、形式、情感和态度而让其被听到、被感受到,这正是朗西埃提出的“歧感政治”,即感性秩序的重新分配。朗西埃指出,黑格尔曾发现,慕尼黑皇家美术馆珍藏的缪里洛画作里,衣衫褴褛的乞儿被表现得像古典时代的神祇或贵族一般逍遥自在。这与世人往往认为乞儿地位低贱、好吃懒做、经验贫乏的流俗意见不同,画作越出伦理秩序、再现秩序所规定的可感秩序,即不只是贵族或神祇才配得上气定神闲、自足安然的喜悦,低贱者也会有如此高贵瞬间。就此,朗西埃从黑格尔论画的裂缝,看到绘画的审美表现中新的美学体制的开启。这与他分析过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某工人报纸上的一段文本相呼应,文章描绘了铺地板工人在工作的间隙,抬眼透过向花园的窗户,眺望远方的广阔风景、任想象翱翔的情景。缪里洛的画和报纸文章都开启了朗西埃所说的美学异托邦。“歧感政治”即“可感的异质性”,这是对伦理体制的增补,也是对布迪厄所讨论的习性、感知的区隔秩序的扰乱,“在空间的具体位置与共同体的伦理秩序之位置的关系中产生了一种扰动”[18]19。
“歧感政治”的提出,最初包含着对关系美学注重协商意味等论述的批评,朗西埃指出它们对政治歧感的忽略,是将政治和审美分别对待。“歧感政治”将美学带出自治独立的话语系统,以跨领域和忽视身份、象征等级的方式重塑社会领域,即美学不仅仅指涉无关乎功利和知识概念的艺术趣味、形式、媒介问题,还与跨越社会等级、消除话语区隔的对话、交流或事件都发生关联。美学沉降到日常经验领域,在旧有的审美秩序(伦理和再现秩序)中不被感知、不被再现的事物、主题、行动,在新的美学识别系统中被感知和呈现,因而歧感美学是对感性形式的重新分配,同时呼唤解放的观众来参与,这本身就是一种元政治。[18]19
在笔者看来,朗西埃、毕莎普和伯瑞奥德、凯斯特等关于参与式艺术究竟应该是协商式还是对抗式的争论,孰是孰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参与式艺术的美学机制具有借鉴意义。此外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协商对话、朗西埃的感性的重新配置,列维纳斯的“他者”、巴赫金的“表演性身份认同”、南希的“共通体”等思想,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型公共艺术强调在地实践和场域感知所蕴涵的美学转向的意味。新的艺术要求进一步突破主体哲学,突破认识论审美框架,也突破从作者中心视角看待艺术生产,要求建立新的美学坐标,去领悟时代精神对平等的主体间对话、对多元化的日常生活的呼唤。
五、结语:在“场域”中生成“居间性”的城市参与式艺术
在国内“混现代性”的社会语境(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杂交并置)中,越来越多的艺术实践开始冠以“参与”“现场”“艺术节”等词语,在一片“参与”的语词喧哗中,我们发现逐渐迈向中产阶级化的城市、城市创意经济也试图向艺术借力,导致独立、前卫性的“艺术参与”同中产阶级化社会中的 “大众参与”混同与重叠。不少昙花一现的艺术节或艺术项目热衷于以“参与”为名,以期吸引和招揽观众,参与式艺术似乎一夜间开始繁盛起来。然而在浪漫的参与幻觉中,我们想问,这究竟是艺术参与社会的有效成果,还是导致艺术丧失品格和精神的参与噩梦?在缺乏长期营造的眼光和策划实践推动下的短视参与,无异于某种被工具化的临时生产,只是浮光掠影的时尚和潮流而已。笔者认为,这同参与式艺术试图培植的美育共同体和城市公共精神背道而驰。当城市需要重塑其空间架构、区域划分和功能结构时,社会参与式艺术在城市空间中作为一种实验方案渐次展开,重塑城市的空间和灵魂,这两种诉求有其呼应、交叠和重合处,然而对于艺术的在地实践者而言,是否需要更深入地讨论:参与式艺术仅仅是实现城市空间再生的工具吗?实验性参与式艺术对艺术和社会机制的批判立场是什么? 限于篇幅,本文就此打住,以问题的方式告一段落。
在解分化时代,被现代性分化所区隔的小世界,正在不断走向新的连接与综合。本文通过观察实验性参与艺术实践如何回应解分化时代的内在要求,即其对参与意识和公共性的呼唤,并援引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对此的相关讨论,进而厘清实验性参与式艺术在美学机制上的转向。在笔者看来,有生命力的参与式艺术,总会寻找自己的独立气质和方法,一方面参与城市空间塑造的新浪潮,强调观看者的参与和建立交互关系;另一面,艺术家进入社会现场,置身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或“场域”中,注重具身化的体验与感知,并以持续性项目或公共空间建构的方式,表达艺术的公共关怀,重新面对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城市空间等问题,让被遮蔽的社会群体、社会维度被感知和被发现。唯此,“场域感知”才能作为一种方法,在具体的“情境”和“场域”中使人们感受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我的居间性关系,并促成新感性和艺术语言的生成。[19]而这对于展开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实践和批评,对于当代艺术在中国土壤中的落地生根都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