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原地
2021-03-24张金晖
张金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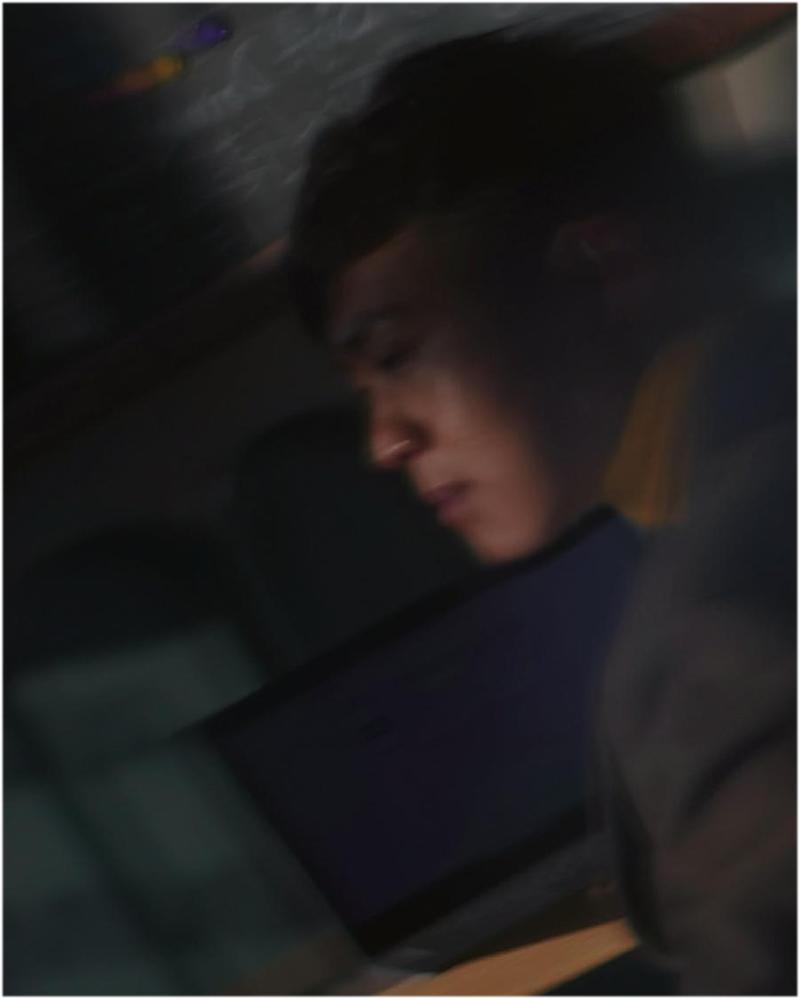
730
A730,位于朝阳医院门诊楼7层最外侧,是眼科医生陶勇被患者砍伤前的常驻诊室,也是去年出院以来,他依旧每周出专家门诊的地方。
自伤医事件后,这间原本独立的诊室最内侧墙壁被打通,与其他诊室一樣,互为连通,方便陶勇和同事进出。但与其他诊室不同的是,这间诊室的电子叫号屏上,并不会显示陶勇的名字,而是以其他医生名字代替。
即便如此,病人们依旧知道里面是谁在坐诊——首次被家长领来就诊的孩子,会在进门后和父母窃窃私语,眼带兴奋地观察这个“新闻里”的医生;复诊的老病人和朋友,则会带上鲜花礼物来看望陶勇。
有位年轻患者,是去年1月20日那场恶性伤医事件的近距离目击者,她和陶勇简单回忆起当天的场景,语气稍显激动:“我当时都被吓得坐在地上了!”陶勇态度平静地安抚道:“你眼底没什么问题了,恢复得多好,咱都越来越好。”

伤愈后,陶勇每周只接诊十个病号,下午1点开始,5点停诊。为患者检查时,陶勇会坐在裂隙灯前,用右手调试仪器,受伤的左手辅助患者扶住额头,或抬起他们的眼皮,虽然动作略为僵硬,但他却没叫过助手帮忙。
大多数患者听从陶勇和助手的安排,就诊时秩序井然。诊室里氛围祥和,好似那场惨案从未发生过。只有当陶勇低头抬手时,衣服盖不住的隆起疤痕,才会从他的领口和袖口处清晰蜿蜒出来。
这天下午,陶勇最终超额接待了二十一个病人。晚上7点,当只余最后两位病人时,诊室里的祥和氛围被打破了。
“您怎么总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当一位患儿母亲在施治前还反复追问“孩子眼底是什么情况”时,和病人柔声细语一下午的陶勇逐渐抬高音量:“不能总让修电脑的人给您解释电路板怎么构成的吧?”
接着,患儿母亲焦虑地改变了询问的方向,交流很快上升为类似辩论的角力。
“我们是不是来看晚了,未来大趋势会怎么发展?”
“那能告诉我您下一胎大趋势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我哪儿知道!”
“这不就对了吗?”
其他医生和志愿者闻声赶来,患儿母亲情绪开始变得激动:“我们一大早大老远的坐车赶过来,中午都没吃饭,就为了给孩子看病……”
陶勇则用右手解开左腕袖口,露出左手臂,指着大片虬结的伤疤道:“谁都不容易。”
患儿母亲暂时安静下来,决定先让陶勇为孩子打针。但几分钟后,表情严肃的陶勇从治疗室疾步走出。“这针我不敢打。”他向追在身后的患儿母亲解释,后者在楼道里喊了起来:“你不能这么对孩子……我们花钱了,你们就得给治啊!”
助手闻言,赶忙把面色变得更难看的陶勇带回诊室,关上了门。
留下
虽然一直在公众面前分享积极走出阴影、战胜伤痛的“正能量”故事,但不可否认的是,除去左手神经肌肉血管断裂、左手和枕骨骨折、颅骨外伤、失血1.5升等显性外伤,这场恶性伤医事件在年轻的“80后”主任医师陶勇身上,还留下了更多隐秘深重的痕迹。
重回诊室后,他变得比以前更谨慎,非常关注陶勇的李洪军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在诊室里,你要是走他后边过,他都得回头看看是谁”,但没出事前,“这个情况他不在意。”
李洪军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天赐爸爸”,他儿子“天赐”是陶勇的老病人,父子俩北上求医的经历,是陶勇在接受媒体采访和新作《目光》中,多次提到的励志故事。
现在,李洪军是陶勇与北京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彩虹之家光明天使志愿服务队”固定志愿者,在朝阳医院眼科为病患提供辅助就诊、心理疏导等服务,也反向为医务人员缓解工作压力。
我目睹全程的诊室纠纷,是由李洪军出面与患儿母亲进行沟通、调和矛盾,和我复盘这件事时,李洪军也试图解释陶勇难看的脸色,“受伤后,要是有啥着急事了,他确实比别人想得更多一点。”
遇到不太讲理或者难以沟通的病人,之前的陶勇或许会应对得更淡定从容,但李洪军也觉得,依靠强大的自控力,陶勇肯定能“慢慢来缓和”这些激烈情绪,因为这一能力曾支撑着陶勇“从仇恨当中走了出来”,并最终回到诊室。
北大医学院的同门师妹“老梁”,却很难理解陶勇具备的这种情绪控制力,“老陶被砍完后居然还出门诊?我特震撼。我心胸没他那么广,我要是他,基本上是会报复的。”“老梁”甚至觉得,师兄陶勇也许是那种罕见的“天生无痛感”的人。
陶勇并非“老梁”身边唯一的恶性伤医事件受害者,九年前,她是北大人民医院的住院医师,曾亲眼目睹同楼层耳鼻喉科的邢医生被患者割喉,满地鲜血的画面是她至今不敢触碰的回忆。

这场事故带来的创后应激障碍伴随“老梁”多年,“血压高,整一年睡不着觉,每天就像行尸走肉”。她最后只得辞去工作,赴美留学深造,并切断了与除导师、陶勇和另一位长辈外,那家公立医院其他所有同事的联系,“一看到他们,我就想起当年的痛苦。”
一次恶性伤医事件,哪怕仅作为旁观者,无论亲疏,其受到的伤害都不可小觑。一所大型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医生洪欣告诉我,在网上看到陶勇受伤的消息后,身边同事“哀声一片、义愤填膺,全是负能量”。
陶勇在ICU抢救的那段时间,除了互相疏解内心的“绝望”和“无奈”,洪欣和同事们最常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自我保护”,几个医生在自己诊室的抽屉里藏了能反制暴徒的辣椒水喷雾,一种由小金属片编织而成的“防割内衣”的淘宝链接,也在朋友圈里流行起来。
“他做过一万五千多台手术,一个人发表的SCI论文,比我们这种普通三甲医院全院加起来都要多。”在洪欣眼里,陶勇算是医学界的“神仙人物”,她不懂为什么这样的医生也会被病人报复,她同样也不明白,“被人往死里砍”的陶勇为什么还能回到一线?
曾为陶勇挡过刀的病人家属田静,心里也抱有这种疑问。陶勇脱离危险后,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看陶勇的视频采访时,田静总忍不住去打量画面里他受伤的左手。
“我手现在也不怎么好用,(手指)弯不了,也伸不直,使劲攥拳头也攥不上。”田静拦下一刀的左手两指,一年后依旧不能恢复灵巧,现在她带孩子复诊时,还是会偷偷观察陶勇的左手,思忖自己这就“挺烦的”“影响挺大”,那陶医生受伤更重,“端个杯子都难”,他怎么就能这么快走出来?
“顶流医生”
“苦难是美德的机会。”在陶勇联合好友李润完成的新书《目光》中,作家周国平这样为他作序。
身处舆论和苦难中心的陶勇,在被患者砍成重伤114天后,重回了朝阳医院眼科诊室,正常接诊。
七个月后,受伤的左手依旧难以复原,陶勇每天都需要在家人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曾经闲暇时,陶勇还会玩几把王者荣耀,保持自己每个新赛季的钻石水准,但现在,只要右手空闲,他就得去用力按摩左手,反复将不停挛缩、产生瘢痕的手筋和肌肉重新扳开。
陶勇无法再回到熟悉的手术台,但他带着缠上绷带的左手,走上了“脱口秀大会”的舞台,用曾经不擅长的幽默方式,调侃伤害自己的凶手:当时医院这么多人,你都能精准把我砍伤,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视力恢复得特别好吗?
苦难也给陶勇带来了更多公开表达的机会,他的微博粉丝迅速增至百余万,新书《目光》出版二十万册……他不断接到各类媒体邀约,与邓亚萍、董卿、许知远等名人对谈,成了医疗圈外的“顶流医生”。
看到陶勇迅速“转型”,老友兼经纪人张笑觉得理所当然,陶勇内心强大,又是“眼科医生里最顶尖的那一批”,深厚的行业积累让他有能力“去做更多事”,而“做手术,可能本来只在他人生中占三分之一,受伤后调整一下比重,不至于整个人重心就没有了”。
调整至新的人生权重后,陶勇变得比之前更忙,“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郁闷”,除了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留给科研、带学生和看诊,他还要“抓紧时间”借新身份去做更多事,比如去探索一个更好的医患相处模式。
去年11月,陶勇联合北京红十字会发起了“北京朝阳医院光明天使项目”,引入更多和李洪军一样、能从患者视角考虑问题的志愿者,用他们的服务为就诊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医患矛盾释压。
“那天天赐爸爸跟她分享了自己(带孩子看病)的经历,最后你看,这个妈妈学会给你道歉,然后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合适。”采访中,陶勇和我说起那天与患儿母亲发生纠纷的后续:当晚,李洪军出面调解后,态度缓和的母亲带着孩子在陶勇的施治下,最终完成了注射。
“看病的效果常常取决于(医患)彼此的一种信任”,这是陶勇从出门诊看病人的第一天起,就不断意识到的问题,但在今天的宏观环境下,他也发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正在普遍流失,这或许也是医患关系变得敏感的主因。

“治疗疾病,很多时候就难在,你可能改变不了所处的一个环境。”从医近二十年,面对处境艰难的病人,陶勇会尽可能为其减免费用、绕过繁琐程序提供便捷治疗。但成为一起恶性伤医事件的受害者后,他开始思考,除此之外,自己在大环境之下,能不能去营造一个医患关系更和谐的“微环境”。
陶勇也向我解释了自己那天为什么一开始拒絕为患儿打针:“我给这个孩子治疗过多次,没收费,也很照顾他。但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家长她非常习惯以自我为中心。”
治疗室里,患儿母亲的一些言论,直接将自己对医生的抱怨和不信任展现在了孩子面前。看着同样对注射环境表现出不满的孩子,陶勇意识到,“如果我只是一味去迎合她,最终你治好了一个孩子的眼睛,但同时,你给社会增加了一个戾气的种子。”然后,他选择先暂停治疗。
“目前,全世界都没找到一种绝对好的医疗模式,它有个‘不可能三角。”坐在冬末清晨的阳光里,陶勇伸手在空中描出一个虚拟的三角形:“费用、技术,还有服务这三件事,迄今为止没有都达成满意。”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医患双方如果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去诠释问题,要求对方来做出改变”,最终结果,“就像两块木头打架,不是A木头战胜了B,或者B木头战胜了A,而是两块木头摩擦起火,火把两块木头都烧了!”
陶勇觉得,自己不能纵容这样的思维,而是要在力所能及的“微环境”里,不断去提倡并落实“换位思考”的正向价值观。“个体是环境中的一个动物,而家庭是每个人生存的最小单元”,亲密家属的负面情绪,最终会反向“感染”一个本身具有良好“依从性”的病人,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心态,他也将成为未来医患冲突的隐患。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你不仅是要救人,也要去治心。”陶勇总结道。
第二座高峰
陪伴陶勇工作几个月后,张笑觉得,自己发现了支撑陶勇快速复原的新秘密——他身边充满了“‘微循环的正能量”。
负责陶勇对外合作的接洽事务后,张笑能近距离感受到一些老患者对陶勇的关怀和热情,他被替陶勇挡刀的田静追着问过地址,对方想在年节时,第一时间给陶勇家寄去生鲜年货;在医院做志愿工作的李洪军,常亲手做些糖葫芦和芝麻饼,除了送给陶勇,还不忘给张笑也捎上一些……
“你对人家好一点,人家就会加倍对你好,因为他能感受到一个医生对他的真诚。患者只要是个善良的人,就会把这种善意放大好多倍,然后就表现出对陶医生的回馈。”张笑说起之前媒体们拍到的一些画面:很多来探望陶勇的患者,会因为他的伤在镜头前流泪。“那些都不是假的啊。”他强调道。
正向的“微环境”和均衡的医患关系,能给予医生的情感反哺,其实相当持久可观。
46岁的石燕红,是陶勇2019年录取的博士生,她199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军医大学,从医二十余年,从河西走廊的基层部队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再到兰州一家三甲部队医院,最后来到北京深造。辗转多地,收治过很多病人,石燕红到今天还能清晰记起自己研究生毕业时,收到的一本黑色笔记本。
“当时我在急诊科锻炼了一年,有个老太太过来,可能是心脏不舒服,我简单地给她做了检查,发现有心梗前兆病表现,就直接收住院。”石燕红回忆,也许是当时自己收治迅速,老人得到了及时治疗,抑或是周围的护士对病人和家属的态度也不错,半个月后,她收到了老人儿子专程送来的礼物——一本在扉页上写着“人民的好军医——石燕红”的笔记本。
“还在家里放着呢。”石燕红笑着和我比划笔记本的大小,“黑颜色,这么大一本,我记得挺清楚的。”
成为医生,要做的并不只是奉献,能获得的也并不只有牺牲,这是陶勇坚持的观点,也是他选择回到公立医院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陶勇的观点,回国后在私立医院工作的师妹“老梁”,曾多次劝他转去病人更少、出诊环境更舒适的中高端私立医院。被陶勇婉拒后,“老梁”觉得,“80后”师兄陶勇有点“又红又专”,与惜命的自己相比,更像是老一辈的医生,“就像我俩共同的导师,都能把自己当天灯点了,去照亮病人。”
但在日常采访中,会用雷锋的故事来举例的陶勇,却并不全盘认同这样的观点:“不是说只为了成全他人,所以我要从医;也不是说只为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所以我要从医。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自利的基础之上实现利他,这两件事情是融合为一的。”
“我也在索取。”在微博上,陶勇这样回复那些留言要向他学习,去无私奉献的年轻医学生们。
2020年10月15日,“世界盲人日”,陶勇第一次在微博上写下了“天下无盲”,这是他未来人生的新愿景。
“天下无盲”不是句空话,也并非一夕之念。陶勇一直对两个小患者抱有很大遗憾,“广西的薇薇,还有山西的小岳岳”。两个孩子曾做过白血病骨髓移植,也都患有病毒性眼病。但孩子往往不能及时将眼病告知父母,在做完骨髓移植手术后,免疫力又极大下降,病情更易恶化。
“现在薇薇就完全失明了,岳岳有点视力,靠着智能眼镜还能够上学,但实话说,都是治晚了。”陶勇摇了摇头,但他也不沮丧:“所以,我就更想去推动一个项目——在骨髓移植病房,直接进行眼底照相,通过网络上传图片,后台人工智能分析,早期诊断、早期发现,然后结合眼内液检测技术进行确诊。”
陶勇给我认真算了个数:全国每年新增8万个白血病患者,做完骨髓移植后,出现病毒性眼病的概率是5%,“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每年可以给中国减少4000个盲人!”
除了医疗科研,陶勇的“天下无盲”,还囊括了更多人文性的内容。他受邀成为《盲童文学》杂志的专栏作家,还正在写作新书《壮壮寻医记》,讲述一个患上白内障的农村孩子不甘失明,走出山村寻医的励志故事。“这是一本专门给盲童来读的书。”陶勇介绍道。
陶勇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正让他日益接近“天下无盲”的理念,而这也是他“新的幸福”的来源。
好友张笑能一定程度上理解陶勇所处的状态:“人生有二座高峰,第一座高峰是你的职业,而第二座高峰是道德快乐的高峰。陶医生在医生职业领域,相对来说已经到一定高度了,属于他更大的价值感、持久的快乐,是来自于第二座高峰。”
张笑能感觉到,陶勇正在攀爬属于他的第二座高峰,这样的过程予他而言,“是莫大的快乐。”
希望
成为“顶流医生”后,陶勇的衣品,算是老同学李润最操心的一件事。去年,在北京一起创作《目光》期间,李润曾短期担任过陶勇的专职经纪人,帮他打理上镜形象。
但李润回深圳后,很快在陶勇的一段媒体采访视频中发现,他倒退回了大学时醉心实验、不修边幅的邋遢状态:“蓬头垢面,衬衫皱得简直像是从洗衣机里直接拉出来的。”
李润马上提醒陶勇:你得注意点形象。然后建议他赶快减肥,并顺手揽下了给陶勇购置行头的任务。
不过,陶勇的适应性远比李润想象的要强。去年年底,陶勇在自己的微博超话发了一张组图,照片中,他从套着病号服的圆胖医生变成了身穿西服套装的都市精英。粉丝们留言点赞,他自己也配文调侃:我发生了什么?是在我昏迷时(被)拉进了整容科手术室吗?
去年录制《鲁豫有约》时,主持人鲁豫曾问过陶勇,接下来要干什么?“我说,我是要提升自己颜值的!”头上顶着几个小发卡,正被造型师调整妆面的陶勇,转头向我认真道:“我们必须尊重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有一句话叫‘始于顏值。”
瘦身成功的陶勇,已经是能玩转微博超话,会主动和粉丝互动的社交媒体达人,他在网络的信息潮流中适应良好,也同时葆有自己的清醒思考。
张笑告诉我,陶勇初次被科普“饭圈”文化后,就在粉丝群里发表了自己的原则,清晰反对他个人向的“饭圈崇拜”,“意思是说,我就是个普通人,你们不要用所谓的想象标准要求我,我也不会要求你们活成我设计的标准样子。”陶勇希望他和粉丝之间能彼此尊重,同时坦言:我是有家有室的人,你们在我身上YY(意淫),我也不是很喜欢,不可能满足你们那些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