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侃,石壁上的微笑泥土里的花
2021-03-16许晓迪
许晓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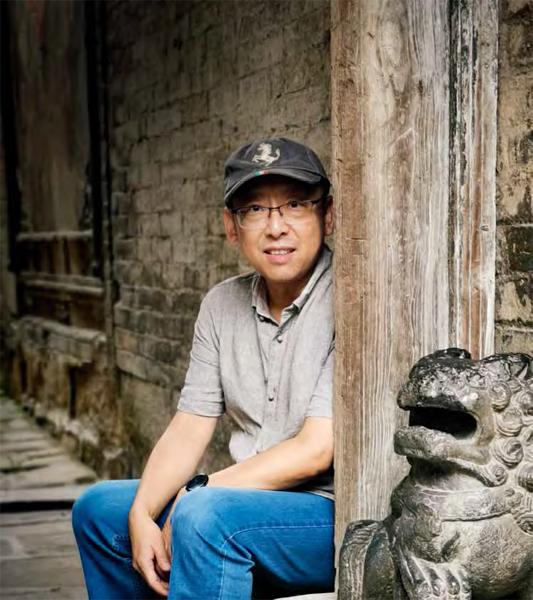
杭侃
小说《古董局中局》里,作家马伯庸讲了一桩“佛头奇案”。
唐朝,武则天建造明堂,用异邦美玉雕刻了一尊毗卢遮那佛像,供奉其中。谁知,遣唐使河内坂良被珍宝吸引,用计窃于己手。世家子弟连横奉命追回,争执下,佛像一分为二,佛头被带往日本,佛身则留在连家。千年后,军阀混战,时局动荡,连家后人许一诚为保护国宝,设下迷局,却背负上不白之冤,身败名裂,枪决而死;孙子许愿由此踏上为祖父沉冤昭雪、探访秘宝之旅……
故事是“马亲王”虚构的,背景却是真实的。一个世纪来,“身首异地”的佛教造像遍布中国石窟古寺,脖颈之上的空荡也是一个民族的“断首”之殇。
2021年除夕夜,一件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的佛首,亮相央视春晚舞台。在它静穆柔和的微笑背后,是历经毁弃、漂泊、流离后的超脱与悲悯。
这段国宝传奇的讲述者是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现场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尊微微含笑的佛首,见证了天龙山石窟精湛的艺术水平,具有重要的实物标本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而第一版解说稿的结尾,更带着一位考古工作者的深情:“我们在鉴定的时候围绕着这尊佛首反反复复地看,从哪个角度看,它都颔首微笑,非常打动人。”
“我很舍不得这句话。”杭侃说,他争取了半天,还是没能在舞台上讲出。
渡尽劫波的佛首
隐没于太原40公里外天龙山丛林中的这批洞窟,最早开凿于东魏时期,历经北齐、隋、唐、五代不断增凿,于明清之际衰落,除了附近僧侣居民,鲜有人知。
1918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建筑史权威关野贞根据太原县志的简略记载,翻山越岭,最终找到天龙山石窟所在。久远年代的精美佛像令他狂喜,3年后,他在日本《国华》杂志上发表考察报告,震惊学界。此后,从日本艺术考古学者常盘大定到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各国学者纷至沓来。
隨之而来的,还有别有用心的文物贩子。1924年和1926年,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两次到天龙山。他找到山下圣寿寺的净亮和尚,掏出10根金条,希望他帮忙盗割佛像。层层加码后,净亮被拉下了水。历经1400多年风雨的天龙山石窟,开始在锯齿、铁锤下面目全非。此后,各国古董商纷纷前来,精美的佛像几乎被割窃一空,流落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在中国石窟寺中,天龙山的破坏程度最为惨烈。
1996年,杭侃第一次来到天龙山,帮师兄李裕群做测绘工作。“在持续一个月时间里,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高照,我们每天起早贪黑,上山下山,一天往返两次,认真做好每一个洞窟的实测工作,晚上则在山庄整理图稿和文字记录。”李裕群在2003年出版的《天龙山石窟》后记中写道。
那时,天龙山已成为景区,松涛溪鸣消逝于游客的喧嚷中。净亮和尚早被冯玉祥判了死刑,圣寿寺也被阎锡山的军队烧成废墟,重建的寺庙东面,耸立起一座仿古的天龙山庄。
“头被盗凿,凿痕高 0.49米,身高(至肩)1米,身体风化严重,服饰不清,双手已残,原手似施说法印,右胫压左胫,结跏趺坐于束腰叠涩须弥座上。”当年的考古报告中,曾如此描述第八窟北壁的那尊佛像。
2020年12月12日,被盗凿的佛首重回祖国。两天后,杭侃作为专家之一参加了佛首鉴定。在鲁迅博物馆小小的库房里,他终于见到了当年测绘时佛像空荡荡的颈项上,原本是怎样一副神情,“它的笑,好像跟你有交流,仿佛在说,对这个世间很满意”。
在一篇文章中,杭侃如此描述这种“神秘的微笑”是如何被创造的:“他(制作者)把自己的虔诚和喜悦,一丝一毫地雕刻进了造像里。就像米开朗基罗一样,‘自己手中的雕刻工具,是在粗糙的石头表面下,唤醒里面早已存在的生命。”
“怎么拿两个学分这么难啊”
这样一种艺术,诞生在战祸不已的魏晋南北朝。
398年,鲜卑人拓跋珪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称帝,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460年,高僧昙曜在平城西侧武州山上,为北魏的5位皇帝开凿了5座大窟,后世称“昙曜五窟”,从此拉开云冈开凿的序幕。从高鼻深目、挺拔健硕的游牧气质,到清矍飘逸、褒衣博带的南朝风貌,佛像的变迁也是一部文化融合史。

左上图:1922年,日本学者拍摄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像。右上图:2020年12月12日,被盗凿的天龙山佛首回归祖国。下图:云冈石窟20窟的露天大佛,是云冈最广为人知的一座佛像。

杭侃(左)与学生考察祁县子洪石窟。
杭侃的微信头像是云冈第五窟的一尊佛像。它不像唐代的,丰满、富贵、自信;也不像宋代的,充满烟火气。那是北魏独有的一种神性,“有悲悯之心,俯视众生,洞察一切,又保持着对世间的超脱和距离”。
2月最后一天,大同落了雪,云冈石窟游人寥寥。站在洞窟里,十几米高的佛像雍容含笑,也带来强大的压迫和震慑;仰头看层叠蔓延至穹顶的大小雕像,万花筒般的眩晕感。时间施行着涂改一切的特权,这一侧还是生动纷繁的佛传故事,回过头,那一边只有几座历经渗水侵蚀、风化到一片混沌的石块。
20窟的露天大佛前,几个游人在拍照留念。它是云冈最广为人知的一座佛像。1993年冬天,也是一个大雪天,杭侃第一次站在這尊大佛前。
那是他走上石窟寺考古的第八个年头。1986年大学毕业后,杭侃被分到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做中小型石窟调查。有的寺院荒废已久,他和同事们要花钱雇当地村民,在丛生的树木杂草间砍出一条路。
上世纪60年代生人,大多经历过“破四旧”“批林批孔”的运动风暴。杭侃一开始看不进去佛教的东西,“无数个世界有无数个佛,神神道道的,很不喜欢”。但做测绘不免爬上爬下,看着看着,他觉得那些故事“蛮好玩”,几年后,“慢慢觉得有点意思了”。
但写考古报告却成了难题。杭侃决定重新读书,考入北大考古系,师从宿白。
宿白,中国考古学一代宗师,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佛教考古、建筑考古以及古籍版本诸方面成就斐然,从主持过元大都、金中都发掘工作,为历史名城大声疾呼的“考古界良心”徐苹芳,到守望敦煌半世纪、被称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都曾受教于他。
杭侃入师门时,宿先生已70岁,但精神头儿依旧,住在朗润园,“每天自己扛着自行车上下三楼”。他上课全是干货,慢条斯理念事先写好的讲稿,时而在黑板上补绘一幅图,一节课下来,学生累到手臂酸胀。
有时,宿白会让学生到家中上课,几个人挤在沙发上,如坐针毡。“他让我们提问,问不出来就亲自‘拷问,那更恐怖,所以每次都挖空心思想问题。”杭侃印象最深的课是“汉文佛籍目录”,宿先生让他们抄讲义,“他的讲义改得乱七八糟,各种符号,‘菩萨是两个草字头、大藏经的‘藏是‘艹+丈,看了直晕”。还让他们抄吕澂的《佛典泛论》,杭侃抄得手上起了茧,说给老师听,宿先生就让他看自己的老茧。
宿白是中国石窟寺考古的拓荒者。1950年,他参加雁北文物考察团,到大同云冈考察。此后,东至辽宁义县万佛堂,西至敦煌莫高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以及中原地带的响堂山石窟、龙门石窟,江南的栖霞寺石窟,西南的大理石钟山石窟,他都进行过记录、测绘、摄影和研究。1959年,宿白在西藏做了5个月调查,足迹遍及40多座佛教寺院。当时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他用步量目测,“八九不离十”。
杭侃见识过老师田野调查的功力。一次去宣化一间寺院考察,“我们嘻嘻哈哈进去了,拿着相机各种拍,宿先生说,拍什么拍,看懂了吗?真没看懂。只好他看哪儿,我们就装着看哪儿。”杭侃说,“一个地方,他走过去,围着转一圈,进深、面阔就(测)出来了。”
第一次云冈之行,也是宿白先生敦促他去的。一次课程作业,宿先生说文章写得有点意思,让他去云冈看看。“那时没有电脑,我就用复写纸,拿剪刀浆糊剪剪拼拼。折腾了六七次,从近3万字删到七八千,宿先生说我,让你删哪一块儿,跟割你的肉一样。我心想,怎么拿两个学分这么难啊?”
没想到有一天,宿白先生拿了张条子,让他连文章一起送到《文物》发表。这篇《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被杭侃看作自己第一篇真正的学术文章。
满身泥土的学科
宿白先生很少接受采访,对无数名誉头衔,唯一认可的称呼是“北大教员”。杭侃也不愿多谈自己的故事。“田野考古日复一日,很平淡也很枯燥,无非是天天背着包和三脚架去测量,就干这点活儿。”
走上考古之路本是偶然。“当时完全不知道考古是怎么回事,但可以下田野,还能玩相机,觉得很好玩。”杭侃第一次实习去的是河南南阳,那里有个南召县,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他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树上的蝉,个头儿特别大。
1986年夏天,杭侃去黄河小浪底淹没区参加文物调查。晚上没地方住,在地上垫块布就躺下,有时幸运,能睡上水泥做的乒乓球台。吃的就是自带的干粮,偶尔碰到当地老百姓,擀点面、撒上葱花,能吃上一碗面。更要命的是晚上的蚊虫,久不见人血,轮番扑来,一夜之间就肿起70多个红疙瘩,没有止痒药,只能等到白天,贴着发烫的岩石止痒。
1994年春天,杭侃独自一人开始三峡工程淹没区古代城址的调查。4个月里,上起重庆江津、下至湖北宜昌的22个市县,他都走过一遍。怕资料丢失,每晚回到旅店,他都将当天的记录抄写一份,寄回北大。
在杭侃看来,风餐露宿本就是考古者的常态。他有时晚上借宿在破庙里,用东西把门顶着,能听见门外的狼用爪子来回抓挠的声音。有一次,他在河南考察石窟,用手扒着,从这边的窟门爬到另一边的窟门。同行的人仰拍了一张照片,“我妈看了照片就哭,她不敢想象,儿子怎么像个猿猴一样,挂在悬崖上”。
对杭侃来说,最难的不是这些,而是测绘那种不高不低的洞窟,“蹲下来够不着,站起来又顶着了,只能半蹲着,用尺子量也不顺手,时间长了特别难受”。他的腰不好,平时有一个小工作台,可以站着看书。这次回大同,他特意带来,“因为要进洞窟,日本人的书很大,时间长了抱不住,摊在台上就方便了”。
所谓“日本人的书”,是京都大学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云冈调查、测绘6年之久,于50年代陆续出版的《云冈石窟》16卷32册。报告用日文、英文编写,甚至不附中文提要,用宿白先生的话说,“是对我们最明显的蔑视和侮辱”。
然而迄今,研究云冈必不可少的考古报告仍然只有这些“日本人的书”。“相比景区的经营,基础报告的编写才是最重要的。没有新材料,就没有新观点、新问题、新学术。”杭侃说,“云冈是个‘老者,再保护也只是延年益寿,不可能万寿无疆。它总有毁废的那一天,如果没有考古报告,我们如何复原它,告诉未来的人这里曾经存在过什么?”

年轻时的杭侃与老师宿白。
“考古是个富矿,我们要做‘转译者,打破时空的隔膜和专业的围城。”杭侃说,他有多年博物馆工作经验,于2015年发起“源流运动”,从公号运营到线下活动,“把考古所得的知识体验带入日常生活”。
他至今怀念80年代,那时“城里城外”的人自由往来,思潮恣肆。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利用陶器、青铜器、甲骨文、画像石、石窟雕塑等各种考古材料展开美学探讨,“既有哲学家的眼光,又有文学式的表达”。在考古界,俞伟超掀起了新考古学思潮,相比“整天拼陶片、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更关注文物背后创造者的精神世界。
1996年,俞伟超出版《考古学是什么》,当年的学生张承志在序中说,同样研究历史,使不使用考古学方法有巨大差异。“因为考古队员真的触摸着逝者的遗留,从陶铜的冰凉触感到灰坑烧土的余温,都强烈地影响着思维,使他们无法回避这个学科最朴素最原初的问题。仿佛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或者当个特殊技术工人,或者攀援成为思想家。”
这段话,深深印在了杭侃脑海中。年轻时,他热爱文学,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泰戈尔、海涅、莱蒙托夫和“朦胧诗”。他曾认识一位诗人,在他的手抄本里读到过一句诗:“有种子,点点色色,遗忘在无路的花园,等待花开的日子,等待复活。”
考古学大概也是这样,在无路的田野发现零散的种子,静待它们花开、复活。
杭侃
江苏省南通市人,1982年考入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宿白。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考古、佛教考古、文化遗产学。1998—2003年,在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工作。2007年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现任云冈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