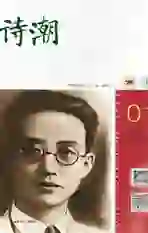花楸树 [组诗]
2021-03-15韩宗宝
韩宗宝
杉树
谁把时光和杉树
制成一张古琴
谁的命若琴弦
谁把时光和杉树
打成棺木 杉木是谁
最后的衣衫
春风中琴声如咒
棺木空空 衣衫空空
杉树在高山上肃立
巨大的安静和悲伤
那些压抑的流水
让一棵杉树陡然失语
谁在杉树下弹琴
谁坐在棺木和春天的
阴影里出神 空空荡荡
悲伤
我的悲伤毫无来由
但它像夜空的星辰一样固执
这些莫名的悲伤
还要持续多久
当我独自一人
站在星空下 站在旷野上
我仰起头来看到了什么
那照耀我的是什么
我头顶微茫的星光是冷的
而我胸口无法排解的悲伤是热的
美人计
你是美人 也是一条计策
来吧 为了河山
为了江山 只能出此下策
你看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而你是豪杰中的豪杰
你双重的美 代表着双重的悲剧
你的前世也是美人 你有一颗
明月之心 你把隔世的爱情
交付给小人 交付给火焰和铁器
红颜和青春永远是徒劳
在无限空茫的历史中
你看到自己的哀愁大于一
小于国家 对于濒临破碎的国家
美是多余的 你恰当而不合时宜的美
沦为工具 道具 面具
战争应该让女人走开
可用来堆砌胜利的是你
柔弱的身躯和心碎
作为一幕剧最重要的底牌
镜子里的你还是完好的
除了画眉和琴弦 没有人知道
你究竟忍住了多少 哀愁和绝望
那一剑向你愤怒地刺来时
你看到自己弯曲的眉毛和嘴角
微微上扬 你用最后的死亡
完成了对这场战争和男人的嘲弄
你目中无尘 心高于天 奈何命薄如纸
永远包不住冷酷无情的火焰
你温柔的白骨 依偎着青山和青草
你光彩照人的形象 和美学无关
和深渊有关 被关在一场荼蘼的花事
和关内浩荡无边的春风里
薛宝钗
关于你 我总想到那只
薛定谔的猫
它一直飘忽不定 难以琢磨
如你那让人永远猜不透的心机
其实你的心事很浅
如曹雪芹在大观园里虚构的那场雪
你是悲剧的另外一个主角
你用轻罗小扇扑到的那只蝴蝶
并不是梁山伯祝英台所化
你在诗词中雪藏着自己的美
天再暖 你也忍住不融化
那些香气不绝如缕
你如雪的美犹如盛开的白色牡丹
你似雪又非雪 你冠压群芳
面冷心热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旧瓮
不是济慈的希腊之瓮
是中国的一位祖父的瓮
我那未曾见面的年轻的祖父
祖母说这瓮是他的遗留之物
半个世纪后年迈的祖母离世
如今祖母离世也十几年了
旧瓮还在院子的天井里待着
父亲说母亲生前和旧瓮对视过
她用水瓢舀过装在瓮里的水
那是父亲从井中新汲上来的清水
除了水 舊瓮还装过什么
年深月久 它自己也记不清了
旧瓮身上最初的痕迹已经漫漶
它也许是祖父的祖父留下的
在装水之前 或许装过土和粮食
都是杳不可查的陈年往事了
一只深陷于命运的旧瓮
从我出生 它就一直沉默着
仿佛疲倦于苦役般的时光和永恒
再多的水也无法缓解它的渴
瓮的孤立的形状是它难言的悲伤
瓮中的天空不断地被打碎
终于有一天 它也被打碎了
我似乎听到它长舒了一口气
仿佛如释重负 仿佛解脱和狂喜
一只因拆迁而破茧成蝶的旧瓮
被一个紧抿着嘴唇的中年人
和女儿早年断了的红发卡一起
完整地埋进了泥土 它装过土
它曾经是土 现在被更多的土埋着
和我逝去的亲人们一样 它是安然的
一只古老的旧瓮宿命般地碎了
它重新回到泥土中间 像一次飞翔
在泥土和岁月中它将一碎再碎
瓮的形态已成历史 碎片是它的现实
直到那天 我猝不及防地梦见它
芦苇
我用整个灵魂
注视过站在天空下的你
你也用你的整个灵魂
热切地回应过我
天空蓝得近乎透明
整个蓝色的天空都在摇晃
潍河醉成了一条
酡红色的曲线
从茂密的芦苇丛中
慢慢回过头来的那棵芦苇
浑身上下焕发着
引人入胜的美
潍河里所有的波光
都是灿烂的
整个芦苇荡满目苍翠
芦苇尚未吐出洁白的芦花
我曾经无限地亲近过
一棵高傲的芦苇
它英姿飒爽的背影
就像一段甜而静止的时光
潍河仍然在流动
我遇见过的那一棵
站在河边上出神的芦苇
已经下落不明
我独自一人远远地
看着深陷于记忆中的
那棵青青的芦苇
它的神情依然沉静如水
一棵历尽了夕阳和月亮的芦苇
它高于世间所有的芦苇
它深藏于内心的金黄色秘密
至今无人知晓
花楸树
秋天忧伤的花楸树
结满了红果子的花楸树
多么像一棵快乐的花楸树
以梦和春天为马的花楸树
是故乡苦涩又幸福的花楸树
永远孤独地开着无数白色小花
记忆里那个站在花楸树下
安靜地凝视远方的姑娘
仿佛是另一棵花楸树
苏格拉底的鞋子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苏格拉底的鞋子
也没有看到过苏格拉底
这个雕刻匠之子
他终生以母亲是助产士为荣
他雕刻的不是大理石
是石头一样的灵魂
在雅典 赤足的苏格拉底
他手中的麦穗和苹果
近乎于一个完美的讽刺
没有美德 也没有知识
只有一杯简单的鸩酒
一只牛虻死死地
叮着古希腊和那匹神马
我知道的苏格拉底
仅仅是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
他为人类指出了真理或者道路
并谦卑地让出自己的生命和鞋子
蜻蜓
它那宁静的复眼
和它透明的梦
在夏天 小心地接近水
红色的蜻蜓和蓝色的蜻蜓
极少在空中相遇
像两条过于悲伤的铁轨
我想起了那只红色的蜻蜓
它安静地停留在童年
小菜园简陋低矮的短篱笆上
它颀长的身子浮着淡淡的
红色光晕 它的身后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正悄悄伸向它
那个蹑手蹑脚的人
面容有些模糊 他还是个孩子
他捉住了那只红蜻蜓
许多年后 中年的他放飞了它
让它以标本的形式
重新飞进那个遥远的夏天
这个多事之夏 一场暴雨后
在路边安静的泥泞中
我意外地看到一只蓝色的蜻蜓
它已经静止 或者无力挣扎
完全放弃了求生的本能
它亲近过的水成了它的噩梦
我不知道 它是否还活着
它应该是我少年时曾看到过的
无数的蜻蜓中的一只
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捡起它
帮它擦拭晾干身体 当它振翅而去
在阳光里 它仿佛更加轻盈
而我突然伤怀于 如蜻蜓一般
被制成标本的 或陷在泥淖之中的
我的那些屈从于命运的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