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是音乐文化诸多事项的综合载体
2021-03-14刘晓晨
【摘要】乐器是音乐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以物质形态作为表现形式的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及文化类型对乐器的分类不同,早期的比较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根据乐器发声源材料的不同建立了一套乐器分类法——“霍—萨乐器分类法”。这个乐器分类法将乐器分为了“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及“器鸣乐器”四类。本文以膜鸣类乐器为对象,结合物质人类学等相关理论,讨论乐器如何体现作为音乐文化诸多事项的综合载体。
【关键词】膜鸣类乐器;乐器学;文化载体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4-139-05
【本文著录格式】刘晓晨.乐器是音乐文化诸多事项的综合载体[J].中国民族博览,2021,12(24):139-143.
基金项目:本文由“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培养科研资助项目”资助。
一、已有文献中对乐器学的描述
周晋民在《乐器学研究的五个世纪》(上、下)一文中探讨了乐器学作为一个对乐器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自16世纪初德国的沃登首次通过西方现代印刷技术而发表的有关乐器的综述直至20世纪末这个时间段中的发展过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该学科进行全面了解的机会。文中具体的分期不在此赘述,这一节中,笔者对前人的四部乐器学著作及相关信息进行简要论述,为下文的具体论述奠定基础。
(一)《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2011年,第二版)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是国际供稿人的学术性最强、篇幅最大、最具权威性的音乐辞书之一,于1878年由英国乔治·格罗夫爵士规划并主编出版,初名《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至1980年由斯坦利·萨迪主编的第六版,书名改为《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本文引用的是于2001年出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1]
该词典第18卷“Organology”(乐器学)词条部分相关释义如下:乐器学研究乐器的发展历史、社会功能、设计、构造和演奏形式,从17世纪早期开始,乐器学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如Praetoerios在他的《Syntagnma musicum ii(1618)》一书中就包含了关于乐器的一个重要章节,此章节描述了一些非西方的乐器以及按比例绘制的图释。除为乐器表演者及制造者提供有用信息外,乐器学家还揭示了世界范围内的音乐风格、表演实践和乐器演变间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关系。纪尧姆·安德烈·维洛托(1759—1839)在对古代墓葬及庙宇乐器描绘的基础上,对古代乐器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研究;后来的考古发现,即使是残缺不全的埃及仪器,也使他的结论得以完善和修正。
该词条开始首先阐明了“乐器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端和早期的研究著作及成果。“乐器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确立,是由于19世纪欧美大规模、永久性的乐器博物馆的建立,为其奠定了基础,随着博物馆的建立,对乐器的分类也提出了要求。乐器学学科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越发重要是由于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的提出。及至1941年,尼古拉斯·贝萨拉洛夫(Nicholas Bessaraboff)将“乐器学”作为一个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使用的术语引入,使“乐器学”正式进入了研究的實操领域。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的“乐器学”词条内容实际上阐述了乐器学的学科发展史、代表性著作及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它提出乐器学与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的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为后续研究开拓了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
(二)《东亚乐器考》
《东亚乐器考》[2]是日本音乐学家林谦三所著,该书由序说、正文及附论三部分构成。在“序说”部分中,林氏从历时的角度叙述了从19世纪开始的东亚乐器的研究工作,提出原有乐器研究成果多为翻译中国典籍且屡有谬误,东亚的学者做出了出色的成果。正文分为四章,以东亚各国乐器、演奏法及已有音乐理论为基础,从发声源角度分类,分别从“体鸣乐器”“皮乐器”(即“霍—萨分类之膜鸣乐器)、“弦乐器”“气乐器”角度入手,叙述东亚乐器的历史 。
作者通过对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公元8世纪的一批东亚古乐器(主要是唐代乐器),对部分馆藏乐器进行研究并有部分成果发表,在此基础上形成本书,是研究东亚乐器的代表作。
(三)《中国乐器学概论》
《中国乐器学概论》[3]是以中国的乐器学研究作为主要论述对象的概论性著作,除引言及附录外,共分六章,分别从乐器学概述、乐器分类、中国乐器历史、乐器的文化研究、古乐器研究、声乐、律学、乐学问题等六个章节论述中国乐器学的发展。该书系统的梳理了中国乐器及乐器学学科的发展历史、中外音乐学界对乐器分类的方法及比较、文化学及人类学背景中的乐器学研究、古乐器研究等诸多内容,从历时的角度,全面梳理了中国乐器学研究的理论架构及研究成果,是乐器学研究的一本重要著作。
(四)《日本音乐大事典》“乐器学”条目
“乐器学”条目从“总论”“学科定位”“学科历史”“研究资料来源”等几个方面介绍了乐器学的概况,基于“大事典”的体系,阐述乐器学的概况。
综合来看,乐器学有学科前期发展过程长、学科建立时间短、研究成果众多但未形成体系等现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作为器物的膜鸣类乐器的文化定位——以哈萨克族膜鸣类乐器为例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罗兰·麦克表示:通过观察某一物品的制造和使用过程,可以得到与社会文化制度相关的知识[4]。人类社会一切被生产出的物质都有其属性与定位,人类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投射在被生产的器物中,成为“物质化”的人类文化,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作为乐器分类体系中的膜鸣类乐器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
(一)作为“物质文化”的哈萨克族膜鸣类乐器
哈萨克族是一个文学发展历史非常悠久的民族,尤其是以英雄史诗、爱情叙事诗为代表的口头文学体系是哈萨克族历史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由于膜鸣类乐器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因此,在哈萨克族的口头文学中,出现膜鸣类乐器最多的就是英雄史诗,如英雄史诗《阿勒帕米斯》[5]中的一个诗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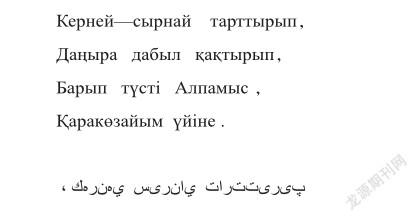

“达布勒是哈萨克族的一种打击乐器,共鸣箱两面蒙有羊皮、牛皮或其他兽皮,侧面装有皮绳或木质的把手。古代哈萨克人作战时曾使用过达布勒,主要是为了召集民众。”
“巴拉般是在许多国家广泛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共鸣箱由木质或铁皮制成,两面蒙有皮革。战争时期,也在一些宗教活动中使用。在乐器歌曲和乐队演奏中使用。吹奏曲与交响曲中用大鼓,偶尔也会用小鼓。在哈萨克民间乐器中达布勒也属于鼓类乐器。”
如上述描述所示,《哈萨克苏维埃大百科全书》中“当额拉”“达布勒”“巴拉般”等三个膜鸣类乐器的词条中都描述了使用达布勒是为了战前召集民众,英雄史诗中关于两者在战争胜利时使用的场景描述更加作证了膜鸣类乐器“在有关战争的场合使用”这一说法同样广泛存在。
作为游牧民族的哈萨克族在历史上由于不同部落之间的纷争会产生战争,在战争中为了鼓舞士气,会使用膜鸣类乐器(即鼓类乐器)激励士兵,作用如同现代部队中的“冲锋号”一样。之所以会使用鼓来激励士兵,与其生活环境与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史诗中关于膜鸣类乐器的描述,即为膜鸣类乐器物质文化属性在民间口头文学中的具体体现。
此外,哈萨克族作为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长期的草原生活产生了大量与草原文化有密切联系的乐器,如:形制与弓箭相似的адырна(哈萨克民间乐器集锦注释),哈萨克族弦乐器,根据打猎时的弓箭而制作,其性质与弓箭相似。同样,作为制作材料与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膜鸣类乐器да?ыра、дабыл、дауылпаз,也同样体现了作为“物质文化”的属性:膜鸣类乐器(鼓)由鼓膜与鼓身(鼓圈)两部分组成,鼓膜由羊皮或骆驼皮制成,鼓圈由樺树木弯制而成。上述两种材料皆为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作为战斗中的武器、宗教仪式中的法器及日常生活中娱乐所需的乐器,虽然使用场合不同,但其所属的物质文化属性及其文化定位鲜明的体现在了各自的功能中,成为哈萨克族重要的文化符号。
(二)作为“精神文化”的哈萨克族膜鸣类乐器
麦克·罗兰:强调人类不仅是生物有机体,同时也是文化有机体,并了解生物条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即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类是怎样的,也是理解人类是怎样同时被作为社会人的一个重要层面。拥有社会属性的人在社会活动中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产生有别于他者的文化特征。
作为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哈萨克族,其民族构成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体系,在民族内部有若干部落联盟,每一个部落联盟下又有若干部落。为了与其他部落做区分,各部落有自己的印记与口号,这些口号与古代哈萨克族先民的信仰、部落之间的关系等诸多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在物品中刻上印记是标示部落身份、宣示部落主权的主要方式。这些印记同样会被刻在哈萨克族膜鸣类乐器的鼓圈上,在聚会、战争时,人们呼喊口号、敲击膜鸣类乐器,这些带着部落印记的乐器成为部落的“代言”,同样也成为部落成员的“精神寄托”。
这里所说的“精神文化”,包括一切体现民族特征、民族思维的地方,例如哈萨克族宗法制度中,数字“七”所代表的意义及其物质和仪式中的表现就能体现出这种“精神文化”,如:游牧时代婚嫁双方的家庭要隔七条河,代表无血缘关系;在系谱文化中,七代之内都是近亲;在纳乌鲁兹节时制作的纳乌鲁兹饭包含了七种谷物等。哈萨克族上述关于“七”的宗法习俗,叶舒宪在《原型数字七之谜》[8]中提出:“神话中的原型数七不仅是无限时间的象征,也应该是无限空间的象征。”及“七这个数字之所以成为原型数字并具有了宇宙象征意义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史前人类藉神话思维获得的空间。” 黄中祥亦在其文章《维吾尔、哈萨克语中的四十和七反映的文化特征》[9]中对数字七在哈萨克族信仰、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也有论述。
类似的“精神文化”体现在膜鸣类乐器上就是在乐器中有各自部落的口号和印记,这些印记与膜鸣类乐器一起构成了哈萨克族作为游牧民族的精神寄托。
三、膜鸣类乐器的音乐学属性
上文讨论了膜鸣类乐器在广义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领域的内涵及特质,下文中将以哈萨克族膜鸣类乐器为例,讨论具有物质属性的膜鸣类乐器在音乐学范畴中的特征,重点阐述膜鸣类乐器作为音乐文化事项综合载体的体现。
(一)物质人类学视野中的膜鸣类乐器
1923年,英国社会人类学开创者之一拉德克里夫-布朗曾指出:新型的社会人类性学应该是一门“不考虑历史的、比较性的及普及性的研究社会系统的自然学科。”这一论断导致了人类学界排斥以博物馆与物质文化的收藏为基础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成立了社会人类学研究实验室,关注身体与文化技术中的技艺的人类学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欧美人类学界逐渐重视物质文化的研究,以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为开山之作,他在书中呈现了物品何以能被视为人们被社会化为社会存在所需依托的首要方式。[10]
在人类社会中,所有物品的产生,实际上是人类思维“物化”的过程,物品则是人类思维的具体体现,如:哈萨克族的拨奏弦鸣乐器“杰特根”由七根马尾弦构成,这其中的 “数字七”与“马尾”就分别体现了哈萨克族传统文化中的思维习惯与生产方式。膜鸣类乐器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多的要数流行于中国南部地区及东南亚各国的“铜鼓”文化,如《东南亚铜鼓研究》[11](万辅彬、韦丹芳)。关于北方少数民族膜鸣类乐器的研究成果,以《鼓语——中国萨满乐器图释》[12]为代表,该书分为三个部分,以鼓为线索,分别以“萨满祭祀活动”“象征符号”及“世俗生活中的萨满艺术”为论题,探讨了作为萨满仪器具的“鼓”的流变。对哈萨克族膜鸣类乐器的研究,无论是人类学、文化学亦或是音乐学界,还未有成果,这为哈萨克族膜鸣类乐器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膜鸣类乐器在生产生活中的定位——以游牧文化为例
1.祭祀与治疗——与上天沟通的物质媒介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大自然未知之处甚多的原始时代,人们往往通过占卜、祭祀等方式实现与上天沟通。借助膜鸣类乐器的“声响”特性,实现人与上天的沟通,正如薇薇安·贝基在其著作《仪式时间》中认为“人们用铁器制造不协和及刺耳的声音”[13]。这种“不协和、刺耳的声音”是为了打破两个世界的隔阂,起到沟通的作用,正如游牧时代萨满法师在占卜及为人治病时使用包括膜鸣类乐器在内的“响器”作为打破平衡、联系法师本身与上天的媒介。
作为沟通媒介的膜鸣类乐器、宗教或疾病治疗的仪式行为以及仪式的接受者三者共同构成了“天人对话”的系统,膜鸣类乐器则成为沟通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膜鸣类乐器敲击的节奏、力度及宗教执仪者仪式动作的变化,都是人与上天交流的具体体现。
2.战争催化剂——鼓舞士气
《左传·庄公十年》中的《曹刿论战》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及“擂鼓进军、鸣金收兵”的记载,说明古人对膜鸣类乐器在战争中的对提振士气、鼓舞斗志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在少数民族中,膜鸣类乐器无论历史记载亦或现存使用都非常普遍,如:南方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各类铜鼓及北方少数民族各类皮质鼓面的鼓。
作为跨界游牧民族的哈萨克族,有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由于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殊影响,在哈萨克族的民间口头文学类别中数量最多的便是英雄史诗,哈萨克族在民族产生、发展、壮大的各个时期,与不同的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了如库布兰德、阿勒帕米斯、塔尔根等一大批勇士与英雄,也产生了相对应的英雄史诗篇章。
在文学的诸多类别中,口头文学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它与民间歌曲的传播方式类似,都是在民间以口头传播的形式流传,由各个时期众多民间即兴讲唱艺人进行搜集整理与传唱,因此也有与民间歌曲相类似的“母体”与“变体”的结构。口头文学的母体是一个个故事主题,一个完整的史诗篇章由若干故事主题构成,其中,在英雄史诗中不可或缺的故事主即为“战争主题”。膜鸣类乐器在战争主题的各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线索,起到贯穿整个史诗情节的作用,如:出征时的鼓舞、冲锋时的鼓劲、凯旋时的欢迎及见到爱人的激动等情景描述中,都有各类膜鸣类乐器的出现。可以说,膜鸣类乐器贯穿了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的每一个场景,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
3.音乐本体——当代民族小型乐队中的膜鸣类乐器
音乐学的研究中,首要任务就是音乐本体的研究,膜鸣类乐器作为诸多民族早期宗教法器起始,至战争时鼓舞士气的“军乐”,时至今日,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原有生产方式下的物品作用大多转换,膜鳴类乐器也转换成了纯粹的乐器。以哈萨克族为例,在当代哈萨克斯坦,有许多小型化民族乐队,如图兰、HASSAK等,它们具有鲜明的特点,如:具有浓厚的哈萨克族风格(穿着古代哈萨克族服饰)、小型化(人数在3—5人左右)、乐队由多种乐器构成(打击乐器、弦乐器、拟声乐器等)、演奏与哈萨克历史情节有关的乐曲等。膜鸣类乐器在这些民族小型化乐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演奏有关于古代战争情景的乐曲时,膜鸣类乐器起着模拟情景、烘托气氛的作用。
四、作为音乐文化诸多事项的综合载体——乐器学视野中的膜鸣类乐器
日本《音乐大事典》中对“乐器学”的定义及作用解释为:“乐器学不仅对作为物质或物体的构造、制作状况进行考察查,而且把考察范围扩展开来,对乐器与从乐器产生的音现象及至音艺术(音乐)的相干关系,人所具有的对于乐器视觉、触觉、听觉上的关系,在人的社会结构或者文化形成中乐器所具有的意义等,从尽可能多的侧面进行考察。”[14]乐器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而是与民族音乐学、音乐声学、音乐工学、音乐心理学等多学科相互借鉴,共同作用于乐器研究领域。同时,乐器学的研究亦可以反作用于上述学科。各国音乐学家都曾编撰乐器学相关文献,如中国《史记》中的记载及朝鲜《乐学轨范》、日本《教训抄》、印度《乐舞论》、法拉比《音乐全书》等。
(一)膜鸣类乐器的文化学意义
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中》一书中提出“把东亚乐器作为乐器发展的几个大的文化圈来辨别其所属,是通过乐器来考察音乐文化的潮流所必需的办法”,他参照德国音乐学家萨克斯用地理研究法进行乐器分类的办法,将东亚乐器分为9个相互关联、相互交叉的文化圈。同时,林谦三认为,一种乐器与一种文化圈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民族迁徙不断变化,因此,要动态的看待乐器的发展变化。乐器作为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民族成员的思维意识、习俗习惯的物化表现,如维吾尔族的达普,其形制为圆形鼓圈、蒙羊皮,若干金属制铁环栓于鼓内。羊皮,是维吾尔族物质生活、生产资料的来源,内部的铁环象征原始萨满教信仰时的仪式法器。又如,哈萨克族阔布孜,有两根马尾弦、蒙骆驼皮,两者都是哈萨克族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工具:牧民以放牧为生,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用品取自马匹,骆驼在哈萨克族转场时不可或缺。此外,阔布孜的形制、演奏方式等特征在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其他游牧民族中皆有体现。这个现象说明了膜鸣类乐器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乐器学研究中的膜鸣类乐器研究
《日本音乐大事典》“乐器学”词条对乐器学的研究范围有如下表述:乐器学不仅对作为物质或物体的构造、制作状况进行考察,而且需把考察范围扩展开来。一方面需要在对过去、现在、将来在历时性的展望中进行,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对各民族、各种文化,这种空间性乃至共时性的展望中进行。唯有这样做,才有可能进行超越时间、空间的综合性的把握。
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其代表作《音乐人类学》[15]一书中提出“文化中的音乐”这一定义,意在将音乐作为文化整体的一个构成部分,音乐的发展变化与其共生环境息息相关。对膜鸣类乐器的研究也同样如此,要进行“文化中的乐器研究”“文化中的膜鸣类乐器研究”。要对一类膜鸣类乐器进行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到乐器本体,即乐器学的研究,还需要关注与乐器相关的自然、人文等因素对乐器的影响,综合考量。针对膜鸣类乐器的研究,在基于乐器学理论分析膜鸣类乐器本体之外,还需注意从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角度关注膜鸣类乐器的存现状态及与其相适应的环境之间的关联。
五、结语
本文运用物质人类学、乐器学、音乐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成果,结合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等历史文献中有关膜鸣类乐器的记载,论述了乐器作为音乐文化诸多事项的综合载体,为笔者后续的乐器研究提供了史料文献、奠定了研究基础。
注释:
1.《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斯坦利·萨迪、约翰·泰瑞尔(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
2.《东亚乐器考》.林谦三(日)著.钱稻孙(译).曾维德、张思睿(校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8月
3.《中国乐器学概论》.刘勇.人民音乐出版社,2018年3月
4.《物质文化与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麦克·罗兰专访》.麦克·罗兰,卞思梅.《民族学刊》,2014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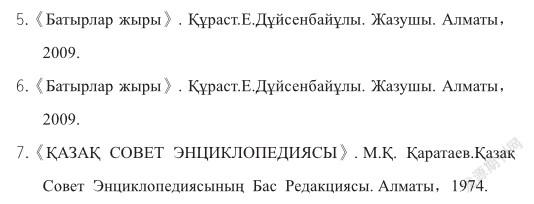
8.《原型数字“七 ”之谜——兼谈原型研究对比较文学的启示》.叶舒宪.《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9.《维吾尔哈萨克语中的四十和七反映的文化特征》.黄中详.《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3卷第2期
10.《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迈克尔·罗兰(著).汤芸、张原编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6年11月
11.《东南亚铜鼓研究》.万辅彬、韦丹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1月
12.《鼓—中国萨满乐器图释》.刘桂腾.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11月
13.《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迈克尔·罗兰(著).汤芸、张原编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6年11月
14.《日本<音乐大事典>词条“乐器学”》.[日]杉田佳千、山口修,应有勤译、罗传开校对.《乐器》,1994年04期
15.《音乐人类学》.(美)梅里亚姆(著),穆谦(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4月
作者简介:刘晓晨(1990-),男,浙江,汉族,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学。
3724501908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