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时代的刑民责任界分与承担
2021-03-10晓今
晓今

2020年12月6日,第十一届博和法律论坛在上海举办
《民法典》的颁布使我国正式构建起了系统性的民事法律体系。在《民法典》实施之际,刑法如何与时俱进与之衔接协调,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热议的焦点话题。如何解决刑民法律关系的交叉与竞和,如何明确刑民法律关系责任的界分与承担,如何协调刑民法律价值选择与规范体系等问题,都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研究价值。
本届论坛主办方为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上海市普陀区法学会、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在主办方的欢迎辞中,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主任林东品认为:“刑民交叉、界分、协调问题的探索已不再是一个法律应用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对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制度,甚至法律文化等一系列涉及法治本源的深刻追问;也不再仅仅是实现个案公正的现实需要,而是实现核心行业法治大衡的必由之路。”也正是基于这点,论坛邀请了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多领域、多学科的全国知名专家学者,邀请了资深检察官、法官、律师大咖,共同探讨民法典时代罪与罚的相关议题。
“我们是不是要出刑法典呢”
施伟东/上海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
在民法典时代,我们刑法人,特别是刑法学的专家学者怎么面对刑民交叉问题?我们要针对界分刑民交叉问题做出有效的协调,首先是慈悲心肠,再是雷霆手段,应该以谦抑审慎的态度来把握法律的实践、认知。
受《民法典》出台的激励,现在有学者提出我们是不是要出刑法典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可考虑的选项,但前提是研究,对于未来中国法治建设,如果需要一部刑法典,我想在大家的努力下是可以推動实现的。
“重刑主义在刑民关系中留下了很多负面影响”
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刑民关系发展到今天,跟它的历史走向是有紧密关系的。
中华民族在法的观念、法的源头、法的制度上一开始就是以“严刑竣法”登上历史舞台的。据史书记载,中国最早的刑事案例是以“刑杀立威”开始的。《国语》和《韩非子》都有记载:传说禹会诸侯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怒而杀戮之”。我想不过就是违反行政法规或者说最多对禹有点不尊重,何必杀头呢?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以刑杀可以立威,以刑杀可以维护权贵。
重刑主义让我们在刑民关系当中留下了很多负面影响和沉重的包袱。我想用六个方面来加以概括:
一,“先刑观念”模糊了刑民界限,造成了刑法一法独大的局面;二,“先刑观念”违背了刑法属于第二次违法规范形式的原理,损害了前置的权威性;三,“先刑观念”助长了社会的猎奇心理,大量浪费司法资源而效果适得其反。四,“先刑观念”必然会增加犯罪总量,加重了监狱的关押压力;五,“先刑观念”会助长一些人的哀情表演,通过社会舆论“绑架”司法机关;六,“先刑观念”往往会导致片面解释刑法,造成刑法技术运用的走样。
“刑法和民法的观察角度和解决方案有很大差异”
车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刑法和民法虽然不是包含性的全面接壤的关系,但也是接壤程度最高的两部法。过去我们一直讲刑法是民法的保障法,但实际上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实际上这两个法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刑法相对于民法而言有一定的独立性,也表现出某种重复性。独立性体现在双方有的时候会共用一个法学概念,但仅仅是形式和名称相同,这个概念的实质内容和界定方法差别很大。另一方面,在有些不同的概念当中刑法内容的确立也会受到民法的影响,这就是刑法相对于民法的从属性。独立性首先体现在思维方法上,我个人觉得刑法更侧重于实质性的思考,民法更强调规范性思考。比如我们都知道民法可以根据一个人失踪的时间来决定他在法律上、规范上成为一个“死人”,进而展开财产分割,但是对于刑法来说必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对于死亡,民法可以规范性地决定,刑法则必须事实性地认定,如果一旦出现规范性认定,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很多“亡者归来”的冤案往往就是由于没有践行刑法“死要见尸”这样一个事实性认定所造成的。当然,有的时候刑法也有强调规范性的部分,比如刑法规定14岁年龄以下不负刑事责任,但是一个13岁的杀人犯事实上完全理解杀人的含义,一个15岁或16岁的智力异常儿童可能脑子不太灵光,只能给那个13岁的少年当一个跟班,但是13岁杀人不负刑事责任,15岁杀人要负责任,这是刑法规范上的界定,这个时候不去考虑某个犯罪人事实上的认知和控制能力。除此之外,刑法和民法的规范目的不同,社会任务不同,因此有的时候面对同一个社会现象,观察的角度和解决方案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个人信息保护更多是民刑互动的问题”
韩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企业合规与监察研究中心主任:
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民刑法之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保护的客体。民法规范对个人信息的界定划分为私密信息和非私密信息,分类的意义在于从个人行动自由、生活安宁和人格尊严角度对个人信息作出区分。
而刑法规范是将个人信息区分为所谓的个人敏感信息和个人一般信息。其背后所代表的立法逻辑可能还是考虑到个人信息中所承载的行动自由、人格尊严,同时反射出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因此,两个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出发点、落脚点有差异,但的确是互相关涉的。
民法尽管强调人的识别性、人的尊严、个人身份的还原性,但是对个人身份的还原性的考虑也事关公共秩序、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同时,尽管刑法从公共秩序入手来规范个人信息和分类个人信息,但是它一定指向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行动自由。因此两个立法在立法目的上是高度交融和高度结合的。
第二是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益范围的差异。关于这个问题,民法的视域,个人信息本身不具有法律保护地位,保护个人信息更多是从对个人信息的数据、素材所反射、承载的特定的人身权益、人身利益的保护来加以考虑的。
而刑法的个人信息保护除了个人的人格利益以外,更多的还是考虑一种超人格利益、超个人利益的法律范畴,也就是经由个人的人格法益上升到公共利益、社会秩序乃至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保护。
第三个就是关于民法和刑法对于侵害个人信息不法行为不法性界定的差异,这是一个理论难题,也是民刑交叉、交融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一般认为在民事侵权责任的范畴里面,界定行为的不法性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如果一个行为直接侵害了绝对权,这样的行为天然具有不法性。比如说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等。第二个层面,违反保护性的法律是构成民事不法行为的第二个认定标准。当然,保护性的法律本身也有其局限性,成文法国家的规范总有一些漏洞和不足,因此我們还发展出来第三个规范,就是以故意背离公序良俗的方法加害他人利益的,是作为民事不法行为一个兜底性的规定。
“怎样在刑民交织的案件里追究刑事责任呢”
张绍谦/上海交通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关于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区别主要有七点:第一,体现了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同,刑事关系是国家和犯罪分子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公法关系,体现了惩罚和被惩罚,而民事关系体现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自治关系;第二,法律责任的本质不同,刑事责任体现的要么是道义和谴责,要么是社会责任上的预防和矫治,而民事责任本质是利益的恢复和社会关系的修复,它体现的是对被侵害者个人利益诉求的满足;第三,两种法律责任的正当性基础不同;第四,法律责任的严重程度不同;第五,法律责任的规范依据不同,刑事责任依据的是刑法,不允许法外制裁,而民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是《民法典》,追究民事责任,除了依据法律规定以外,一定条件下还允许根据传统习惯、公序良俗等非民事法的规定来进行裁判;第六,强制性和专属性程度不同;最后一个是法律责任的追究程序不同,刑事责任必须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来追究,一旦起诉,除非是自诉案件,否则就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而且对于证明的标准要求比较高,而追究民事责任程序相对比较宽松,而且证据的证明没有要求达到必须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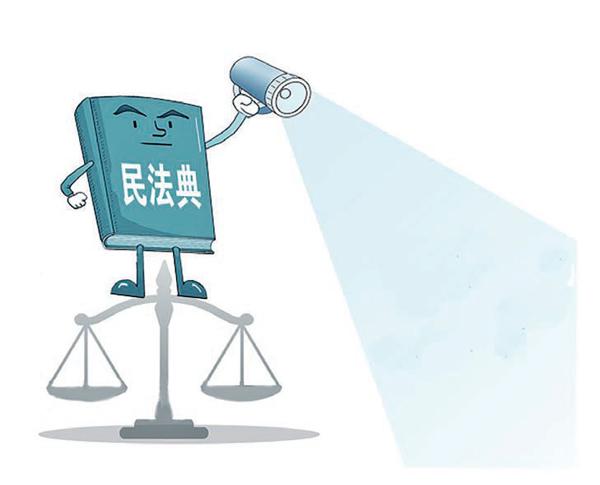
有的时候一个行为同时产生刑事、民事两种责任,但因为追究的程序和证明标准不同,导致无法满足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要求或者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明标准时,案件性质就可能转为民事案件,追究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在刑事、民事交织的案件里面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个人感觉基本思路有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严守罪刑法定原则,避免刑法介入民事纠纷;第二,要坚守刑法谦抑精神,避免滥用刑事责任;第三,要重视刑法二次规范的性质,正确协调刑事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第四,惩罚犯罪应当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并重,要重视社会关系的修复;最后,需要根据刑民责任的不同情况区分处理。
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司法认定时首先必须严格区分,不能混淆,让刑法的归刑法、民法的归民法,让可刑可民的尽量归民法;其次,要充分重视发挥两者的作用,该并存的并存,该转化的转化,该影响的相互影响,使两种责任在我国整体法律体系中和谐相处、协同作用。
“我非常赞同刑法的归刑法,民法的归民法”
朱晓喆/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所所长
本质上来说,刑民交叉其实是一种法律的竞和现象,我们在刑法内部有各种法条的竞和,在民法内部也有各种请求权的竞和。现在刑法和民法同时去关照同一个案件事实的时候也发生了竞和。刚才张老师讲刑法的归刑法,民法的归民法,要依据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截然不同的构成要件认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后果,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
民法对于损害赔偿、财产返还有相关的认定标准,而且是比较开放的。民法已经到了对于受害人的权益保障比较成熟的程度,刑法为什么要固步自封呢?我们是不是要把刑法中保护受害人财产权益或者精神损害赔偿权益的部分功能交给民法?我观察了很多实践当中的案件,涉及刑民交叉的案件,大部分可能是操作衔接上的问题,所谓民刑交叉或者民刑冲突究竟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我是比较存疑的。当然,最后司法机关在处理交叉案件的时候最好进行协调,以实现法秩序的统一。
“数据能不能作为刑法当中的财物”
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眼下,当我们说刑民方面法秩序统一性的时候,只是以行为性质作判断,应该遵守一种原则,或者非法,或者合法。但是相同概念有可能要做不同的解释,这里面就涉及民法对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是有三分的,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都有可能作为刑法上的保护客体。而财产犯罪是以传统的财产犯罪理论,即以侵犯物权和侵犯债权的框架建立起来的,其行为对象和认知客体不包括知识产权。
当然,有一点也必须要承认,我们刑法当中对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的保护的确不只是为了保护民法中抽象的权利,我们是要使得民法对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的行使,在现实上成为可能,所以我们保护的是事实性的支配、占有。如果有不法行为人要直接拿走你的财物的话,你在民法上的所有权不受影响,但是你作为所有权人对于所有权的行使就会受到阻碍。
眼下刑法保护模式当中对于一般财物的保护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区分的,我强调的是,数据能不能作为刑法当中的财物?在讨论虚拟财产的时候,刑法学界比较主流的观点往往认为它具有经济性的意义,可交换,直接把它放到财物当中。可是我们发现数据本身跟知识产权一样,它是具有共享性的,但是跟知识产权不同的地方就是知识产权的权利具有专属性,而数据不具有专属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不放到一般财物当中,为什么权属更加薄弱的数据能够放到财物当中保护呢?这一点显然是值得反思的。
民法上的占有和刑法上的占有,因为保护目的、构成要件的不同,一个偏重于事实,一个偏重于规范。
“我不太赞成说‘刑民交叉是伪命题”
姚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不太赞成说“刑民交叉是伪命题”,哪个刑事犯罪不涉及民事啊?今天很多学者都提到了不同的构成要件、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价值判断,诸如此类,这才有衔接的问题,而且是全方位的。
另外,两个法的角色功能是不同的,在社会规范体系当中的定位不一样,是不是有一个先后或者手段上适用不同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在评判民事法律行为时,适用的法律当然首先是民事法律或者司法规范。
民刑两法在衔接的时候要考虑到一個原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刑法是作为最后手段,要先从民法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法律有能力解决过去的问题,也有能力回应新发生的情况”
黄祥青/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就刑民交叉问题,我谈三个具体的观点。
第一,刑民交叉问题讨论的范围。一些具体的行为究竟是属于犯罪行为还是属于一般的民事违法行为,犯罪的界限界定在何种程度?这样的问题是经济活动当中一个罪与非罪的问题,可以去普遍讨论的。严格来讲,刑民交叉应该是两个主体同时并存。对罪与非罪的问题,一旦法律的界限和政策明确以后,要么就是一个刑事犯罪的问题,要么就是一个民事违法、追究民事责任的问题,并不存在两者同时并存和交叉。所以把这样的问题区分开来,是有利于我们行业对刑民交叉问题进行更深一步讨论的。
第二,讨论的标准问题。我认为无论是按照同一法律关系还是同一事实,似乎都不及用行为更能够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用行为的观点来看,它是法律关注的重点,法律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都共同关注行为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可以把单一复合的主体和复合的行为看作是复合行为,复合行为就应该在一个法律体系下,或者说有秩序地在多个法律体系下分别进行评价,而不能对复合行为刑事作刑事评价,民事作民事评价,甚至得出明显背离的评价结论,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认为,刑民交叉问题研究的基础对象首先要聚焦行为问题,行为包含单一行为,也包含复合行为。
第三,我们聚焦这些行为,聚焦相关的重点问题以后,如何来解决它的法律责任问题。对于同一个问题,刑事和民事法律都有规定的情况下,应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我们在坚持这些手段的前提下也应该关注现实和未来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法律、规范更多地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形成的经验、规则,但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许多新问题尚未形成立法和司法解释等有效法律手段,这些新型问题能不能用既存的法律手段去解决呢?我觉得法律有能力解决过去的问题,也有能力回应新发生的情况,不能说我们的法律对于未来没有规制效力。当然在有规制效力的情况下,我不主张刑法一定要坚持二元规制,应该允许有例外。
“刑事法领域看待民刑关系,很大程度是立场的问题”
孙万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
民法典时代的罪与罚也好,民刑交叉也好,民刑界定也好,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既包括对刑事法益、民法法益该怎么理解的问题,也包括对规范性本身该怎么理解的问题,当然还包括解释观念的问题、程序方面的问题。
刑事法领域,我们怎么来看待民刑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立场的问题。各方专家学者各取所需,表现出了从自身角度出发看待问题的合理性。
《大禹谟》的一段话:“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某种意义上,我们如果堆集大量的案例以后,你会发现它就是“罪疑惟轻”。中国古代,法官适用“罪疑惟轻”的案例是非常多的。
很多学者讲到刑法是最后的保障法,最后一个关口,最后一个手段,最后一个结果,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形式性的概念,并不能因为刑法是保障法,就说只有建立在前置性违法的基础上,刑法才能介入。刑法的独立性表现在哪里?轻犯的法益到底是什么?当一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被害人个人的侵犯,还具有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时候,我们刑法要评判的不再是被害人和被告人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侵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说故意杀人罪到底是因为民事侵权侵犯他人的生命而构成的犯罪,还是它天生就是犯罪?我们刑法学者非常困难,也非常痛苦,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涉及前置法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标题是“民法典时代的罪与罚”,这个名字起得不仅好,而且很有文艺范儿。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叫《霍乱时期的爱情》,是讲一对恋人50年的时间里,经过了战争、瘟疫,然后共同维护爱情的尊严。同样,今天我们在这个主题下进行探讨,我觉得非常贴切。希望在座的专家学者们也能用自己人生的50年时间守望、保护我们的司法公正。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