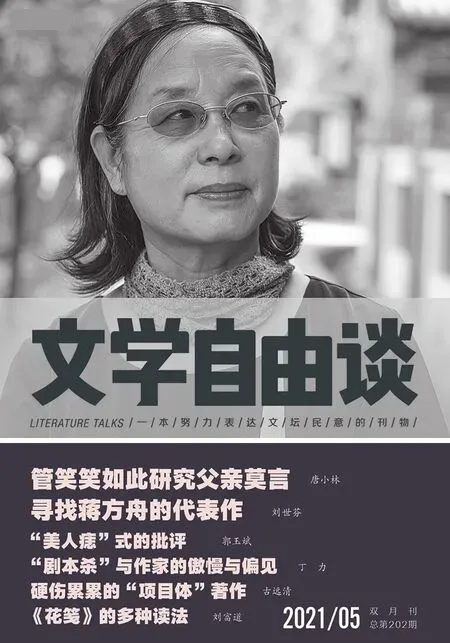在高端“躺平”的诗歌
2021-03-08□铁舞
□铁 舞
忽然,很想借用一下在网上很火、还上了热搜的“躺平”这个词。
制造一些舒适的话语,然后在自己的话语床上“躺平”——这是在读上海《思南文学选刊》里的一些诗歌后,感到很不舒适的感受,虽然我很喜欢这本杂志。这是上海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由几位青年批评家操持的一本文学选刊,据说是在新媒体文化环境下,强势回归文学初心,探索社会化办刊思路的一次尝试,希望可以起到推广品质阅读,营造都市文化氛围的作用。由一批青年批评家遴选的这样一本刊物,我相信能指示未来。
因为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诗歌究竟怎么啦,它未来的属性究竟在哪里,等等,于是又集中读了从2017年到现在《思南文学选刊》里的诗歌,却不免产生了很多疑问。我并不认为这些诗歌是优秀的。选者的口味有点洋气,被视为“海上高雅”,但他们确实是我在本文一开始说的“制造一些舒适的话语,然后在自己的话语床上躺平”——这种并不让人窒息,但又是一种让人慢慢“温入”的自我愉悦。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碎片化日常,生活表征优化缺失
我想先举一首《点燃我的每一个字》的诗为例,全诗九个章节,一百多行。我之所以举这首诗,因为这一首表现的是上海,而全篇却都是个人的小情绪。诗中类似“你说了句暖心话,一瞥间/甩出个满星满月的水袖/刷屏洒落小红花”的句子,不算轻薄,但也够“湿嗒嗒”的了。或许这是一种口味,不知道是否像冰柠薄荷味。我并不喜欢这首诗。在徐家汇这个地方,我写过《地铁建设者》,那种开膛破肚大开挖的场景,你没有见到过;我写过《徐光启夜观天象》,衡山路的夜风景我也写过。然而,读《点燃我的每一个字》这首诗,更让我感觉像是咀嚼绿豆芽似地稚嫩,它似乎在表现魔都人的羸弱,没有东方巴黎的豪华、开阔。这样的诗能和彼岸纽约诗人对话吗?当然,用这一首诗来证明所有的上海诗人,也是不对的。我不说这种品质不好,但一定不是最好的。读一首诗看它的开头和结尾就知道了。且看第一节:
我记载你的繁华/没能放下/一只白帆的气球逼近/系了领巾的气球/挂在炫然一新的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尖顶/在孩子满街快乐的一天/绿灯了,你伫足远晀
再看第九节:
去,去喝世界的啤酒/衡山路上,吧台成排/你中了彩我套了房他换了车/小外撩妹无需爱马仕/衡山路的周末夜未央/击鼓传花喝了这吧又那吧/街角飘来叹息的吉他/父老乡亲啊,我回不去了/醉醺醺看到我妈的微信/小心他给你的糖,是假糖/街坊叫我妈雷锋大妈/死了好几年,还不肯闲着/伤心的吉他又哼哼唧唧/我的家乡发大水,求你了/刚喝嗨,妈的微信又来了/那个放空债的,要来打卡了/反正我信妈,她的话特灵/一个个没喝完,都做了鬼去/去,去衡山路啤酒的世界/街角飘来悠扬的小提琴
中间部分我们就不要读了吧。上海人是蛮喜欢讲格调的,这首诗说得上是“上海格调”吗?我认为是,也不是,至少调门还不够高。上海人的善良、温暖、柔润、坚强,我就没有充分感受到。
作者陈建华是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著有《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等,是一个学者型的海归诗人。编辑之所以选录这首诗,可能读出了这首诗的“洋”气,很适合编辑部的口味。——我的担忧也在这里。陈建华没错,他怎么写我们管不着,作者写诗只是放松自己的手段。但占着选刊位置的年轻人,你们的口味决定着诗坛的导向。我们在刊物里读到这首诗时,还以为是一首长诗,其实这些诗是作者在不同时间段写下的一些片段感触,并无完整的创作构图,这从网上查阅,就知道了。选刊刊登时,删去了作者的写作时间,所以细读下来就感到是碎片化的组合。全诗弥漫着一种病恹恹的感觉,我想为什么到九段就结束了呢?还可以平“淌”下去呀!
我想再强调一下,诗人怎样写、写什么都不是问题,我们无法去教导诗人。然而,刊物选什么,无疑有着极大的主观性。既然是“品质阅读”,我们又能读到什么样的品质呢?上海诗歌要都是这样“软不拉几”的,实在愧对了这个国际大都市。我实在不知道读完这首诗后,如何能够“点燃”它的“每一个字”。
二、场独立性缺失,滑向“佛系”依存
作为一本文学选刊,自然不会只盯住上海本地诗歌,它选编的眼光一定是全国性的。下面我们就看一首著名诗人陈先发的《词在奔向对应物的途中》,选自其诗集《九章》。光看题目就感觉作者非常聪明,他并不像陈建华那样“一路平淌”,而是选择了“杂咏”,你就无法用“整体”这样的视角去要求他了。
读陈先发的诗,我感受到的是一种阴郁。他打造出来词语空间的品质就是阴郁,虽然说诗人忧郁甚至病态都很正常。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且举这一首《群树婆娑》为例,可以看出诗人的写作状态:
最美的旋律是雨点击打/正在枯萎的事物/一切浓淡恰到好处/时间流速得以观测//秋天风大/幻听让我筋疲力尽//而树影,仍在湖面涂抹/胜过所有丹青妙手/还有暮云低垂/令淤泥和寺顶融为一体//万事万物体内戒律如此沁凉/不容我们滚烫的泪水涌出//世间伟大的艺术早已完成/写作的耻辱为何仍循环不息……
这一首似乎是质询“写作的耻辱”,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升华一下,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也许是最根本的,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最核心处开始推理,他为何这样写……是对自己的写作不满吗?这种质询的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是“万事万物体内戒律如此沁凉”,“淤泥”和“寺顶”的寓意很明显。世间伟大的艺术早已完成,诗人还写什么呢?诗人的写作一直处于病恹恹的状态,选刊的十首,像孤岛、碎片、死者、躯壳、灰烬、消失、黑暗、呜咽,这类词占据了大部分诗篇,成为常用词,每读一篇都感觉到压抑,感觉到诗人患了死亡恐惧症,唯有以写诗来平衡自己的内心。诗人甚至怀疑究竟活在哪里。这是不是深刻?搞不明白。
再看这一首《葵叶的别离》:
露珠快速滑下葵叶/坠入地面的污秽中/我知道/她们在地层深处/将完成一次分离/明天凌晨将一身剔透再次登上葵叶//在对第二次的向往中/我们老去/但我们不知道第二只脚印能否/精确嵌入昨天的//永不知疲倦的鲁迅/在哪里/恺撒呢//摇篮前晃动的花/下一秒用于葬礼/那些空空的名字/比陨石更具耐心/我听见歌声涌出//天空中蓬松的鸟羽、机舱的残骸/混乱的/相互穿插的风和/我们永难捉摸的去向//——为什么?//葵叶在脚下滚动/我们活在物溢出它自身的/那部分中。词活在奔向对应物的途中
这组诗的标题“词活在奔向对应物的途中”就出自这一首诗中。如果我说这首诗写得很放松、很自然、很亲切,那说明我的心理有问题。
后来我还读了选刊之外《九章》诗集里其他一些诗,如《膝上牡丹花》《死者的仪器》《渐老如匕》《梨子的侧面》《身如密钥》《滨湖柳》等,无一例外地指向衰老和死亡,格调一片灰暗。我看到有人评论陈先发的诗歌,其中有一个说法:恰如他自己所说,是“写碑”,简洁而又深刻,留白也很多,意味深长,这正体现了陈先发对本土化美学的追求。他的语言融合了古典诗歌的凝练和现代语言的灵活,超越了不中不西的翻译体,真正形成了个人特色和美学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力的风格。——这些话显然是过奖了,单说所谓深刻吧,现代诗人似乎都以把诗笔指向死亡即为深刻,这种“泛死亡”的指向,多少说明一些诗人写不下去了,于是就在“天堂”前徘徊,找一张“死亡”文化的床“躺平”一下。而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远不如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他的《死亡也并非是所向披靡》,那铿锵的调子多么鼓舞人心。
还有人评价:《九章》体现了一种史诗意识或史诗抱负。这史诗既是他自身的一种心灵史和精神史,同时也包含着社会史。这个结构富有开放性,是把社会各方面,天地万物、社会经济、众生百态都整体涵盖其中的一个体系。在这方面,陈先发达到了一个典范性的创作状态。——这显然是捧场到极致了,把这些话放到其他另一个人身上,恐怕也说得过去。
据报道,陈先发诗集《九章》出版以来,引起诗坛广泛反响。有评论家认为,诗人陈先发创作生涯逾三十年,诗歌成就卓然。《九章》系列文本的完成,标志着他由个体诗人到总体诗人的转换。——我不禁想问:什么叫“总体诗人”?我并不认为“总体诗人”是一个不好的称呼;恰恰相反,我希望有这样一个总体诗人,就像惠特曼歌唱的:“无穷”——“整体”的思想呵!诗人揭示隐藏在人类感情及行为背后深不可测的内心自我,似乎应该在这一点上定位才对。如果说他是一个总体诗人,我们没听到他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如果说已经走向整体型认知,那么他对世界总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能坚定地说出“世界首先是坏的”吗?如何认识这“坏”?在一个“坏”的世界里,如何为坚守理想而唱哭?可以说,陈先发的诗没有生气,《九章》以一种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语言的舒服区,不是高端“躺平”是什么呢?可见我们一些舆论看似热烈的背后,实际上充斥着毫无营养的评价和泡沫。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盯着陈先发的诗说话,皆因他太有代表性了。我发现,不少著名诗人,步入老年的标志就是喜欢谈论死亡,喜欢从原先开阔的社会视野,转入个人内心的阴暗,在天堂门前徘徊,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和世界接轨。现在好了,这种情景像细菌一样过早地传染到青年诗人们身上,似乎这样能早早地攀附上人生高端的成熟,他们的诗就能和陈先发媲美了。在这本选刊里我读到很多这样的诗歌,他们常常空叹人生,滑向“佛系”依存,场独立性缺失。如“厌倦了生而为人,我持续善行,是为了托生成世界尽头的海豹”(倪湛舸《进化论》),“大风即起,摇落了众生窃窃私语的耳朵/啄食的燕雀也将四散”(江离《游上天天竺法喜讲寺后记》),“于一盏新茶的气候中我看世间轮回如叶片/甘味去尽/茶苦滞留 你又从《碧岩录》的第一页翻起/只与菩萨相悦”(嘉励《湖上》),等等,不是说这些诗写得不好,而是说这些诗整体上呈现的精神面貌是下落的,甚至是萎靡不振的,看不到时代精神。也许诗人们也应该学会回溯事物的本质,重新思考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该怎么写了。
三、散装语言,艺术结构的精致性缺失
令人感兴趣的是,我读到一组朱琺的《诗经今译》,在新诗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上,我欣喜地看到人们在做着种种实践。我读朱琺的《诗经今译》,不亚于读到洛夫先生的《唐诗解构》。关于洛夫先生的《唐诗解构》,我曾经发表过看法,那不过是习诗的一种手段,朱琺的《诗经今译》使我又想到同样的问题。选刊选了《蔽甘棠》《厌行露》《摽有梅》《野有麕》《日月诸》《击鼓鼞》等,这些译文颠覆了传统的译法。我想从朱琺的《诗经今译》里选一首有代表性的诗作来分享,其他的就不做更多的分析了。
我曾就这首诗在微信群做过一次阅读调查:一首《诗经·关雎》被今译成这样,你们如何看?——
关雎鸣
那漂在黄河上的绿色岛屿,/定睛看来竟是雎鸠沉静下来的/鸣音。我处在未来的目光/穿过成双飞鸟,寻求妳/留在这里的曼妙安静的身段。//但挡住去路的是我的睫毛/深深嵌在我左眼和右眼里/宛若参差不齐的荇/水里一种已经陌路的食物/被梦境和清醒分别啮咬。//我在昼夜之间不知疲倦的左右翻滚。//我不停变幻着身法手势/绕开所有漂浮在水里的思绪/眼看着正在变成行动的隐喻/又像要走过琴瑟表面/一根根高高在上的丝弦。//谁知道我最擅长于虚构婚礼/任凭人群把我的左右手/都束缚在微笑里。但是谁/居然找回那些圆如锺鼓的声响/妄想去呼应最漫长河流中一曲/妳那时还曼妙安静的身段。
我注意到原作的题目《关雎》,在朱琺的笔下变成了《关雎鸣》,似乎着重倾向于一个“鸣”字。我还注意到选刊里的诗篇都以这种方式取题。整篇文字不是一对一的,而都是现代散文式的分行。微信群里的一些人陆续发表看法,涉及三方面的事实:一、传统和现代;二、为什么可以或不可以这样译写;三、假如这不是一首译诗。第一反应是专家型的:“外文或古典诗词的译作应遵循原作原意而译成现代语言,朱琺先生是依原题而改作,与译无关。”(海客)还有很多人表示不喜欢。也有引起一些积极反应的,有人甚至还拿出自己译写的新格律体作品与之对照。朱琺的翻译显然是今天的年轻人随意性很强的自由译写,只是和原作沾着点影子,语言是散文式的装配。说到这一点,我发觉《思南文学选刊》里诗的语言大都是散文化的,如“不断回旋上升的是谁的灵魂?薄明时空虚的穹窿,粗粝的条石与飞肋的棱线究竟能勾留住多少愁?”(汪涌豪:《但还是相信》)“晚饭后,夜垂下来/父亲习惯去河边散步/尽管饭前的争论/依然像牛羊的嘴,缓慢地/吞咽着细节地部分/即使这样”(张猫《陪父亲散步》)……这反映了今天新诗写作的一个普遍倾向:平滑流畅。然而,结构性的语言艺术的精致性缺失,好像根本没有人注意这一点;似乎语言的散装化、随意化是天经地义的,没必要质疑。我不完全反对朱琺的创新译法,我认为这是现代派的后制处理,好像一幅现代书法,有时候只是取其一角,做抽象处理。只是谓之“译”,需要重作一些解释。
在我眼里,《思南文学选刊》是一本优秀的刊物,它选的诗,未必是一些“排行榜”所青睐的,这证明还是有选编人独立的眼光。然而,即使如此,我仍从这里读出了一点中国诗歌的“危机”。当发现这些诗歌在某个高端上也是“躺平”的时候,我就想,由这样一些诗歌决定中国诗歌的未来,有点于心不甘。于是拿起笔来写这篇文章,希望以后在所选的诗歌里,能看出大气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