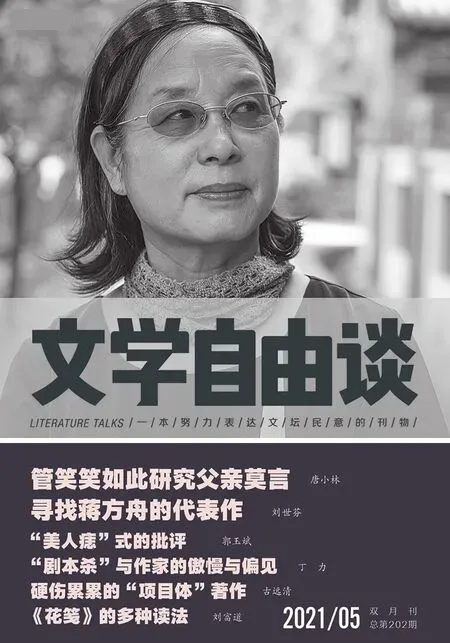寻找蒋方舟的代表作
2021-03-08刘世芬
□刘世芬
2021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关注到一部新书《跟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这是青年作家蒋方舟的科幻新作,书名的长度不知能否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我“饶有兴味”地读完,却没有期待中的兴奋,一头雾水中嗅出一丝跟风赶浪的痕迹。蒋方舟似乎是在赶一波科幻热,但显得却不那么笃定。
这部书对我的吸引,除了书名的噱头,还有书的内容简介中显露的“疫”迹,疫中读“疫”,就有了别样的“疫”味。突然就想:这部科幻小说,算不算蒋方舟的代表作呢?于是问身边几位作家朋友:蒋方舟的代表作是哪个?他们竟约好似的语塞,有的说“没读过”,有的“读得不多”,有的则把“少年天才”“清华破格录取”等名头搬上来。一个大红大紫的天才作家,谈起她的代表作却含糊其辞,这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
《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下称《散步》),收录了四篇小说:《在海边放了一颗巨大的蛋》《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在威尼斯重建时间》《边境来了陌生人》。这四个故事均发生在浩瀚的宇宙,但年代不明。题材涉及外星的馈赠、时间的失序、历史的自我重复等,名为“南十字星”的星球贯穿全书,堪称星际漫游,充满幻想又与现实的世界若即若离。第一个故事“缝合”了一块石头和外星人,整个石头来源于外星人的游戏,人类的大发现不过只是一个球;第二个故事有了当下疫情的影子,一条主线“再现”了《鼠疫》和“新冠封城”情节,外加反战思考和一些《1984》的路线,另一条主线借鉴了前几年讨论的人类科技文明终极形态的故事,总之就是“鼠疫”加“新冠”的变种;故事三是关于平行宇宙和时间旅行,穿插主人公和父亲的观念冲突;故事四有“罗生门”的味道,再加一点《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来自星星的你》的套路和痕迹。于是有网友直接把这部书简称为“缝合”和“再造”。
我一贯想象力贫乏,经常看不懂那些火爆上映的科幻大片。记得韩少功说过:一个问题我想清楚了就写论文,想不清楚就写小说。此时的《散步》就有些怪异,仿佛一些不太过关的翻译:生硬、刻意、做作、故作高深。相较于蒋方舟先前的杂文和散文,此时这部小说显得尤其不够真诚。
当然,从这部科幻作品可以看出蒋方舟是多么努力地尝试新东西,她无疑是想取得“巨大突破”,但表现在作品中却是想把太多的东西塞进去,元素太多,虚实杂糅,借鉴过度。比如,行文直接化用博尔赫斯、艾略特等大师的经典意象和名句,情节也常有某种即视感。对科学概念描述的硬伤,或许正显示出一个文科生的软肋,作者本身的科学素养和素材组织能力难以撑起这样宏大的话题,以至不能简洁且准确地交代故事所涉及的科学概念,或解释拖沓、表述不清。难怪有读者认为,《散步》最大的缺陷是“形式大于内容”。相对于文中突兀出现的看似深刻的哲理性总结,这本书的实质内容十分杂乱隔膜,语言撑不起内涵。
我并非反对蒋方舟为科幻发声,问题在于蒋方舟是否有必要“赶”这个“场”。如果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虽不够“硬科幻”,但“软”到脑洞大开,有太多现实主义批判的意味,那么,蒋方舟在《散步》里则只是借用了科幻这个吸睛的外壳,其新意的匮乏,中庸而讨巧,不能不说是给她减分的。
蒋方舟的写作经历,在她的各种简介中比比皆是:七岁写作,九岁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打开天窗》,十一岁出版《正在发育》,同年给《南方都市报》供稿;十二岁写成长篇小说《青春前期》《都往我这儿看》,开始成为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十五岁出版《邪童正史》,并获“中国少年作家杯”一等奖;十六岁当选中国少年作家学会主席,十七岁出版首部长篇小说《骑彩虹者》。
《正在发育》的封面,用的是蒋方舟稚气十足的娃娃脸,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还拱在母亲怀里撒娇,可此时的蒋方舟已经成为小小作家。据说,蒋方舟从四岁到七岁,已经读了好几千本书。梁文道以前也曾说,蒋方舟的问题是看书太多了,这似乎也印证了那“好几千本”。
蒋方舟在《打开天窗》中谈到孩子的心思常常比大人难猜,他们也产生嫉妒、憎恨、厌烦……他们也会跟风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他们眼里也不尽然全是美,也有丑与恶。天真如孩童,深沉亦如孩童……
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蒋方舟的“高情商”。那一时期的童书里,她曾写到作为女生的小心思,比如一个亲戚家的小女孩,“她长得比我好看,五六岁时,眉眼间就有种少妇的俏丽”。那女孩“比我受宠和娇纵,爱生气,总爱把人锁在门外,动不动就让人哄”。于是,还在学前班的小孩子,竟玩起了心计:“我就暗自决定成为‘成熟懂事’的那一个”。当那个小亲戚大闹饭桌,忙着挑食,尖叫着挣脱种种食物安排,五六岁的小方舟却“连连欠身,含着下巴面带微笑,给在桌的所有大人布菜和倒酒”。尽管这违背她的常态,她仍隔着整个圆桌冷冷地看着那个小亲戚,为了是做出一副和她截然相反的样子,一定要处处举止都和她形成参差对照。这样的孩子时刻让自己标新立异,木秀于林,懂得让自己区别于环境。小大人的语气和姿态,让人怀疑蒋方舟是否跳过了童年。
在《天上掉下个蒋妹妹》中,“以我妈为首的大人主张喜欢薛宝钗,以我为首的小孩主张喜欢林黛玉。等到再过几十年,以我妈为首的大人全老了,以我为首的小孩就主张喜欢林黛玉,让他们没办法,只好改变观念了”。要知道,冰雪聪明的林妹妹十四岁,而人家蒋妹妹才九岁。想想你的七岁和九岁在做什么?上学了吗?如果上学,你是否曾为作文绞尽脑汁?
世间事就是这么吊诡,那么多成年人写儿童作品,可是九岁的蒋方舟已经在写这样的句子了:“是怎么想到会给自己的右腿写信的哇,实在太好玩儿了”,“很早就开始学会拟人化手法写东西,而不是物即是物,我的右腿就是我的右腿”。
二十岁那年,蒋方舟在《人民文学》发表了长篇散文《审判童年》,用手术刀般锐利的笔触剖析自己。她说自己年少成名后,就在家人、邻居、媒体面前,扮演一个天才作家的样子。蒋方舟是标准的儿童文学作家,而事实上她几乎从未“儿童”过,一“出道”,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成人作家序列,完美践行了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名言。
这类成年前的作品,大多属于一个小女孩的小心思小伎俩,可以作为“神童”的佐证,却未必符合代表作的标准,故在这时期谈“代表作”,就免了吧。
成年后,蒋方舟似乎跟长书名摽上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文章开头》出版于二十二岁那年。这是一部寓言式的短篇小说集,讲述了九个有关逃离的故事。九个故事各自独立,人物却彼此勾连,前一个故事的配角是下一个故事的主角,在前一个故事中发生的一件小事,改变了后一个故事中主人公的命运。这部作品,可以概括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时间是感情的刽子手。
看下面这样的桥段:“有些人灵魂里的东西会让你激动!”“我”冷笑道:“哼,是他钱包里的东西让你激动。”
在《拉萨·绿度母》中,这个女孩笔下,夫妻间的“床戏”竟如此恐怖:“唐鹏知道此时最好的办法是把她拖到床上大干一场,急切地进入她,以示尊重”,但“此刻的他完全做不到,他盯着老沈的腿,依然匀称而光滑,却发现自己没多余的爱与尊重可以榨出,哪怕一点点”。在《三亚·手铐》中,“地铁口,有个很瘦的年轻人蹲在地上,面前放了个纸箱子,箱子上写着‘相信未来,创造未来。原创诗歌,十元一首’。箱子里放着一沓A4的纸,柯宏志翻了几首,满目‘故乡’‘姑娘’‘远方’,选不出一首像样的,可还是往箱子里扔了十块钱”。
看了这样的描写,你觉得蒋方舟还会相信谁?她会让自己成为诗人么?
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一个青年作家,特别还是一个“美女作家”书写疼痛、冒犯和黑暗。透过她讲别人故事的云淡风轻,我似乎听到一个初涉人世的花季少女内心的雷霆,以及这个世界初时打在她心底的烙印,这种烙印一直延续到她成年后,延续到她的写作中。她的小说不是情意绵绵,而是一场场生命谋杀和人性大起底。超级恐怖,超级凶残,超级血腥,露出森森白骨。幻想、浪漫、梦、嬉戏、陪伴……这些词,在她那里,稀薄得就像喜马拉雅山巅的空气。这样的人,她会相信怎样的爱情?这就不难理解,她的世界,没有爱情,只有需要。而更恐怖的,当知道这背后的操刀者竟是一个豆蔻年华的美少女时,你怎么办?到最后,她让自己相信了拜伦:一切悲剧以死亡结束,一切喜剧以结婚告终。
读雨果、托尔斯泰、莫言,哪怕是与我同龄的作家,我会击节赞叹,而读到晚自己一辈的蒋方舟,我真的恐怖得如坠冰窟。不知她作品中这些对人性深深的悲凉感,是否源于童年时的“几千本书”。年纪轻轻,看透一切,反映在文学上,未必不是一把双刃剑,并成为作品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代表”蒋方舟吗?我不确定。
对于成长,蒋方舟曾说:“所有天才儿童都是对于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这也似乎决定了蒋方舟断不会像方仲永那样“泯然众人矣”,是一定新作频频的。至于最近被翻出来热炒的《东京一年》,流水账式文体,显露出应景的痕迹,就别提“代表作”了吧。
这些年我也注意到,许多读者都认为蒋方舟的杂文和随笔优于小说,对此我倒有同感。这就是2013年出版的思想随笔集或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刚出版时我读到的是其中第十一章,这篇关于作家和国家的章节堪称蒋方舟的“思想之最”,里面的某些见地也深得我心。我特别惊讶于蒋方舟对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所作的诸多思考:“作家,可以为一片树叶哀恸,为一抔黄土作传,可以为一个无名的囚徒请命,可以为一场世界大战殉身。这其中,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作家没有改造社会的义务——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诚实反抗社会的义务,有以正直对时代保持悲观的距离的责任”;“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读着这些句子,有那么一些时刻,我差不多就把这篇作为蒋方舟的代表作了。
书中另一篇谈马原的《中国作家梦》,蒋方舟表现得异常尖锐:如果你把它看作中国版的《巴黎访谈》,那就错了。作家们聊得最多的,不是“你觉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谁对小说语言的贡献最大”,而更类似于“你觉得王朔和苏童谁更有钱”。在当时的采访里,有几个问题是被问得最多的:“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的稿费是多少?”“你海外版税能拿多少?”
你能想象,小小的她,感叹“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时的模样吗?写这类文章时,蒋方舟作为批判者,自称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但我却习惯于蒋方舟充当这类批判者的角色,也乐于阅读她这种很另类、战斗檄文式的文章。
蒋方舟最近发表的一篇随笔,是谈莎士比亚的《英雄叛国记》。英雄马歇斯在敌国浴血奋战,生死未卜的时候,他的妻子非常担心,但他的母亲却说:“我宁愿有十一个儿子为国家战死,也不愿一个儿子毫无作为。”蒋方舟坦言,通过马歇斯的故事,她想说,“做自己”是一项辛苦和严肃的事业,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如此轻率简单。年轻的时候练了十八般武艺,一心以为可以路人皆知、改变世界,最后不过成了生存的拙计,勉强足够保全自己而已”。
感觉她比同龄人,不,是比同代人多活出几个世纪。蒋方舟坦陈自己“不想做一个歌颂遥远的月亮有多皎洁的人,而想看到它黯淡坑洼的一面”。事实上,正是那些文章让她更真实,更独立,不被他人所左右——这样的文章,分分钟就成为我心目中的“代表作”了。只是不知“元芳”怎么看。
封面作者自述
毛姆借由笔下一个“二”到极致的男主人公,说过一段奋不顾身的话:“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儿。我由不了我自己。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着出去,不然就会淹死。”“挣扎”一词,历来与痛苦孪生,毛姆却来了个“幸福的挣扎”——剥离其痛苦成分,赋予主人公最大的表达自由度,同时又让他获得最“嗨”的精神愉悦度。物役累重,得以超拔。我无意将此处的画画儿等同于我的写作,却不妨碍我享受这个“挣扎”的过程。事实上,“跌进水”的人也许根本无意“出去”,恰如那个主人公,非但没淹死,挣扎一番,竟游弋自如,直到问鼎“冠军”。我游龄尚短,泳姿平平,却不惮做一只文学的丑小鸭,或许哪天一不小心,游成了白天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