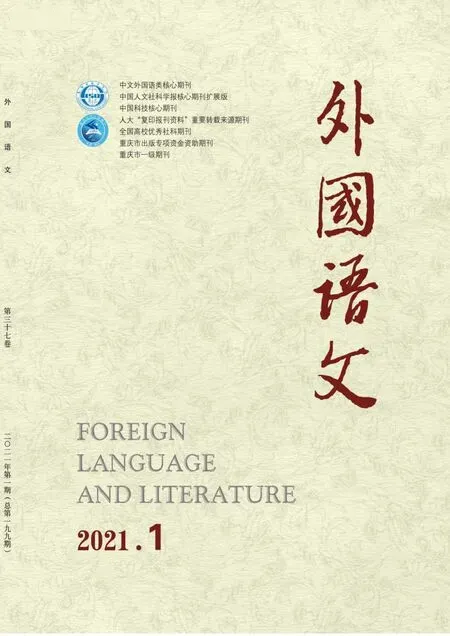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
2021-03-07张荻荻
张荻荻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0 引言
即便20世纪美国诗坛群星璀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在其中仍尤为闪耀。作为美国现代著名诗人、意象派主将,威廉斯提倡客体主义、本土主义、口语入诗等理念,晚年相继获得全国图书奖(1950)、博林根奖(1953)、普利策诗歌奖及美国艺术与文学院诗歌金质奖(1963),被授予多个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由于超前的诗学理念和实践,威廉斯被誉为美国诗歌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里程碑。他在西方影响广泛深远,在美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越艾略特,成为众多后辈诗人效仿的榜样,艾伦·金斯堡、查尔斯·奥尔森、“黑山派”“纽约派”等均受其影响,奉其为“精神导师”。在西方,威廉斯获得顶礼膜拜,但在中国很长的时间内却知音寥寥。甚至在2015年,第一本中文诗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选》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向读者,此时距离其1909年在美国出版第一本诗集已逾百年。威廉斯的诗学价值长期被低估,造成了研究的相对落后。对威廉斯在中国的接受史作历时性的梳理,有助于客观评估其诗学研究现状,发现其中局限性及不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同时,在全球化迅速发展、文化多元共生的语境内,通过探讨威廉斯的诗学影响,可进一步理清中国新诗发展的思路,推进中西文学关系向深层迈进。
1 “唯见缥缈孤鸿影”:早期译介的冷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有关于威廉斯的译介寥若晨星。目前,就笔者遍寻报刊书目资料,仅发现1944年1月《文学集刊》第2辑上发表的《诗抄四首》中刊登了威廉斯《冬树》一诗,而国内关于威廉斯的研究,一开始基本是以零散式、印象式开展的。其中,《现代》杂志是指引当时学界了解意象派及威廉斯的重要途径。1932年,阿部之二在《现代》发表《英美新兴诗派》一文,其中对威廉斯的诗评价为“一种不安定的,杂然的近代性的作品……他起初用着定形的音律,后来逐渐变化为散文形”(阿部之二,1932:563)。1933年前后,《现代》开展了关于“什么是意象派诗”的讨论,翌年,徐迟发表《意象派的七个诗人》,虽然威廉斯未被选入“七个诗人”之列,但在介绍“意象”时,引用了其《全部毁灭》一诗,但徐迟认为这“不属于意象派诗人的意象诗”(徐迟,1934:1016)。同年第5卷第6期“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上,邵洵美发表《美国诗坛概况》,在“结论”一章中述及威廉斯,指出诗人有“向外的”与“向内的”的区别,鲁宾孙代表前者,艾略特及后期的威廉斯代表后者:“前者的作品出版,有时候可以销到几十万本,而后者的作品则几乎有使一般人不能了解的情形。前者是去迎合一般人的趣味,而后者则去表现他自己的人格。前者是时髦的,而后者则是现代的。前者是在现代文化中生存的方法,而后者是在现代文化中生存的态度。前者是暂时的,而后者是永久的。”(邵洵美,1934:889-890)同期薛惠发表《现代美国作家小传》一文,简介了威廉斯的生平,评价“其诗及散文形式务求新异……诗集有The Book of Poems(1917),Sour Grapes(1921)等”(薛惠,1934:1257)。
然而,除《现代》杂志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关于威廉斯的介绍寥寥可数。甚至连对美国新诗运动进行详细介绍的论文,如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1922)、朱复《现代美国诗坛概论》(1930)大篇幅介绍了意象派的创作原则及主要诗人,但对威廉斯却只字未提。即便是有所介绍,也仅仅是一笔带过,如《文学》杂志刊登了英国Louis MacNeice的《英美现代的诗歌》一文,仅在介绍肯明斯诗歌形式编排时,对比了威廉斯对“行数的安排全不关心”(Neice,1937:1552)。
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二三十年有关于威廉斯的介绍也仅见零星篇什且评价不高。20世纪60年代初,袁可嘉《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一文对威廉斯稍做提及,视其为庞德等人领导的“意象派变种”(袁可嘉,1963:64)。70年代杨熙龄发表《美国现代诗歌举隅》,在“庞德与艾略特”一章简单提及了威廉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受重视,60年代开始流行,并指出《无产阶级画像》《小梧桐》两篇具有“浓厚的意象派色彩”,“但是他提出诗歌的‘客观主义’理论,人们认为也只是意象派理论的翻版”(杨熙龄,1979:281)。同时期,躬耕于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关系研究的学者赵毅衡在《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一文提及“脱节法”时,提到威廉斯“把每行压到只剩一个词”,“在美国,‘梯形诗’不是‘马雅柯夫斯基体’,是威·卡·威廉斯首先在较长的诗中稳定地采用这种写法,或许应该称‘威廉斯体’。”(赵毅衡,1979:6-7)
可见,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威廉斯在中国接受语境内几乎销声匿迹。这一局面的发生并非偶然。一方面,从威廉斯的生平轨迹来看,由于其主业为医生,虽然诗歌创作生涯长达60年,却常年被艾略特、庞德等诗人的光芒掩盖,直到晚年才声名鹊起,因此在中国的传播也起步较晚。另一方面,从接受语境的现实情形来看,由于国内频繁遭遇战争、政治运动的冲击,西方现代派文学译介的流脉一度中断,威廉斯的译介和研究也受到影响而停滞。此外,该时期威廉斯译介的悄无声息也与当时中国新诗的期待视野息息相关。在“工具论”“反映论”等艺术功利化思想占据主导,长期推崇复杂诗歌技艺的文学生态场域内,其诗语言平易朴实、取材生活日常无法引起诗歌界的关注和重视,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略显寂寥的译介及研究,造成了此时期威廉斯在中国知名度有限,在影响方面,更多是作为意象派的一员作用于中国新诗。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意象派诗歌运动被视作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评论家称其为“美国文学史上开拓出最大前景的文学运动”。20世纪初,欧美诗坛沉浸在冗长无聊、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诗风中,以T.E休姆、F.S.弗林特、庞德为主的一些英美青年诗人对此产生不满,从而发起意象派诗歌运动。意象派的诞生昭示着新的诗歌局面的形成,其强调运用意象,要求诗歌凝练、清新,对扫除当时泛情滥理、苍白空泛的诗风发挥了积极作用。20世纪以来,意象派通过中西方的诗学交流反复作用于中国新诗发展,产生了多维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初,留学在外的胡适受到意象派“直接处理事物,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绝不使用任何对表达无用的文字”等若干原则的触发,提出著名的文学“八事”,按下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启动键。而在新诗初期的发展历程中,闻一多、戴望舒、施蛰存等现代著名诗人也一定程度受到意象派的影响。
2 “小荷才露尖尖角”: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升温
新时期伊始,随着西方文学译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威廉斯逐渐频繁地进入中国诗歌界的视野。其中,积极探索于现代主义前沿的著名学者袁可嘉为威廉斯的译介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其在《世界文学》发表《威廉斯诗九首》是新时期较早关于威廉斯诗歌的翻译,同时期发表的论文《从艾略特到威廉斯——略谈战后美国新诗学》及《威廉斯与战后美国新诗风》对威廉斯引进中国发挥了较关键的作用,两文不同程度提及了威廉斯取材生活化、语言口语化、本土特色、可变音部等特征,并谈到其对战后美国诗歌的重要影响。
在翻译方面,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特征之一是录有其诗的选集大量出现。选取较有影响力的选本窥其一斑:1985年,袁可嘉与郑克鲁等人合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译威诗10首;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赵毅衡编译《美国现代诗选》,含威诗22首;湖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申奥编译《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含威诗23首。198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裘小龙翻译的《意象派诗选》,含威诗两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黄晋凯等编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象征主义意象派》,选译威诗两首;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外国诗(三)》,含袁绍奎译威诗11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现代诗钞》,含江枫译威诗八首。198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二十世纪外国诗选》,选译威诗三首。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未凡、未珉合编《外国现代派诗集》,选译威诗10首。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威廉斯的翻译依然延续了发展的势头,但数量及影响力对比80年代有所回落。但是,除诗歌外,威廉斯散文、传记等方面译文陆续面世,如1993年《世界文学》发表郭洋生、颜治强翻译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自传:选译》,选译“医学”等八章,为威廉斯的隔洋传播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威廉斯研究中,学界对其评价有所提高。涂寿鹏将其列为“现代主义先行人物”之一:“在现代派诗人先驱者中,威廉斯寄兴趣于直感体会和美国口语以及诗歌的新形式。”(涂寿鹏,1990:147)曹国臣肯定了威廉斯的民族传统及创作成果:“在美国始终存在着对以英欧诗歌传统为基础的艾略特——新批评派持批判态度的人……他们重视威廉斯则由于他是美国本土诗人的代表,威廉斯一贯强调美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并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曹国臣,1992:100)此外,随着学界对意象派的研究逐步深入,除庞德外,威廉斯也受到一定的关注。不少论述把威廉斯当作意象派的主要作家、意象派的领导人之一,在介绍意象派运动及诗歌艺术特色时常引用其诗,包括《红色手推车》《南塔刻特》《窗前少妇》《诗的形象》《影子》《典型的景色》等,提及威廉斯语言简洁、节奏自由、意象并置、通感性、视觉性、本土特色、反诗、排斥隐喻、多元化、无规则和个性化等特点。
其次,概述性的专篇研究逐渐进入视野。部分研究从历时性的角度进行,如洪振国《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歌创作(上)(下)》(1993)论述了诗人的创作发展过程,总结其诗中“客观主义”“本土主义”“继承惠特曼传统”等主要特点,并以其长诗《帕特森》为对象阐述其诗歌理念。有的研究从诗歌整体性特征着手,总结其本土特色、客观主义、运用民间语言等特点,但也有学者对其创作持保留态度,客观指出存在的问题:“由于强调描写一切生活经验,不分重要与否,诗的题材是扩大了,但也变得浮泛了。……由于提倡自然流露和即兴创作,有些诗篇显得粗制滥造。由于提倡兴之所至的开放体,形式存在于可有可无之间,故难以发挥它对内容的加深挖掘的反作用。”(朱新福,1995:56)
此外,有关于威廉斯的文本研究开始兴起,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红色手推车》等名篇。作为威廉斯的代表作,有关于该诗的研究林林总总,大多围绕创作背景、语言、韵律节奏、意象及内在意蕴等方面进行,总结其绘画性、客观主义、日常性、现代性等特点。该诗的成功使威廉斯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如唐晓渡充分肯定了其地位:“美国最重要的现代诗人之一……史家往往把他与庞德并称,列为与艾略特——新批评传统相对立的另一支传统,或称‘反学院派’的代表人物。”(唐晓渡,1991:32)其他研究中涉及的诗歌包括《帕特森》《伟大的数字》《情歌》《便条》《寡妇春怨》《贫穷老妪》等,主要从主题、语言、艺术技巧、意象等方面进行解读。
在众多研究中,不得不提郑敏对推进威廉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研究已陆续提及威廉斯,而成果集中体现在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一书。在对西方诗歌史的介绍中,郑敏在《威廉斯与诗歌后现代主义》《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与〈反风气论〉》等文大篇幅专述威廉斯。除了介绍威廉斯生命轨迹及诗学特色,郑敏的研究强化文学史意识,将威廉斯放置在美国诗歌发展链条中勾勒出其重要地位,在多篇文章中将其视作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奠基者以及“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当代美国诗人。同时,她深入分析了威廉斯超前的艺术观,其中之一为打破欧洲文化中心论,还有在对待世界的认识、诗的语言、诗的动与静功能上等方面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特征。对于国内威廉斯的研究现状,她指出还处于“甚至还说不上正式开始”的阶段(郑敏,2012:346)。
总体而言,20世纪末20年威廉斯在中国的译介及研究逐步升温。在影响方面,伴随着西方思潮的大举入境,威廉斯及其后继者对该时期新诗口语化、日常化等潮流产生了重要的启发意义。部分学者已察觉,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的发展局面与美国20世纪中叶诗坛颇为相似。在美国诗歌史上,当《荒原》面世,威廉斯震惊它如同“原子弹”,使美国诗歌倒退几十年,随后他追随意象主义、客体主义,重视口语的叙述性及当下性,积极推动美国诗歌在20世纪后半叶脱离经院派隐晦难明的诗风,重返坚实的大地,而80年代中期的中国诗坛,以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诗人在对朦胧诗的反叛中,主张从平凡生活中取材,以口语为武器对抗精致密集的意象体系,以世俗情怀对抗英雄主义情结和精英立场,掀起了一股通俗化的诗歌潮流。这股潮流的兴起,既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关,也离不开西方资源的触发。
随着西方文学译介活动的蓬勃开展,《红色手推车》《便条》等诗歌作品经由各类诗歌选集、文学教材的传播,在爱好诗歌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时期不少诗人及流派所主张的民间写作立场、日常化叙述、拒绝隐喻、关注事物“在场性”等理念,都一定程度受到了威廉斯的影响。如威廉斯创作了著名的诗歌《特此说明》(也译作《便条》):“我吃掉了/放在/冰箱里的/李子/那可能/是你/省下来/当早点的/请原谅/它们很好吃/那么甜/又那么冰。”(威廉斯,2015:200)而于坚写作的《便条集》,并不迷恋宏大的叙事,也不刻意雕琢语言,而致力于思维的发散性、形式的随意性、语言的口语化,注重生活流的记录,在思想姿态及语言风格上与威廉斯遥相呼应。于坚曾提及对威廉斯的欣赏:“在诗歌上,它导致我容易与那些注重具体事物,注意世界作为‘现象’,而不是本质、精神实体的作家产生共鸣,如新小说派、自然主义……拉金、威廉斯一类。”(于坚,2010:164)。同时,便条式的创作引发了许多诗人的共鸣,被誉为“后口语”诗人代表的伊沙曾高度赞扬这种写作方法:“一位美国诗人把诗歌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概括为‘便条’,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关于现代诗歌最懂行和最具发现性的说法。”(伊沙,2015:168)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威廉斯对美国当代诗歌影响深远,如“嚎叫派”创始人金斯堡自称受20世纪“40年代早期威廉斯的特式瑜伽”影响开始写诗(金斯堡,2013:198),并致信请求结交,作为威廉斯的崇拜者,金斯堡致力于运用真实直率、富有声音效果的口语记录美国当代社会状况。随着1984年金斯堡访华,其作品在中国文化界广泛流传,逐渐成为诗坛偶像式的存在,不少诗人都坦承曾受金斯堡的影响,如伊沙称“金斯堡是在我青年时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位诗人……他是我的‘精神导师’之一”( 伊沙,2017:249),而“他们”诗派、“莽汉”诗派的创始人于坚、李亚伟等均提及接触金斯堡作品后“深为震撼”(于坚,2009:107)。这种隔空影响,更加深了威廉斯和中国当代新诗的缘分。
3 “满园春色关不住”:新世纪初的繁荣
21世纪以来,随着外部环境宽松及中外交流增多,威廉斯的译介研究呈现出更为繁荣的局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3.1专著的出现
该时期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专著的出现。先是2006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跃军的专著《美国性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该书从美国实用主义诗学和美学的起源与发展谈起,重点围绕杜威哲学观,综合展示了威廉斯诗学观念与实用主义的契合之处,是国内第一本威廉斯研究专著。此外,翻译方面也取得新突破,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傅浩翻译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选》。该译诗集共选466首诗,几乎占威廉斯诗歌总量的一半,主要来自《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汇编》(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VolⅠ-Ⅱ.A.Walton Litz & Christopher MacGowan,eds.,New Diretions,1986;1988)。2017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赫伯特·莱博维茨著,李玉良、付爱玲译《来自天堂的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传》,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其生平及创作的传记,除诗歌外,该书对其自传、散文、小说及话剧等均有所涉猎,弥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缺。遗憾的是,该书作者特别提到两本威廉斯研究的重要著作《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美国背景》及《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一个崭新的赤裸世界》在国内尚未被翻译。
3.2文本研究的丰富
21世纪初,文本研究继续往前推进,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首先是研究的文本对象更丰富,《帕特森》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论者们从该诗的写作背景、内容、结构及形式等方面着手,充分肯定了其艺术价值及在美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同时,学者所运用的视角和理论较之前更为多元,除了关注威廉斯诗歌的后现代特征,还有运用现象学、女性主义等理论。此外,除了具体文本,该时期的研究也开始将威廉斯诗作按照类别进行分析,如小品诗中的意象美、抒情诗中的创新性特征、风景诗审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移等,从而使文本研究更具系统性。
3.3诗体研究的开端
威廉斯终身致力于美国诗歌形式的革新,对此多有论述并亲身参与诗学实践。目前已有学者关注这一点,如张跃军《并行而非对立——试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的结构特征》(2001)归纳了威廉斯借助于转喻而拒绝隐喻、将诗歌与散文融汇的形式结构特点,并指出其与斯蒂文森代表美国诗歌的两种写作方式,前者代表模糊模式,后者代表象征模式,总结威廉斯诗学结构与主张的关键是并行并非对立。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较多关注其自由诗体式,指出此形式承继惠特曼并加以创新,实现了与内容的契合。而其他学者主要从视觉艺术、音韵节奏等方面论述其在形式创新方面的努力。
3.4诗学观念研究的渐进
在威廉斯笔耕不辍的创作生涯中,其诗学观念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部分学者留意到威廉斯早期曾受济慈和惠特曼等人影响而模仿浪漫主义诗风,认识到局限性后实现风格的转变。再者,威廉斯意象派时期的相关特质也受到关注,论者们注重勾勒其在意象派的创新性,如意象并置、绘画技巧入诗等。此外,不少学者对其“客体主义”理念进行探讨。部分研究试图挖掘该特征产生的原因,如武新玉《“恋父”与“弑父”:从庞德的意象派到威廉斯的客体派》(2009)结合“影响的焦虑”理论,探讨美国诗歌从庞德到威廉斯、从意象派到客体派的演变过程与原因;也有论者认为威廉斯对中国道家诗学有所吸收,形成客体主义诗学观念。除探求原因外,部分学者还从其诗作主题、语言和形式等方面分析客体主义的诗学表现。除了以上,“本土主义”也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内容,姜可立较早对此进行系统论述,他1988年在《威廉斯诗歌民族化的道路》一文中从美国题材和本土语言两方面总结了威廉斯在坚持民族化方面所作的贡献。至于其他研究,学者们从实用主义、和谐诗学观、民主精神、女性主义等方面对其诗学观念进行了多角度透视。
3.5色彩视觉研究的兴起
21世纪以来,运用色彩视觉理论成为威廉斯研究的一个趋势。一方面,研究者对其诗色彩语言进行分析,总结出强调对比、注重调和等特色。另一方面,从视觉艺术出发对透视技巧、立体主义绘画技巧及特殊的外在形式进行分析。其中对立体主义探讨较多,指出其运用多重视角、单一色彩、并置拼贴等表现手法,归纳其诗同存性、分析性和色彩感的特质。在此类研究中,李小洁、王余的分析较为深入,《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空间化诗歌》(2009)、《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的色彩表现》(2011)等文分别从绘画语言的空间意识、视觉创作技巧、诗歌形式结构,以及色彩张力、色彩情感等角度挖掘诗歌的艺术魅力。除总结规律外,也有学者对其原因作出分析,分别从家庭、康定斯基“内在音响”理论、艾莫瑞展览与立体主义绘画、斯蒂格雷茨艺术群体等方面的影响入手,总结其诗将平凡事物陌生化、强调语言的视觉性和生命力等特色。
3.6对比研究的繁荣
20世纪美国诗坛热闹非凡,威廉斯与许多伟大诗人一起构成了绚丽的景色,对比研究成为挖掘其艺术魅力的着力点。其中,主要涉及对象包括“前辈”惠特曼、“宿敌”艾略特等。惠特曼作为美国“民族诗人”,部分学者从精神气质及创作特色等维度探求两者相似之处,如反叛精神、乐观主义精神、倡导自由诗体、主张本土语言、注重音乐美感及色彩运用等。而威廉斯与艾略特的恩怨情仇也是20世纪美国诗坛饶有趣味的看点,早在80年代,涂寿鹏《威廉斯、奥尔森与美国当代诗歌的发展》(1986)一文将艾略特与威廉斯、奥尔森作比较,总结了威廉斯诗歌注重“此时此地”的特征及诗韵方面的特点。此后论者也纷纷从生平经历、个人气质、诗学特色等方面将两者进行比较,大多指出艾略特崇拜欧洲传统、威廉斯立足本土的差异性,对威廉斯的诗学地位持肯定态度。在同时代诗人中,威廉斯与庞德的关系最为密切,研究中也多有体现,此外对弗洛斯特也提及较多,多围绕哲学理解和诗歌特色等方面分析两者异同点。其他的对比研究涉及范围甚广,主要包括肯明斯、毕肖普、肯尼思·伯克,甚至中国诗人艾青等。
3.7东西交流研究的深入
自20世纪90年代起,意象派与中国关系研究成为热点。威廉斯作为意象派重要诗人,在此类研究中常被提及。其中,许多学者认为意象派在意象选取、处理方面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红色手推车》常被引用为“意象并置”手法应用的典型例子。除了影响研究,也有纯粹的对比研究,提及威廉斯的部分主要涉及形式、日常语言、意象、视觉特色、“任物自然”观念等方面。除零星的论述外,数篇论文专门探讨了威廉斯与中国的关系。较具代表性的是钱兆明《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2010),该文详述了威廉斯与中国的关系,包括对白居易诗的借鉴、与华裔诗人王燊甫合译中国诗等。2016年,钱兆明出版了意象派研究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在第二部分论述了威廉斯与中国文化的碰撞,既包含完整资料的罗列,又结合文本进行合理阐释,以“跨文化”立场为异质文化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3.8其他研究的进展
21世纪以来,以威廉斯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队伍不断壮大,关于威廉斯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开始涌现,根据知网的搜索,截止至2019年共有近20篇。较多学位论文讨论了威廉斯诗歌的视觉特质,还有从女性形象、浪漫主义及地方主义的诗学特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特征、“思在物中”的诗学理念、艺术的多样性、诗歌艺术的不确定性和内在性、“艺格敷词”等方面进行探讨。国内目前为止唯一一篇关于威廉斯的博士论文《诗性想象与现实“澄”现——现象学视阈下威廉斯诗歌美学研究》(2014)出自梁晶之手,该文以胡塞尔等人的现象学美学思想作为参照,审视威廉斯的诗歌“创作基石”——“想象”,该文主要从哲学层面对威廉斯的诗学世界进行解析,一定程度拓展了其研究外延。
接受与影响是较为复杂的过程。21世纪以来,威廉斯的译介研究蓬勃开展,而对新诗更多转化为潜在的影响。20世纪末中国诗坛爆发的“盘峰论争”“龙脉诗会”等事件预示着新诗中民间力量的崛起,而新世纪以来诗歌发展面临互联网技术革命及媒介扩展等新局面,促使20世纪末20年得以发生、发展的语言通俗化、题材日常化的诗学潮流进一步扩大。此外,在西方诗学界威廉斯被视作后现代主义诗潮的开创者,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追溯了后现代主义的来源,认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最先在诗歌领域提出这一概念,以显示对以艾略特为首的“象征主义式现代主义”的质疑和反对(卡林内斯库,2015:298),从而兴起新的思潮,虽然文中未明确提及,但威廉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股由威廉斯开启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潮,在中国诗学界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播种阶段,21世纪初,在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裹挟下影响力日益深远,其解构性、开放性等特质引领中国新诗走向更为广阔的疆域。诚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已出现反崇高、反中心、反诗美的端倪,但相对而言仍然是含蓄隐约的,而21世纪初兴起下半身诗派、低诗歌、垃圾派、梨花体等游戏化、狂欢化的诗歌运动,在解构传统文体概念、审美趣味方面进行着更为大胆的实验,这些行为均能在威廉斯一脉的诗学创作中寻觅到踪影。在美国诗歌史上,威廉斯被视作先锋,在形式上他时常颠覆传统,作品不设标题、故意在诗行开头使用小写字母、开展跨文体写作等行为曾引发巨大争议,同时,在内容上他突破传统美学标准,认为任何事物均入诗,大胆融入欲望、丑、俗等元素,使诗拥有更包容的“胃”。诸多相似之处均表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新诗发展已逐步融汇到世界诗学潮流之中。
4 结语
从历时的角度看,威廉斯在中国的译介及研究,经历了早期的冷清、20世纪末的升温,再到21世纪初的繁荣。在内容上,一方面学者们在诗学表现及内涵等维度不断向纵深处挖掘,另一方面则迈出学科的藩篱,向艺术、哲学等领域延伸。然而对比国外对其研究已逾百年,覆盖全面,目前国内所取得的进展仅为其诗学宝藏的冰山一角。威廉斯进入中国诗学界已数十年,但翻译状况仍不容乐观,近半诗歌未得以译介导致威廉斯的普及率较低,与其在美国诗坛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相符,同时第一手资料的匮乏一定程度制约了研究的开展,对全面认识20世纪美国诗歌来说不免是一个遗憾。学界整体也面临平衡性欠缺的困境,对威廉斯的诗学观念、艺术表现及外部影响等方面着力甚多,甚至出现一些重复性、低质量的研究,但对其诗歌本体问题,如语言及形式研究则浅尝辄止。威廉斯的诗歌语言极具革命性,他坚持使用普通美国人的语言,注重发掘俚语及方言的特色,致力于建立有本土特色的诗歌,而深入分析其诗的语言因子,更有利于挖掘其诗学内涵。此外,威廉斯诗歌的形式问题虽被部分学者所关注,但论述深度仍有所欠缺。事实上,威廉斯对诗歌的节律研究颇深,曾撰《言语节奏》《论节拍》等文,其诗学理念及实践也经历了从关注自由体诗到创立“可变音节”的过程。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仍比较冷清。
无疑,在与中国新诗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威廉斯一定程度对新诗产生了影响。但由于译介及研究的局限性,其诗学魅力仍有待诗学界深入发掘。威廉斯诗学品质中最值得称颂的是超于时代的创新精神,因此其诗也长期面临“非诗”的质疑,不被主流诗学界所认可。区分“诗”与“非诗”的关键在于,何为诗歌的标准?而标准并非永恒不变。需辩证看待的是,某种意义上“非诗”也意味着探索与革新,而历史已证明,诗歌的发展需永葆活力,必须要有如威廉斯般敢于突围的勇者。此外,中国新诗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干涸的灵感河床及贫瘠的诗意土壤中,寻觅到新的创作源泉及精神基座,汲取发展壮大的动力。而威廉斯利用民间资源以吸收地气的滋养,关注色彩艺术以扩展书写的可能性,强调口语的活力以发掘“意趣”的美学潜力,甚至对意象的选取、组合、应用,以及对形式及节律的革新,都值得新诗创作者思考及吸收,从而拓展新诗的审美空间。因此,进一步发掘威廉斯的诗学内涵,不仅可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还对探索新诗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