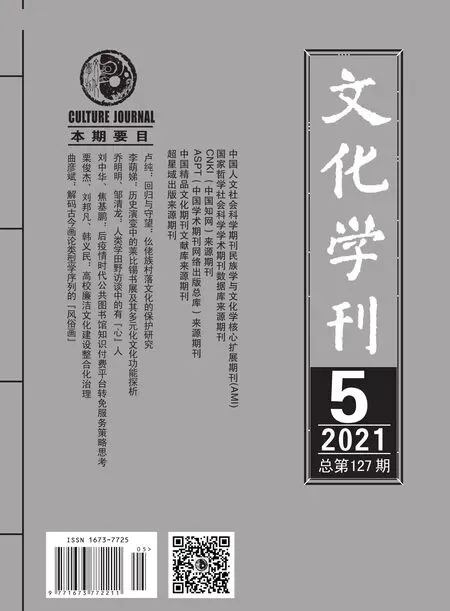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的美学理性和感性特征
2021-03-07何兰
何 兰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林语堂带着满满的民族文化自信,深入挖掘出古老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神秘和诗意元素,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用艺术的手法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推销给了西方现代读者,满足了他们因受工业化大生产压迫而渴求自在生活的内心需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
本文采取西方美学的视角,分析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这一作品的理性和感性特征,为解读林语堂作品提供新的路径,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美学上的借鉴。
二、西方美学的理性和感性特征
根据“美学之父”鲍姆加登的定义,美学(aesthetics)是“感性认识的科学”[1]。西方美学经历了从古典美学到现代美学的演变,在此过程中,美学研究的特点从科学理性走向自然感性[2]。
在古希腊时期,人体雕塑模仿精密的人体比例,反映出科学和自由的精神,符合毕达哥拉斯提出的美在和谐的思想。柏拉图认为美的外在形式是对自然万物的模仿,美具有客观性。中世纪推崇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数从始于一,美是秩序的组合。黑格尔把美看作理念的感性显现,他从普遍的范畴推演出了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由此可见,西方古典美学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以及一种科学的理性精神和个体的自由精神。
西方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折发生在工业革命后,工业化的大生产为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奠定了基础。依赖于感官经验的方法变革是撬动西方美学现代转型的杠杆[3]。从此,古典美学科学理性的思辨方法走向末路,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美学的经验主义。这种现代美学方法摈弃了超感性经验的理性推演,强调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身体感觉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甚至把人类的五官感觉看作人类所有思维活动包括想象力和判断的基础。人们判断一个事物美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种愉悦的情感。
从此过程中,美学研究的关注点从客观的物,即外在世界,转向人的内在世界,美学开始探索内在于人的审美感受。摆脱了理性一元主导后,审美回到了对普通或平常的东西的经验,寻求这些经验中的审美性质。实用主义代表杜威认为:“美感它本身就来自于人的生理和人周围的环境的不断冲突和平衡。”[4]
三、《生活的艺术》的美学理性和感性特征
生活无疑会充斥着枯燥世俗的内容,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商业化地复制艺术,使得艺术迅速世俗化,在这样不堪的社会状况下,如何把普通的生活艺术化,这是一个美学问题。
在美学领域中,艺术(art)的原始含义就是技术,生活的艺术就是生活的态度和技巧。一方面,林语堂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性视角来超越日常生活中的烦琐表象,把读者带入古老中国道家“逍遥”的思想境界,展示出人与自然世界的自由和谐;另一方面,林语堂为日常生活琐碎添加上感性的绚丽光环,使之非日常性,从而消解了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无趣,为西方读者呈现了一幅幅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美景,帮助他们在物化的生活现实中追寻精神上的平衡。
(一)超越日常生活烦琐表象的古典美学的理性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时时刻刻被社会规范所制约,被裹挟着向前奔跑。如何认识现实世界,如何实现人的价值,在《生活的艺术》中,西方读者可以找到符合西方古典美学理性视角的答案。
林语堂首先指出了普通人看待现实世界的态度问题。在他看来,一个普通人有时会不完全相信报纸上所刊登的内容,甚至不完全相信所看到的是生活现象。果真如此的话,这种“不全信”的判断力便是审美判断力,具有美学哲学的意味。
林语堂紧接着给出了中国哲学家的审美方法。“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富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5]14睁着眼睛的时候,中国哲学家看到表象,看到忙碌终日、成败盈亏的现实生活;而在梦中,哲学家进入自己的思考状态,不被生活的表象所遮蔽,识别到生活的本质,获得保持自我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这种超越日常烦琐表象的理性思考,与西方古典美学所提倡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兼备的理性思考正好一致。
依据这种科学精神,人的生老病死被看作一个生物过程[5]56,而人生的诗意,就源于对于这种循环的生物规律的体验。人生的经历,犹如春夏秋冬,不同的体能状况与不同人生阶段的特征相匹配,即使是老年阶段,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以生命的火花闪灭,长睡不醒为特征,与童年期、青年期和壮年期的特征相互对照,构成人生的多样与变幻,像四季一样成为自然世界的美的一种表现形式,归于自然世界的静谧和谐。
与这种生物学的科学精神相伴的是个体的自由之美。既然人生有其生物学的必然规律,则没有必要惧怕死亡,重要的是尽情享受人生。因此,辞官归田的陶渊明饮酒抚琴,过着“夕露沾我衣”和“鸡鸣桑树颠”的日子。这种生活诗意自然,完全摆脱了现代社会的异化作用,获得了自由个性的存在形式。这种形式的活着就是自由之美的绽放。
日常生活的烦琐表象淹没了人的自我,但是林语堂推出中国圣贤的理性的思考方法,把生活的烦琐转化为和谐,在自然本真的生活状态中找到自由,这既是古代道家看待世界的方法,也是西方古典美学看待世界的方法。
(二)凸显日常生活琐碎“非日常性”的现代美学的感性
林语堂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忽略日常生活表面的琐碎无趣,充分凸显日常生活的“非日常性”,为大众读者展示出日常生活神奇而富有差异的另一面。
借助于东西方文化中伟大人物的作品,林语堂描述了听觉、嗅觉、视觉在日常生活中的触发作用,通过身体美妙的感官,人们可以主观地获得有别于客观世界的个人生活世界。例如,他引用了梭罗的一节文章,在这一节里,梭罗这样描述蟋蟀的鸣声:
一只蟋蟀的单独歌儿更使我感到趣味。……它们就这样永恒地在草根脚下唱着。它们的住处便是天堂,不论是在五月或十一月,永远是这样。它们的歌儿具有宁静的智慧,有着散文的平稳,它们不饮酒,只吃露水。[5]195
林语堂又列举了金圣叹的快乐时光,在这些时光中,感官体验到的美与内心的自在逍遥密不可分:
重阴匝月,如醉如病,朝眠不起,忽闻众鸟毕作弄晴之声,急引手擎帷,推窗视之,日光晶荧,林木如洗。不亦快哉![5]202
在这两则例证中,蟋蟀的鸣叫和鸟儿的啼声原本属于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但是在感性化的美学视角中,它们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6],其“非日常性”被凸显放大。一只蟋蟀的鸣叫,不再是鸣叫,而是歌儿,具有宁静的智慧;一群鸟儿的啼声,不再是啼声,而是点晴之声,且是鸟儿作弄出来的。这样由感性而触发出的美妙意境,改变了日常生活之物的常规属性,使得一切皆非常物,具有美学中“非日常性”的审美意义。
不仅虫鸣、鸟叫这些自然界的声音具有“非日常性”,而且满足人们味觉和嗅觉享受的商品,如烟、酒、茶,也超越了其作为商品的世俗属性,成为日常生活中风雅的象征,在大众的消费文化中获得了“非日常性”,参与了审美生活的重新构建。
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把烟描写成了中国男士快乐思考和交流的条件。没有烟的时候,成年男子好友之间的见面会拘谨而短促。但是,只要把烟点上,彼此的心扉就会敞开,无虚饰而有意义的交谈就成为现实。此外,茶也不是单纯的饮品,它“永远是聪慧的人们的饮料”[5]333,“引导我们进入引向一个默想人生的世界”[5]332。茶如隐逸,酒如豪士。在林语堂的笔下,如果说茶让人们静心品味生活,酒则可以使得人们开怀抒发意气。美酒所诱发出来的想象力是惊人的,可以托举着现实进入幻象之地。
感性意义成就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7]。借用现代西方美学的感性视角看,《生活的艺术》通过凸显日常生活的“非日常性”,实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四、结语
毫无疑问,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从中国古老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日常生活,有意无意之间,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古典美学一致的理性视角,不仅满足了他们超越眼前日常生活琐碎的心理需求,而且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生活智慧,体现出一定的西方古典美学的理性特征。
不过,《生活的艺术》并不是一部关于认识论的作品,它关注的焦点是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性存在,因此,在推介中华民族传统的日常生活艺术时,林语堂使用了西方现代美学的感性视角,通过凸显日常生活的“非日常性”,为属于人类物质层面的生活添加上了深刻的形而上色彩,赋予了作品相当程度的西方现代美学的感性特征。这得益于林语堂对西方美学的认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及对那个时代人们精神需求的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