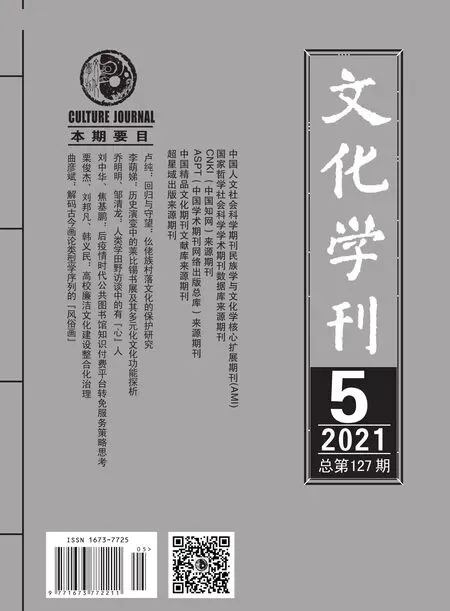回归与守望:仫佬族村落文化的保护研究
2021-03-07卢纯
卢 纯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国一些少数民族村落的封闭式状态逐渐被现代思想、大众传媒、新型科技、潮流文化等打破,使这些民族村落的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会行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中国一直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在这一阶段,抓紧摸清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加强对传统民族村落文化的保护,才能避免因错误的观念、短期的开发利益等各种原因造成对少数民族村落文化的破坏。仫佬族是广西一个世居少数民族,他们主要聚居于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如今仫佬族村落的文化保护也面临着现代化、城镇化发展的考验,出现许多突出问题。因此,本文对仫佬族传统文化内容和村落保护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探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发展的思考。
一、政策下民族村落文化的保护基点
文化生态观认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它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在少数民族地区,村落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场域。中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极为重视,很早就开始注意到传统文化与地方社会传承发展之间的关联,命名、入选了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以及开展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出台很多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政策,其主要目的都是在提升村落居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保护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保持地方文化特色,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一)村落保护发展政策
对于一些村落的保护问题,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始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项目;2012年,在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一步推进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就其出台对“传统村落”[1]“历史文化名镇(村)”[2]“少数民族特色村寨”[3]等概念的界定和相关的评选条件来看,除强调传统村落中古建筑、古民居、文物古迹等物质遗产遗迹的保存情况,也关注优秀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延续,鼓励多元化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一些村落中本身也包含许多具有民族特色古村落,传承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关于对这些村落保护工作的指导,建议“整体保护,兼顾发展”[4],强调“活态传承、合理利用”[4]“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等”[3]。可见,在这些相关的保护政策文件中,其基本内容都是强调整体性的活态保护传承,要求处理好保护传统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目的是通过保护促进村落的发展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当代传统村落保护,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多数是以政府为主导,在政策、财政等方面给予重要保障。在此笔者简单梳理了政府等有关部门在进行传统民族村落保护中关注的重要方面:首先,要有整体性的保护规划。作为具有一定空间场域的传统村落,其生态环境、特色民居、文化艺术、民俗风情、文物古迹等相互关联,制定保护规划要立足民族村落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历史的遗物遗迹、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在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和提高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合理编制保护规划和实施计划,有序开展保护工作。其次,原真性保护并突出特色。对民族村落历史文化的保护应坚持因地制宜,防止照搬照抄,每个传统民族村落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及民族特色,深入挖掘,保护优先,并合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再次,要注意可持续性。传统民族村落的文化保护要注意其活态性。明确传统村落的保护主体为村民,政府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保障村民的参与及监督权,调动村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并协调好政府、村民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
(二)广西民族文化整体性保护实践
广西十分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除了加强各个民族文化项目的保护外,也注重在整体性的空间场域中激发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广西传统民族村落的保护与利用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其保护的力度和成效还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推动。多年来,广西在进行传统村落保护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截至2019年,广西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总量达到280个,涵盖全区14个地级市[5],其中不乏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第一、二、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挂牌名单中,广西共有137个村落入选。在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导和推动下,广西在探索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保护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以民族文化整体性保护为基础建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至2018年底,广西建立有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即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和6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即壮族文化(百色)生态保护区、侗族文化(三江)生态保护区、苗族文化(融水)生态保护区、瑶族文化(金秀)生态保护区、桂派戏曲曲艺艺术文化(桂林)生态保护实验区、壮族文化(崇左)生态保护区。其中,罗城仫佬族传统文化纳入了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范围内,这对仫佬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积极意义。2018年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6]对自治区内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工作进行指导。传统村落中除建筑艺术、文物古迹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一项内容,而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以保护区域内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传统文化及其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与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目标一致,因此,在对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广西少数民族村落的民居、建筑、文物、文化等方面的保护。
二、仫佬族村落的文化传承
仫佬族有20多万人口,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东门镇、四把镇、小长安乡、下里乡、龙岸镇等是仫佬族的主要聚居区。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仫佬族人建村立寨,聚族而居。仫佬族以耕种畜牧为传统经济生活基础,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据调查,在罗城仫佬族的传统村落中,至今仍保留有许多文化生活习俗。
仫佬族村寨一般依山傍水而建,就笔者调查走访的石围屯、大勒洞屯、大梧村、铜匠屯等仫佬族村寨现存的传统民居来看,一般都为砖瓦建筑,人畜分开,虽然独门独院,但每户院围墙相连在一起,据说这样可以便于走亲访友,以前有山匪时还便于逃走避难。正屋为三间两层,前厅两侧房间为长辈房,后厅一间则为晚辈房,阁楼间一般堆放谷物、农具等,也有些用作住房。在前厅正中央设有神龛,逢年过节都要祭拜供奉祖先和神灵。此外,在正屋进门右侧还建有仫佬族的传统地炉,但现已基本不使用。
在仫佬族人口中,罗姓、银姓、吴姓、梁姓、潘姓、谢姓等人数较多。就笔者在仫佬族村寨收集到的族谱资料来看,他们大多以“冬”及其分支为单位来进行族群世系和村史整编,可见仫佬族的“冬”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群体,而同一姓氏的“冬”及其支系大都会聚居在一个村落内。仫佬族各“冬”一般都会建有自己的祠堂,也有居住在同一个村落的几个同姓“冬”支系联合建一个祠堂。例如,东门镇石围屯居住的主要是仫佬族银氏四冬的族人(仫佬族银氏有八个支系,即八个“冬”,现存四冬、五冬和八冬,其他各冬或后继无人,或并入其他支系中)。小长安乡大勒洞屯为吴姓二冬的后代。目前,仫佬族“冬”的社会组织仍然是祭祖、聚会、节庆活动等的组织单位之一。
仫佬族保留有很多传统节日,如一月春节、二月祭春社、三月三祭婆王、四月初八“牛生日”、六月初六“驱虫保苗节”、七月中元节、八月中秋、九月重阳节等都是民族传统节日。其中,依饭节是仫佬族中最隆重的民族节日之一,多以各姓氏“冬”(或其支系)或村落为单位组织祭祀活动,届时会有仫佬族师公举办隆重的仪式道场,祭神祭祖,祈福还愿。节日期间,还有聚餐访友,十分热闹。仫佬族人信奉多神,有玉皇大帝、土地、灶君等道教神灵,有观音、如来佛祖、二郎神等佛教神灵,也有白马娘娘、梁九官等民间神灵。其多元文化信仰包含了仫佬族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巫术崇拜等习俗。在仫佬族村落中常建有神庙,如在石围屯、大勒洞屯建有的土地庙、社王庙、婆王庙、圣母宫、土主庙等。一般的节日多是在家屋神龛上简单供奉祖先和神灵。一些特定的节日,还会到村庙中进行供奉。仫佬族人认为每个村寨或地域都有地方神灵的保佑,社王和土地管村落人丁和平安,婆王管生育和子嗣,牛王管牲口等,因此,仫佬族人逢年过节及特定节点都会到神庙中供奉。此外,清明节除家庭各自拜山外,联宗祭祖则以房族或“冬”为单位进行祭拜。可见,这些传统节日和信仰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仫佬族村落中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不仅如此,在一些仫佬族村落中还保留着刺绣、草编等手工艺,还能看到村落榕树下的唱山歌,戏台上的彩调表演等。可以说,仫佬族村寨仍是其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场域。
三、仫佬族特色村寨文化的保护模式
2014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中石村石围屯入选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2017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小长安镇龙腾村大勒洞屯入选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这两个仫佬族传统村落各有特色,经过发展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形成了自身的保护发展模式。
(一)石围屯:以旅游发展带动传统文化的保护
仫佬族村寨石围屯位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的西北部,距离县城约4千米,是一座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仫佬族古村落,主要居住的是仫佬族银氏四冬族人(1)石围屯的最早无史料记载,有文献资料记载推测有六百多年历史。“今东门镇中石村大银屯银氏四冬、五冬族谱序称:……明洪武戊申年(1368),分徙而及新林里(今东门镇中石村一带)……”见1993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仫佬族的历史与文化》第20页。。据调查,村落内的古民居多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建筑,虽然几经翻修,但都较完整地保留了仫佬族传统民居风格,目前遗留下来的有70多个古民居。这些古民居多为砖瓦式建筑,屋檐下常绘制丰富的图画,少数窗户还保留有雕工精致的木雕窗花。村落内的仫佬族风俗浓厚,周围山清水秀,适于耕种,整个村落的文化生态环境较为和谐。
从2012年石围屯被列为省级的“特色村寨保护发展”试点村落开始,政府部门开始投入资金对古村落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和修复,至今在村落建设和文化传承上取得了一定效果,现已成为展示仫佬族民俗文化和发展仫佬族旅游文化产业的新农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逐渐完善。2011年石围屯依托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项目修建了通往村落的水泥路,道路总长0.8千米,路基宽6.5米。现今,在国家多项政策扶持下,逐渐建起了文化娱乐中心楼、灯光球场、蓄水池、休闲广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并投入使用。同时,为了发展古村落文化,还修建了仿古的仫佬族门楼、文化长廊、凉亭等建筑。
二是注重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县政府实施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工程,对传统仫佬族民居进行保护性修复。还对村落中的两处文物古迹进行保护,包括村边70多米长的防御石墙和溪边一座2.4米高的永安桥功德碑。2009年,永安桥功德碑列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县人民政府在其原址上新建了一个碑刻保护亭,命名为“民族团结古碑亭”(2)永安功德碑石上所刻文字一部分已难以辨认,据石碑旁整理的文字描述:“永安桥功德碑刻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碑正面刻序文,一为记录中石银氏始祖历史及迁居历史,二是反映永安桥兴建事由及募捐情况。其他方面则具体刻建桥倡导首士及工程捐款人名。永安桥功德碑记载的银氏始祖及徒迁历史事件清楚,时间准确,是罗城反映村史、族史的珍贵历史碑刻。现桥虽已毁,但碑刻尚存,碑中记载了建桥时有银、潘、谢、罗、梁、吴、张、李等20多种姓氏的人捐款建桥,可以想象当时建桥情景是多么和谐友好。因此它是古代仫佬族地区民族团结协作的历史见证,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团结古碑,是广西著名的历史碑刻。2013年,县人民政府在原址恢复建设碑刻保护亭。”资料为笔者于2018年10月30日在石围屯调查采访所收集。。此外,村中还建立了两层楼的“石围屯仫佬族民俗博物馆”,收集整理了400多件仫佬族民俗文物,包括有仫佬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服饰饮食,以及神龛祭祖、地炉场景等,成为集中展示仫佬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
三是以公司形式带动旅游产业发展。石围屯村民组织成立了广西石围古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旅游项目主要有古民居游览、民俗博物馆参观、仫佬族特色饮食、仫佬族歌舞表演等。在发展民族旅游业、宣传仫佬族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公司还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部分古民居已无人居住,损坏比较快,公司有部分资金用于对古民居的维护;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利用村落资源组建了石围屯文艺队,排演了山歌、舞蹈、游戏竞技等以仫佬族民俗文化为基础的旅游节目;还开发了仫佬族土酒、刺绣等民族产品,增加了部分村民的收入。
(二)大勒洞屯:以政府为主导的村落维护与文化建设
大勒洞屯距离罗城县城10千米,位于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小长安乡龙腾村。它是仫佬族保存有古民居最多的特色村落,内有80多个具有二三百年历史的古民居,连片分布,基本框架保存完好,建筑风格民族特色较为浓郁。村落形成于明末清初,当地主要居住着仫佬族吴氏族人,据村民描述,他们祖先是从罗城四把镇大梧村中迁移到此处,见这里风景秀丽,有山有水,易于耕种,于是世代在此定居生活下来。现今,虽然大勒洞屯的民族建筑特色保存较为完整,但是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村民思想观念保守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村落文化的保护与长期发展。
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中,大勒洞的仫佬族民居群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但是由于村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主动性不高,其村落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建设起步较晚。目前,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村落环境维护和文化保护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方面,古村落民居保护与现代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进行。2014年,县政府设立了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工程对大勒洞屯进行保护和开发。保护村内的百年古榕树、对古民居群进行了修缮、整理铺设古石板路、吴姓古祠堂也得到了保护性修复等,基本保存了古村落的原貌。同时,大勒洞的基础公共文化设施已基本建成,有文化服务中心楼、篮球场、广场娱乐设施、凉亭等。其中,修建了“大勒峒仫佬族古民居生态博物馆”,收集了村落民族生活用品等进行陈列展示。此外,在村落建设上,成立了村庄规划建立理事会,积极发挥村民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以村貌改造和古民居修护为基础发展民族旅游。2016年,借助大型古装历史正剧《于成龙》在大勒洞屯取景拍摄的契机,通过政府协调,在其村落旁仿村落古民居搭建了罗城古城门、县衙、关帝庙、春晓学堂、酒肆、铁匠铺、竹器铺等27个场景,成为县城内较有特色的旅游点,进一步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综合上述内容,可见在近几年的传统村落保护中,仫佬族村寨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民族文化,如文物、遗址、传统民居、习俗等在就地和活态保护中获得生机;也在文化旅游的开发式保护中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对文化的保护也有一定激励作用。
四、结语
近些年来,一些少数民族村落在这种社会聚变中发生转变,如钢筋水泥的房子代替了适应生态环境的干栏式建筑,水泥路代替了石板路,进入了生产机械化等。不可否认,这些转变使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原生态的村落空间、建筑艺术、民族文化等逐渐消失,加上目前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出现了空心村的现象,村落的人文景象更显凋敝,同时,这些无序的新建筑与原有的自然生态、乡俗风貌极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传承与发展。再者,由于过度或无序的开发旅游,一些少数民族村落盲目拆旧建新,也给民族文化整体性保护带来了破坏。可见,这些少数民族村落的文化内涵和特色在还没有得到深入挖掘的情况下,它们的旅游开发出现了商品化、模式化的现象,也使得原有的村落文化、民族文化被曲解利用,如果不对此进行监督管理,大批少数民族村落的保护都会面临开发即被破坏的新问题。因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村民的生活期望都至关重要,因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保护,对少数民族村落发展的科学规划,都迫切且重要。
得益于以上国家和广西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支持和重视,仫佬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古村落历史的延续有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仫佬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村落整体性保护中的重要一环,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使石围屯、大勒洞屯的仫佬族传统文化保护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政策的指导及财政的支持。但是,在村落文化保护的实Z践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一方面,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劳动力流动频繁,民族文化的传承缺乏人才。农村普遍兴起了修建现代楼房的风气,给传统民居的整体性保护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在大勒洞屯,村民在村边连片建起了现代楼房,而原有的古民居基本废弃不用,缺乏“人气”,使得传统民居的修复赶不上自然损坏的程度。另一方面,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缺乏动力。在石围屯,旅游公司的运作模式较为单一,游客数量较少且消费不高,其旅游公司的收入很难维持对旅游产品项目提升的开支。在调查中发现,政府、村民、企业等群体在村落保护和发展中时常因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产生矛盾,使得一些好的政策方案、文化保护内容、产业发展项目等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或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仫佬族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应该在把握国家相关政策方向的前提下调适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激发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调动村民保护古村落文化、民族文化的积极性与参与性,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回归生活,才能真正守望并延续仫佬族村落的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