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伊斯兰贸易文献与博物学
——以贾希兹《论商业之洞察》矿物部分为核心
2021-03-04陈巍
陈 巍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作为以观察为主要方法获取和整理知识途径的实践,博物学被视为现代科学的源头之一。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在批判其先辈的同时,将自然探知作为构建哲学教育的重要部分,此后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从时空分布、分类、外在和内在性质、诸因解释、民俗传说等各方面形成对自然界诸事物蔚为大观的知识积累。尽管思想语境经历了从逍遥学派自然哲学向强调物质一元论的斯多噶主义的转变,但古典时代的博物学在将近一千年间,保持着追求客观中立、以“目的因”为导向的历时性叙述、对经验性的观察重视度甚于精密计算,以及兼具旁征博引和慎思明辨来体现和满足对陌生事物浓厚兴趣等鲜明特点。[1]这在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发展中大放异彩。
然而,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之间数百年里,博物学是如何在沉寂表象之下保存生命力的,这一问题迄今仍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数百年间,伊斯兰文化区作为中转站[2],对包括博物学在内的古典时代知识遗产进行了吸收、综合和创新。博物学抵触从神话、成见、臆想等非理性源头中为自然现象寻找原因,这让它可以渗透进伊斯兰文化许多需要运用理性辨别和收集各类知识的领域和相关著作。
与博物学知识积极互动的一个对象就是贸易文献。作为物质与知识跨空间、文化、族群、阶层交流的重要途径,贸易行为在伊斯兰世界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陆海交通各节点常汇集“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赶集买卖”[3]。来自远方的知识借此通过丝绸之路等交流网络构建的欧亚非世界体系中流动。在商业行为里,所获关于计量、货币、物产、运输路径、风俗习惯的信息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参与者能否获利。而掌握相关知识的商人们能否合乎社会规范地运用这些知识,则关系到市场的正常运行乃至国家财政收入,这就要求监管者等参与贸易的其他角色也需掌握相应知识。这使当地知识体系中存在的博物学因素能够渗入到记载贸易细节的著作之中。
另一方面,关于贸易这一人类交往的重要方面,伊斯兰世界和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都留下了许多专门文献[4]。此前学者对于这类文献多关注其中少部分与中外交流相关的片段,对文献所含知识的总体特性,以及它们与所属文化知识语境的关系,都缺乏整体性的探讨。因此对贸易文献所载博物学知识展开讨论,有益于更全面地获得对古代丝路沿线文化分布与交流的认识。

1 博物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发展
伊斯兰教兴起后,影响很快波及西至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东至中亚的广大地方。伊斯兰教义对信徒们追逐知识的鼓励,以及阿拉伯帝国创建初期较宽松的统治政策,把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统治核心区域——两河流域,以及稍外围的埃及、叙利亚和波斯等地此前长期存续的各类知识聚拢融汇,形成新的阿拉伯知识传统,带来了中世纪前期伊斯兰科学的繁荣。
埃及和叙利亚处于罗马帝国疆域内,而波斯乐于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招降纳叛,故古典时代博物学在这些地方均有传承。例如,年代最早的带有博物学色彩的报告,就来自服务于波斯宫廷的卡里安达的西拉克斯(Scylax of Caryanda,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和尼多斯的克忒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公元前5世纪)等人。他们记录了印度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沿海一带的见闻。[7]这些记载显然具有面向古希腊和古波斯两种背景读者的主旨。公元5世纪以后,基督教东方亚述教会(即景教)把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传承的希腊化科技著作翻译为叙利亚语。[8]不过总的来说,叙利亚语文献中的博物学著作不多。除医学外,目前仅知他们翻译了一部生理学专著,并在其中增补了关于地理学和诸如树木、岩石等自然物的内容。[9]
博物学并非伊斯兰科学最早关注的领域,统治者起初更功利性地偏好医学、炼金术和占星术。直到8世纪,仍只有扎比尔(Jabir ibn Hayyan,约721—约815)从自然哲学角度对植物学进行过论述。[10]这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知识体系在伊斯兰博物学开创阶段就带来了影响。到9世纪,这套体系已经为伊斯兰世界广泛接受,为人们提供了获得教养的基础框架。[11]在其学习序列中,包括对生物基本概念的《动物学》和更深入阐发自然性质的《自然诸短篇》被放置于对天体运行规则的熟悉之后,是仅次于被视为探索终极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重要内容。
在亚里士多德知识体系跨文化移植的同时,伊斯兰学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整理他们长期积累的动植物知识。在8世纪后期兴起的词典编纂活动中,一些学者对动植物按不同属性进行了非亚里士多德式命名、分类和描述。[12]例如基拉比(al-Kilbī,逝于约820年)和阿斯玛依(al-Amaī,约740—828)、安沙里(al-Anrī,逝于约829年)都把植物划分成可生吃的、微苦的、可用作药材的等类别([13],814页)。其中阿斯玛依不仅列举了276种植物的名称,还记述了马匹解剖后各部位的名称,以及一些野生动物的情况。从后世对其生前逸事的记载来看,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博物学知识已经成为宫廷知识竞赛的一项内容。[14]

伊斯兰教鼓励广大地域内信徒到圣地朝觐,以此为基础开创的游学传统凸显了贾希兹缺乏实地考察的局限性。年轻一代学者注重亲身体验甚于书本知识,他们热衷于借助旅行充实要绘制的地图。由中亚人巴尔黑(Abū Zayd al-Balkhī,850—934)创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地理学派,它不同于托勒密以测定经纬度为主的数理地理学传统,而与斯特拉波的人文地理学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和老普林尼一样在伊斯兰世界少为人征引。[19]巴尔黑学派的研究方法具有一些人类学的特征,如10世纪的穆卡迪西(al-Muqdisī,约946—991)为搜集足够资料不惜任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在考察期间他曾借用教师、抄写员、商人、奴隶主、牧羊人等身份与各行各业人员交流,在每个地区他可停留达数月甚至一年。[20]穆卡迪西把各地信息按地理历史概况、气候、学校寺院、商业、风俗、特产等分类,动植物知识往往出现在风俗、特产等类别下。[21]
巴尔黑学派在注重实地考察的同时,仍把宗教经文作为无法逾越的真理,这种时代局限性我们也可以从仅限于为荷马史诗做注的斯特拉波那里看到。宗教因素甚至把巴尔黑学派视野限制在伊斯兰文化区以内。生活在10、11世纪之交的大学者比鲁尼(al-Bīrūnī,973—1050),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一束缚。在跟随君主出征印度期间,比鲁尼深入调查了印度西部地区的文化,以穷根溯源的方式探讨了这里的科学、宗教、地理、语言文字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知识。[22]比鲁尼在著作中申明了他对其信仰的忠诚,同时他在研究中尽可能保持克制,不强求他人接受自己观点或标准,他的记述是“历史的”而非“论战性的”。[23]在另一部著作《宝石学》中,比鲁尼除同样广征博引、巨细无遗地总结了包括红宝石、钻石、珍珠等29种宝石,以及数种矿物的价格、外观、传说、分类、鉴别知识之外,还在前言中探讨了宝石反射光芒的原理([24],xxiii-xxix)。这与他的同时代人海什木(Ibn al-Haytham,约965—1040)对光学的研究遥相呼应,显示在一流学者中博物学与专精的特定学科之间的结合。在下面一节,我们将多次引用比鲁尼这部书中的论述。




2 贾希兹《论商业之洞察》中的博物学知识
对于贾希兹,前文已略述他的《动物学》在伊斯兰博物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这并非他庞大文集里唯一显示出博物学特征的作品,在他另一部反映伊斯兰商业早期发展的论著《论商业之洞察》中,我们也可以窥到博物学因素。因此书简略,国际学界对它所载知识评述不多,国内学者也只有张广达曾注意到书中与中外丝路贸易有关的部分内容[34]。
贾希兹被认为是首个对社会阶层、城镇活动等经济问题产生深刻认识的伊斯兰学者。《论商业之洞察》虽然以他署名,但没有列于他身后的著作目录之中。在目录中另有两部没有流传下来的著作,一部涉及植物、手工艺和纺织产品,另一部讨论交易、信贷和诈术。《论商业之洞察》恰好综合了这两部书的内容范围。[35]根据传统观点,本文仍以贾希兹作为该书作者。

《论商业之洞察》篇幅不大,除序言外全书共7部分。其中前6部分分别与金银特性与鉴别、宝石鉴定、芳香物品鉴定、纺织品的产地与质量、各地名贵商品和特产、猎鹰与猛禽等方面的知识有关,长短不一。最后部分则分类概括了在评判各类事物时应当遵循的标准。本文选取该书序言、与金银和宝石有关的第1、2部分,以及最后的尾篇,来对其中所含矿物学知识展开分析(7)书中所提及的各类猎鹰亦是伊斯兰世界对动物认识与人类文化互动极为密切的方面,作者拟结合贾希兹《动物学》等文献另文详述。。
2.1 《论商业之洞察》序言中的博物学因素
在序言中,贾希兹提到他写这部书是为了提供能够在各国获得的关于贵重货物、奢华饰品和珍奇宝石的详细描述,以便有识者借此汲取经验。“任何能够获得的事物都因为可以获得而价格便宜,而昂贵者正因为其在面对实际需求时难得和稀缺而昂贵”。为此,贾希兹引用来自多种文化的谚语,强调如果在一片土地上找不到所需事物、利润、财富,就应到另一片土地上寻找。这紧密地契合了《古兰经》中提出的鼓励到远方求知的训诫,贾希兹首先强调的把教义解释作为商业驱动因素,对后世伊斯兰经济学具有深远影响[39]。不仅如此,贾希兹强烈的世界性倾向在序言末段再次得到确证,他在文中高呼波斯人警句:“众人们!在你和你所居住的地域之间并没有与生俱来的联系,因此最好的地方也就是那些对你最有益的地方。”([5],4- 5页) 这些倾向的语境显然和当时伊斯兰文化鼓励人们在广大疆域内迁移流动的风气有关。结合贾希兹所处时代,现代读者很容易想到他生前已初步汇集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游记[40]。后者的记述总体上以途经各地时间为序,亦不乏对重要商品的专题讲述,其内容多有从实地见闻角度可与《论商业之洞察》相参照之处。贾希兹尝试把著作的取材范围设置为当时已知世界的所有地方,并把关于同类事物可获取的所有种类纳入评判范围之内。如前节所说,这也对后世学者为求知而远离故乡形成了一定激励作用。在序言最后,贾希兹不无诙谐地特别提到:最好的工艺是使用丝绸来织作,最好的生意是纺织品贸易,这构成了他在书中布局相隔较远,但所论详细的第4部分的主要内容。
2.2 第1部分“关于识别金银,及其检测”
该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纯金的色泽、不易被其他物质败坏的性质(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物理和化学性质的部分内容);黄金的价值主要来自其性质的稳定性,以及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褪色;最好的金币和银币的识别依据;纯银和掺有杂质的银的不同气味和相互碰撞所发声音([5],6- 7页)。

通过与其他在伊斯兰文化圈内较有影响的论著比较,我们有望更加明确贾希兹对内容设置的目的。首先是一部托名亚里士多德的《石志》,该书原为叙利亚语,可能于9世纪由胡奈因·伊本·依沙克(Hunayn ibn Ishq,809—873)译为阿拉伯语。《石志》对金银的论述分割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金银矿,后一部分为金银性质。其中后一部分提到金、银、铜合金颜色按不同比例而变化,以及金银的医学特性([41],155- 156,177- 178页),可能由于这些性质与商业有一定距离,贾希兹舍弃了这些内容。另一部可用于比较的是比贾希兹晚约1个世纪的也门学者哈姆达尼(al-Hamdni,约893—945)所著的《论金银冶炼》(Kitābal-Jawharataynal-atīqatayn)。此书堪称中世纪数百年间该专业领域中最杰出的著作,融合了大量古希腊和南阿拉伯半岛矿物学的理念和实践知识,其中在第41章(全书共57章)对通过颜色、硬度、与铁撞击的声音、重量的细微差别等辨别金银币纯度和优劣的方法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如哈姆达尼认为纯金颜色发红,通过试金石,劣质金会变为黄色、白色、绿色、暗灰等色,纯金很软,啮咬可留下痕迹,纯金金币撞击铁石可发出最清脆优美的声音等。[42]对比之前贾希兹的描述,显然哈姆达尼所述具有更高的精确性。比鲁尼在《宝石学》中对金银的论述也颇多征引([24],199- 210页)。他不但阐述了金银的由来、什么物质可以归属为金银、金银矿藏的位置、伴生矿物和金银冶炼、金银的比重等内容,还记载了许多远到中亚的关于金银和金银矿的逸事传说。我们无法判断贾希兹是否了解这些知识,他有可能只是根据所设定的目标读者群体有针对性地择取了几个他认为关系密切的要点。

2.3 第2部分“对重要宝石及其价值的考察”

关于珍珠的定价,中世纪相关著作中常有记载。(9)参见文献[44],注意此文所总结中世纪阿拉伯宝石价格表的注释(第384页注释59和61)中,错误地把9世纪价格来源(应为贾希兹)与13—14世纪价格来源之一(提法施)相颠倒。贾希兹仅仅提到其标准在于珍珠种类和尺寸。在比鲁尼等后人著作里,则详细列出不同重量珍珠的官方定价。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的价格表的制定有可能逐渐被以某个浮动价格为基础,辅以按尺寸和质量比例换算的定价方法。如20世纪初在红海一带活动的冒险家亨利·曼弗雷德(H. de Monfreid,1879—1974)记载,为获得一批珍珠的价格,先确定一颗谷粒的重量,这个重量的珍珠基础价为1金法郎(当时珍珠贸易常用的货币)。然后称量珍珠重量,除以谷粒重量后求其平方。如一颗珍珠重3谷粒,则其价格为3的平方,即9金法郎。下一步再鉴定珍珠的质量,不同质量对应在此基础上再乘以多少倍数。行家只会说某颗珍珠的价格是多少倍,而不会说它价值多少法郎[45]。这体现了文人心目中的珍珠价格表与实际交易所用技巧和规则之间存在的差异。
在珍珠之后,贾希兹讨论了刚玉(al-yāqūt)(10)Adi Setia英译本将此词译为sapphire,即透明的蓝宝石,并不确切。Sapphire一词源于古希腊语sapphirus,泰奥弗拉斯托斯指出它是一种深蓝色宝石,而普林尼则说东方sapphirus是一种带有金色斑点的宝石,即青金石([43],136页)。这与硬度仅次于钻石的al-yāqūt显然不同,故本文将其译为刚玉。关于丝绸之路上的红宝石,王一丹有较为系统的论述[46],所用史料与本文可相互补充。。他提出这类宝石按照颜色从优到劣依次是清澈透明的红色(bahrumānī)、玫瑰红色、黄色、天青色和无色。这表明当时人们已能正确地把这几种刚玉(主要成分均为氧化铝)统辖于同一大类之下,而较只能按产地将红宝石和蓝宝石分别叙述的普林尼,以及4世纪伪托俄尔浦斯所作的《论矿物》(OrphicLithica)[47]都要有所进步。不过贾希兹所述知识也非其首创。《石志》里提到刚玉分为三种:红色、黄色和深蓝色,其中红色宝石最为珍贵,它耐火且拥有很高的硬度,同时拥有最高的药用价值,黄色刚玉的耐火程度甚至高于红宝石,但蓝宝石却不耐火([43],135- 136页)。这则记载与贾希兹的论述或具有同源关系,但贾希兹略去了耐火以及物性方面的内容。不同颜色刚玉之间的等级差别在比鲁尼的著作中也有相同记载,不过比鲁尼还引用了肯迪(al-Kindī, 约801—873)的实验,指出红色是刚玉原有的颜色,而其他颜色均可以通过加热方式去掉([24],62页)。
贾希兹提出天然和伪造刚玉之间有三个方面的区别:比重、放在口中吮吸的凉感,以及可否用锉加工。真正的刚玉比重较大,放入口中有凉感,只能缓慢地锉其表面,而假刚玉则正好相反。这三条标准在普林尼《自然史》中均可看到详细说明,普林尼还提到可在假宝石内部看到气泡等辨别依据([48],Book XXXVII,Chapter 76)。从现代角度来看,对于第一个方面,刚玉的比重约为4,在所有宝石中几乎仅次于锆石,与当时常见的假红宝石比重差异明显。如在形成于罗马时代埃及的《斯德哥尔摩纸草书》中,有两个通过给水晶染色冒充红宝石的配方[49],而比鲁尼则说与红宝石最接近的是红玉髓([24],43- 44页),这两种矿物的比重分别为2.22—2.65和约2.6,明显低于红宝石,由此可见古人用比重法来鉴别红宝石具备一定科学依据。古人容易进行比较的主要还有在硬度方面,刚玉要更胜一筹。因此在比鲁尼的著作里,认为将红宝石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类似宝石进行分辨的最好方法,还是用真正的刚玉去与鉴定目标相互研磨,刚玉在研磨后不会发生变化,而其他硬度低于它的宝石则会出现磨痕([24],45页)。

在刚玉之后,贾希兹述及的是祖母绿(al-zabarjad)(11)Adi Setia英译本将此词译为chrysolite(绿黄色橄榄石),al-zabarjad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所指并不严格,可涵盖祖母绿(阿拉伯语为zumurrud,托名亚里士多德的《石志》和比鲁尼《宝石学》中均称zumurrud和al-zabarjad是同一物质的两个不同名称)和橄榄石等众多绿色宝石。根据比鲁尼转述,拉齐和肯迪等阿拉伯学者也曾把两种宝石搞混,因为他们记述的重2密斯卡尔的绿宝石价值仅为10第纳尔等等。从贾希兹对这种宝石价格的描述来看,此处所指应是祖母绿而非橄榄石。。对于这种宝石,贾希兹所言不多,其辨伪方式与刚玉基本一致,亦为比重、凉味和硬度。其价格为0.5密斯卡尔重的祖母绿可售2000密斯卡尔黄金。在古典时期文献,如普林尼《自然史》、泰奥弗拉斯托斯《论石》、托名亚里士多德《石志》等著作里,祖母绿通常比红宝石等刚玉占据更大篇幅,且排序更靠前。但在中世纪伊斯兰著作里,二者的地位则被颠倒过来,塔米米(al-Tamimi,逝世于990年)(12)塔米米是10世纪活跃在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医学家,其宝石学著作主要关注的是宝石物性带来的生理功能。[50]、比鲁尼、提法施等学者的著作中,祖母绿均被放在红宝石之后,篇幅也不大。与贾希兹仅模糊提及祖母绿的比重不同的是,比鲁尼给出如把同样体积的红宝石重量作为100的话,祖母绿的重量为69.5([24],141页),这与其实际比重2.7—2.78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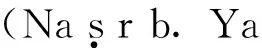

对于石榴石(al-bījādhī),贾希兹认为颜色如火焰般深红鲜艳为最好。石榴石越坚硬、尺寸越大,其价值越高。辨别石榴石优劣的方法是将它靠近羽毛,羽毛竖起程度越高,其品质越优异。重量为半密斯卡尔的优质石榴石价格为30第纳尔,但真正珍贵的具有极致色泽、即便在夜间也可看到光泽的石榴石是无价的。
石榴石在铜器时代已经非常普遍,在古埃及到古希腊文化中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并成为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到地中海世界贸易路线上的重要商品之一。到古罗马时期,由于红宝石的竞争,石榴石在人们对宝石珍贵性认知方面略有下降。[52- 54]如前所述,在便于古人检验的各类特征中,石榴石和红宝石几乎仅在硬度上存在些许差别,因此很多文献并没有明确把它们区分开。例如普林尼提到的carbunculus泛指所有红色宝石,他还错误地把石榴石的产地从印度记为小亚细亚的Alabanda([48],Book XXXVII,Chapter 25)。
至于辨伪方法中提到的吸引羽毛竖起的能力,显然贾希兹错误搬用了电气石(又称碧玺)的性质。红色电气石与红色石榴石在外观和硬度上均较为接近,区别就在于电气石具有压电性和热电性,故在受热或摩擦后可以产生静电磁场而吸附周围较轻的物体。在迪奥斯科里德斯和普林尼的著作里曾提到一种称为lyncurium的由猞猁的尿液凝结成的类似石头的物质([55];[48],Book XXXVII,Chapter 57),泰奥弗拉斯托斯提到它具有如琥珀般的吸引力,不仅能吸附稻草和小木片,甚至能吸附薄的铜或铁片([43],51,109- 113页)。有学者以此推测lyncurium即为电气石,并称泰奥弗拉斯托斯最早记载了它的热电性。[47]问题在于作者们为这种类似石头的物质赋予产自动物排泄物的来源,这与古典时期地中海世界罕见的电气石的性质明显不同。因此lyncurium究竟为何物,目前还无法得到确切答案。此外,《石志》中提到石榴石可以吸引头发、稻草等([41],143- 144页)。比鲁尼在论述红刚玉的最后附带记载了石榴石([24],72- 75页),但没有提到它能吸附轻小物体的性质。中世纪学者对电气石的详细记载,或最早见于提法施。他记述产于斯里兰卡山中的电气石“与头发或胡须摩擦后,放在地上可以抬起稻草或其他物体”([56],115页)。这种宝石性质与产地、名称准确对应的过程,或许也反映了中世纪丝路贸易渐趋紧密所导致的知识传播。
关于本卷最后两种宝石——水晶(al-ballūr)和钻石(al-mās),贾希兹的描述也非常简略,仅列出其价格评判标准为颜色、纯净度和尺寸。其中贾希兹指出,最好的水晶除了清澈、无色、纯净外,还有被制成“法老的玻璃”的那些。玻璃在近东和古埃及均很早出现,甚至炼金术最早的目的即为制作用来冒充宝石的玻璃,出于此原因,水晶和玻璃成为《斯德哥尔摩纸草书》等早期炼金术文献中讨论最频繁的对象。在贾希兹其他著作如《动物学》中,也提到将水晶用于玻璃制作,8世纪学者扎比尔的著作则给出了详细的工艺和配方[57]。
在商业手册这一文体内,贾希兹于《论商业之洞察》中简写或忽略的一些宝石,如钻石、珊瑚、玛瑙、缟玛瑙等,在迪马士基的著作中得到了篇幅不亚于前述宝石的介绍([38],33- 38页)。这显示在丝路沿线贸易技巧得到发展的同时,商业手册也成为宝石知识在贸易活动中不断被择取和沉淀的场所。
2.4 第7部分“尾篇”的博物学意蕴
在“尾篇”里,贾希兹呼应了序言中实用的世界主义,排比式地列举了便于求知者评判事物的标准,以及在求知后普遍适用的行为训诫,进而总结补充了正文部分里对各项事物的陈述。这些标准再次验证了在正文里,贾希兹对知识的聚集绝非追求“无用之学”,而是具有高度目的性,哪怕他的目标读者可能只是文雅的知识阶层而非有志于远涉重洋经商求财之人。
首先,贾希兹极为简练地区别了8类事物或人物最珍贵的品质。如更有价值的服饰是“更柔软、更奢华和更让人容光焕发的”,更昂贵的珠宝是“更纯净、更耀眼的”,更高贵的人在于是否“更睿智和更随和”,更令人憎恨的敌人在于他是否针对“我们更亲近的人”等等([5],29- 30页)。在此贾希兹把正文中所论述的对象,即自然和人造物扩展到对人和人际关系的评价,作为随后规训人们行为的过渡。
在一段告诫读者撇开命运给人带来的浮名,要善待穷人、施舍弱小等格言后,贾希兹论述了认知事物质量优劣的五种途径:观看它是否富有吸引力和纯净;嗅它是否芳香怡人;品尝其味道是否甘甜爽口;听其音调是否纯粹和谐;触摸它是否柔软精细。前卷所述正文内容,固然是这些认知途径的注脚,而这些方法更重要的运用领域,或许还是贾希兹接下来所论的人事。他提到善人容易相处、充满喜悦、谦逊有礼,而恶人贪得无厌、小肚鸡肠、面色阴沉、性情多变、缺乏幽默、言辞粗俗。对于被鼓励外出寻求知识或财富的人而言,这些描述都需要他们运用前述五感去予以认知。最后,贾希兹借3世纪萨珊波斯君主沙普尔一世之口,说智者不宜对醉鬼、掮客、小丑、病人、占卜师、诽谤者和健忘者说任何重要的事情。这既是另一条对读者的提示,同时也将这些人排除到所设读者群之外。([5],30- 31页) 这些内容显示《论商业之洞察》各卷搜罗的知识带有工具性。如果说普林尼《自然史》的目的在于以百科全书的形式歌颂世界性的罗马帝国,那么贾希兹著作的目的则在于以简明手册的形式,启发读者从对物的认知出发,提炼对世界的普遍认知的方法。
3 结 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概括本文尝试论述两个层面的问题。
在具体层面,本文聚焦于贾希兹《论商业之洞察》这一丝路文化交流意义甚于博物学意义的文献,通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相关文本进行比较,探查它在伊斯兰博物学发展脉络中的定位,讨论中世纪前期伊斯兰博物学向商业领域渗透的情况。
从《论商业之洞察》写作目的、资料来源、叙述方式等方面来看,该书具有以商业手册为主、博物成分为辅,重于充实见闻、轻于指导实践,知识来源广泛但疏于考辨等特点。就所载知识而言,贸易中常用的贵金属和宝石识别优劣、了解价格、辨明真假等是该书最关注的方面。尽管未必读到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贾希兹仍能够接触到足够资料来完成他的概述,我们通过知识的比对,可发现贾希兹的著作沿袭了古典时代到中世纪早期的泰奥弗拉斯托斯、托名亚里士多德、托名俄尔浦斯等人专著里的相关知识乃至错误阐释,同时他在绿松石等原产自波斯地区、同时古希腊人缺乏重视的门类又较前人有所发展。另外他还引用了一些早期炼金工艺,这意味着贾希兹或许融汇了来自西部的地中海沿岸和来自东部的波斯知识,而这也正是当时刚刚形成的阿拉伯语科学语料库的主要来源。
在总体层面,即把《论商业之洞察》置于中世纪伊斯兰博物学的发展脉络中观察,可看到该书舍弃与贸易关联不紧密的矿藏分布、开采、加工、民间传说等博物学文献原本堪称丰富的记载,序言和终章里尽管显露出应广泛吸收知识的世界主义倾向,但这些文字更重要的目的仍在于从伦理方面为读者提供训诫,从实际操作层面为教义加注。一面割除博物学兼收并蓄、言无不尽的特点,一面增强教义伦理对知识的统辖,从横向上它与贾希兹其他著作如《动物学》等呈现出近似特点,在纵向上它显现的缺乏独立性、内容单薄浅显、方法规范严谨性不足等特征,也契合于从亚里士多德传统向与宗教神秘主义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的新倾向游移的古典时代晚期博物学体现的知识趋向。中世纪伊斯兰科学接受吸收古典时代晚期地中海沿岸知识时,最初以炼金术、占星术、医学等具有近似性质领域为重点,《论商业之洞察》可视为此种倾向在博物学领域的体现。
即便在发展初期,博物学就已向商业等领域渗透,《论商业之洞察》具有使后世两方面著作彼此交叉影响的作用。贾希兹作为一代文坛巨子,在该领域创立初期贡献了重要著作,他的局限性又引发后世学者的思考和批判,他也就成为了伊斯兰博物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贾希兹以后的比鲁尼在宝石学著作中多有商业信息,迪马士基的商业手册则充实发扬了贾希兹所载博物学内容。随着中世纪伊斯兰科学传统的树立,知识内容里以道德训诫为重心逐渐转移为亲身观察和理性思辨,伊斯兰世界商业的繁荣则为博物学者提供更加广阔的信息来源和进行验证的机会,这都为知识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目前以丝路跨文化比较视角重新整理解读古代科技文献的研究远未充分展开,特别是仍有丰富史料未得到丝绸之路史和科技史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论商业之洞察》尽管篇幅不大,但作为博物学和渗透于商业贸易的文本,它展示了丝路沿线知识汇聚、择取、表述的情况。本文的分析讨论或有助于丰富深化我们对丝绸之路跨文化知识交流与传播的认识,亦期待可为学界把更多文化传统、知识领域和文本类型纳入关注提供参考。
致 谢本文阶段性成果曾于2019年11月在中央民族大学“边疆与博物学”工作坊作报告,得到袁剑、李鸿宾、刘华杰等老师的评述和指正。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硕士生杨婉莹协助译释了相关阿拉伯语文献。特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