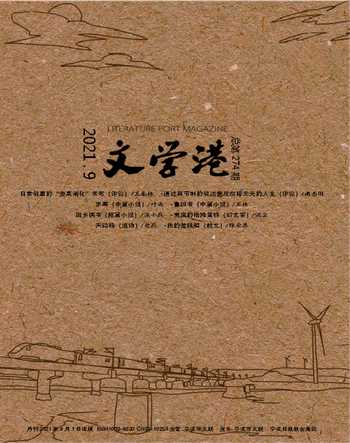朽木(组诗)
2021-02-28杨泽西
杨泽西
黄昏时刻
蚂蚁的尸体从阴影中爬了出来
蚂蚁它没有动,是太阳
挪动了它的黑暗
诗歌寄居在黑色汉字里
语言仅仅是一条通道
从一个词语跳进另一个词语
我在房间中,被阴影笼罩着
试图借助一枚汉字的入口
倾听体内汉语的回声
空间幽闭,我从所有事物的阴影中
捕捉到一个虫洞的光点
但它仍会随着时间发生位移
黄昏把最后的光線锁进黑色的瞳孔
万物在余光中轻轻地颤抖
慢慢蜕掉光的壳
一首诗再次遁入白纸之中
没有一丝回响。夜色中
丝瓜的触角抓住了虚空
晾衣绳
你一旦存在
就有了自己的异端
在开始和结束的地方
被命运打上结
这便是你短暂的一生
你的身体上常常出现
多个人形,他们
虚脱在衣服的骨架里
你撑着这所有的重量
空无一物的时候
你才属于你自己
但风一吹
你又在自己的身体里摇摆
更多时候你需要下坠的引力
暴雨过后
你孤零零地悬挂在院子里
像绞索
拧出自己的血
空 白
绝对的空白是不存在的
没有一丝污点的雪地
将会导致雪盲症
一只黑白相间的喜鹊
成为了你视觉的落脚点
你身体里的冲突开始缓和
你不可能成为你自己
剥离了群像的映射你只是一点空白
在绝对的空白中你将变黑
无形的锁链在空气里
你是其中一环,生活是铁
诗歌是容器和短暂的钥匙
为确定自己的位置
你从一环跳到另一环
你在环中空白的地方
花 鸟
万物皆不是比喻,
又都是比喻。
蜂是花的鸟。
那是一个不为人类所知的
真实的世界。
我的眼球同一时间
只能聚焦于同一个花束,
蜂眼里分裂出的
却不是同一个我。
鸟站在树枝上,像个逗号,
鸟鸣完成了树诉说的一部分。
我们听到的
已被短暂的空白转述它的语义。
同样的,目之所及
是光和阴影和解后留给宇宙的遗产。
我们在黑暗中辨别自身,
用物质粉刷世界的颜色,
在语言中寻求那最不真实的交流。
沉默是这世间唯一的信使。
皮影戏
其实一开始它不会动
它也不会说话
它只是一片纸或一张兽皮
是有一双手、一张嘴操控它
在光的投射下
它开始进行各种人的动作
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光
也没有上帝
没有光就没有阴影
这光和影形成的矛盾之奥秘
也就不会被人捕捉
从此制造出更多黑与白的冲突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人
没有人,就没有演绎这场皮影的工具
就没有了这场皮影戏
没有人,就没有人间
没有人间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其实从你到来的那一刻起
这一切都已准备好了
有光,也有影
有一双手和所有制造好的工具
你只好穿上人皮
开始在影子里表演
寂 静
我没有看到鸟在枝头
但我听到了鸟鸣
是寂静送来了声音
羊在草地上吃草
我看着它们
我的眼睛要比我愉悦
干旱露出井底
绳子终于断了
几只青蛙在里面徒劳地弹跳
如同写作那无意义的钟摆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枯竭了
在空无中反复打捞一个词
最后又把整首诗插进寂静的宇宙
我在院子里坐着
吹着暖风,晒着太阳
此刻我不动用知识和思想
我也算得上是一种植物
这幻觉让我感到平静和放松
但这寂静是短暂的
一旦我意识到我是一个人
朽 木
我到河边散步
看到了一截朽木
我是幸运的
不是谁都有机会散步
并从一截朽木中看到不朽的部分
因为易朽,它的身上长满了木耳
所以它能听到大自然中美妙的声音
大多时候人们都是忙碌的
不会停留下来用心观察身边的事物
河水的波纹是如何一圈一圈在晃动
花蕊里的花粉都是什么形状
树上的鸟雀又在捉弄自己的羽毛
光线从树叶的缝隙里掉下来
又组合成好看的阴影
这些都是无用的事物
我们正是在无用之中
才审视到自己的内心
夕 光
多么富足的时刻
夕阳把它最后的金子撒在大地上
万物因自己的内心而变得富有
祖母在林子里拾捡干柴
收获了物体之外多余的财富
太阳像一枚鸟蛋
落入树枝上的鸟巢里
被黑夜孵化出一只毛茸茸的月亮
婴儿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着了
寂静为人间带来了福音
孤 灯
能听到寂静之音
朽木之上长出了木耳
一张木椅子只有空着的时候
才能听到它体内树的回声
空无继续塑造着我
偶尔有陌生句子抚慰白纸
让两个孤独的汉字
在词语的意义里重逢
又重新回到诗歌的无意义
已不再为诗人的身份感到难为情
一盏孤灯照着另一盏孤灯
所有的光线都可以省略
我们在重合的影子里现身
照见彼此
春雨后
蜘蛛网上挂着几颗晶莹的水珠
阳光下像宇宙的眼睛
我看它们的时候,它们也在看我
杏树软软的花骨朵,婴儿的拳头一样
伸出来向春天索要光——
这人间幸福的乳汁
鸟鸣如空气中小提琴的点缀
每一件细小的事物
都在寂静里发出和声
微风的手指轻柔地滑过植物的琴弦
春雨后的田野更明亮了
麦子饮着甘甜的雨露
人们在小路上散步
聊着琐碎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