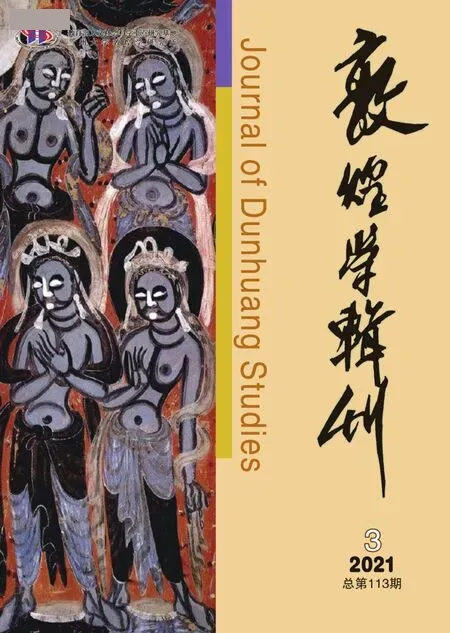北齐徐显秀墓菩萨联珠纹探源
2021-02-24郑炳林
沈 雪 郑炳林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徐显秀墓位于山西太原王家峰村,即北齐时晋阳城附近,2002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下简称徐墓)。墓的甬道两侧和墓室内四壁等均绘有壁画,共有300多平方米。此墓一经发掘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墓中精美的壁画为丝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墓中北壁、东壁和西壁中出现的联珠纹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诸多关注,尤其是东壁和西壁出现的联珠纹,其图案颇为相似,都是联珠圈内有一人物头像:头戴宝冠,宝缯垂肩,面容安详静秀,与中原菩萨形象实无二致,故荣新江将这一图案称为“菩萨联珠纹”(1)荣新江《略谈徐显秀墓壁画的菩萨联珠纹》,《文物》2003年第10期,第66-68页。,本文延用这一名称。
据徐显秀墓志,徐为忠义人,其祖安,为怀戎镇将。墓志称徐为边地少年,先入尔朱荣军中,后追随高氏,官至太尉。(2)常一民、裴静蓉、王普军《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第4-40页。据考证,忠义郡当为蔚洲治下,此地人民多为怀荒等边镇旧民,对徐显秀少时的边镇属民身份当无疑议。(3)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01-203页。六镇之地除了鲜卑武将,还有粟特人,突厥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多民族文化杂处的背景下,虽然徐为汉人,却有可能熏染了较为浓厚的鲜卑习俗,且多与胡人有所往来。从徐墓壁画和出土文物来看,有学者认为墓葬整体受祆教文化因素影响,甚至怀疑墓葬中之所以会出现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人骨,极有可能是因为施行祆教的葬俗导致。(4)郎保利、渠传福《试论北齐徐显秀墓的祆教文化因素》,《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4-122、155-156页。联珠纹图案具有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背景,联珠圈本身即象征光明。菩萨联珠纹的联珠圈和菩萨头像各自关联到不同的宗教背景,却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图案中,其背后原因和意义值得深究。如徐墓壁画中的这一菩萨联珠纹确有极大可能是实际存在的纺织品,那么这一织物是哪里生产的?图案的来源又是哪里?这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文化脉络值得一探。
一、是否为实际存在的织物
徐墓壁画中菩萨联珠纹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为西壁牛车旁侍女的下半身衣服边缘和袖口边缘(图1、图2),一为东壁马鞍袱的边缘(图3、图4)。这两处地方都是以纺织品的形态呈现的,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两个织物图像都是实际存在的菩萨联珠纹织物?会否是画匠的即兴创作?本文认为这种菩萨联珠纹织物应是实际存在的织物。

图1 东壁备车图侍女

图2 侍女袖口处联珠纹

图3 西壁鞍马局部

图4 马鞍袱上联珠纹
从壁画绘制情况来看,不同于同时代的北齐娄睿墓和湾漳大墓等,徐墓壁画用笔简练、快速,犹如行云流水,且人物形象和细节刻画的非常生动,足见绘制者技法成熟、功力深厚。(5)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齐徐显秀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7页。以徐显秀当时的地位和背景,负责绘制壁画的人应是顶尖的工匠或画师,更会根据徐家人的要求尽量将主人生前的尊荣表现出来,凡入画的内容必要有所依据,所以人物服饰、画面布局也都非常讲究。虽然笔法流畅画得很快(据发掘简报,墙角还有没来得及丢弃的剩余颜料),但画面内容多是有所参照的,画家自己创作、自作主张将菩萨面容绘入联珠圈内的可能极小。

图5 撒马尔干大使厅壁画 (采自《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 粟特王出行图局部)
再看马鞍袱上的联珠纹,与牛车旁侍女服装身上的联珠纹,菩萨面容、图案构成均极为相似,只是颜色不同。这种联珠纹织物装饰马鞍袱的形制可在中亚的壁画和浮雕中找到类似的例子(图5),图5中壁画虽然漫漶,仍可见马背上鞍袱的边缘饰以联珠纹,只是其联珠窠较大,撒马尔罕壁画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联珠纹“鞍袱”。所以徐墓壁画中所绘联珠纹马鞍袱应为实际存在的织物。
除了菩萨联珠纹外,北壁墓主人身前的两位侍女,所着服装上也有两种图案的联珠纹,一为联珠对兽对鸟纹,一为联珠花卉。在我国出土的织物中均可找到类似的图案(图6、图7)。因此,东壁和西壁画中的菩萨联珠纹也应是现实中存在的织物。从丝路沿线出土的联珠纹织物来看,这种织物一般是锦、绮等,都属于比较奢侈昂贵的,且多为胡人所穿着。那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三位面容不似胡人的侍女身上呢?这三个侍女的情况有所不同:北壁两位侍女立于墓主人身前,束发,头戴四角冠,外着小袖衫,细观其身上的联珠纹织物不是作为锦缘,而是整件衣身都是用联珠纹织物制成的,整体造型颇有胡汉融合的味道;西壁牛车侍女,其发型绝非束发,整体打扮更似西胡。史载北朝杂以戎夷之制,“爰自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高氏诸帝,常服绯袍”(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5《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30页。。又《北齐书》文宣帝诏曰:“……又奴仆带金玉,婢妾衣罗绮,始以创出为奇,后以过前为丽,上下贵贱,无复等差。”(7)[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1页。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侍女穿着如此华丽又“富有创意”就说的通了。整个墓室壁画中只有三位侍女穿着此等昂贵独特衣料制成的服装,究其原因,当是因为身份有别于其他婢女(从三个侍女在壁画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应是近身服侍的婢女),且也可以此烘托墓主人生前的荣耀与尊贵,至于为什么是联珠纹织物,而非其他图案的织物,应与徐显秀鲜卑化的汉人身份和当时胡风当道的社会风气有关。南北朝时随着丝路贸易的兴盛,各种异域风情的织物也已为人们所熟悉。又北齐时,朝野上下受胡风浸染甚深,“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茲風至今不绝后”(8)[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7《礼仪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63页。。高氏皇帝祀胡天,常服绯袍,上行下效,侍女衣料中出现联珠纹或身着胡服也只是这种风气的反映罢了。新疆阿斯塔那206号墓就曾出土过一个头梳高髻,身着精致间色裙的唐代女舞俑,身上所穿半臂就是联珠对鸟纹锦制成。

图6

图7
从服装形制上看,牛车旁侍女所穿服装,下半身的菩萨联珠纹应是作为镶拼的衣边和下摆的锦缘出现的,上半部分的联珠纹当是袖口的锦缘。有研究者说这件衣服下半身
是间色裙,从已经发现的间色裙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间色裙的下摆通常不会再镶拼这么宽的锦缘。只是若为胡服类的袍服,何以是右衽呢?史载“披发左衽”才是胡服的面貌(9)[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6页。。
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上)》中有一件北朝时期的袍服(图8),同样也为右衽,下摆的镶边也较宽,只是领口和袖口的款式与牛车侍女所着袍子不同(10)赵丰、尚刚、龙博编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上)》,北京:开明出版社,2014年,第219页。。此处值得指出的是,图8中领口及肩膀镶拼其他颜色织锦的细节属于粟特人服饰特色(11)在片治肯特壁画,两个国王举办的宴席的中可见。,而大袖和右衽属于汉族服饰的细节,却同时出现在这一袍服上,这恰恰是南北朝时期胡汉交融在服装上的一个反映。另日本Miho博物馆藏北朝石棺床J板块右幅图像,在下方“地上世界”中(12)姜伯勤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9页。,有一舞蹈女子,所穿袍服与徐墓中联珠纹侍女所穿十分相似:交领右衽,下摆镶边上的圆圈应为联珠纹,窄袖,且袖子较长,袖口有镶边(图9)。这一石棺床为在华粟特人祆教信仰的一个反映,其中有诸多胡人形象,J板上方的四壁女神经学者比定为娜娜女神。此处有几个细节值得探究:

图8 北朝锦袍(采自《中国物质文化史·纺织(上)》图4-5-2)

图9 Miho博物馆藏北朝石棺床 (采自《中国祆教艺术史》彩图五)
第一,细看徐墓中胡服侍女袍服下摆,画匠有浅浅地勾勒一条横线,将衣缘图案分成一横一竖两个部分描绘,注意比对勾线上下宾花细节即可发现-这与前述舞蹈女子袍服的细节不谋而合,虽然一个是墓室壁画像,一个是石刻像,表现手法不同,但两位工匠都将衣服的细节刻画了出来,这只能说明这种袍服的衣缘就是这样裁制拼缝的。且Miho石棺床双阙上也有头戴三棱风帽,身着交领右衽袍,腰束带,足登长靿靴的人物形象,与徐墓壁画中许多人物如出一辙。这诸多相似之处,应是不同领域的工匠对当时服饰形制的描绘与刻画。因此,这件衣袍应是当时生活中常见的款式,且为胡装打扮的女子所穿着,画匠只是将现实生活中的服饰入画而已。
第二,J板上的女子并没束腰带,上半身的交领衣襟也没有镶拼锦缘,只有下半身有锦缘,这个细节也与徐墓中一样。但一般这类的袍服,通常会整个衣衽都装饰锦缘。二者有别于常规却一致的细节,正好说明,这类胡服就是真实存在的款式。至于是如何做到只在下半身镶拼锦缘的,有可能采取了上下分裁的方法,裁剪方式类似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一件出土于北高加索的卡夫坦(Caftan)。(13)这种袍服在中亚曾经非常流行,波斯人、粟特人都穿着这种服装。这件卡夫坦专家将之复原后,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上下半身不是连裁的,而是在腰部开缝分裁,并于腰部侧襟处缝了纽袢以闭合。(14)Nobuko Kajitani. A Man's Caftan and Leggings from the North Caucasus of the Eighth to Tenth Century: A Conservator's Report.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36,2001,pp.85-124.
第三,徐墓中胡服侍女的发型与J板中女子有相似之处,但J板中女子明显脑后有发髻,徐墓中侍女则没有。有学者指出阿旃陀17窟中有女子发型与该侍女发型类似。(15)在《试论北齐徐显秀墓中祆教文化因素》中作者指出《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图19、20阿旃陀17窟壁画中的女子发型,与徐墓中胡服女子发型类似。二者轮廓虽有相似,但17窟女子为卷发,徐墓中侍女则更像辫发盘在头上。史载南北朝时高昌“女子头发辫而不垂”(16)[唐]姚思廉撰《梁书》卷54《诸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1页。,说明当时确有辫发不垂的发式。无论如何,总体上来看,徐墓中的这位女子整体是做胡人打扮。
北魏前期孝文帝改制前,拓跋鲜卑仍着鲜卑服饰,小袖袍在北魏早期墓葬和石窟中,十分常见,这种袍服基本上为交领,左右衽和对襟都有,长度及膝,在领口边缘和下摆都有撞色的镶边。(17)孙晨阳主编《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匈奴、鲜卑卷》,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可参见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画像砖中人物(18)张宝玺编《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5页。和云岗石窟十七窟供养人形象。(19)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译《云冈石窟》第2期第1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窟图版。孝文帝推行全盘汉化的政策后,褒衣博带的汉服和袴褶这类受胡服影响出现的服装,在人们的生活中都司空见惯。六镇起义后,以高欢为首的统治集团多以鲜卑自居,反对孝文帝以来的汉化政策,服饰上又趋于胡化。如徐墓中所常见的,交领右衽的长袍、长靿靴搭配以及改良后的“垂裙皂帽”(三棱风帽)的形象,具是经历汉化以后的鲜卑服饰。如牛车侍女所着衣袍,当是受西域服饰风格影响的胡服,其渊源可追溯到粟特人和萨珊波斯人所穿的卡夫坦(如前文所述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件袍服),种类多样,包括交领和对襟的款式。谢尔盖.琴科夫曾基于中亚地区的考古材料地对5-8世纪的粟特服饰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其中就有交领、小袖的长袍。(20)Yatsenko S A,the Late Sogdian Costume(the 5th-8th cc.AD),Compareti M.Eran Ud Aneran: 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ch Mars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http://www.transoxiana.org/Eran/Articles/yatsenko.html,2003.除了上文提到的Miho博物馆藏北朝石棺床之外,关于在华粟特人的着装,在北周史君墓、西安康业墓石椁中也有发现。如北周史君墓石堂南壁浮雕中举杯的粟特人形象,也穿着交领右衽的袍子,衣衽、下摆和袖口均有镶边。(21)杨军凯著《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37页图版一四。
如上所述,徐墓中牛车旁侍女所穿袍服应是当时常见的胡服款式,用来做衣缘、下摆和袖口的菩萨联珠纹也应是实际存在的织物。如此说来,此处真实地发生了“穿戴”和“使用”,但从当时的崇佛氛围来看,却有不敬之嫌。难道说,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图案的纺织品只是昙花一现,未在其他地方出现的原因?又或是联珠圈内并非菩萨头像?这些疑问应与其产地、输出对象和图案母题息息相关。
二、菩萨联珠纹产地溯源
在目前发现的联珠纹织物中,联珠圈内经常出现的图案有羊、鹿、野猪头、天马、含绶鸟、森木夫(senmurv)等动物,多具有宗教或文化含义的,联珠圈本身也象征者光明。这类图案早期通常与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称之为祆教)联系在一起,后来随着这种纹样在丝路上的传播,其宗教含义慢慢淡化,装饰性增强,并被各个地方的文化赋予新的内容传承了下来。徐墓中所见的联珠纹图案明显受到了萨珊波斯艺术的影响。然而,徐墓中的菩萨联珠纹,其人物形象,无论是画法还是人物面容,都是汉地的菩萨无疑。要诞生这种融合了祆教装饰图案、佛教偶像和中原艺术风格的织物,其产地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生产条件:优秀的织工、生产材料(如丝),结构较为复杂的织机。
第二、社会背景:这类菩萨形象和联珠纹织物同时广泛存在于社会环境中,且为人所熟悉。
第三、输出对象:通俗的讲,就是生产出来给谁穿,或者是谁定制了这种织物。
联珠纹织物从纺织材料上看,主要有丝织物和毛织物,尤其是丝织品,占大宗。菩萨联珠纹织物若是产于汉地,那么极有可能是锦,且从我国目前出土的联珠纹织物来看,确实锦比较多。众所周知,我国的丝纺织业极为发达,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就属于经锦,只是南北朝时战乱频仍,是否还有实力生产出如此精美复杂的织物呢?
自汉时起,已设有东西织室作为官营手工作坊,(22)[清]孙星衍,[清]庄逵吉校定《三辅黄图》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1页。产品有“锦绣、冰纨、绮縠”(23)[宋]范晔撰《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2页。。此时丝织业已非常发达,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四川地区,尤其是蜀锦,“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24)朱启钤著《丝绣笔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5页。后五胡入主中原之时,都非常重视对劳动人口的掌控,搜刮工匠归政府管制,如拓跋珪攻占中山,即将“百工伎巧十余万口”,迁至京师。且多承旧制,如石赵的中尚方、御府和织成署的织锦工巧,就有数百。(25)韩国磐著《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7-168页。邺中织锦署织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不可尽名也”,除此之外还有“鸡头文罽、鹿子罽、花罽”。石虎“又尝以女伎一千人为卤簿,皆着紫纶巾、熟锦袴、金银镂带、五纹织成靴”。(26)[晋]陆翙撰《邺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页。
由此可见当时丝织品不但种类丰富,产量也颇为可观,且罽属于毛织物,源自西域,说明胡人工匠当时亦不在少数。《艺文类聚》载:“梁皇太子谢勑賚魏国所献锦等启曰,山羊之毳,东燕之席,尚传登高之文,北邺之锦,犹見胡绫织大秦之草,戎布纺玄莵之花……又谢东宫賚辟邪子锦白褊等启曰,江波可濯,岂藉成都之水,登高为艳,取映凤皇之文,至如鲜洁齐纨,声高赵縠。”(27)[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85《布帛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58页。北朝所产织锦,质量亦不在蜀锦之下,且各个品种的丝织物都继续生产,丝路贸易发达,来自大秦的胡绫和印度的戎布还是随着胡人商队如约而至。
至北齐时,又设有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紬绫局。(28)[唐]魏徵、令狐德撰《隋书》卷27《百官志》,第843页。官营作坊如此发达,必然具备生产材料、技艺高超的工匠和相应的织机。民间也有许多贵族,家有小型作坊,私藏工匠,屡禁不止,如毕义云“家有十余机织锦”,并因此而获罪(29)[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卷47《毕义云传》,第658页。。又祖珽尝“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百余匹”与人赌乐(30)[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卷39《祖珽传》,第514页。,可见当时北朝确有出产西方风格的丝织物。(31)中亚的联珠纹织物是纬锦,织机及织造技术与我国不同,一般计量单位用“张”,而产自我国早期的锦为经锦,计量单位用“匹”,后来因为丝路贸易的往来,我国才习得了纬锦的织造技术。从此处行文来看,用“匹”作为计量单位,应是产自山东无疑。青海、新疆等地都曾出土联珠孔雀纹的织锦(图10)。

图10 联珠孔雀纹锦(作者摄于青海藏文化博物馆)
那么南朝是否也具备同样的生产条件呢?自东晋以来,大批北人南迁,其中不乏诸多工匠,遂也将丝织技术带到了南边。南朝政府大力劝课农桑,“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又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32)[梁]沈约撰《宋书》卷54《孔季恭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0页。益州此时仍是丝织品的主要产地。隋时,何稠曾为隋文帝制波斯锦,“锦成,逾所献者”。其叔父何妥史载为细脚胡,入蜀后为南梁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之事而致巨富(33)[唐]李延寿撰《北史》卷82《何妥传》、卷90《何稠传》,第2753、2985页。。何氏作为细脚胡,据考即为粟特商胡,曾为萧梁王室制作西方风格的丝绸和金银器。(34)林梅村《何稠家族与粟特工艺的东传》,收入荣新江、罗丰《栗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1页。
从上述史料和考古材料来看,当时的北齐和南朝,都具备生产这类织锦的条件,但是菩萨形象是如何走入联珠圈内,成为纺织品图案的呢?为了探寻这一联珠纹织物产生的来历,有必要追究佛、祆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情况。
佛教和祆教都属于外来宗教,或许在佛教进入中国初期,由于信众对于佛教尚不甚了解,所以在瓦当或是其他器物装饰中出现了佛教神祇的人物化形象,但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深入,这种现象逐渐消失了。南北朝时,由于战乱频繁,统治者依赖佛教巩固其政权故大力推崇,百姓希望从中找到精神寄托故信仰供奉。然而细究起来,南朝和北朝在佛教信仰方面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北朝重在“力行”,南朝重在义理。北魏臣工自诸王以下,以致阉党、羽林、虎贲等,多舍宅立寺。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为北朝佛法之特征。(35)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1页。《洛阳伽蓝记》载:
景乐寺,太傅清河文献王怿所立也……寺西有司徒府,东有大将军高肇宅,北连义井里……有佛殿一所,像辇在焉,雕刻巧妙,冠绝一时……至于六斋,常设女乐……及文献王薨,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后汝南王悦复修之。悦是文献之弟。召诸音乐,逞伎寺内。(36)[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5页。
如上所见,舍宅立寺当为力行供奉的“虔诚之举”,但实际对佛教的信仰颇为表面化,逞伎寺内实为不敬。北齐诸帝亦崇信佛法,却也胡化甚深。《北齐书·神武纪下》记载:
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护军祖莹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37)[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卷2《神武帝纪下》,第12页。
在这四十万户中也包括了西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其中不少应是西胡。(38)[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第161页。何以见得呢?北齐诸帝多有喜握槊、胡乐者,且后来多有胡人近臣如穆提婆、高阿那肱受封高位,胡风之盛,胡人之多可见一斑。
相对北朝而言,南朝帝王即位,年岁稍长知学者,靡不讲理佛学,并重学理。帝王之信佛者,多于佛寺设斋,又尝于宫殿设四部无遮大会,或无碍法善会。会中帝或亲行讲经说法,大赦天下,并且为之改元。更有梁武帝、陈武帝舍身入寺。(39)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02-303页。究其根本,皆因南朝诸帝均以汉文化为出发点而接纳佛教,与北齐高氏以鲜卑自居,看待佛教颇为不同。
徐墓中的两处菩萨联珠纹图案,其菩萨形象颇为一致:头戴三叶宝冠,宝缯束扎后垂下,面庞圆润静秀。这一风格的菩萨造像,在北齐境内十分常见(图11、图12、图13)。(40)李晔《山西北朝菩萨造像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6世纪天竺佛像一再东传,高齐重视中亚胡伎艺和天竺僧众,对北魏汉化政策的抵制,使得此时的北齐造像不再是“褒衣博带、秀骨清相”,而是具有笈多时代秣菟罗艺术风格。(41)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文物》1999年第10期,第44-59页。但又不同于犍陀罗式的高鼻深目,此时的菩萨面容更为本土化,五官更为柔和圆润。李裕群在论及成都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时曾指出,北齐邺城地区和太原地区的佛教造像都受到了南朝的影响。(42)李裕群《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0年第2期,第64-76页。从成都出土的菩萨造像来看,也可找到如徐墓中联珠纹内的菩萨形象(图16)。南北朝造像,此时都受到了笈多风格的影响,大量的僧侣或经西域沿陆路来到中国,或从海陆来到中国,随之而来的一定也有擅长造型的域外工匠。这里考察其时丝路沿线发现的造像,或可发现一些与本文提到的图案构成有关的线索。(图14、图15、图16)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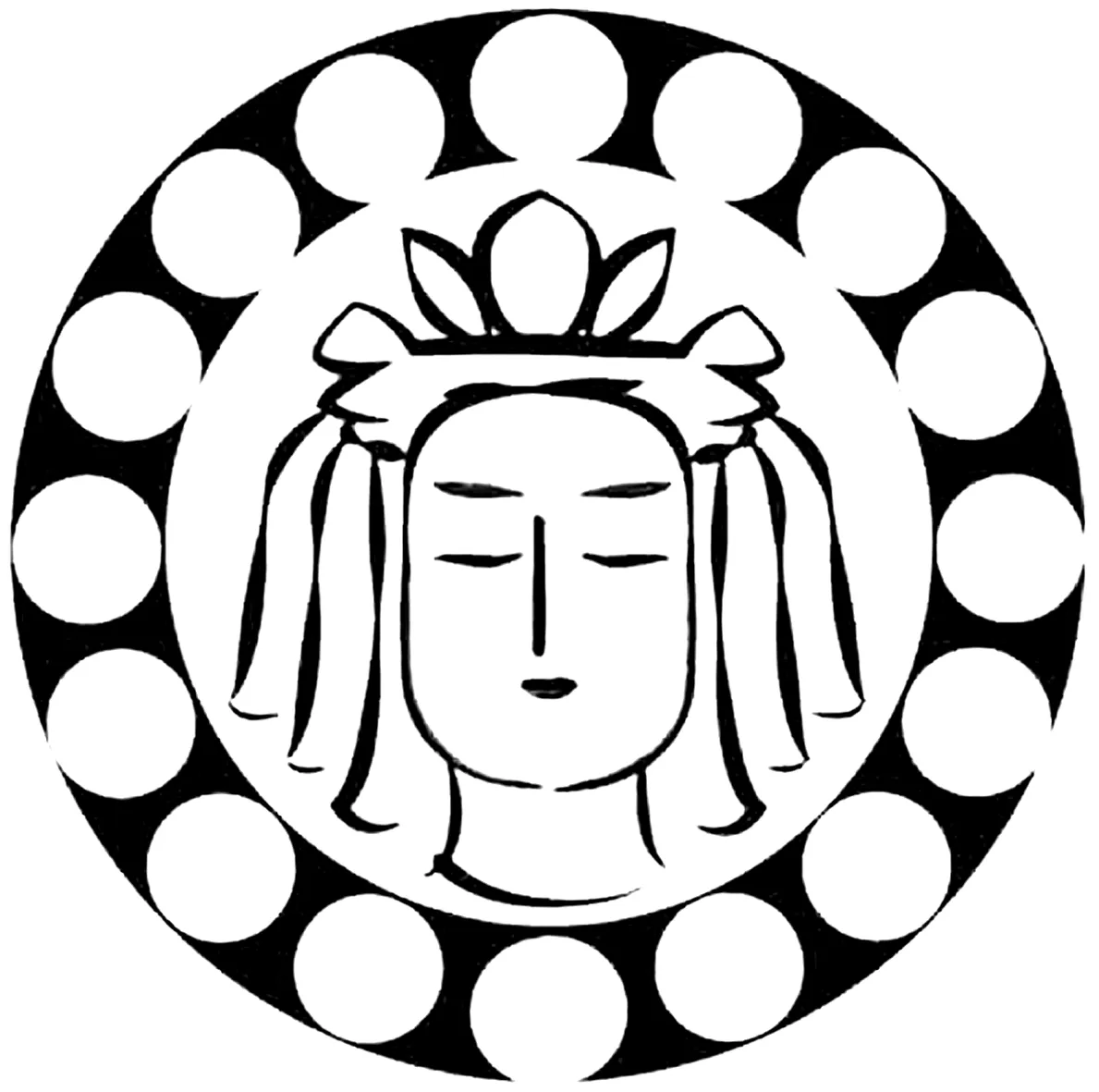
图16
图14来自印度中部地区,是笈多时代(5世纪晚期)。在印度,这种神龛是极为常见的寺庙装饰形态,龛内的圆形部分俗称月亮屋或牛眼睛,联珠圈内,柔和的人物面庞是笈多时代的常见造像特征之一。(43)Bromberg A,the Arts of Indi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Himalayas at the Dallas Museum of Art, Dallas:Dallas Museum of Art,2013,p.55.这种神祇头像与“月亮屋”的组合,在5-6世纪北方邦还可找到类似的构件,但神龛整体发生了一些变化。(44)在故宫博物院等编《梵天东土·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2》中图95、103、106均为月亮屋型神龛,龛内是印度教的湿婆或战神。笈多时代,统治者采取宽容的宗教态度,雕刻这些印度教寺庙的工匠同样也负责雕刻佛教寺庙,所以这种壁龛形式并不一定是印度教独有,也会应用到佛教寺庙的装饰中。图15是斯坦因在新疆焉耆明屋遗址发现的陶砖,6-7世纪,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内,菩萨头戴三面宝冠,呈现出犍陀罗造像风格。这三张图片中的人物面容并不相似,但是其联珠圈+人物(神祇)的构成形式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彷佛在揭示着某种联系。
本文认为菩萨联珠纹织物产生的方式可能有两种:第一,随着丝路上西域、南北朝僧侣及商人往来于中西,这种图案构成形式也随之沿着丝路来到了中土,纺织工匠参考其他艺术形式,创作了菩萨联珠纹。历史上也不乏不同领域的工匠相互借鉴图案的例子,比如纺织品中的勾连雷文在青铜器上出现,又比如固原北魏漆棺画中的交波纹也有类似结构的图案出现在织锦上;(45)赵丰、齐东方主编《锦上胡风: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8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4页图21。第二,中亚地区已有类似构图的联珠纹织物传入中国,纺织工匠将其本土化了。美国大都会馆藏有一件王者半身像联珠纹织物(图17),这块7-8世纪的中亚织物有两层联珠圈,联珠圈内的人物形象与萨珊波斯王者的形象相近。菩萨在佛教中是释迦摩尼的前世,是世俗中的王者。在佛教造像中,菩萨头戴宝冠的形象,即与此有关。在敦煌莫高窟早期的菩萨造像中,其头冠就受到了萨珊波斯王冠装饰元素的影响。(46)赵声良《敦煌石窟北朝菩萨的头冠》,《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8-17页。如果将“菩萨”作为王者的另一种形象,代入联珠圈内也合乎情理。

图17 中亚出土半身像联珠纹锦采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品号 2008.79
那么,徐墓中的菩萨联珠纹究竟是诞生于着装“以创出为奇”的北朝,还是宫人会“服用射猎锦文”的南朝?(47)[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19《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19页。
如果菩萨联珠纹出现在南朝,那么益州地区是最有可能的地方。这里同时具备了出色的生产条件、可参考的佛教造像以及往来于中西弘法的僧侣和经商的胡人,但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诸多僧侣布道宣教,大力推动了益州地区的佛学教义的发展,(48)曹中俊、李永平《益州佛教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关系:以僧侣、义理、造像为考察中心》,《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第28-41页。加之南朝统治者不同于北朝的对佛教独一无二的虔信态度,菩萨联珠纹不可能诞生于益州。最根本的原因是,徐墓整体具有很浓厚的祆教信仰的暗示和装饰趣味,在这一语境下,“菩萨头像”出现在“胡服侍女”的服装上,即“以佛入祆”,用佛教中的菩萨形象构成富有祆教意味的织物图案来装饰卡夫坦类的胡服。这里对比莫高窟420窟及402窟中出现在菩萨天衣上的联珠纹,即可发现,莫高窟的两处洞窟整体为佛教的语境,天衣上的联珠纹是“以祆入佛”,成为佛教神祇服装的装饰图案。两相对比之下,徐墓中的菩萨联珠纹如果出现在益州,则有悖于益州佛教的实际情况,即便此地有胡人会穿着联珠纹织物,但纺织工匠既缺乏动机,也实无必要将菩萨头像织入联珠纹内。
结语
综合以上论述,徐墓中的菩萨联珠纹应当出产于北齐境内,其原因总结如下:
1.符合北齐“以创出为奇”的攀比、竞奢的社会氛围。
2.北齐当权者兼祀胡天,佛、祆并重,地位不相上下,如此上行下效,对佛教的信仰是为了满足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并不深究义理,贵族甚至“逞伎寺内”,缺乏敬畏之心。
3.如徐显秀这样的贵族,即为这类织物的输出对象:胡汉杂糅的成长背景,深染胡风的信仰,想要通过奇珍异宝彰显尊荣的需要。
4.佛教造像遍布,头戴三叶宝冠,宝缯垂肩,面容秀润的菩萨形象已为人所熟悉。
5.随西来僧侣一起传布到中原的“联珠圈+神祇”的图案形式。
6.有生产能力织造媲美蜀地的锦,且已有按匹计数的“联珠孔雀罗”,联珠纹织物都已经开始了本土化生产。
菩萨联珠纹织物的出现,从图案上来看,是粟特美术形式伴随着两种不同宗教在丝路上的传播,融入当时的北朝社会,并与中原艺术相结合。反过来,也体现了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祆教与佛教,如何看待与之相关的服饰风格。从织物生产的角度,则反映了当时的纺织品生产还是比较发达的,不但没有因为战乱而减弱倒退,反而由于上层阶级追求奢靡享受等原因,进一步发展,已经能够吸收外来的织物风格并进行模仿和创新。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来看,菩萨联珠纹之所以昙花一现,也许就是因为人们对佛教的理解逐渐加深以及佛教地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