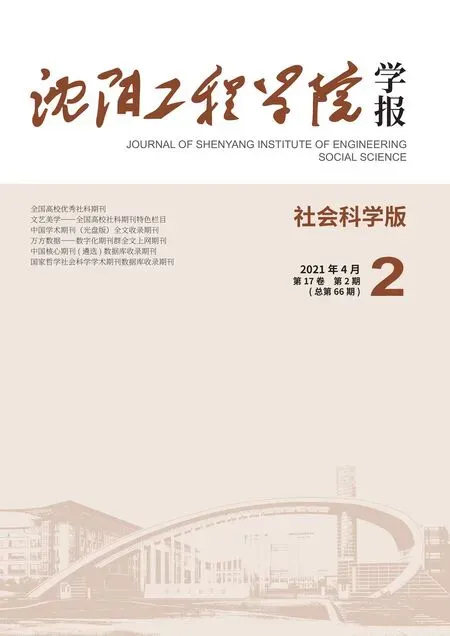《别让我走》的身份认同研究
2021-02-13张天歌
张天歌,王 钢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四平 136000)
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身份认同的焦虑,“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将到哪去”等问题成为现代社会中困扰人类的谜团。作为移民作家的石黑一雄借助克隆人这一现代科技的产物表达了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其中既包含作家因为移民经历而对自我身份归属问题产生的困惑,也包含作家对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滋生的焦虑。
一、《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自我身份迷失
小说《别让我走》是石黑一雄在2005 年出版的一部科幻小说,作家一改前几部作品中明显带有民族、国家叙述色彩的写作方式,放弃历史与种族的枷锁,转而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与世隔绝、同当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名为黑尔舍姆的空间场所,并讲述了生活在其中的克隆人凯茜与朋友汤米和露丝三人短暂的生活经历。小说背景设立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格兰,主人公凯茜及其同学都是克隆人,他们在全封闭的学校黑尔舍姆中长大。在成长过程中,克隆人们被来自人类世界的教师告知他们作为克隆人的身份以及会在将来为患有疾病的人类不断捐献器官直至死去的命运。小说中的克隆人在接受正常教育成年后会离开黑尔舍姆去往村舍,在村舍与来自其他封闭地区的克隆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最终,主人公凯茜与汤米和露丝分离,汤米和露丝作为器官捐献者相继死去,凯茜作为看护工作者则目送了她的朋友们的死亡。
《别让我走》沿用了石黑一雄一贯的记忆主题,叙事节奏缓慢,故事情节以凯茜的回忆娓娓道来。在克隆人们本就短暂的生命中,作家最为着重叙述的就是凯茜们对自我身份的追求。凯茜与其他克隆人自出生之日起就生活在黑尔舍姆这个全封闭式的学校中,黑尔舍姆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监狱,将克隆人与外界牢牢隔开,克隆人也如囚犯一般,按需领取生活用品,每天早上接受训话。整个学校看起来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所描绘的“全景敞式建筑”,充当狱卒角色的就是来给克隆人上课的人类教师,他们将为人类做贡献是克隆人的义务的观点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凯茜们,并时时刻刻监视着克隆人的行为和思想是否有异常。“除了监视功能,全景敞式建筑还是一个实验室,它可以被当作一个进行试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尤其是可以利用孤儿重新采用具有重大争议的隔绝教育”[1]228,克隆人们在一个看似世外桃源的空间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时时刻刻受到人类社会的压制,几乎无法从外界得到有关自我身份的任何认知,“隐性的权力关系每时每刻都在运行着”[2]58。他们从没有被灌输过“父母”的概念,也不知父母为何物,在受教育后,克隆人们才发现自己的人生没有来处,这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茫然与惶恐。
小说还讲述在黑尔舍姆有一位被克隆人们称呼为夫人的女士。夫人的存在很是神秘,她不同于其他教授知识的教师,她一年大概出现一两次,偶尔也会出现三次,每次来到黑尔舍姆都要带走克隆人们在课堂上做得最好的手工作品,据说它们是被带到夫人的私人画廊收藏起来。而夫人与其他来到黑尔舍姆的人类教师不同的是,她从不与克隆人们接触,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眼神上。对此,露丝大胆猜测夫人是害怕他们。为了验证这个猜测,在夫人来到黑尔舍姆的那一天,克隆人们一拥而上围住了她,企图从她的表情中得到答案,但是夫人只是僵直地在原地一动不动。凯茜后来回忆道:“我至今都能栩栩如生地看到,她似乎在拼命压抑住周身的颤抖,那种真正的恐惧,怕我们中的哪一个会不小心碰到她。……露丝说得对:夫人确实怕我们。但她害怕我们就像是有的人害怕蜘蛛一样。对此我们毫无准备。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要怎么想这件事,我们自己会是什么感受,被人那样看待,当成蜘蛛。”[3]40夫人面对克隆人们接近时表现出来的惊恐为克隆人们的自我认知带来更深的疑惑,克隆人们只想过自己可能是被遗弃的孤儿,却不知实则是被人类创造出来用以解决医疗问题的怪物。对自身身份的追求与越来越深的身份迷失使凯茜们陷入了更大的焦虑之中,黑尔舍姆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将克隆人们囿于其中。
而凯茜们在被告知他们只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克隆人时,他们开始在人类教师带来的报纸与杂志上寻找自己可能的原型。心高气傲的露丝认为自己是照着某一位在大都市工作的白领丽人仿制出来的,并在离开黑尔舍姆后试图去小镇找到自己的原型,但结果令露丝大失所望,她与那个看起来像是她原型的人类女子没有一丝一毫相像。露丝寻找原型的失败给予了克隆人们巨大的打击,在这之前克隆人们都将自己的身份认同确立在原型身上,但如今原型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这也就间接证明他们的自我身份处于完全迷失的状态。而令克隆人们最无法接受的,是露丝所披露的可能事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废柴复制来的。吸毒的、卖淫的、流浪汉,也许还有罪犯,只要不是变态就行。这才是我们的来源。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不明说出来?……如果你想去找原型,如果你认真想去找,就得去那些龌龊地方找。你得去垃圾堆里翻。去阴沟里找,那才是我们这些人的出身之地。”[3]185-186至此,克隆人们才意识到追寻“我是谁”这个问题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除去为人类捐献身体器官,他们的存在或许不具有任何意义,克隆人的价值就是在贡献出身体后毫无希望地进入生命的终结。
二、石黑一雄的国际化作家身份
小说《别让我走》中所展现的克隆人自我身份迷失的情节与作家石黑一雄自诩的国际化作家身份有着紧密联系。作为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身上同时具有两种文化特质。在六岁前,石黑一雄生活在日本长崎,之后随家人移民英国,开始接触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在学校中石黑一雄接受的是纯英式教育,但在家中,他的父母依旧坚守日本的方式生活,不仅讲日语,而且还保留大量的其他日本文化的痕迹。东西方两种文化语境的差异性始终贯穿、交织在石黑一雄的成长过程中。
石黑一雄成为作家后的前两部小说的主题都是战后日本人民的精神状态,这两部作品在英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石黑一雄成为英国文坛上的一颗新星。但小说的日译本在作家的母国日本却并不被人接受,原因在于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描写的日本文化语境并不贴近日本现实,而是作家本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想象与再创造的结果,换言之,这是只属于石黑一雄心中的日本。“对于移民作家来讲,家乡永远是值得回忆的”[5]76,石黑一雄离开日本时年纪尚小,对日本生活环境的记忆随着年纪增长也逐渐变得模糊,他的日本题材小说很大一部分是作家本人的杜撰,并没有进行实地考察。石黑一雄本人也承认:“对日本的印象完全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但是,我所以这样做,并非是为了写小说,而是很单纯地出于自己的小孩子情节。我在西欧长大,而情感则与日本相连并为日本所吸引。写小说时,我总是想写‘我的日本’。”[4]67在移民英国后,石黑一雄被迫割断了与日本本土的联系,对此,作家迫切想要通过族裔文化的追寻来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证。在石黑一雄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时,他曾试图讲述关于英国的故事,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情节应如何开展,而当作家将故事背景置回日本、主人公也更改为日本人时,故事接下来发展就开始变得顺利起来,甚至连石黑一雄的英国同学们也纷纷希望他可以写作出一个关于日本的小说作品。由于石黑一雄的日裔身份,西方媒体经常希望他可以解答英国人对日本这个国家的好奇问题,并由此期望石黑一雄可以成为日本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发言人。但很显然地是,石黑一雄所有对日本的了解都是筑基在童年短暂的记忆之上的,数十年的去国分别使得他除去自然身份上的日本性外已与英国人无异。即便如此,在被问及关于代言日本的问题时,石黑一雄还是对族裔文化表达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如果我从1960 年离开日本后能够经常回到这个国家,或者在我的成长经历中能通过各种途径对日本的各方面更为了解的话,我想我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去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来代表日本,或者说成为一个在英国的日本代言人。”[6]58
石黑一雄被读者们所关注的除去作家身上的日本性,还包括与日本性共存的深深的英国性。如果说日本是作家想象中的故土,那么英国就是作家面对的现实。石黑一雄一直坚持用英语写作,并由此被归入英国作家或欧洲作家的行列。在完成以日本为背景和题材的前两部小说后,石黑一雄的小说背景便转向了英国,对英国社会的熟悉使他可以更好地对作品的内容进行描绘。但作家又不能完全割除他在写作时的日本式思维,无法将自己的身份置回于单一的族裔或国家中,这使得他开始了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在小说《别让我走》中,石黑一雄将主人公的身份设为克隆人,虽然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姓氏部分则简单地只用一个字母替代,比如凯茜·H。姓氏是代表人类身份的重要象征,顺着姓氏溯源可以将某个人归于某个家族、种族甚至是民族和国家,姓氏的缺失则意味着小说中的凯茜们没有身份的代表性。而石黑一雄以其带有明显大和民族色彩的姓氏在西方成长,就注定了他不能将自身归属于西方社会中。石黑一雄从不避讳他在写作中展现出来的明显的英国性,但也从不将英国性作为他写作的唯一特征。相反的是,石黑一雄对写作中展现出来的日本性和英国性都保持着微小的距离感。看起来石黑一雄在英国社会中生活得如鱼得水,但实质上英国性只是表现在石黑一雄写作的外化之中,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将自身归属于英国的文化传统中。而令作家尴尬的另一情形则是故乡日本远隔万水千山,可望而不可即。这种故乡与第二故乡都无法完全使石黑一雄获得真正身份归属的境地自然会导致作家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茫然,从而使得他由于对日本现实的模糊无法为日本代言,同样也因为身份的无归属而无法为英国代言。“我没有清晰的角色定位,既没有要代言的社会,也没有要为之书写的国家,似乎没有什么人的历史是我的历史”[6]58,移民经历的特殊性使石黑一雄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无根作家”。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石黑一雄只能自诩为“国际化写作”的作家,这也是他在身份认同无果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
三、身份追寻与人性反思
石黑一雄在小说《别让我走》中虽然借克隆人的遭遇艺术化展现了身份迷失主题,其在自我身份定位上也自诩为“国家化写作”的作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本人徘徊于身份问题而无法自拔。事实上,石黑一雄在展现身份迷失的同时,也试图为身份追寻提供可能性的路径,并由此上升到科技社会中对人类命运进行反思的高度。
在小说《别让我走》中,石黑一雄构建了一个科技发达的社会。人类创造出克隆人用以治疗疾病,并对克隆人的生命不断进行榨取,迫使克隆人在有限的生命中献祭出自己的全部价值。凯茜们在短暂的生命中对自我身份进行孜孜不倦地探寻,在被告知既定的悲剧命运时也没有表现出绝望与悲怆,而是毅然接受了注定的命运,背负起人类强制给予他们的捐献责任。在此过程中,克隆人与人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人性上的差异,石黑一雄借此带给读者关于人类自身的反思。
克隆人根据人类复制而来,小说中的克隆人们在黑尔舍姆接受的教育同人类孩童接受的教育并无不同。凯茜们学习音乐、绘画、诗歌等课程,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情感体验。在凯茜的回忆中,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着妒忌、喜欢、宽容等复杂的情感。除去生理上的不同,克隆人与人类无异。但人类却剥夺了克隆人的生理权利:他们无法繁育后代。在小说的描述中,童年时的凯茜曾有过扮演母亲的行为:“我当时正随着歌声轻摇慢摆,怀中还抱着一个想象中的婴儿。事实更令人尴尬,我当时抱着一个枕头,来代替小宝宝,那也不是我第一次这样做,当时我舞步缓慢,闭着眼睛,每当这几句歌词出现的时候,都会跟着轻声唱:‘哦,宝贝,宝贝,莫失莫忘……’”[3]80这一小说情节暗示出,在情感表达中克隆人等同于人类,克隆人身上同样拥有着本该人类独有的“人性”,且这份人性充满爱意、难能可贵。
但与小说中克隆人表现出来的人性之“善”相比,小说中真正的人类却走向了“善”的对立面。人类站在剥夺者的角度对克隆人进行控制,虽然凯茜们被允许拥有性生活,但他们时刻受到来自人类监护人的身体检查,避免在性生活中患上传染病。黑尔舍姆每一周都会为克隆人做一次身体检查,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但这种检查并不是基于对克隆人的爱,而是完完全全将克隆人当作捐献器官的容器,因为容器的完好无损会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益处。而捐献器官对克隆人身体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器官的摘除会使克隆人陷入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也许是第四次捐献,即使事实上你已经完结,你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意识,然后你会发现,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许多捐献,许许多多;不过不再有康复中心,不再有看护员,也不再有朋友;除了眼睁睁看着你余下的捐献手术,你没有什么事可以做,直到他们啪的一下把你的身体关上为止。”[7]257无论克隆人在短暂的一生对自我身份进行怎样的追寻与重建,对于人类来说他们的行为都是无意义的和徒劳的,死亡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克隆人的头上。而克隆人除了等待,也别无选择。但即便是在生命健康受到人类的严酷压迫、内心对身份追寻感到无望的状态下,克隆人们还是在被告知既定命运时选择勇敢地走向死亡的结局,扛起注定的责任。本该闪烁人性光辉的人类在小说中体现出“非人性”,而被创造出来的作为“非人”的克隆人反而充满着“人性”之光。在此对比下,小说暗示出克隆人在精神高度上已经实现了对人类的压制。
小说《别让我走》作为一部科幻小说,反映的是现代社会中尚未发生的状况。但科技的不断进步使人类难以确保未来不会有克隆人出现,假使克隆人真正出现在人类社会,人类应该怀有怎样的一种态度面对他们,是像人道主义者一样为其生存状况奔走发声,还是丧失人性心安理得获取来自克隆人的馈赠?石黑一雄借小说的科幻色彩,预言了一个未必不可能发生的沉重话题,使读者察觉到科技高度发展背后可能会出现的人性之“恶”。
四、结语
小说《别让我走》中克隆人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无归属感同作家本人极为相似,克隆人作为被创造出来的个体,无法认同进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石黑一雄通过对克隆人身份问题的艺术化展现表达了他对自身身份归属的疑惑与迷茫。对此,作家不断借助记忆主题的书写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起来,试图在一种时间链条式的关系中实现身份的确证。与此同时,石黑一雄还在身份认同主题的展现中拓宽视野、将目光触及全人类,以客观的态度对人性的本质进行了带有预言性的理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