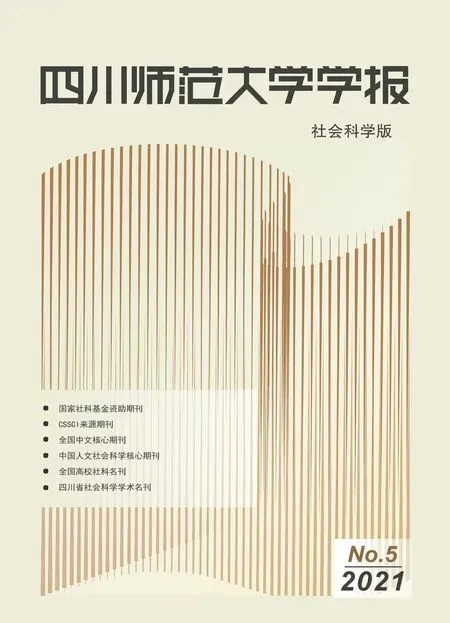“阆中引力”:政区地位变迁对蜀官道走向的影响
——兼论巴蜀古代交通路线空间变化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2021-02-13陈俊宇蓝勇
陈俊宇 蓝勇
蜀道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热点,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蜀道各道中,金牛道是由陕入川的核心道路,其中入川以后的线路(即南段)传统上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广元-昭化-剑州(剑阁)-梓潼-绵州(绵阳)-罗江-德阳-汉州(广汉)这条西线,但金牛道南段其实还有一条东线,即广元-苍溪-阆中-南部-盐亭-潼川(三台)-中江-汉州线。就驿路主线和支线层面而言,两条线的地位在明清时期发生过转移。早在1957年,黄盛璋就在《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一文中提出了“剑阁道潼川支线”的说法,并对支线路线作了具体描述(1)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地理学报》1957年第4期,第429-430页。,但主要是就战争路线而言。1986年,李之勤等人在《蜀道话古》一书中明确提到了“明代的川陕驿道南段,系取金牛道南侧支线由广元经阆中、盐亭、潼川、中江、汉州至成都,而不经剑州、梓潼、绵州一线”这一变化(2)李之勤等《蜀道话古》,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随后,蓝勇在《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一书中对变化的前后过程进行了简要梳理,并列有《明代四川北路驿站表》和《清代北路驿、铺、关、店表》(3)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4页。。此后30年,对金牛道的研究,要么侧重在北段,如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4)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47-58页。、孙启祥《金牛古道演变考》(5)孙启祥《金牛古道演变考》,《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317页。等,要么侧重在南段西线,主要关注对广元、剑阁境内文物遗产的保护和开发(6)如黄家祥等《蜀道广元段考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第60-67页。。2019年,蓝勇已指出,“虽然金牛道在蜀道的南线诸道中地位最为重要,遗产资源也最为丰富,但相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7)蓝勇《近70年来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3期,第13页。,尤其是对金牛道南段东线苍溪到广汉段进行研究的成果十分稀少。在涉及南段东线的研究成果中,李久昌《蜀道交通兴衰的历史脉络》(8)李久昌《蜀道交通兴衰的历史脉络》,《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11-12页。一文大致是复述李之勤等人的说法,卢艳秋《康熙年间四川地方管理研究》(9)卢艳秋《康熙年间四川地方管理研究》,湘潭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1页。一文更是一笔带过,另外易宇《清代四川地区嘉陵江流域陆路交通研究》(10)易宇《清代四川地区嘉陵江流域陆路交通研究》,西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25页。一文则从清代“僻北路”、“僻东北路”的角度对相关铺递及里程有所梳理。总体而言,对金牛道南段东线的研究基本陷于沉寂,缺乏新的突破,尤其是缺乏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更没有从明清时期巴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变化对官道走向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
一 明清金牛道南段主驿路路线的变迁
金牛道南段自通路以来长时间都是以走西线(即剑阁道)为主,这早已是共识。其间,虽偶有微小的路线调整,但大格局上没有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元代。据考证,元代金牛驿道在四川境内可考者,有朝天陆站、宁武陆站、临江水陆站、人头山陆站、剑门陆站、隆庆陆站、垂泉陆站、伯坝陆站、绵州陆站、罗江陆站、白马陆站、德阳陆站、汉州陆站、成都本府站14处(11)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第53-54页。。这表明元代金牛道南段驿路仍走的西线。同时,东线则一直是以支线的身份作为交通的辅路。据黄盛璋推测,东线至晚在唐至德二年(757)已开通,“三台古为潼川,为唐东川节度使的治所,常驻重军,因此我们推想此路之辟为通道,或在唐至德二年分剑南道为东西川之前,因交通之故,使潼川成为重镇”(12)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地理学报》1957年第4期,第429页。,在唐、宋时均发生过经由此路攻入成都的战事。
从明代开始,金牛道突然出现主线、支线地位倒转的情况,东线一跃而成驿路主线。明初官修《寰宇通衢》云:“京城至四川布政司并所属各府各卫……神宣驿,六十里至沙河驿,七十里至龙潭驿,六十五里至柏林驿,四十里至施店驿,五十里至槐树驿,七十五里至锦屏驿,六十里至隆山驿,六十里至柳边驿,六十里至富村驿,六十里至云溪驿,六十里至秋林驿,六十里至皇华驿,六十里至建宁驿,五十里至五城驿,六十里至古店驿,六十里至广汉驿,六十里至新都驿,四十里至锦官驿。”(13)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附录一《寰宇通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177页。成书于景泰年间(1450-1456)的《寰宇通志》,也在卷66《潼川州》中记载了潼川州的皇华驿、建宁驿、云溪驿、富村驿、秋林驿、五成驿、古店驿等驿,在卷63《保宁府》中记载了保宁府的锦屏驿、隆山驿、龙潭驿、百林驿、施店驿、柳边驿、槐树驿,在卷61《成都府》中记载了成都府的锦官驿、广汉驿(14)陈循等《寰宇通志》卷66《潼川州》、卷63《保宁府》、卷61《成都府》,《玄览堂丛书续集》,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影印,第62册第14页、第63册第10页、第61册第19-20页。。
明代四川的方志中有关的记载也较多。如正德《四川志》卷14《保宁府》记载保宁府有隆山马驿、槐树马驿、柳边马驿、问津水马驿、柏林马驿、施店马驿,卷18《潼川州》记载有皇华马驿、秋林马驿、建宁马驿、五城驿、古店马驿、云溪马驿、富村马驿(15)熊相纂修《四川志》卷14《保宁府》、卷18《潼川州》,四川省图书馆1961年抄本,第28、21-22页。。另据嘉靖《四川总志》卷16《经略·驿传》记载:“国初疆理封域,即设邮驿以通往来。自成都府锦官驿,由府属之新都军站、广汉驿,北由潼川州境古店军站、五城驿、建宁军站、皇华驿、秋林军站、云溪驿,保宁府境富村军站、柳边驿、隆山军站、锦屏水马驿、槐树军站、施店军站、柏林军站、柏林递运所、龙潭军站、问津水马驿、沙河军站、神宣军站、神宣递运所抵陕西宁羌州境,为北路。”(16)刘大谟修、王元正等纂《四川总志》卷16《经略·驿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第46页。万历《四川总志》卷20《经略二·驿传》“隆山”作“龙山”,余同(17)虞怀忠修、郭棐等纂《四川总志》卷20《经略二·驿传》,万历九年(1581)刻本,第9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四川备录上》也称:“自成都府锦官驿,由府属之新都军站、广汉驿,北由潼川州境古店军站、五城驿、建宁军站、皇华驿、秋林军站、云溪驿,保宁府境富村军站、柳边驿、龙山军站、锦屏水马驿、槐树军站、施店军站、柏林军站、柏林递运所、龙潭军站、问津水马驿、沙河军站、神宣军站、神宣递运所抵陕西宁羌州境为北路。”(1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四川备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0页。嘉靖《保宁府志》卷4《建置·驿传》中记录了此道的锦屏水马驿、柳边马驿、问津水马驿、隆山马驿、槐树马驿、富村马驿、龙潭马驿、柏林马驿、施店马驿等,并有“东驿道往来岁无虚日”之说(19)杨瞻修、杨思震纂《保宁府志》卷4《建置·驿传》,嘉靖二十二年(1523)刻本,第21-22页。。由此可知,在明代当时当地人眼中,利、阆、梓至成都的路线称为“东驿道”,反知原来行走在剑州、绵州入成都的主线可能称为“西驿道”。嘉靖《潼川志》记载了此路的秋林、建宁、皇华、五城、富村五驿(20)嘉靖《潼川志》卷2《建置》、卷5《赋役》,民国抄本,第2-10、13-14页。。另外,万历《潼川州志》记载的沿途秋林驿军站、建宁驿站、古店驿军站、皇华驿民站、云溪驿民站、五城驿民站,都是在这个东驿道上的,而且有民站和军站之分(21)万历《潼川州志》卷7《驿传》,《日本藏巴蜀珍稀文献汇刊》第1辑第7册,巴蜀书社2017年版,第399-400页。。
可惜的是,目前所见的文献都没有明确提到这个变化的具体时间、成因、相关过程等。因此,乾隆《昭化县志》卷6《政事下·道路》有“明驿道自保宁而下成都,不知辟于何时”的说法(22)李元纂修《昭化县志》卷6《政事下·道路》,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第12页。。据前引黄盛璋的说法,这条路本身应早已存在,只是明代从哪一年将它定为主驿路的,不得而知。虽然不能精确到年,但仍可大体推断。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九月,“庚申,修《寰宇通衢》书成”(23)《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明实录》第8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第3423页。,因此东线成为主驿路的时间不会晚于此时。又,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二十五年(1392)间,景川侯曹震奉命修治西南驿路,“自二月初七日兴工,五月十五日工歇;至秋九月初一兴工,次年正月十五日工毕,凡八阅月”,其中“保宁驿道至陕西汉中府界,委成都后卫指挥佥事王清,提调军民以修治之”(24)《叙永文钞》,叙永县编史修志委员会1983年编印,第2页。。《明实录》及杨慎《景川曹侯庙碑记》亦分别记录道:“(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己未,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复辟陆路,作驿舍邮亭,驾桥立栈,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贵州以达保宁通陕西,由是往来者便之。”(25)《太祖实录》卷214“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明实录》第7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第3162页。“皇明洪武中,命景川侯曹公震往平治之。陕西自宝鸡达汉中,贵州自永宁达云南之曲靖,四川自保宁达于利州……川陕云贵四处,东西南北,广轮经纬,五千余里,置驿奠邮。”(26)杨慎《升菴集》卷4《景川曹侯庙碑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驿路的变迁,似与此次大规模的道路修治有关。故,金牛道南段东线开始成为主驿路的时间,大致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至二十七年(1394)之间。
此外,隆庆四年(1570),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称,驿路从朝天驿可分为两路,“朝天驿,即朝天岭,极高峻。西南由保宁府驿道达于成都,西北由剑州剑门关达于汉州入成都”,并记载了具体的路线途程:“北京至陕西、四川路……神宣驿。七十里朝天驿。西北去剑州。即朝天岭。属保宁府广元县。六十里沙河驿。七十里龙潭驿。六十五里柏林驿。四十里施店驿。五十里槐树驿。七十五里保宁府阆中县锦屏驿。六十里隆山驿。六十里柳边驿。南部县。六十里富村驿。六十里云溪驿。六十里秋林驿。六十里潼川州皇华驿。六十里建宁驿。五十里中江县五城驿。六十里古店驿。六十里汉州广汉驿。六十里新都县新都驿。四十里至四川布政司成都府成都县、华阳县锦官驿。……朝天驿西北分剑阁路。朝天驿。廿五里广元县。廿里昭化县。廿里剑门关。八十里剑州。百廿里梓潼县。百三十里绵州。九十里罗江县。百里德阳县。九十里汉州。六十里新都县。四十里至成都府。”(27)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附录二《一统路程图记》,第211、210页。天启六年(1626),程春宇《士商类要》亦记载道:“北京由陕西至四川省陆路……神宣驿。四十里朝天岭。岭极高峻。西北去剑州。西南三十里至沙河驿。六十里至利州卫。六十里龙潭驿。六十五里圆山驿。六十里柏林驿。四十里施店驿。五十里槐树驿。七十五里保宁府。阆中县锦屏驿。六十里至隆山驿。六十里柳边驿。六十里富村驿。六十里云溪驿。六十里秋林驿。六十里潼川州。皇华驿。六十里建宁驿。五十里中江县。五城驿。六十里古店驿。六十里至汉州。广汉驿。六十里新都县新都驿。四十里四川成都府。成都、华阳二县锦官驿。”(28)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附录三《士商类要》,第346-347页。这类说法是不准确的。对此,李之勤指出:“明代有关图书多言从朝天镇向西或西北分有一支通往剑门关的驿道,亦属误会。实际上明代驿道过广元之后才分二支,大驿道南下阆中,再折西南去成都,支线由广元向西南,经昭化入剑门,经绵阳去成都。”(29)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9卷第2辑,第54页。
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记,与中国古代文献的方位记载模糊有关。严格地讲,因当时朝天驿地位重要,加上对具体山川形胜不了解,人们误将其当成金牛道东西分界的起点,并将走朝天西南经剑阁误会为西北,将南走龙潭正道误会作西南。可能正是因为当时从朝天驿开始直到剑阁一直是行走陆路,故正德九年之前广元城只设有问津水驿。正德九年(1514)十二月丁巳,“广元县问津水驿宜改为水马驿,添设马匹以节龙潭、沙河二驿之劳”(30)《武宗实录》卷119“正德九年十二月”,《明实录》第66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第2412页。。嘉靖《保宁府志》卷4《驿传》亦云:“问津水马驿,在广元县西门外。站船马四只,夫四十名。马二十五匹,夫三十名,系正德九年添设。”(31)杨瞻修、杨思震纂《保宁府志》卷4《驿传》,第22页。就是说,从正德九年开始,广元城才正式设有陆路马驿。
尽管明代曾多次对西线的旧路进行修复,但主驿路一直为东线未改。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驿路系统崩坏。川内局势稳定后,清廷开始着手对驿路系统进行重建。康熙《四川总志》卷33《驿传》云:“皇清开复全川后,四川督抚司道因时度势,酌量冲僻,顺治十六年(1659)、康熙二年(1663)、六年(1667)三次题请,设陆站五十一、水站三十四。”(32)蔡毓荣等修、龚懋熙等纂《四川总志》卷33《驿传》,康熙十二年(1674)刻本,第2页。这大体恢复了驿路系统,并延续了明代以东线为主驿路的局面。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正[祯]的《蜀道驿程记》和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方象瑛《使蜀日记》,都记载了走的东线(33)王士祯《蜀道驿程记》、方象瑛《使蜀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7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第10-13、50-51页。。
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金牛道南段再次发生主线、支线地位倒转,西线重新成为主驿路。王士祯《居易录》卷5云:“蜀道剑门驿路自明末寇乱,久为榛莽,予壬子岁(即康熙十一年)入蜀,由苍溪、阆中、盐亭、潼川以达汉州,率皆鸟道。二十九年四月,四川巡抚噶尔图上疏,自广元县迤南历圆山等十二站始达汉州,计程八百二十里,多崇山峻岭,盘折难行。查得剑门关旧路仅六百二十里,臣乘农隙刊木伐石,搭桥造船,以通行旅,遂成坦途。”(34)王士祯《居易录》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10页。彭遵泗《蜀故》即引此说(35)彭遵泗《蜀故》卷6《蜀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79-80页。。乾隆《中江县志》卷12《驿铺》、乾隆《昭化县志》卷6《政事下·道路》亦分别云:“康熙二十九年,为驿路宜就坦近等事,改移驿站自汉州由德阳以至广元。”(36)张孙松修、陈景韩等纂《中江县志》卷12《驿铺》,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第5页。“今驿道明天启四年(1624)初凿山开径,崇正元年(1628)功始竣道……当时系僻径也,国朝康熙二十七[九]年始改为驿道。”(37)李元纂修《昭化县志》卷6《政事下·道路》,第12页。显然,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之间的东驿道时期,仅仅只有298年的时间。
二 金牛道南段东线路线走向的变迁
南段东线的整体路线为:自广元往南入苍溪境直到阆中,过嘉陵江折向西南入南部境,再西经盐亭、潼川、中江到汉州。金牛道南段东线,从明代成为驿路主线,到康熙二十九年恢复为支线,虽然地位有升降,但其路线总体上的变化并不大。在总体稳定的情况下,路线内也还是有一些局部的调整。
(一)中江县西段的驿路变化
乾隆《中江县志》卷12《政事·驿铺》云:“明。本县应递马四十匹,古店驿马三十二匹……国朝。五城驿,城内,站马二十匹,马夫十名,杠夫三十名,康熙二年设。古店驿,治西六十里,站马二十匹,马夫十名,杠夫三十名,康熙五年设。县门铺城内,东由潼川铺三,牟谷铺九里,回水铺二十里,朝宗铺三十里。西由汉州铺六,余岭铺十里,平易铺二十里,便民铺三十里,走马铺四十里,西城铺五十里,皂角铺七十里。康熙二十九年,为驿路宜就坦近等事,改移驿站自汉州由德阳以至广元,是为中路,两驿站马杠夫并撤。现在中江额设铺司兵十四名内,东路底塘铺司一名、铺兵一名,回水铺铺司一名、铺兵一名,朝宗铺铺司一名、铺兵一名;南路底塘铺司一名、铺兵一名,南垭店铺司一名、铺兵一名,朝阳店铺司一名、铺兵一名,兴隆场铺司一名、铺兵一名。”(38)张孙松修、陈景韩等纂《中江县志》卷12《政事·驿铺》,第4-6页。嘉庆《中江县志》卷2《驿传铺递》的相关记载与之略同。道光《中江县新志》卷2《建置·铺递》云:“中江昔为驿站孔道,西由古店至汉州以达省垣,东由潼川至广元以达京师。明设本县应递马四十匹,古店马三十二匹。国朝康熙二年,城内五城驿设站马二十匹、马夫十名、杠夫三十名。五年,古店驿站马二十匹、马夫十名、杠夫三十名。城内设县门铺,东由潼川,铺三:牟谷铺九里,回水铺二十里,朝宗铺三十里。西由汉州,铺六:余岭铺十里,平易铺二十里,便民铺三十里,走马铺四十里,西城铺五十里,皂角铺七十里,是为古道。二十九年为驿路宜就坦近,改移驿站自汉州趋德阳、罗江以至广元,是为中路,两驿夫马铺兵并裁。”(39)杨霈修、李福源等纂《中江县新志》卷2《建置·铺递》,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第18页。
通过对以上资料的梳理,中江县境内驿路的整体变化是比较清楚的。以康熙二十九年改金牛道驿道为节点,由此境内驿站全裁,同时县东往潼川的三铺只保留了回水、朝宗二铺,县西往汉州的六铺则全部被裁撤,改设为县西南往金堂的各铺。兴隆铺与金堂县交界,据嘉庆《金堂县志》卷9《防御·铺递》记载,兴隆铺接金堂县莲花铺,再经黄土铺、赵家铺、姚家铺、红瓦铺到新都县,最终到成都(40)谢惟杰纂修《金堂县志》卷9《防御·铺递》,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第3-4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江县西从余岭铺到走马铺的驿路是曾单独发生过变化的。正德《四川志》卷18《潼川州·邮驿》云:“中江五城驿,在治北,古店马驿,在治西五十里,俱洪武中建。总铺。双鱼铺、飞黄铺、芳基铺、走马铺、西城铺。牟谷铺、回水铺、朝宗铺。”(41)熊相纂修《四川志》卷18《潼川州·邮驿》,第22页。明嘉靖以前,西出中江城,过双鱼、飞黄、芳基三铺到走马铺,路较崎岖。嘉靖四年(1799),中江县令余祺舍迂就直、弃险从易,改驿道走三铺之北,并迁三铺位置,后又改三铺名为余岭、平易、便民。道光《中江县新志》卷2《建置·铺递》附有《余岭新道记》,对此事的前后过程有详细的记载:
中江当两川、云贵、秦陇行旅之冲,实剑外剧县。县西二十里有山曰高崖,壁立云矗,俯瞰群峰,势与青城、大峨伍。山之麓故有铺曰双鱼,逾双鱼五里,溪水自此下,夏秋之交,辅以行潦,其悍滋甚。有司者尝桥之,号曰高桥。桥西上数里为铺曰飞黄,出飞黄之上十里曰芳基,又十里曰走马。自双鱼而上,逆坂重现,时相勾连,巨细石铓,赑赑齿齿,行者必择地,然后可以投足,至走马稍已。又所在乏水泉,当溽暑时,公私往来无以济渴,暍不死则病。循县西五里,出双鱼之北,历两河口蛮洞,直距芳基、走马之间一径弦直可通辙迹,而少纡回演迤艰难攀跨之状。夹径有井,或寒泉错出石鏬,沕潏漫羡,其声淙淙然,疑所谓井渫不食者,官道不出于此而出于彼,何也?新建余侯祺来令之五年,不为苛皦之政,县以无事,乃属其土人而告之曰:“吾闻道茀不治,司空不视,涂泽不陂,川不梁,周单子所以知陈之亡也。今官道之利害,前人之智非不能及此,而不肯一举手,或有意举手而夺于群咻,惮而不为。智及之而不为,不仁;惮于人言而不为,不勇。不仁不勇,吾无以令为也。兹将舍其迂而就其直,弃其险而从其易,佥其谓何?”皆应之曰:“然。”遂以嘉靖四年十一月庚申,刊木夷秽,凿两河蛮洞之道而通之,下上连延仅三十里,广加故道三之一,并徙双鱼、飞黄、芳基三亭于形胜之便区。取南之直以易北,不伤于民;撤旧亭之材以为新,不费于财。首尾两阅月厥工告成,而县之人忘其劳,途之人始得便周行之安也。两河当高桥上游十里,其患差小,乃废高桥旧趾,改创石桥二于其上,为桥之空各三,桥之阳为亭一。不侈不陋,亢爽可嘉,榜之曰仰止以休行役之士大夫,凡所规画,动适人意,旄倪欢呼如出一口。会按察使九川吕君道夫适以入觐,过而嘉之,遂更旧铺之名双鱼者曰余岭,飞黄曰平易,芳基曰便民。(42)杨霈修、李福源等纂《中江县新志》卷2《建置·铺递》,第19-20页。
经过嘉靖四年这次改道后,中江到汉州驿道便由新高桥过,新高桥附近后又发展成场,为“隆兴场”。清末《中江县乡土志·道路》云:“(中江县城)西出小南门,渡凯江,经谭家街,至五块碑二里,西北至五里坡三里,龙王潭十里。此水即余家河上流,源出会棚场福嘉沟等处,经双龙桥、新高桥南流二十五里至龙王潭。循龙王潭小河西岸西北逆上至新高桥十里。新高桥,县西微偏北二十五里,旧有驿店二十余间,为本县与汉州交通要道,止为行人往来住止食宿之区。今始立场兴市。西距集凤场十五里……场西过云津桥,至云梯岭,抵便民铺,俗名土地垭,五里皆斜坡路,循山斜上至集凤场十里。集凤场,俗名走马铺。”(43)游夔一编《中江县乡土志·道路》,光绪末抄本,第22-23页。《四川省中江县地名录》云:“隆兴俗名新高桥。此地在过去是中江到成都的必经之路,因过河无桥不便,明嘉靖年间县府令九保和一保各建1桥。九保所建桥先落成,取名老高桥;一保落成后,取名新高桥。后因商业往来日益繁荣,人们称为‘隆兴’。隆兴之名沿用至今。”(44)四川省中江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中江县地名录》,1986年,第101页。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从集凤到中江,过去曾有两条石板路:一条是经隆兴,先后经过集凤、何家山、隆兴、向家坡、龙王潭、干塆、鸡屎树、龙背、太平桥、中江;另一条是经石垭子,先后经过集凤、天公堂(今又作天宫堂)梁子、石垭子、老街巷、高石墙、鲇鱼桥、五块碑、中江。从距离和方位而言,走石垭子这条路线,与明嘉靖以前的旧路线比较吻合,所经余家河正好在隆兴下游约10里处。自嘉靖四年改走新线后,经过400多年的沉淀,不再有旧线的记忆。如今当地人回忆集凤到中江的老路,多是指经隆兴的老路,石垭子只是一条支线,不仅绕,路也更不好走,一般只有石垭子沿线的人会走。与此同时,石垭子这段路还存留有所谓“阿弥陀佛”的戏称,即过去从中江经石垭子到集凤,要从山下往上爬数公里,到山顶才能停顿和松一口气,直感叹“阿弥陀佛终于爬上来了”,与嘉靖以前旧路线沿途行走的艰难情形相类似。
(二)阆中县南段驿路变化
这段主要是天宫院到铺垭塘的路线问题,并涉及到隆山驿(铺)的地址定位问题。正德《四川志》卷14《保宁府·邮驿》云:“隆山马驿,在治西南四十里……白坡铺、大风铺、隆山铺、淳风铺、西水铺……俱在治西。”(45)熊相纂修《四川志》卷14《保宁府·邮驿》,第28页。嘉靖《保宁府志》卷4《建置下·驿传》云:“隆山马驿,在府城南四十里……正南曰白坡、大丰、隆山、淳风、西水、侯垭,亦南部界,达于盐亭。”(46)杨瞻修、杨思震纂《保宁府志》卷4《建置下·驿传》,第22-25页。雍正《四川通志》卷22《铺递》云:“白鹤铺,在县西十里。大风铺,在县西二十里。隆山铺,在县西三十里。淳风铺,在县西四十里。西水铺,在县西五十里。”(47)黄廷桂等修、张晋生等纂《四川通志》卷22《铺递》,乾隆元年(1736)刻本,第8页。嘉庆《四川通志》卷89《武备·铺递》、民国《阆中县志》卷20《武备》皆云:“白鹤铺,在县西南十里。大风铺,在县西南二十里。隆山铺,在县西三十里。淳风铺,在县西四十里。西水铺,在县西五十里。”(48)常明等修、杨芳灿等纂《四川通志》卷89《武备·铺递》,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第15页;岳永武等修、郑钟灵纂《阆中县志》卷20《武备》,民国十五年(1926)石印本,第60页。咸丰《阆中县志》卷3《兵制》云:“白鹤铺,县西南十里。大丰铺,县西南二十里。隆山铺,县西三十里。淳风铺,县西四十里。西水铺,县西五十里。”(49)徐继镛修、李惺等纂《阆中县志》卷3《兵制》,咸丰元年(1851)刻本,第43页。由此可知,明清时期,从阆中县往西南经南部县到盐亭县的铺递,基本没有变化。但隆山铺旧址不详,应在现在的天宫镇境内,具体位置目前有争议。一种说法认为,隆山驿(铺)在如今的天宫院,这种说法现在比较普遍(50)如蒋小华等主编《南充文物旅游揽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阆中市文化局等编著《走进天宫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李志杰主编《古镇·码头》,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另一种说法认为,隆山驿(铺)在龙山驿村,淳风铺才在天宫院。如李家驹《阆史索征续》一书便记为:“白鹤铺→千佛岩→大丰铺→十里观→铺垭塘→隆山马驿→将军庙→淳风铺(天宫院)→西水铺(西河塘)。”(51)李家驹《阆史索征续》,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四川省阆中县地名录》亦云:“龙山驿。古代阆中通往成都要道的驿站,因位于龙山脚下,故名。”(52)四川省阆中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阆中县地名录》,1987年,第59页。从相互间的距离来看,如果隆山驿(铺)是在天宫院的话,那离西水铺(今西河塘)就太近了,根本没有淳风铺的生存空间。因此,笔者认为,隆山驿(铺)在今龙山驿村境内的说法比较合理。
关于天宫院到铺垭塘的路线,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走将军庙过,另一种是走福星场过。福星场是民国初年新兴的场。《四川省阆中县地名录》云:“民国初,此处曾修一小场,命名福星,取福星高照,生意兴隆之意。”(53)四川省阆中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阆中县地名录》,第59页。当地人也介绍称,解放前,这里曾经是个小场,但当时场街并没有多少房屋,而且存在时间也不长。对照地形图,可以明显看出,走将军庙、龙山驿村的路线,和走福星场、陈家坡(属双桥村)的路线,分别在山的两侧,是两条平行路线。就距离而言,前者明显更绕。民国《阆中县志》卷6《交通·陆路》云:“西南走成都。自南津关经铺垭塘、西河、天宫院,抵万年垭,约六十里,入南部界,经盐亭、潼川至成都,约六百六十里。”卷2《疆域》附《阆中县舆图》更绘有省城大道,沿途走南津关、白鹤堡、大风堡、铺垭塘、福星场、天宫院、万年垭(54)岳永武等修、郑钟灵纂《阆中县志》卷6《交通·陆路》、卷2《疆域》,第27、4页。。可见,民国时候是走福星场这条路线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另一方面,如果隆山驿(铺)的位置是在今龙山驿村境内,那么将军庙、龙山驿村这条路线应更早,而福星场、陈家坡这条路线则是后来兴起的更节省距离的新线。
(三)阆中至广元驿路的选择
明代及清初从广元到阆中的驿路有陆路和水路两种。嘉靖《四川总志》卷16《经略·驿传》云:“又自陕西汉中南界水路,由九井驿、朝天驿、问津驿、龙滩驿、虎跳驿、苍溪驿、盘龙驿、顺庆府境龙溪驿……至重庆府入大江,为北水路。”(55)刘大谟修、王元正等纂《四川总志》卷16《经略·驿传》,第46-47页。万历《四川总志》卷20《经略·驿传》的记载与之相同(56)虞怀忠修、郭棐等纂《四川总志》卷20《经略·驿传》,第10页。。这条水驿路本来是从陕西到重庆的路线,但正好也要经过广元、阆中境,可以为走金牛道东线的人群所利用。因此,出于便捷性和舒适度的考量,沿驿道经陕西入川到成都的人,有不少(尤其是官员群体)在走这一段路的时候,往往更喜欢走水驿路。如康熙十一年王士祯、康熙二十二年方象瑛都是从朝天上船,经广元、桔柏、昭化、虎跳、苍溪,到阆中城后才又重新走陆路。需要注意的是,苍溪县城只有水驿,不设陆驿。《寰宇通衢》、嘉靖《四川通志》、《一统路程图记》、万历《四川通志》、《士商类要》等均将槐树驿和锦屏驿记为两个相邻的陆路驿站,其他明代或清初文献也都没有记载苍溪陆驿。乾隆《苍溪县志》卷1《疆域》云:“陆路自广元白林沟入本邑永宁铺交界起,至施店驿十里,金针铺二十里,一碗水二十里,槐树铺二十里,烟峰楼二十里,尖山子二十里,入阆中。”(57)丁映奎纂修《苍溪县志》卷1《疆域》,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第39页。民国《苍溪县志》卷8《方域·关隘》云:“城北二十里为大石坎,石磴陡绝。又北十里为槐树驿,下至烽火塘经元马铺三十里,上至白鹤铺三十里,系由阆达利通衢。”(58)熊道琛等修、李椿灵等纂《苍溪县志》卷8《方域·关隘》,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第22页。民国《阆中县志》卷2《疆域》附《阆中县舆图》绘有走广元大道,沿途走瓦口隘、五里子、烟峰楼(59)岳永武等修、郑钟灵纂《阆中县志》卷2《疆域》,第4页。。烟峰楼即烽火塘,今苍溪县云峰镇。乾隆《苍溪县志》卷2《铺递》云:“烟峰铺,县东三十里,今存。”同卷《古迹》云:“烟峰楼,河东大路,雍肃公虞允文治蜀,遇军务辄举火相通,至今存其名。或曰胭粉楼,因任妃得名。二说存参。”(60)丁映奎纂修《苍溪县志》卷2《铺递》、卷2《古迹》,第40、48页。《四川省苍溪县地名录》云:“公社驻地烟峰楼……因驻地有一山峰,似高耸入云,称云峰山。乡以山名。”(61)四川省苍溪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苍溪县地名录》,1982年,第33页。综上可知,从广元到阆中的陆路不经苍溪县城,而是直接顺着苍溪县城东面的山路经槐树、烟峰楼往南。
与此同时,苍溪县城虽然不在金牛道南段东线的驿道路线上,但也有路相通。民国《苍溪县志》卷8《方域·关隘》云:“城正东十里为金垭隘,又十里为烽火塘,南行三十里为尖山塘,形势险要,过土地关入阆界。”(62)熊道琛等修、李椿灵等纂《苍溪县志》卷8《方域·关隘》,第22页。则苍溪到阆中是先往东经金垭到云峰,与驿道相接再往南。另外,我们在阆中、苍溪交界处的下五里子实地调查时发现,有另外一条去苍溪的老路,先后走下五里子、柳树梁、麻石垭、张王庙、青冈嘴、文焕桥、苍溪,这条路比经云峰、金垭绕行的旧路要近得多,应该是年代更晚的到苍溪的支线。
三 蜀官道选择道路险远的原因:“阆中引力”
李之勤认为:“交通道路的选线条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距离远近,里程多少;一是地形夷险,修筑和通行难易;三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物资供应和安全保障条件如何。三者之中,第一点是受客观自然条件严格限制的常数,在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也不可能发生多大的变化。第二点虽然也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却是人力可以改造克服的,至少可以改造、克服一部分。第三点的差别变化就大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会发生极不相同的变化,先进和落后,优势和劣势,有时甚至会颠倒过来。”(63)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56-57页。
从距离里程和通行难易来看,东线都明显不如西线。就前者而言,噶尔图在疏请改驿路时提到,西线比东线能近至少200里。乾隆《昭化县志》卷6《政事下·道路》亦云:“自柏林驿而下长岗直走,较今道为坦,但迂远几三百里。”(64)李元纂修《昭化县志》卷6《政事下·道路》,第12页。就后者而言,亲自走过东线的王士祯,在《蜀道驿程记》中屡次提到“乱山”、“险恶”、“峻绝”、“路峻”等字眼(65)王士祯《蜀道驿程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7帙,第11-12页。。后来,他又回忆称:“由苍溪、阆中、盐亭、潼川以达汉州,率皆鸟道”,并引证噶尔图“多崇山峻岭,盘折难行”的话来描述东线的艰险(66)王士祯《居易录》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第9-10页。。乾隆《昭化县志》卷6《政事下·道路》亦云:“广元以南冈峦起伏,跋涉亦艰,至保宁南路又不若梓、绵之坦矣。”(67)李元纂修《昭化县志》卷6《政事下·道路》,第12页。
我们在实地考察中也发现,东线与西线驿道相比,西线从成都出发一直到罗江县白马关都是处于平原大道之中,而从罗江到剑门关一线也多是浅丘与平坝相间,但东线要东出成都平原就要翻越龙泉山,到苍溪以后到广元一直是以深丘、中丘地貌为主,道路回曲陡险都更加明显。所以,今天我们在对两线的考察中,无论是仅剩的路基,还是存留的石板,东线整体上都要窄一些。
但是,为何明代要选择一条又险又远的道路为驿道主线呢?这似乎主要与沿途地方的发展有关。早在30多年前,蓝勇就认识到,驿路改走东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明代保宁府地位重要”(68)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第31页。。阆中在巴蜀历史上的地位,学界远远没有认知到。既往的研究表明,阆中先秦时期即为巴国故都,在汉晋时期是四川盆地除成都之外的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宋时期嘉陵江中游阆州、果州、梓州一带更成为巴蜀地区的重要经济区域。元代以前,虽然东线的地位很重要,但西线从利州向西南所经的剑州、绵州、汉州都是二级政区建置,地位应该说也是不亚于东线所经政区,为平衡政区地位而选择平近之线就很自然。但是,从元代开始,在政区建置上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变化。元代开始设置路总管府、散府,来辖属府、属州、属县。成都以北的路总管府和散府,只有广元路和潼川府,由此导致唐宋的绵州、汉州失去了原有的二级地方政区地位;剑州属于广元路,绵州属于潼川府,汉州属于成都路,三者均降为三级政区(69)周振鹤主编、李治安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174页。。潼川府的治地为郪县(今三台),东部地区一度更为重要起来,但元代金牛道仍然是走西线,所以整个元代四川盆地的南北官道绕开了潼川府治地。但实际上,从元代开始,从广元经阆中、三台、中江到成都均设有站赤,如广元陆站(宁武陆站)、板石陆站(广元昭化东板石)、永宁陆站(在苍溪北永宁乡)、槐树陆站(苍溪东北槐树乡,又叫怀恕站)、宝峰陆站(阆中县,又称锦屏站)、潼川陆站(今三台县)、中江陆站(又称中汜站,今中江县)、成都本府陆站(成都市)(70)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第265-266页。。所以,元代是一个金牛道东西线并重的时代,与当时金牛道东西政区地位并列有关。到了明代,四川盆地政治经济大格局又发生了更大变化。明代以府、直隶州辖散州、县。明初洪武四年(1371),改元代的广元路为广元府,以原属广元路的保宁府直属四川行省,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将已经降府为州的广元州并入保宁府,成为保宁府属广元县(71)周振鹤主编、郭红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成都以北金牛道路沿线只有保宁府、潼川直隶州两个二级政区,进一步强化了保宁的地位。而从明代开始设立的守巡道建置,川北巡道治保宁府,更是将阆中的地位抬升起来。正德《四川志》卷3《布政司·历代年表下》云:“分巡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道,一年一更……分守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道,一年一更,各道俱左右参政参议为之。”(72)熊相纂修《四川志》卷3《布政司·历代年表下》,第55-58页。《大明会典》卷210《都察院二》亦云:“四川按察司,川东道、川西道、川南道、川北道。”(73)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210《都察院二》,《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后来在川南和川东道之间增设上下之分,所以明末《蜀中广记》是按上川东道、下川东道、川西道、上川南道、下川南道、川北道六道来分区域。可以说,道是从明代开始由一个分巡分守的巡察派出机构逐渐演变成高级政区。川北道的具体建置时间是哪一年呢?嘉靖《保宁府志》卷1《舆地·沿革》云:“国初明氏以保宁府等处来附,遂仍为保宁府,隶四川布政司属川北道。”(74)杨瞻修、杨思震纂《保宁府志》卷1《舆地·沿革》,第3页。有研究表明,川北守道设置于明初永乐年间(1403-1424),而巡道可能是在明景泰二年(1451)初设(75)苟德仪、汪秀平《川北道的辖区与职能演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8页。。可见,明代初年川北道就已经存在。显然,从明代金牛道地区的政治格局来看,东线有川北道分巡治、保宁府治、潼川直隶州治,而西线属于保宁府的剑州和属于成都府的绵州、汉州都是隶属于府的散州,政治地位远远不能与东线相比。明代阆中是金牛道南段地位最重要的城市,这个吸引力可说是明代金牛道东移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官道绕开保宁府、川北道,从管理上来看是不合理的。这种重要性,到了清初更加明显。清军入川,先后与大西、南明军对峙,皆以保宁为基地,设省治于此长达十余年。这些都是东线在明代成为主线并一直延续到清初的重要原因。
但是,清代初年,金牛道南段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有上升趋势,随后自雍正五年(1727)从成都府独立出来,由散州升为直隶州,西线形成了剑州、绵州、成都府相连的格局。随着四川盆地的政治经济重心继续向东南的推移,就整个嘉陵江流域来看,顺庆府、合州、重庆府的地位在清代远远超过保宁府,保宁府在整个四川盆地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大大下降,“阆中引力”相对削弱。在这种背景下,东线始终存在的路程迂远和路况艰难两大缺陷便更加突显出来。故从清代康熙雍正时期开始,明代的“东驿道”再度回归支线地位,再次成为地方性的辅路。
四 巴蜀古代交通路线空间变化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从古到今,四川盆地交通道路线路的易位、改线十分多。从路线空间变化差异上来看,可以分成通道的地位易位、通道路线大区间改道、通道路线小区间改道三种类型。影响交通路线地位易位、路线改道的原因也较多,而且不同变化类型可能的原因也有一定的差异。
(一)交通通道的地位易位
以四川古代的交通发展来看,整个道路走向的重要性一直受到整体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而随之发生变化。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出现过一个东移南迁的过程,而四川盆地也同样受其影响而出现盆地内经济政治文化重心逐渐向东南推移的现象。宋以前,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黄河流域,特别是汉唐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关中平原,四川盆地的核心区也在成都平原和嘉陵江中游一线。所以,金牛道是进出四川盆地最重要的通道,“蜀道”之名由此而更加显要。同时,四川盆地南下云南的通道也以盆地西部的灵关道(清溪道)、西南夷道(石门道)为重。到了宋代,在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背景下,整个四川盆地大格局发生较大变化,金牛道的整体地位相对下降,金牛道上名声极大的朝天驿知名度大减,而东面的长江峡路地位相对升高起来,元代以来重庆的朝天地名(如朝天站、朝天驿及朝天门等)日益彰显出来。
明清以来,这种格局更加显现,长江峡路在明代已经有“蜀道”之称,四川盆地与外界交流交通的主要通道向东推移,长江峡路成为四川盆地对外交通的第一主道。同时,四川盆地与云贵的交通也东移到从泸州经乌撒入蜀旧道进入云贵地区,西面的石门道和建昌道地位下降,以至建昌道“久已荆榛,仕人以至差役,不复经由”(7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外郡·入滇三路》,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7页。,石门道则“川陆具存,久而榛塞”(77)张天复《皇舆考》卷10《云南图序》,《玄览堂丛书》第7辑,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版,第36-37页。。
唐宋时期,四川盆地东西交通的有南、北二道。北道从成都东经遂州、合州到渝州,合计约900里。南道从成都东南简州、资州、昌州到渝州,合计约950里。但是,唐宋时间,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格局背景下,四川盆地北部的地位更显重要,故四川盆地东西交通的北道更为重要。从唐宋北道向东可延续到万州,道可东经邻水、邻山县、梁山军梁山驿到万州高梁驿、万州羊渠驿(万县),即为明清小川北道的雏形。但从元代开始,整个四川盆地东南的地位上升起来,东南地区交通路线的地位也开始上升,特别是明代的成渝东大路开始成为盆地内最重要的通道,在盆地北道地位下降的背景下,小川北道的地位虽然重要,但比之于成渝东大路却相对偏静。
阆中的行政建置,从明到清的地位并没有减弱,但在整体的区域中,阆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却大大下降,显明的例证就是下游的顺庆府成为川北新的政治经济核心区,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区和建国初期的川北行署都设在南充而非阆中。所以,清代金牛道南段主线也失去了绕道阆中的必要性。在明代人眼中的“东驿道”,到清代则逐渐成为历史。不过,像明代金牛道这种将主线选择在长度多300里且高山险境更多的道路而放弃传统老路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明代金牛道的主线变化,主要是因为政治格局变迁的重大影响而选择险远,具体原因则是阆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显赫所致,此就是所谓的“阆中引力”。当清代绵州地位的抬升、阆中经济地位下降后,绕道阆中的险远劣势进一步被放大出来,以致康熙年间出现了主线回归唐宋旧线的结果。
(二)路线大、小区间改道
梳理历史上的蜀道变迁情况可以发现,即便是在道路方向整体不变的情况下,其线路区间内的改道也经常出现,并有大小的区别。
大区间改道,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就是金牛道北段主线变化。金牛道北段,在汉晋时期是沿勉县旧阳平关经白水关沿白龙江入蜀为主线,但唐宋时则以新阳平关以南嘉陵江为主线,元代开始则以宁羌州、神宣驿为主线。宋元以来,这类改道并不鲜见。如元代建昌道从成都南下至浍川站(会理)后,不再像以往折向西南渡拉鲊古渡过金沙江,经今姚安入云南,而是向南经黎溪、姜驿,从今江边渡口经元谋县入云南,并一直为明清沿用。产生大区间改道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云南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即从唐宋以洱海为中心转向以滇池为中心,治中庆路(昆明)所致。另外,元代建昌道路线一度改行经今甘洛和米易县治,但在明清时又在这一段恢复唐宋的旧路线,也是与当时的政区格局变化有关。宋元明清时期,渝黔古道是从黄葛渡经温泉场、百节场到綦江,但清末从海棠溪经崇文镇(黄葛垭)、鹿角场、界石场到綦江成为主线。渝万通道在清末以前一直是从分水经百步梯上蟠龙再下陡梯子至梁平为主线,但清末改由分水、花岩、亭子铺至梁平为主线。
小区间改道的变化,主要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将旧道废去而开新道,但路线一般不长,多是数里来计算。另一种是另开支道而两道路并行的形式,这种改道路线也不长,长的局限在几里之间,短的仅几十米的距离。如金牛道在朝天峡段,宋代以前一直是沿峡谷下行栈道,南宋以后栈道破败,改由翻朝天岭上的碥路而行。其它如小川北道上梁平佛尔岩、大竹九盘陡嘴以及威远新场古佛顶盐茶古道上,都有几十米的双线并行道路。
在影响传统中国道路空间变化的原因中,政治经济格局、道路险远度、修路技术力量一直是影响线路选择的三大重要原因。但是,在不同的路线变化类型上,影响因素并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重要交通路线的地位发生变化,更多是受整体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大变化的影响,道路的险远相对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金牛道南段在明代只是因为保宁府、川北道的政区地位而舍近求远、弃平走险,将阆中、潼川一线作为主线,形成了明代的“东驿道”。同样,从四川盆地南北二道的变迁也可以看出,在盆地内部经济格局向东南推移的背景下,主道选择了南道,但南道实际比北道距离更远。又如,明代从四川盆地南下云南,如果从成都经泸州取乌撒入蜀旧道到云南,实际上比从成都经雅安取道建昌道,或者经宜宾取道石门道路途更遥远,但明代人选择从泸州入云南的道路更为普遍。相对而言,路线的大区间改道的原因往往较为复杂多样,可能在许多时候都是政治经济大格局与对道路险远的考量、技术投入的因素同时存在,但有些时候也仅仅是技术和资金投入与道路险远的因素。如小川北道在清光绪以前一直以蟠龙百步梯的南线为主,下上百步梯和凉风垭陡梯子较为陡险,但光绪以后投入大量资金在悬岩上开凿了花岩北线,道路从分水上花岩相对更为平缓,去险陡变便捷的诉求和技术、资金投入等前提因素成为重要的改道原因。至于小区间的改道与并行的原因,则往往是技术、资金因素所致。如朝天峡栈道主要是在北宋开始因木栈容易受到破坏,外加栈木短缺而失修,只有改绕行在朝天岭开路,而梁平佛尔岩段、大竹九盘陡嘴段碥路并行,多是技术进步和资金投入后的改险为夷所致。因此,政治经济格局、道路险远度、修路技术力量和资金等因素,一直是中国传统道路空间变化的主因。即便时至今日,道路空间变化的主因亦大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