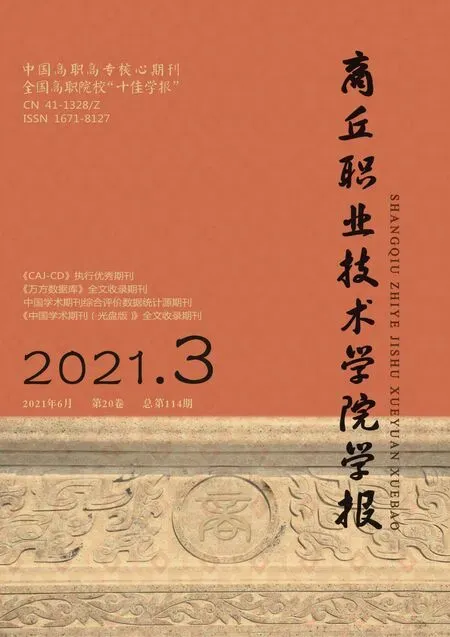清代传奇《繁华梦》研究综述
2021-02-01台梦雅蒋小平
台梦雅,蒋小平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王筠不仅是乾嘉年间著名的女诗人,也是清代的第一位女性剧作家,清人对其评价颇高。其创作的《繁华梦》和《全福记》是现存明清妇女戏曲创作中少见的长篇,其中以《繁华梦》最负盛名。《繁华梦》叙写长安才女王梦麟为不能如男儿般建功立业而伤怀,于是善财童子奉命来到王氏梦中将其改作男儿身。变作男儿身的王梦麟因久慕西湖之景,辞别父母家兄,出门游历。在杭州、苏州邂逅了家道中落的胡梦莲以及农家女黄梦兰,并分别以玉环、玉钗私聘为妾。游玩归家的王梦麟对自己私聘妾室之事不知如何开口,最后在其兄长的帮助下,王夫人(王梦麟母亲)将二妾室接来家中。自此,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一妻二妾和谐美满。就在王梦麟觉得人生圆满之时突然梦醒,夫人、妾室皆不在旁,自己仍是身处闺阁之中的女子之身。王梦麟为此郁郁寡欢,后经麻姑下界点化,才恍然醒悟,梦醒入道。
截至目前,学界对于《繁华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繁华梦》作者王筠的考证,这一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王筠的生卒年、婚姻状况以及文学作品的考证上;二是男女作家创作观的差异研究,这一研究是将同时代的男女剧作家的作品对比分析,以探讨他们的创作侧重点;三是关于“拟男”表现手法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围绕“拟男”表现手法的文学功能展开,透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剧作所呈现出来的鲜明主题。
一、对《繁华梦》作者的考证研究
对于《繁华梦》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都涉及了对其作者王筠的考证研究。20世纪初,谭正璧在《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一书中对当时的知名女性剧作家进行了生平考据,同时也将王筠以及阮丽珍等小有名气的几位女作家也纳入其中进行了考察。之后,周妙中在其专著《明清剧坛的女作家》中,对王筠等几位女性剧作家进行了生平资料的发掘以及作品评价。王永宽的《王筠评传》(后收入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除了对王筠生平进行考证外,还从心理学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全新角度对女性创作以及当时女性的真实生命状态作了探究。2003年,台湾著名学者华玮的《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一书出版,书中第二章节对以王筠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生平进行了评述。除了专著外,也有单独对王筠生平进行考证的论文,如殷伟的《清声谱出叶云韵——简介清代女戏曲家王筠》、韩郁涛的《清中期戏曲家王筠生平新考》、邓丹的《清代女曲家王筠考论》以及彭磊、高益荣的《清代女曲家王筠考》等。另外,在一些研究王筠作品的文章中时有出现对王筠生平的考证,如李紫旭的《清代女作家王筠研究》以及韩郁涛的《清中期女性曲家王筠传奇作品研究》,这些文章在剖析作品前都对《繁华梦》的作者王筠的生平资料做了详细介绍。
这些文章主要从王筠生卒年、婚姻状况和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对于王筠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具体如下。
(一)关于王筠生卒年的考证
学界对于王筠生卒年的考证研究主要以王永宽和周妙中为代表。关于王筠卒年的时间,王永宽根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十五中王百龄的传记记载,推断其卒年为公元1819 年[1]。至于王筠的生年,周妙中在《清代戏曲史》一书中明确将其记载为公元1749年,但并无明确依据[2]。
关于王筠的卒年,学界基本认同王永宽“王筠卒于公元1819年”的说法,主要的分歧存在于其生年时间上。关于王筠的生年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以周妙中为代表的“公元1749年之说”,这种说法在学界颇受推崇。如《长安县志》中描述:“王筠,1749—1819,清代长安人。”[3]《清代诗文集汇编》四百二十五卷《槐庆堂集》中载:“王筠,字松坪,生于乾隆十四年(1749)。”[4]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一文中对周妙中的考证持认同态度,同时对于王筠的生年做了考证。邓丹根据王筠之父王元常的一首题诗,而判定王筠的生年与周妙中的说法较为接近:“此诗作于乾隆丁亥年,即1767 年。诗中所说‘廿年珠玉掌中擎’表明此时的王筠年约20岁,以此推算王筠的生年确与周妙中所说的‘1749年’比较接近。”[5]53
第二种说法是以韩郁涛为代表的“公元1748年之说”。针对上文提到的邓丹关于王筠生年时间的推断,韩郁涛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既然可以根据王元常的一首诗确定王筠出嫁时间为乾隆丁亥年,即王筠二十岁的时候,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出王筠生年的准确时间应为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第三种观点是以彭磊、高益容为代表的“有待商榷”的说法。他们通过对一些文献资料的搜集梳理,认为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王筠生于公元1749年的结论还值得再商榷。例如,在《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中有“王筠,1749?— 1819,字松坪,号绿窗女史”[6]的记载,在《戏剧通典》中亦有“王筠(1749?—1819),清代女戏曲作家”[7]的说法。这些记载对于王筠生于公元1749年之说都持有怀疑态度。
综上,尽管学界对于王筠生年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后期研究者在涉及王筠生卒年的问题时基本上还是沿用了周妙中、王永宽的观点。如邓长风的《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李修生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以及江庆柏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文章,对于王筠生卒年的考证,均与周妙中、王永宽的观点一致。
(二)关于王筠文学作品与婚姻状况的考证
学界普遍认为,王筠除有《繁华梦》《全幅记》两部戏曲作品外,还著有诗集作品《槐庆堂集》《西园瓣香集》。然而,对于这种说法,王永宽却坦言:“这两种诗集笔者均未见。”[8]656至于王筠的婚姻状况,周妙中和王永宽观点一致,均认为,王筠嫁给了同乡的一名穷书生。但是,在他们成婚后不久丈夫便离世了。
2007年,邓丹在《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一文中对王筠的生卒年、文学作品以及婚姻状况等做了新证补充。其中,对于上述王筠的文学作品和婚姻状况的论断,邓丹则通过文献考证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首先,对于王永宽提出的未见王筠诗集这一观点,邓丹提到了自己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了《西园瓣香集》,这部诗集的中卷上题有“长安王筠松坪氏著”[5]53。由此可知,王筠确有诗集存世。其次,有关王筠之夫的考证,邓丹从王筠的一些诗作中发现,王筠之子王百龄曾在翰林院任职,在此期间,他写过《家书频问归期而八月告假不果,因附四诗以慰二亲悬望》《送闫望卿第后荣归》两首诗。这两首诗里,字里行间均是对父母的想念,这就表明王百龄中进士之后,他的父亲仍然在世。之后,邓丹又根据王筠的出嫁时间以及百龄中士的时间推断出王筠夫妻共同生活的时间。邓丹认为,王筠“自1767年出嫁至1802年其子百龄中进士,她与丈夫一起生活了三十六年”[5]53。这一观点推翻了之前以王永宽、周妙中为代表的关于王筠丈夫婚后不久离世的说法。除此之外,邓丹还发现,在王筠的诗词中“多写亲人家事,却不曾提及自己的丈夫,由此认为王筠对于这段婚姻怕是只有失望”[5]53。这一新观点也使得之后的研究者们认为,不幸福的婚姻也是王筠创作《繁华梦》的一大原因。
二、对男女作家创作观差异的研究
《繁华梦》的作者王筠是一位女性剧作家,因此,对《繁华梦》展开研究时,学者们都注意到了关于男女作家创作观的差异性。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者们是从戏曲题材以及男女作家的作品对比来展开研究的。
(一)戏曲题材对比
性别的差异,加之不同的生活经历使得戏曲作家在从事戏曲创作时会将目光投向不同的领域。男性剧作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社会问题,而女性剧作家则比较关注内心的情感世界。如李小慧在《明清妇女的戏曲因缘》一文中就指出,在明清戏曲作品中,相对于男性剧作家喜欢在戏曲中反映有关妇女的私奔问题、妓女问题、妻妾问题、妒妇问题等,“大多数女作家极其不愿写‘私奔’‘妒妇’等有关妇女问题的剧作,也不愿触及治国平天下等沉重的社会话题,特别是清代的那些闺秀之作,主题较集中,主要写女性的才干与情爱,烘托出女性对生活的感受。如王筠借剧本《繁华梦》第2出《独叹》中剧中人王氏之口,说出有才女子欲在社会上大显身手的愿望,以及才不得展的苦闷与不平”[9]。
(二)男女剧作家作品对比
1.《繁华梦》与《雌木兰》对比
由于女性身份的限制,明清女性作家在从事戏曲创作时往往需要借助男性的身份来表达自身的情感需求、生存境遇以及人生理想。因此,大量女扮男装的情节出现在明清时期戏曲作品中,《繁华梦》便属于这样的戏曲作品。但这种情节并非是第一次出现在戏曲作品中,徐渭的《雌木兰》与《女状元》中亦有此类情节。研究者便将这些作品进行了分析比较,李凌志曾在《王筠〈繁华梦〉与徐渭〈雌木兰〉中女性意识差异性研究》一文中将《繁华梦》与《女状元》进行了对比,探讨了两位作者关于女性意识的不同观点。他在文章中阐明男女作家所具有的共同的女性意识,即在他(她)们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王梦麟、花木兰均是通过“换形”的方式完成了身份转变,并且通过自身的才能(一文一武)才获得认可。另外,李凌志用更多的篇幅对男女剧作家女性意识的差异性展开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根据剧作情节,他认为,相比于女性剧作家对于爱情生活的描绘,男性剧作家则是将关注点放在了政治抱负上。《繁华梦》中,对王梦麟的仕途经历笔墨较少,却对王梦麟及一妻二妾的婚姻生活细节描写详尽。而在《雌木兰》中,则主要表现花木兰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场面,而对于其情感生活的描述少之又少。二是关于两部剧作不同结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差异性。《繁华梦》结局写王梦麟在麻姑的点化下梦醒入道,这是作者借用一种虚幻的方式来中和欲望与现实的冲突,而《雌木兰》则以木兰回归女性身份为结局,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木兰身上的个性,且透露出了男性剧作家关于女性意识的局限性。
2.《繁华梦》与《邯郸梦》对比
王梦麟作为《繁华梦》中的主要人物,碍于女子身份才华无处施展,只得借助梦境换身男装,实现功成名就的理想,后经麻姑点化方才醒悟,类似的情节在汤显祖笔下的《邯郸梦》中也有发生。不同的是,这两部剧作出于不同性别的作家之手:《繁华梦》出自女作家王筠;而《邯郸梦》则出自男作家汤显祖。因此,这两部剧作实则存在巨大差异,在这差异之中透露着男女剧作家戏曲创作观的不同。彭磊在《清代才女王筠生平与著述研究》一文中便以这两部剧作为例,提出相比于男性剧作家(汤显祖)对主人公出将入相、宦海沉浮的描写,女性剧作家则注重对主人公婚姻、家庭的描写。另外,张文雯在《明清女性剧作情感抒写研究》一文中也以这两部剧作为例,通过对《繁华梦》与《邯郸梦》两个剧本的“功名观”“婚姻观”与“结局的顿悟”三方面的比较,认为在叙述怀才不遇的生活经历时,不甘的怨愤是男女性剧作家共同的心态,不同的是,女性剧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充满了对爱情婚姻的向往;而男性剧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则更向往功名利禄。关于两部剧作的结局,更是透露着男女剧作家的不同,“两个主人公同样是经过点化后顿悟,但王梦麟却不及卢生悟彻底”[10]。
三、对《繁华梦》中“拟男”手法文学功能的研究
中国戏曲与性别文化颇有渊源。性别文化不仅在戏曲舞台上有着生动的体现,在戏曲题材中也有所展现,“易性乔装”剧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严敦易先生把这种通过易装换性现象称为“拟男”描写。在中国古代,性别意识提倡的是“男不言内,女不言外”[11]。直至明清之际,随着才女群体的出现,这种性别意识才开始受到质疑。那些才华横溢的女性渴望像男性一样建功立业、考取功名、获得美好姻缘。但是,由于受到性别的限制,她们想要展现才华的渴望以及内心对爱情婚姻的诉求却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而只能停留在闺阁之中。她们将这种现实中无法实现意愿的烦闷延续到了她们的戏曲创作中,在剧作中,她们不得不借助男性的身份去实现这些愿望。于是,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往往借助梦境的方式改头换面成为男儿身,借男性的身份走出闺阁,考取功名,在证明自己才华的同时,也主动寻求自己的美满婚姻。而《繁华梦》作为“拟男”手法的典型代表,其主人公王梦麟便是借助“易性乔装”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一)“拟男”手法下的人物塑造功能
首先,“拟男”的表现手法为《繁华梦》中主人公王梦麟的活动范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自古以来都是文人才子的毕生追求,而身为女子身份的王梦麟也有对才华、功名、婚姻的渴望。在第2出《独叹》中,王梦麟家门数代科甲,自己也有一颗光宗耀祖之心,却碍于女性的身份而无迹可寻:“俺虽未从师,略知文义。但生非男子,无路扬名显性。”[12]33-34在欣赏美人图伤感之际,王梦麟又为图中美人倾心,于是焚香拜画,感慨自己若是男儿身必定将画中女子娶回。对于女子身份的愁烦足以说明王梦麟的一颗男儿心,而“易性乔装”使得王梦麟由女转为男,走出了闺阁,参加科考,寻访美人。最后不仅高中状元,更是得到一妻二妾的美满结局。
其次,在《繁华梦》的人物塑造上,有着很明显的“自况”性。“自况”性戏曲是指戏曲家在进行戏曲创作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和愿望要求投射到戏曲人物身上的一种戏曲。明清之际,“自况”性戏曲作品数量逐渐增多,至清代,文人作家们尤其是女性剧作家更是将“自况”性戏曲作为表现自我、达到“写心”目的的重要工具。根据陈磊磊做的数据统计来看,“清代共有42位作家叙写‘自况’性戏曲”[13],不少女性作家也在其中。到了清代,女性戏曲作家数量逐渐增多,她们开始借助戏曲来记录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对人生的感慨,在对自我需求与性别、婚姻、家庭间种种矛盾冲突的描写中表达了女性的境遇与诉求,王筠的《繁华梦》便是典型代表。
《繁华梦》一共25出,叙写关西望族、长安才女王梦麟才华横溢,不满自身女性身份,在梦中“换性”,借助男性身份实现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愿望,最后发现不过大梦一场,在麻姑点化下参透人生,遁入空门的故事。这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抒情剧,目的是抒作者之胸臆。
显然,剧中主要人物王梦麟是作者王筠的化身。首先,两人家庭背景几乎吻合,均是长安人氏,出身于名门望族;其次,剧作中的王梦麟与作者王筠一样是个才女,却恨自己是个女儿身,导致才华无处施展。王元常以及王百龄都曾为王筠的《繁华梦》作跋,王元常写道:“女筠,每以身列巾帼为恨,因此撰《繁华梦》以自抒其胸臆。”[12]142-143王百龄在序跋中也说道:“太孺人秉异质,通书史,常以不获掇巍科,取显宦为憾,因撰是编,以抒胸臆。”[12]142之后,学者殷伟也提出:“王筠少时嗜好读书,生性聪敏,富有才华,常恨自己身为女儿家,故而终身积怨,遂以笔来自抒胸臆,发泄积怨。”[14]31李祥林也在自己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一文中指出,王筠“自恨身为女子,不能如男子般建功立业,遂作传奇《繁华梦》抒其胸臆”[15]。
在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中,对于王筠生平的介绍和评价也和剧中王梦麟多有相似之处,如西安市地方志在对于王筠的记载中说道:“王筠自幼性格豪爽,有男子慷慨之态。胸怀宏愿,才情非凡。”[16]中国戏曲志中也有“王筠博览群书,十三四岁便能吟诗填词,被誉为‘长安才女’”[17]的记载。
再者,剧中王梦麟所娶的一妻二妾在王筠的交游记载中亦能找到人物原型。王梦麟的两位妾室黄梦兰和胡爱莲,在第2出《独叹》中就有所透露。不甘女儿身的王梦麟焚香拜画,不禁感叹:“记得那年在邯郸,遇到的黄姬、胡氏二女,真殊色也。一面之缘,匆匆别去,再会无由矣。”[12]35现实生活中的王筠,的确曾与父亲游历邯郸,并且结识了许多闺秀。且根据王元常批注可知,胡梦莲与黄梦兰实有其人。在第19出《双圆》中,当谢梦凤得知家中住有两位与王梦麟订下终身的女子后,心想若是自己现在便松口让他们相见怕日后自己被轻视,便有意乔装成妒妇试探难为他一番。两人经过一番较量后,最后4人得以融洽相处。对此情景,王元常曾有批注:“其口角光景,颇似作者乃堂。”韩郁涛也在《清中期女性曲家王筠作品研究》一文中说道:“王梦麟其父曾登皇榜,其母淑德贤明,家有长兄,这与王筠本人的家庭背景几乎完全吻合。一妻二妾,亦有人物原型。由此可见,王筠多是以身边熟知的女性为原型来塑造剧中的女性角色。”[18]273
(二)“拟男”手法下的主题深化功能
“拟男”的表现手法在《繁华梦》中除了具有塑造人物形象的功能外,还具有深化作品主题的文学功能。
明末清初以来,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甚至鼓励女子读书。另外,伴随着王阳明心学思潮的影响,才女文化逐渐兴起并兴盛。清代,女性剧作家的数量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多。她们借助戏曲创作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因此,书写女子的才华成为明清才女群体创作的一个重要议题。明清才女自身的学识又使得她们的主体意识愈加清醒。然而,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女子举步维艰,她们只能借助戏曲来表达其对自身处境和性别角色的思考。
关于《繁华梦》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繁华梦》表现的是作者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如殷伟在《清声谱出叶云韵——简介清代女戏曲家王筠》一文中说,《繁华梦》改变了传奇体制的旧例,“传奇一般是男角色先上场,而《繁华梦》却先让女子王氏登场,一变传奇体制旧例,这实际上传达了王筠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14]32。然而,对于这一观点有学者提出,虽然王筠《繁华梦》中显现出了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但是却未上升对社会性别、尊卑观念的抵抗。如胡世厚、邓绍基在其著作《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中就指出,王筠的《繁华梦》“表现了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但是王筠并未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封建秩序,她只是幻想在现存的封建秩序中实现她理想的生活目标”[8]655。这种说法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华玮在《明清戏曲中的女性声音与历史记忆》中谈道:“王筠无意表现妇女集体对性别定位的思考,《繁华梦》叙写的仅是她的个人心愿而已。”[19]邓丹在《才女形象与明清女剧作家的性别思索》一文中也指出:“《繁华梦》中除了主人公王梦麟外,其他女性如谢梦凤、黄梦兰等仍是安于扮演传统的女性角色。由此可知,剧作并未流露出对抗社会性别、尊卑观念的倾向。”[20]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繁华梦》的主题表现的是一种女性文人的才名焦虑。如韩郁涛在《清中期女性曲家王筠传奇作品研究》中提及:“《繁华梦》中王梦麟‘做不得投笔班超’的呐喊,实则出自王筠内心的呼喊。而一句‘诗书误我’更是那个特定时代下才女群体的真实心声,王筠正是借助王梦麟来表现当时女性文人的才名焦虑。”[18]277-278
而多数人持第三种观点,他们认为,《繁华梦》的主题是多元的,其是一部展现女性意识以及反映女性真实生存状态的剧作。如唐昱在《明清“易性乔装”剧与性别文化》一文中指出:“多情的才女不会像传统女性那样只会被动地守在闺房中坐以待毙,而是选择女扮男装,主动出门去寻找自己的幸福,这就是一种进步,她们以另一种方式彰显了女性意识。”[21]陈国华在《清代长安女才子王筠戏曲创作探析》一文中指出:“王筠《繁华梦》剧中女性人物以男性的身份表达自我,表达对社会性别的反省。作者笔下的王梦麟对于短暂的女扮男装并不满足,她更加希望自己本就是男儿身,这种思想意识反映了当时女性群体的真实处境。”[22]刘军华在《明清女性作家戏曲之社会性别错位现象透视》一文中说道:“王筠的《繁华梦》以虚幻梦境的方式,表现了女性对性别角色和定位的思考。这种对于性别错位现象的描写,表达的是时代女性想要破除性别樊笼,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在传统伦理压制下真实的生命状态。”[23]
纵观以上对于《繁华梦》的研究梳理,我们既可以看到女性作家群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同时也认识到关于这部作品,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依然很多。首先,对于《繁华梦》的研究,研究者更多的是将其放置在“中国古代妇女的戏曲创作”的整体框架中,而非个体研究。其次,对于《繁华梦》的个体研究,更多的关注点是集中在王筠的生平考证上,而缺乏对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最后,对于《繁华梦》的研究,不管是对作者的考证研究还是对作品的主题研究,其观点都是沿用前人的说法,缺少创新性。这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使对于《繁华梦》的研究更加丰富多彩,为女性剧作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