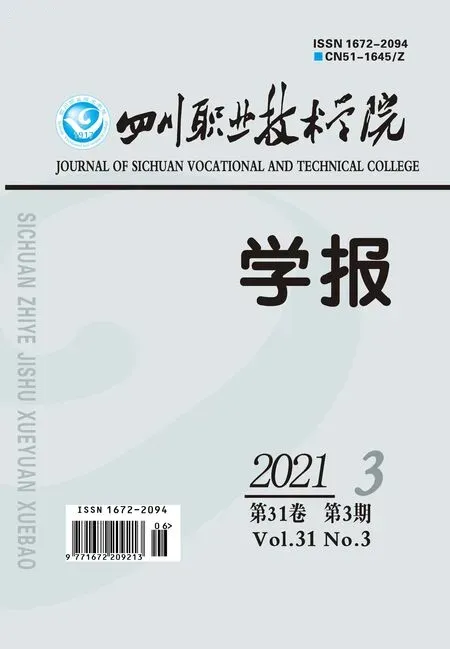在妥协中反抗
——论《妙妙》的性别权力关系
2021-01-31甘传永
甘传永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妙妙》是王安忆写于1990年的一部中篇小说,于第二年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并没有引起评论界过多的关注。这篇写女性故事的小说在王安忆研究中好像也难以放置到合适位置,它总显得“不伦不类”。从王安忆创作的女性地理版图看,它既不是写上海弄堂里的女人,也不是写农村、文工团的女人,亦不是作为外来者进城寻出路的女人。学界的忽略也可能因为这篇小说故事太简单:一个乡镇少女渴望进入大城市,但自己没有本领,只能选择依靠男人来进入城市,但最终失败。乍看这个故事模式确实老套,王安忆好像在二十世纪末还在讲五四时期的妇女问题。但作者却不这么认为,“《妙妙》其实也是写弱者的奋斗,这一类人的命运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关心的……这是我很欣赏,也很愿向其学习的……我很钦佩她们”[1]321-322。重读这篇小说,我发现王安忆在文本背后关注的是80年代启蒙话语结束后,在商品化浪潮和市场化经济兴起的90年代,现代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以及置身其中的女性如何受时代潮流影响、以何种姿态参与。
一、小镇少女“出走”可能性的探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阶层壁垒被打破,个体和市场在经济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个人凭借自己的本领有了发家致富的可能,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人也因此可以进入大城市,这导致城市化发展和阶层流动性的进行。同时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也为偏僻的农村和城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城市样貌,让人们有了了解外面世界的更多途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化刚刚起步,人们对建成现代化的大城市普遍充满着乌托邦式的美好想象,这也通过大众传媒表达出来,都市男女光鲜亮丽的一面被无限放大,城市化潜在的问题自然被遮蔽。这种充满吸引力的城市文化不仅通过报刊、杂志传统媒介展现,还通过电视这种新兴媒介,以视觉化的方式传递到全国各地。这更激发了农村和乡镇的人对大城市的憧憬,在他们心中大城市象征着现代文明,因此去城市生活,体验外面的世界意味着是进入现代文明的一种方式。
头铺镇的十六岁少女妙妙就是通过电影电视、报刊杂志这些媒介来憧憬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员。青春期的妙妙野心很大,心里只认同北上广这三个大城市,其余都瞧不上。她渴望进入这类城市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做一名现代青年。不过妙妙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很肤浅,局限在世俗的层面,简单化为时尚的服饰。因为妙妙只是通过大众媒介理解城市文明,而90年代的传媒表现了向市场靠拢的特性,世俗生活代替了启蒙话语,浮华鲜亮的物质代替了精神追求。这也是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初就清醒意识到的社会转向。整个社会由精神追求转向物欲追求,这也必定伴随着道德滑坡。妙妙充满着对城市现代文明简单又美好的想象,她不甘于平庸的命运,决心一定要走出去。
但在小说伊始作者就封堵了妙妙可能“出走”的一切途径。妙妙学习成绩不佳,所以无法通过考学进入城市;她也不通晓做生意的门道、没有本钱,所以通过打工或经商这条路进入城市也无法完成。她想过出嫁,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但对婚姻的选择有极高的要求,对象必须是北上广的完美男性。可无奈北上广的男性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小镇,所以这条路也走不通。如此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经济条件一般、没有突出本领的乡镇少女所拥有的“出走”的正常途径都失效了。
就如王安忆所说妙妙是不自觉的人,“自觉的人他都是知己知彼地去做,他有理性,于是理性也给他画个圈,有了范围;不自觉的人却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他们的行动漫无边际”[1]321。正因为不自觉,妙妙才能突破常规的局囿,自己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尽管妙妙自己也隐隐察觉到这条路风险很大。妙妙如同在进行一场豪赌,其他途径已经走不通,那就不如破釜沉舟拼一次,只不过她的赌资是自己的身体,因此失败的代价也非常高。
妙妙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产生通过依靠一个来自城市的男人而把自己带入城市这种意识的,而是在与男性接触过程中,意识逐渐清晰,目标逐渐明确。妙妙对电影摄制组的到来感到欣喜是因为她盼望导演会发现她与镇上其他姑娘的不同,从而获得一个电影角色,通过演电影顺理成章的进入城市。所以妙妙与北京男人发生关系只是一个巧合,因为这次关系的发生,妙妙认为她与现代文明建立了联系,精神获得了解放,并认为从城市来的男性是自己与现代文明建立联系的桥梁。这次偶然事件的发生,让妙妙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与现代文明对话的可能,只是差一个中介。虽然北京男人离开,但是她依然期待下一个“桥梁”的出现。在与孙团的关系中,妙妙已经考虑到了婚姻问题,但是自认为具有现代恋爱观念的她因为爱面子没有“粘”住孙团。在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和危险处境时,妙妙才真正明确了通过婚姻进入城市的意识,开始自觉主动地寻找男性“桥梁”。她的目的太明确了,以至于为了这个目的已经不顾一切了,所以她在面对第三个男性——已婚的何志华时,才会表现得那样着急,说出“你为什么不能对不起她?我不要你对不起(我)”[2]259这样的话。
文本中妙妙自觉性程度越来越高,但自己的理想标准却越来越低,呈现出了反向变化。妙妙的理想其实是在不断萎缩的动态变化中。她最初的理想是进入北上广这样的城市,但对男性桥梁的选择上却呈现出“北京—省城—县城”不断下降的趋势,她是在与自己的理想不断妥协。其实妙妙对要去往的“远方”——城市现代文明——的理解是模糊和肤浅的,这在文本中被多次暗暗指出。除了把现代文明简单理解为时髦的服饰外,小说中还多次写到她对电影的喜爱。摄制组要拍的电影是宝妹写的小说,即一个小镇街上的姑娘,独立办厂,成为企业家的故事。但在小镇上早已流传这个小说时,妙妙是不关心的,她关心的也不是拍的内容或演员扮演的角色,而是“扮演”这一过程,在她看来这是一种可以体验两份人生的幸福事情。同时她沉醉于电影中光鲜的青年男女,而丝毫没意识到电影是虚构的,是把生活经过加工处理的,她把电影里的男女当成真实日常生活中的人。她在回忆与北京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场景时,无意识地把自己想象成电影里的女人,自己是完成了一次现代文明的“表演”。对城市现代文明理解上的模糊性就决定了妙妙对自己理想定位的不明确,亦即无法认清自己。这暗含了王安忆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个哲学经典问题的追问。因此妙妙注定是失败的。
但是王安忆并不是想通过这篇小说仅表达花季少女失足这一问题并进行社会批判。王安忆这篇小说写于她去白茅岭女劳教大队采访后,那里的女性多数因卖淫活动而接受劳动改造。王安忆采访后对这里的女性颇感惊讶,并不是惊讶于她们的身份,而是惊讶于她们的人生观:
她对你的人生是批评的,你很平凡,很平庸,没什么意思。而对自己的,还是满意的,虽然遭受了挫折,但这不过是代价,终还是使她避免了和你一样的普通的人生。在白茅岭这地方,千万不要以为她们有什么忏悔之心,她们不过是在体验她们人生的一部分经历……你就简直不知道她的生活热情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她们是人群里的异数[1]323。
王安忆话语背后的意思是抛开违法活动,这些女性都是敢于向父权制象征秩序挑战的人,结果就算失败,但在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主体性和能动性。这就如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对男权主义批判的那样,她们(女性)是一切,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但惟独不是她们自己[3]。白茅岭的这些女性敢于去爱和恨,敢于去做一个“女人”自身,而不是安于循着“女儿—妻子—母亲”父权制秩序规定的身份道路走下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王安忆话语背后隐藏的不安。白茅岭劳改农场的女犯们遵从的生存逻辑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商业社会中的交换法则,这个法则与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格格不入。它反映了商业社会与传统社会,女性商品化与女性私有化家庭的冲突。在社会的语言象征秩序由传统社会向商业社会推进中,女性自身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主动性加强了,而物化的趋势同时却加深了。
王安忆曾在《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城市》中表达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但是她并非一味批判,而是认为女人对男人在人性上具有超越性,“岂不知,女人在孤寂而艰苦的忍耐中,在人性上或许早早超越了男人”[4]。女性在人性上超越男性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妙妙》中,表现在妙妙对生活的韧性和生命活力上。妙妙不被头铺镇上的人理解,成为最孤独的人后,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最后即便已经伤痕累累,但她寻求现代文明的目标没有改变。从文本开始妙妙就因为服饰上的特立独行被当作异类,但她并不因此困惑,反而享受这种特殊,因为他者眼中的怪异正鲜明确立了妙妙自身的主体性。妙妙对生活的韧性也即女性的能动性表现在即使出走的途径都被封堵,但她依然凭一己之力在不断反抗。
然而就像王安忆所说:“她们不自觉,不是说她们不知道要什么,而是不知道不要什么,她们凭着感性动作,茫茫然地,就好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碎成一片,她们最终都是砸碎自己的命运,有多大力气,砸多么破碎……她们都是很盲目的。她们要一样东西就是去要,去要,需要付什么代价,则全然不计较。”[1]321-322妙妙的心理是复杂的,从她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处于波伏娃所描述的青春期危机的少女特性。她避免真实的生活经验,而建构起热情的想象生活,甚至幻想和现实混淆不清。她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否定之中:
希望自己不再是个孩子,却又不接受成人的身份,她一会责怪自己孩子气,一会又责备自己的女性软弱[5]140。
她不接受自然与社会派定给她的命运,但也不完全拒绝它;她自身的矛盾分歧太多,以致于无暇与世界作战;她将自已限制于逃脱现实或对它的象征性斗争之中。她的每个欲望都有与之相应的焦虑;她一心渴望要掌握自己的未来,却害怕与过去断绝;她想‘得到’一个男人,但不要他象对待祭品样地占有她。而在每一恐惧后面,又都潜伏着一道欲望:她害怕被侵犯,却渴望消极服从。于是她命中注定要变得缺乏诚意,满口遁辞注定要受到各种消极观念的困扰(negative obsessions),无法摆脱那种焦虑和欲望相混杂的矛盾心理[5]140-141。
处于青春期危机中的妙妙就是这样,她反抗、不合作,想要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她不退让、不顺从,结果就是被生活碾得粉碎。大部分少女看到这种挣扎的后果,于是便屈服了,安静下来准备接受女人的生活,这意味着少女时代结束,女孩死亡了,一个女人出现了。
王安忆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给了妙妙新生的契机,这是王安忆对女性同性间的体恤与同情。文本设置妙妙最终观看了宝妹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就是说妙妙知晓了那个小镇女子凭自己的努力成为企业家的励志故事。所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妙妙,要想在象征秩序中让自己过得好,第一是生存,首先要让自己安全、健康的活着。经历了风波的妙妙必定有所体悟,做月亮还是孤雁,妙妙自己必已有了答案。
二、“外来者”身份合理性的质疑
与男性作家笔下小镇少女进城的故事不同,《妙妙》中的男性并不扮演单一启蒙者的角色,妙妙也不是被启蒙者。外来者的男性不是象征着城市现代文明,而是代表通往现代文明的桥梁。对妙妙而言,他们是中介,而不是目的。
小说中妙妙命运的转折点是与北京男人的相识,在此前尽管妙妙自认已经具备了进入城市现代文明的基础,但缺失通往城市大门的中介。北京男人充当了这一桥梁的角色。妙妙与北京男人相识和发生关系是偶然的,在撞破两个演员的性事之前,妙妙并没引起这个摄制组里人的注意,甚至在电影女主角眼中妙妙的衣饰是非常像宝妹的。换言之在北京摄制组的眼中妙妙与镇上的少女无丝毫不同,都是土气的,尽管妙妙自认是一位洋气的孤独者。更能证明妙妙骨子里还持有传统思想的是她的贞操观念。妙妙意识里对性的观念仍然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封建的,所以她觉得“她应当看不起他们,蔑视他们,将他们当作下贱的人,这才可显出她妙妙的尊严”[2]228,这种贞洁思想与小镇上的人没有不同。正因为妙妙这种清教徒般的态度引起了北京男人的注意,在北京男人眼中妙妙是很“有趣”的。在妙妙眼中北京男人是现代文明的代表,但他诱奸了妙妙。这里讽刺的是妙妙憧憬的现代文明却以非常罪恶的方式进入了妙妙的身体内,随后抛弃了她,只留下一个老旧的收音机和一个亮得眩目的背影。北京男人的收音机声音是模糊不清的,他的背影亦是让妙妙眼花,这样现代文明以一种模糊不清的面貌留在了妙妙记忆中。
如果说妙妙在与北京男人的关系里代表着被动和权力弱者的一方,那么在与孙团的关系中妙妙成为了一个主动者,甚至以一个启蒙者的强者姿态出现。孙团是省重点大学的学生,对于妙妙而言是一个城市知识分子,是受过现代文明浸润的人。但当妙妙发现孙团在性问题上丝毫不懂和忸怩胆怯,妙妙从心里瞧不起他了。妙妙自认为北京男人使她精神获得解放,而讽刺的是精神只局限在了性爱观念上,妙妙在性上变得大胆、开放,认为这就是现代精神,而且把性当成了爱情。所以当她面对在性方面懵懂的孙团时,不自觉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她教导孙团性爱的技巧,像一个演说家一样讲述性爱观念,而孙团变成了一个被启蒙者、一个听众。这个场面与《伤逝》十分相似,只不过子君和涓生的角色位置进行了置换,女性充当了启蒙者,男性成为了被启蒙者,这颠覆了男性作家笔下的男女性别权力关系。妙妙自觉高孙团一截,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所以她打消了与孙团谈婚论嫁即让孙团负责的想法,孙团也自然不可能主动与初中学历的乡镇少女结婚。这种看似是女性胜利的表象,王安忆却深刻认识到其中的悲剧。结果是孙团走后,留给妙妙一个坏名声。以前是妙妙主动孤立镇上其他人,以此显示自己的“现代”,现在却是她彻底被孤立,面临着一种不仅孤独而且危险的境地,以致动摇了她做现代青年的理想。
在文本中孙团表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官能症”。弗洛伊德认为情爱中正常的态度是温柔、挚爱的情感与感官肉欲的情感的结合,当这两种情感的会合无法达成之际,结果就产生了精神官能症。他认为精神官能症带来的影响是男性经历的情欲活动有客体选择对象的限制:一直维持活动的感官肉欲情感只是寻求无法挑起乱伦禁忌感觉的对象;对于看似值得高度评价的人所产生的印象,并不会导致感官肉欲的触动,而是导致与感官肉欲无关的温柔情感。周蕾看到了弗洛伊德情爱观的理想主义,她认为弗洛伊德式的情爱方式无可避免地将女性区分为两种类型:令人值得尊敬的女性和令人兴奋与堕落的女性。她在书中写道:
这样的区分大大地令人不安,因为它不只造成了男性欲力能量的分离,而且也产生男性对于女性含有尖锐道德主义的想法。女性若非接受温柔情感与性无能,不然就是接受感官肉欲与轻蔑,因为理想化与情欲冲动彼此无法相容:文化中仅有极为少数的人能让温柔情爱和感官肉欲这两股感情恰好融合在一起;男性总是因为对于女性的敬意使得他的性活动受到挫败,他发现只有在地位低下的性客体对象出现时,他才能充分发展其性能力[6]211-212。
孙团面对妙妙时就表现出了这种情感态度的变化。当孙团连吻都不会,被妙妙瞧不起、被妙妙的演讲震撼住时,孙团处于一种自卑的心理。他对妙妙表现出一种崇拜情绪,妙妙此时是一个地位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神性形象,而孙团却以“像只老鼠似的,一下子溜了进来”[2]238的猥琐形象出现。但是在孙团“一动也不敢动时”妙妙却主动投入了孙团的怀里,小说写到“妙妙由他摸索,他不懂的地方,还教他”[2]239。妙妙自身建构的神性形象瞬间崩塌,在孙团眼中妙妙变成了荡妇,一个能被轻蔑的客体,后来孙团天天夜里到妙妙这来的情况更不断加固这种认知。所以孙团到最后不可能再对妙妙产生尊敬的、温柔的情感,不可能对妙妙负责,必然离她而去。同时当妙妙得知孙团对她的真实看法是仅把她当作性的对象时,更有意味的是文本安排了这句话借无赖小发之口说出,妙妙对孙团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妙妙在头铺镇陷入孤独和危险的境地后想到了婚姻,这表示妙妙要主动进入象征秩序了,但坚持自己选择婚姻对象。她选择了何志华,一个县城的小公务员。妙妙此时对自己的理想不断妥协,去往大城市做现代青年的愿望被嫁一个县城小公务员平稳地过日子代替。与前两位男性比较,妙妙与何志华的关系是最接近平等的。何志华因患有失眠病在黑夜中是孤独者,妙妙是小镇的孤独者,两颗孤独的灵魂产生了平等对话的可能。妙妙对何志华带有一股怜悯的情绪,其实是在何志华的痛苦中看到了自己的孤独,即拉普朗虚认为的“返求回到主体自身的自我之上的施虐”[6]190,在这一受虐过程中体现了反身性,由此产生了幻想时刻。但何志华更多的是把妙妙当作一个倾听者,一个可以进行心理发泄的客体。在两者交流中,多数时候何志华是输出者,妙妙是输入者,这也预示着两人之间不会真正平等。妙妙虽然主动选择了何志华,但也在与何志华的关系中丧失了主体性。尤其当她知道何志华是有妇之夫,她与何志华是处于不道德的关系时,妙妙自身也对这种关系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否则妙妙又怎会领着何志华在街上闲逛,主动向世人们挑战,又怎会想让何志华离婚,与她建立婚姻来获得两人关系的合法性呢。妙妙知道自己处于弱者的一方,这从她选择以一种独特方式进入婚姻这一象征秩序那刻起就已经决定。何志华在妙妙这里享受的是一种母亲般的不需回报的心灵抚慰,所以一旦妙妙提出婚姻要求时,何志华必然不会放弃自己现有平稳的家庭生活而一起挑战伦理道德秩序,所以他注定逃离。
三、结语
《妙妙》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张扬了女性自身的欲望,而且在这幅欲望图景上,女性是欲望的主体,既包括小说中妙妙欲望的主体化,也包括女性叙述者王安忆的欲望的主体化,两者互为因果,挑战了男权意识形态下的民族国家想象。这就是女性写作的意义,就像西苏所说“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不是那种保留在象征符号里并由象征符号来保留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是沉默的地位。妇女应该冲出沉默的罗网。她们不应该受骗上当去接受一块其实只是边缘地带或闺房后宫的活动领域”[7]。妙妙以自己的身体和行动挑战着束缚女性创造力、能动性、主体性的象征秩序,而王安忆何尝不是以写作挑战着和挣脱着这种束缚?
王安忆在小说中对女性主体性的强调,对婚姻中两性关系的思考,笔下的妙妙彰显的不屈不挠的追求精神,挑战和重新诠释了现代性想象中性别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塑造。不只是妙妙,还有阿三、富萍、秧宝宝,她们都是普通的平民,她们勤恳坚韧,她们一步步向前,虽然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但王安忆都赋予了她们极大的能动性。谁知道妙妙不会重振旗鼓,向一条新的生路走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