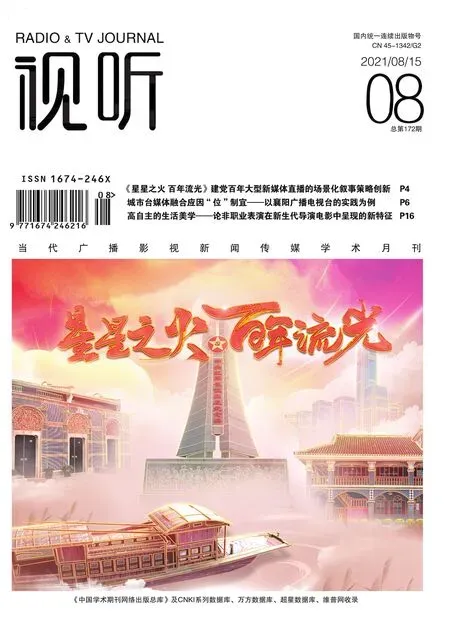《你好,李焕英》:女性意识主导的媒介呈现
2021-01-30夏宇晴
夏宇晴
电影《你好,李焕英》由2016年的同名小品及贾玲亲身经历改编而成,讲述了女儿在母亲即将去世的弥留之际,穿越回母亲正值青春的八十年代,尽力改写母亲命运的故事。电影并非仅停留于表面的喜剧哄闹,故事中蕴含着真挚的母女情,让受众产生情感共鸣。
一、主题明确:突出女性的主体意识
电影并非纯属虚构,而是由贾玲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无论是原版舞台小品还是电影,都具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并且有一定的作者性。电影由女性执导,从女性主题出发,以女性为话题,讲述女性的故事,并与女性身份相契合。影片体现出的女性意识与思考,也是贾玲作为导演在创作过程中和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投射。
影片将镜头聚焦于女性的故事与亲身经历,对女性主题投入更为深刻的人文关注。同时,影片从一种超现实的维度重新审视母女间的细腻关系,趣味地探讨了母女同处“年轻”时的相处模式。不论是从故事内容和表达形式,还是作为导演的创作者身份和主人公的情感传达来说,这都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女性电影。
《你好,李焕英》充分发挥女性的主体性,体现女性的独立性以及自主性,突出了女性的主体身份意识。女性意识是指“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对外来讲,是指“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影片中贾晓玲在八十年代的行为内在驱动是为了弥补母亲年轻时的遗憾,出发点是为了母亲更幸福,即使这种改变命运的结果可能导致自己无法降生,贾晓玲仍然义无反顾。不掺杂其他的逐利因素或是满足他人对自身的希冀与期待,是自发主动、自我选择的行为。
女性意识表达情感共振,最重要的是要依靠于内在张力,即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作为主角的女性角色,在选择与行动动机上不再由外界因素控制而发生变动和适应,而是在特定情景下进行主动选择。
电影在营造笑点与情节安排设计上并没有矮化、物化任何女性角色,反而是通过戏剧冲突与对比,塑造和刻画了鲜活的女性形象。电影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导演对女性角色、女性演员的理解关怀与真切善意。在排球比赛那场戏中,集中刻画了两队女子的激情昂扬与好胜心,彰显了即使无法逆转败局也要坚持到底的倔强与不屈,以及在输掉比赛时不气馁不服输的精神。
电影中有一个刻意安排的细节,即贾晓玲在穿越前认为王琴是因为嫁给了沈光林而生活“幸福”,并且寄希望于改变历史撮合李焕英与沈光林在一起。这时的贾晓玲仍然停留于母亲要通过嫁给“优秀的男人”才可以获得幸福的观念上,即主人公无法通过自我找到出路,导演只能让其依附于男性。观众在这时也会代入想法,会将女性主人公命运的改变寄托于男性与婚姻。但是在电影走向尾声时,人物的命运与结局才揭晓:无论李焕英还是王琴,两位女性的经历都源于自我选择与自身奋斗。王琴虽然言语上尖酸刻薄,行为上霸道好斗,但是她并没有被塑造成出卖感情、依靠职场潜规则上位的女性,也不是因为嫁给了沈丛林而一劳永逸。她也是独立且有思想与一技之长的女性,敢拼敢争取,最后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与能力获得机会,独身去往深圳打拼。
二、女性视角:细腻描绘母女情感
一部女性电影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站在女性视角、以女性为题材、具有女性主义色彩。《你好,李焕英》内外蕴有三层视角:作为现实中的贾玲,对已故母亲的怀念与再投视的眷恋视角;影片中作为青年贾晓玲对遭遇车祸即将离世的母亲的不舍视角;青年贾晓玲意识穿越到母亲青年时代再认识母亲的超现实视角。
多数电影是以“男性他者”的客观存在为审视角度。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分析了在父权制社会背景下拍摄的一系列电影,她们发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要么被定位成男性观赏的对象,要么就是男性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塑造的女性形象,或者是女性在“男性他者”文化影响下的自我投射。在《你好,李焕英》中,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既不是通过剧中男性的眼光去审视和观察,也不是为了刻意迎合观众对于女性的身体凝视,没有在视觉塑造上呈现讨好观众的意味。
贾晓玲的人物形象带有一定的导演本人传记色彩。她有着圆溜溜的眼睛和两颗小酒窝,体型稍胖,整部剧中大多只是穿着素白短袖和牛仔裤的装扮。人物形象是平民化的、接地气的,就像邻家孩子的样子,普通而平凡,善良又朴实。贾晓玲在影片中承担着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人物内心成长过程的转变很清晰,人物的动机和内在驱动力都是为了母亲更加幸福。由先前的改变母亲命运到撮合母亲与沈光林谈恋爱,再到相信并尊重母亲的选择而不应去改变已经很幸福的事实,人物实现了从最初时认为只有让母亲嫁给有厂长儿子才可以获得“幸福”到后期理解并尊重母亲自己的选择和坚持的平滑转变。
影片对于李焕英角色的塑造,则带有一种理想化的母亲光环,更是有一层由导演填上的更加饱满的滤镜。李焕英的角色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外形清纯出众,两股麻花辫,一身碎花裙,言语亲和,人物情感穿透力强。她大方体贴,讲情理,情感独立不受他人左右,自尊心强但也并非去争抢什么。父权意识形态虚构出的理想母亲彻底沦为了“母性的囚徒”,母亲是这些女性丧失了作为恋人、妻子、情人的身份后唯一获得社会认可的角色,而她们作为女性或者说作为一个自在的“人”的需要完全被抹杀。李焕英在成为人母前后都不曾受父权意识影响左右,她拥有独立的人格,自我选择意识强烈,敢于追寻自己想要的、肯定自己拥有的,坚信属于自己的幸福是自己获得的。钢铁厂是故事的发生地,也是李焕英的工作场所。在物质方面,她不需要依靠外界,可以自食其力,稳定的工作可以带来生活上的保障。这也是她精神上独立意识存在的坚实基础。女性也可以工作,在社会上找到展现自身能力的位置。
母亲这一概念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的母亲形象和特征。因此,对母亲命运的关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关注。影片展现更多的是透过贾晓玲的眼睛所看到的关于母亲的故事,穿插着回忆的童年往事。片中的场景会让观众不自觉地将自身的经历代入其中,导演将母女间的感情表达得细腻温柔,这种母亲特有的细腻情感以及母女之间产生的美好情景直抵人心深处。李焕英对女儿的疼爱是不带有偏差的,她重视的是孩子的健康与幸福,在艰苦年代,以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对待孩子。李焕英没有以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和要求来教育女儿,没有以“优秀”来衡量自己的孩子,而是简单地希望她过得开心快乐。在攀比风盛行、嫉妒心强烈的社会,一个母亲有这种淡然的态度和知足心态是非常难得的,她坚信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也可以很幸福,不以所谓的“优秀”来定义贾晓玲。李焕英真正诠释了“你快乐,我就快乐”的含义。
三、亲情内核:激发情绪共鸣
亲情是我们永恒的情感话题,影片的观影过程中有笑点也有泪点,观众感受更多的是真情和来自亲人真挚的爱。电影将现实中的贾玲对母亲的思念和片中的贾晓玲对妈妈的感情杂糅在一起,如镜像一般,将纯粹的真实通过电影来完成与虚构的奇妙统一。片尾坐在红色敞篷车上的到底是片中的女儿还是导演贾玲,观众在此时不需要答案,影片的写意传达已经足够。观众或多或少都能够从电影中看到现实生活中自己母亲的缩影,在观影的过程中,有自身与母亲相处时的场景与代入感,与故事中的角色产生情感共鸣,并将这种情感同化、移情至自身。这种诚挚的亲情与眷恋触碰到了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女性导演能从更多维度和视角呈现母亲形象与母女情,这与导演的童年成长历程、女性主义思潮和理论在中国的普及传播、女性题材电影类型需求密切相关。《你好,李焕英》传达的是温和的态度和性别共存,而非性别矛盾。许多男性导演的叙事视角往往会陷入一种“父权”的叙事偏好,同时期的某些电影为营造笑点,插科打诨,刻意以低俗为乐,美其名曰是“爆笑喜剧电影”,却使女性成为一种男性凝视下的“女性想象”,变成一种点缀在男性话语下的花瓶与附庸。波伏娃认为,女性之所以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作为男性中心文化(菲勒斯)的“他者”而被建构的,是男性主体的客体,扮演着父权制社会给予她们的规定性角色。角色的存在只为突出男性主角的恶趣味和满足观众的笑点,女性角色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不可思议的、不合常理的,母亲在失去了丈夫的情况下便不能通过自身抚育后代,女主人公只能借他人之死嫁祸给父亲来完成复仇,片尾又上演一出为保护女儿而反省认罪的父亲的强行煽情……这些电影中常见的情节,在逻辑与动机上,都让女性处于被拯救、被审视、被选择的位置。
女性意识的传达与女性主体认同的书写离不开社会的整体进步。男性不可能成为女性的避难场,女性唯有寄希望于自我的觉醒。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后,前期不被贺岁档看好的《你好,李焕英》于2021年闪亮登场,合理地填补了观众的“情感空窗”。母女之间阴阳两隔的遗憾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频繁发生着,怀旧、欢笑、反省与感动也因此成为大多数人对这类影片的共同期待。《你好,李焕英》把握娱乐与情感的平衡点,扎根于女性本体,陈述真挚的母女亲情,贴合受众的情感诉求,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