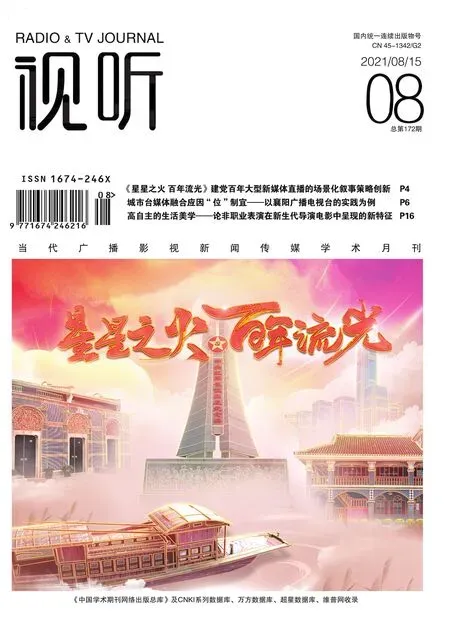《我的姐姐》:知雄守雌的新女性主义叙事策略探究
2021-01-30于永亮
于永亮
从十一年前《唐山大地震》中的幼年姐姐方登到今天《我的姐姐》中的成年姐姐安然,同一个小姐姐张子枫,却让观众对“姐姐”这个词有了更具现实意义的思考。影片《我的姐姐》透视了当下“好”字式中国二胎家庭中的隐性亲情困境,同时也反思了较大年龄差之下仅靠血缘维系而缺乏情感联结的兄弟姐妹情。一提到影视剧中的“姐姐”,许多人也许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欢乐颂》中的樊胜美,《安家》中的房似锦,甚至《都挺好》中的苏明玉等一系列的女性影视形象。而《我的姐姐》这部影片意不在塑造另一个“扶弟魔”形象,其更具突破性的意义则在于让“姐姐”这一被长久忽视的女性群体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荧幕发声,使“姐姐”这一女性家庭身份作为一种显眼的性别身份文化越出以往的女性群像。这部影片女性叙事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以“她者”来叙“她者”的类真实书写(导演、编剧皆为女性),更重要的是将女性叙事的目光从单纯聚焦女性独立困境延伸至两性合作困境。
一、鲜被定义的女性叙事形象
学者何雪平在对范俭的女性纪录片进行叙事研究之后,将镜头叙事下的现代女性形象归类为——传统的“地母”形象、男性化的女性形象、反抗父权制的女性形象以及“双性同体”的女性形象①。传统影像叙事话语常从角色为母、为妻、为女的身份入手来呈现人物形象,少有对“姐姐”这一特殊的女性身份和特别的女性群体进行专门的形象塑造与诠释。当年轻女性乐于被人称为“小姐姐”而非小姐,当《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三十而丽”的口号掀起一股“姐文化”热,带动网络“姐学”的兴起,“姐姐”这一词语就已经走出了女性家庭身份的范畴,彰显出一种更加成熟自信、更具时代感的女性气质。这种被社会女性主义潮流所赋予的新女性形象与气质或许可以给予年轻男性特殊的亲切感,抑或使更多男性敬而远之甚至望而生畏。但不管怎样,“姐姐”一词早已不再只是代表女性年龄身份的一种单纯的性别象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姐姐”一词似乎本身就带有一种自我书写的叙事风格。
影片《我的姐姐》中,对于同样作为具有“姐姐”这层身份命运的女性,安然与姑妈各自为观众展现了她们对“姐姐”这重身份的不同理解。笃信“生而为姐”就该无限牺牲自我的姑妈,在自己女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质问中依然故我地对已逝的弟弟行使着作为姐姐未尽的职责;而安然则带着对自己作为姐姐这层身份的嫌恶,在长辈们以“长姐如母”的道德施压下毫不客气地喊出“我跟他(指弟弟)不熟!”的拒养宣言。同样是姐姐,同样是被牺牲的女儿和女性,安然显然已经突破了身份枷锁宣誓了自己的主体性。影片中姑妈与安然吃西瓜时的对话,通过一段正反打镜头的切换让观众以一个姐姐的眼睛去一窥另一个姐姐的内心。姑妈作为一个叙述者让观众和安然一同了解到她令人心疼的过去以及她被传统规训的“姐使命”。当镜头越过姑妈的肩头聚焦到安然留下沉默泪水的脸庞,能够透过姑妈的视角看到一种被理解的长大,体会到一种只有姐姐们之间才会产生的共鸣与共情。当姑妈只能擦拭着套娃低语俄文,在片刻的回忆中抚摸昔日的“伤疤”时,安然早已开始对过去释然,想要拼尽全力去夺回自己曾经被篡改的命运。同为姐姐,姑妈选择无条件的付出与无下限的忍让,而安然却用自己的独立精神去影响弟弟,从教会他自己系鞋带、用筷子开始,并告诉他:“能靠住的只有你自己。”我们没有必要褒此抑彼,因为我们不能忽视沃霍尔在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中所提出的“未叙述事件”的背景意义。年龄相差不大的姑妈与父亲,相差十八岁的安然姐弟,他们的亲情相处模式必然是大相径庭。所以不管是牺牲自我还是追寻自我,最终都是“姐姐”们自己的选择。现实中会有安然那样看似决绝的姐姐,也会有父母健在却主动将小自己18岁的自闭症弟弟带在身边工作的姐姐②。片中的“姐姐”不只安然和姑妈,安然的妈妈,姑妈的女儿,还有高龄子痫产妇的两个幼小女儿,她们都是弟弟们的姐姐。她们都有着无法选择的身份与命运,但却未必会有相同的选择。
影片开头便是姐弟突丧考妣,这样的戏剧性变故使得片中的主人公被迫正视早已存在的手足情感缺失,并促使安然不得不去领受作为姐姐的这层身份与责任。奥地利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提醒我们:“出生顺位会在个人的生活方式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长中的每一道难题都是源于家庭内竞争的存在和合作的缺失。”而“生理缺陷、溺爱和忽视这三种儿童成长期的情形,都很可能导致当事者对生命的意义做出错误的解读。”③片中弟弟懵懂却自信地叫嚷着:“爸爸说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而安然却在父母墓碑前吐露只想得到一句“我的女儿也还不错”的认可。作为“被忽视者”和“被溺爱者”,安然和弟弟一味地竞争而缺乏应有的合作,各自错误地解读了生命的意义。这其中姐姐和弟弟,男性与女性谁又不是受害者?在常规的女性叙事中,女性被宰割的形象被显化甚至放大了,而男性被剥夺独立自我的成长能力缺失却被弱化了。正是这种潜在的女性叙事话语,让人们容易忽视那些心理晚熟的男性群体在同性竞争压力的挤压下渴望得到“姐姐”式的女性关怀与依靠,甚至他们内心深处如弟弟安子恒一般发出低声恳求:“姐姐,你等等我好不好?”也许女性社会角色中更深层的“姐力量”被许多苦情叙事或悲愤诉说掩盖了,当波伏娃的“第二性”理论为女性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利,一些越来越强的女性却容易走向一种两性割裂的自我偏执与极端。因此女性叙事中的“姐姐”形象,不应该只是一种被同情、被关注的女性身份,她更多地彰显出一种女性的韧度与可依靠的力量,一种可以自我依靠,也可以带给男性依靠的柔性力量。正如影片中所暗示的那样,一味为弟弟牺牲的姑妈们曾经使弟弟们心安,而成长起来的安然们却更愿扶持弟弟走向真正的独立。所以“姐姐”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但她们的形象却应该是有别于“妈妈”和“女儿”的更坚韧、更可依靠的或者想被依靠的形象。
二、女性叙事下的两性视角聚焦
国内学者申丹将我国多数学者对女性主义叙事的理论认知概括为——“主要是从女性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去表达和呈现女性的女性意识觉醒,以及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有女性的性别权威等。‘女性叙事’是女性对自身故事、命运的叙事,是创作者从女性主义视域出发,表述对世界关系认知、体验、情感以及价值等,且更具深层情感力量和诗意氛围的一种叙事。”④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创始人之一苏珊·兰瑟在其女性叙事代表作《虚构的权威》中强调了“站在女性的立场为女性说话”这一核心的理念。但某些女性叙事影片也许对此用力过度,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偏信则暗”的抵触,甚至将女性主义叙事拖入被污名化的危险。在对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的反思与探索中,电影的女性叙事试图穿越“看”与“被看”的影像叙事藩篱,从男性凝视中的女性觉醒,到凝视与反凝视中的女性呐喊,逐渐从激进的“争权”叙事思维进入到一个相对理性的自我反思阶段,从而探寻着一种超脱二元对立的“两性合作”叙事模式。笔者以为,好的女性叙事影片,应该是可以激起两性共鸣的。《我的姐姐》不但聚焦了以“姐姐”们为代表的女性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同时也没有放弃透过弟弟的成长颠簸和舅舅的失意人生所展现出的男性关怀。同为“弟弟”,舅舅也许未必从小就渣,而弟弟安子恒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出“求送养”的懂事举动的。他们一个不曾忘记姐姐的恩情,一个渴望得到姐姐的爱护;一个是人到中年游手好闲的“老男孩”,而另一个是主客观同一的真正小男孩;一个早已成年却在姐姐撒手人寰后“来不及长大”,而另一个在与姐姐相依为命的“斗智斗勇”中练习长大。
影片中的舅舅是一个没长大的弟弟、不负责任的父亲,但他最后依然得到了安然情感上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仅体现在安然一句“我希望你是我爸爸”的台词上。舅舅与安然三组典型的镜头站位,可以让观众在不自觉中感知这一被认可的过程。第一次是在安然新搬进的学区房内,舅舅一直坐在沙发里怂恿安然去诉讼求偿,而安然则一直站立着甚至背对着舅舅忙着晾晒衣服。这样的高低站位营造,再加上二人的对话内容,很容易让人感知舅舅在安然心中的地位以及安然对他的不屑。第二次交谈是在安然参加完舅舅女儿可可的婚礼之后,交还给舅舅相机并与之对桌而坐,此时的正、反打镜头已采用水平视角,对话的内容也恰好是舅舅对自己没能成为一位好父亲的忏悔。此时的他不再油嘴滑舌耍小聪明,而是与眼前这位外甥女以朋友的姿态敞开心扉,追悔人生。安然此刻也对这位舅舅的感情发生了转变,至少知道他确有一颗成为好爸爸的心,于是给到的站位是二人在同一水平位置。第三次舅甥对话是在墓地,安然在父母墓前倾吐完心声并撕碎象征其心结的假残疾证明之后,在走廊避雨时遇到了每月都来看望已故姐姐的舅舅。此时二人均为站立姿势,角色原本的生理身高再加上给到靠前的近景镜头,使舅舅这个人物形象第一次在安然面前清晰而高大起来。于是当安然说出“有时觉得你是爸爸。也不是,是希望你是我爸爸”这样的话时就能让人更多了几分理解。
无疑,影片对于舅舅这个角色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一富有层次感的男性人物也许才是片中那个真正需要被关怀和关注的“弟弟”。此外,影片中“皮衣”和“肉包子”的叙事隐喻,也能让观众感受到安然对于父爱、母爱深藏的渴望。尤其是安然对于皮衣的留与弃,对于肉包子的出神回忆,类似细腻的女性叙事手法或多或少都能让人感受到独立女性所刻意压抑的那种被爱的渴望。从这些变换的叙事视角来看,《我的姐姐》这一影片不能简单地用苏珊·兰瑟所谓的有意讲述自己的、或自身群体故事的“个人型声音”或“集体型声音”来区分其内在的叙事者,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将这种叙事话语视为一种“两性变奏的声音”。
三、女性书写下的男性成长关照
与其说《我的姐姐》是一部关注女性成长与自我救赎的影片,不如说这是一种促进男性自我再认知与探索两性合作的叙事尝试。成功的女性叙事不应只停留在唤醒女性自我意识、凸显女性主体权威上,“她”还应该具有唤醒男性“自我再认知”的作用。“女性叙事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的发展,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有男性对自我身份和性别的重新认知。女性叙事能够让男性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性别和社会角色,甚至给男性带去危机感。以往的男性性别优越感被焦虑感所取代,男性开始意识到女性地位和角色的变化,同时也面临着男性可能沦为‘弱势’群体的这一现实。”⑤发展心理学认为,女性较男性普遍获得生理与心理的早熟,而当今所谓的“姐文化”似乎也是对这种两性身心发展不平衡的外化,女性也常因此不自觉地担负起某种“姐角色”。与之相反,男性的晚熟被他们的性别强势所掩盖,当人生起步阶段的“落后者”成年后却被瞬间要求去战胜甚至驾驭曾经的“领先者”,许多措手不及的成年男性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就在同性竞争的高强压力下带上了“男性枷锁”。在世俗的男性成功标准面前他们似乎无路可退,纵使一生辉煌如“公民凯恩”也无法放下心中的那个“rose bud”。
影片中三个典型的男性角色——失去双亲的年幼弟弟、刚成年不久的安然男友以及人到中年一事无成的舅舅,这三人的表现让观众看到了女性独立与男性成长的交织。弟弟安子恒在影片开始48分钟后才在崩溃大哭的寻找中喊出“姐姐”两个字。他几次对姐姐的呼唤,从情急之下寻找母亲替代者的自发式呼唤,到与竞争者妥协的哀求式呼唤,再到不忍姐姐为难的理解式呼唤,直到最后自我牺牲的成全式呼唤——这种对姐姐不断呼唤的过程加速了弟弟的成长,也暗示了女性力量对男性内在“小男孩”的成长助推。弟弟可以对身为女性的姐姐放声呼唤、真实表达,但成年后的舅舅和安然男友却并不能,因为那很可能被视为一种软弱无能的非男性化表现。
女性主义叙事先驱罗宾·沃霍尔曾提出以“女人气”为术语取代性、社会性别这两大术语,从而取消男人女人的性别区分模式。而“所谓‘女人气’是指那些具有女性气质的人们,无论男人、女人抑或是同性恋人群,只要在举止行为方面体现了性别文化中女性气质特点的都可以称之为‘女人气’。”⑥这一反二元对立和生理决定论特性的理论词汇,对于电影女性叙事的多元包容性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无疑在舅舅、男友、甚至那位肇事司机身上都能看到这种被隐藏的“女人气”。混在老人堆里“学跳舞”的“渣爹”舅舅不时暴露出他爱女的可爱一面,有些妈宝的男友看似软弱却总能在安然身边温情守护,感到良心有愧的司机在与安然的争执中忍让克制,还出于同情帮助安然解决弟弟的领养问题。他们的“女人气”使其看起来沦为“弱者”,但这也释放着他们内心深处渴望被正视、被理解的善良信号。成年后的女性在与男性竞争中被允许落后和失败,但男性却似乎被剥夺了这种权利。当女性主义兴起后男性的“阉割焦虑”与失败恐惧便与日俱增,于是有人把“女权”视为“女拳”并还以拳,通过靶向攻击来释放内心的压力与恐惧。因此高明的女性主义影像叙事更应该对这种男性的“女人气”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并使之得到合理释放的空间,从而多一层对男性精神成长的真诚关照。
四、知雄守雌的两性互进叙事
当脱口秀女演员杨笠被指为“女拳”代言甚至挑起性别政治,“普却信”的调侃听起来似乎不再搞笑;当江西九江的“彩礼贷”饱受舆论诟病,揭露出某些地区经年累月的婚俗沉疴与日益失调的男女比例;当民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出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与再创新低的结婚率,继续沉浸在“男权”与“女权”的话语争斗中似乎就显得不合时宜且没有意义。女性叙事的创作者或研究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父权社会也好,还是当代的多元社会也好,都不存在一种力量能够把一个人突然变成某种性别气质。性别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找到这个过程并描述它,才能客观、生动地展示社会对性别气质的界定与传播途径,才能真实地看到性别气质在不同时代、环境中如何延续、变化、再延续,如何在人们的身体行为方面产生影响,从而才有可能进行有意识的修正,这正是女性主义批评者性别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⑦新一代的女性叙事者担负着重塑两性文化的责任,因此应更具多元包容性。不为了宣扬“女性权利”和“女性独立”而滑向冷漠与偏执,也是新女性叙事需要具备的一种理性态度。女性可以追求自我,但也不应该只有自我。影片中的安然承认自己并不讨厌弟弟,只是与他太过陌生,虽然在她被迫装瘸等一系列闪回出现之前,观众也许会指责她太过无情,但她还是在洗澡时无法回避被弟弟无助的呼喊所唤醒的“姐性”甚至是母性。后来安然在全力备战考研的间隙去看望被舅舅暂养的弟弟,当看到弟弟受舅舅恶习浸染的学坏模样,瞬间的情绪爆发让她无意中诠释了影片开头长辈们口中的那句“长姐如母”,因为只有母亲才会有那种“孟母三迁”的愤怒。看似姐姐在照顾弟弟,但却是弟弟唤醒了姐姐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让她没有因为当初父母的不公与残忍而被恨意继续裹挟。也正是她在心里接纳了弟弟之后才敢于正视自己的内心,进而对死去的父母忏悔并与自己和解。影片中姐弟俩在一起时的行走位置不断变化暗示着姐弟关系的转变。从一开始弟弟有点胆怯地跟在姐姐身后到爬上姐姐的后背,再到最后姐姐从舅舅处领回弟弟时二人手牵手并行的画面,这种从“跟着走”到“背着走”再到“并排走”的变化既显示了二人的亲情增进,也暗示了一种成长的共进。姐姐教会弟弟系鞋带、用筷子,弟弟让姐姐学会了蒸包子,这些生活细节的展示让我们在感受到温情的同时也隐约觉察到到二人成长的相互促进。
反观片中安然与男友的相处直到分手,则可以看作是一种两性共进的失败。男友笃定他们不会分手的原因是二人天然的“互补性”,他甚至说不敢想象安然如果跟一个与她性格相同的男生在一起会不会受欺负。安然的独立、坚强有主见,男友的温驯、随和向母性,在两性关系中这也许不失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气质拼插关系。但原生家庭的经历加上不屈的个人奋斗经历,使得姐姐安然已经逐步成长为一块趋近完整的拼图。虽然年纪尚轻,但她已对许多事(除了眼下这个令人棘手的弟弟)能够“处之坦然”。她的独立代表的是一种成长中的相对彻底的当代女性独立,她需要的是与另一半构建一幅崭新的图景,而不只是做一种简单的“拼插”。但片中这个与她在一起五年的男友并没有做好与之共同再成长的准备,这也许代表了当今社会部分男性对这种新女性主义思维的不理解,甚至是歪曲解读。反观安然这块“带刺”的拼图,面对表姐的误解、同事的冷嘲、司机的自辩,她都以强硬回击——出手打人、大声质问甚至不顾看客的拍摄依然叫嚣。观众被带入她的视角来解读这些行为自然可以接受,但如果单纯地作为局外人来看,安然的自我封闭和过度自我保护让她有时显得不可理喻。她忽略了男友对自己的感化与保护,致使她无法停下来“等”他。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一书中指出,一切人生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三类主题中:职业、社会与性。其所对应的人类追求,即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他人建立良好连接以及对美好两性情感的追求。本片中的安然似乎执着于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对后两种人生价值的体验。这样的女性独立大概不能真正地实现女性幸福,所以像安然这样的极端个体形象似乎也在启示人们去思考所谓“女性独立”与“女性幸福”的关系。女性的确需要追求独立,她们当然有权利追求独立,但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条件和能力的。与其一味鼓吹所谓的“女性独立”,不如帮助她们认清自我与现实,通过探寻两性和谐共进的叙事传播模式,来使女性得到某种心理自适与精神自如。
五、结语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开宗明义:“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深知什么是雄强,却能安守雌柔的地位——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一种阴阳调和的智慧。从前的女性叙事常在试图打破“雄强”的努力中遗忘了“雌柔”的力量。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独立离不开男性的理解,男性的成长亦需要女性的扶持。优秀的新女性影像叙事必然会超脱两性的二元对立,以“两性共进”的叙事话语来观照人类不可回避的“三大人生主题”。在这方面,《我的姐姐》呈现了一类特殊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开启了一种新的女性叙事思维。影片最后为开放式结局,如果姐姐最终没有放弃弟弟,希望不是因为“我是姐姐”,而是因为“我想成为姐姐”。
注释:
①⑤何雪平.范俭纪录片的女性叙事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9.
②22岁姐姐带4岁孤独症弟弟上班:常被误会[N].今日女报,2021-03-18(001).
③[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王晋华译.天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2017:15,134.
④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136-146.
⑥⑦孙桂芝.罗宾·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