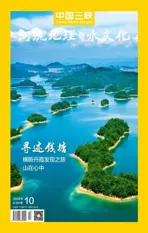钱塘苏小是乡亲
2021-01-30胡亮编辑任红
◎ 文 | 胡亮 编辑 | 任红

西湖夏荷 摄影/图虫创意
1
乾隆十九年春,郑板桥应吴作哲之邀,前往杭州作书作画。后者时任杭州太守,对郑板桥甚为礼遇。在杭州期间,郑板桥曾三次游览西湖,后来他还去往湖州,可能过了端午才回到扬州。
大概就在这年夏秋,郑板桥给杭州朋友杭世骏写信,说他曾在杭州打听苏小小墓,“皆云西泠桥畔是其埋玉处也”,却没有找到,遂想起“禾郡至今有苏小坟”,就怀疑苏小小或葬于钱塘,未必即在西湖之畔。这个杭世骏是诗人、画家,也是大学者,此前二十多年曾主持编修《浙江通志》之《经籍志》。
也许板桥觉得向一位学者咨问一座歌伎的墓有点唐突,于是稍稍辩护,“虽闾巷琐事,大雅所不屑道,在名士风流,未尝不深考也”。这个辩护值得玩味:所谓大雅,可能指向庙堂秩序,在这样的秩序里,苏小小几乎可以让人轻易获得伦理的制高点;然大雅亦非绝对之物,在其扦格不通人性之处,必定有裂隙。
2
关于苏小小,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徐陵一生由梁入陈,曾与庾肩吾、庾信父子出入于南梁太子萧纲东宫。为给梁元帝徐妃解闷,他花费很大精力选录艳歌,得东周至南梁共679 篇,编成《玉台新咏》。清吴兆宜曾为之作注。就在吴兆宜注本的第十卷,收有一首《钱唐苏小歌》。
钱唐是杭州古称,唐代为避讳,改为“钱塘”,此诗改题作《钱塘苏小歌》。后来此诗还见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第八十五卷,改题作《苏小小歌》。
郭茂倩是乐府诗的大选家,对每首乐府诗都写了“题解”,以“征引浩博,援据精审”著称。郭茂倩为《苏小小歌》所写题解就有征引《乐府广题》,“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西陵在钱塘江之西,歌云‘西陵松柏下’是也”,只有珍贵的三十个字。由此推知苏小小生活的时代——南齐与徐陵生活的梁陈时代相去不远。
苏小小夭亡后,历来都说葬于西湖之畔,今天可在西泠桥头见到2004 年再次重修的“钱塘苏小小之墓”。这座墓,李贺必曾亲见;据说徐渭亦曾得见;到郑板桥1754 年游杭州,已然遍寻不见。沈复《浮生六记》写到,“苏小墓在西泠桥侧,土人指示,初仅半丘黄土而已”。可是后来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780 年乾隆南巡,向地方询及此事,到1784 年乾隆再次南巡,“则苏小墓已石筑,其坟作八角形”,甚为精致。
这座为迎合皇帝而重修的苏小小墓也经不起时间的消磨,到了晚清,招招舟子见到的已然另是一番萧条之景,“考其墓址,寔在西泠桥畔。石柱欲圮,户坏略封。凄凉埋玉之乡,惆怅销金之窟”。
继招招舟子后,1917 年6 月13 日,郁达夫还曾月夜访此墓。
3
关于苏小小的历史性记载极少,以至这个文化符号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等待填充与重写。所以愈趋晚近的苏小小,则获得了愈完整的形象。有意思的是,这种文学性重写的成果,从唐诗,到宋话本、传奇,到宋金词,到元散曲、杂剧,到明清小品、小说,到清诗词、诗话、尺牍和笔记,再到现代散文、新诗,完整地践行了唐以后文体演变史。苏小小这个形象以其复杂,满足着不同的时代、作者和读者。
以唐而论,就有包括白居易在内的十余位诗人加入到这个重写的雅集,文体则涉及杂言、五言和七言,乐府、绝句和律诗,形成了一个秘响旁通的韵文家族。到杨维桢出来,借鉴西蜀竹枝词,倡写西湖竹枝词,元以降,唱和者达数百人之多,每有咏及苏小小,则形成了一个前呼后应的拟民谣家族。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文体不断推陈出新的重写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双向拟写的奇妙现象:后人取法苏小小,仿写南朝风格的拟乐府;而被后人反复塑造的苏小小,则不断起用南齐之后的各种新诗律。在若干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里面:宋人教会苏小小吟唱唐代教坊曲,而清人则已经教会她试写近体诗。
不管文体如何演变,历代诗人和作家大多将《钱唐苏小歌》或《苏小小歌》作为最重要、最原始的“输出者”(Transmitter)。在关于两个苏小小的叙事性重写里,曾先后出现三个编码系统:苏小小鬼魂与司马槱;苏小小姊妹与赵氏兄弟;苏小小与阮郁、鲍仁、孟浪。这三个编码系统都具有很高的自足性,互不交叉。其中第二个编码系统指向北宋苏小小,其上游文本当是《武林旧事》,下游文本则是凌濛初的拟话本《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可能凌亦认为这个苏小小不当与南齐苏小小相混,故更名为苏小娟,其姊则仍名苏盼奴。其余两个编码系统则指向南齐苏小小。苏小小与阮郁、鲍仁、孟浪,似乎仅见于白话小说《西泠韵迹》,这个小说虽然晚出,也已成为上游文本,被今之越剧和电影多次采用。苏小小鬼魂与司马槱,最早可能见于宋人李宪民《云斋广录》所录《钱塘异梦》,后来被反复袭用、改篡或演绎,最终形成了支河纵横、波光潋滟的下游文本流域。

苏小小图 供图/文化传媒/FOTOE
4
目今有两个原型诗:吴兆宜注本《钱唐苏小歌》,郭茂倩选本《苏小小歌》。此诗是苏小小的亲笔,还是南齐文人的代笔,今已难以查考。古代学者尤倾向于是苏小小的亲笔。先来看《钱唐苏小歌》,“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再来看《苏小小歌》,“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郭茂倩所见抄本或刻本,至少比吴兆宜所见早五百年,也许更接近徐陵祖本。

苏小小墓 摄影/东方IC
不管是吴兆宜注本,还是郭茂倩选本,“油壁车”、“青骢马”均已醒目出现。
据吴兆宜所引《齐高帝诸子传》,“陛下乘油壁车入宫”,可知油壁车绝非寻常之物。苏小小不过一倡女,居然也乘油壁车。后来《西泠韵迹》的作者出来打圆场,说苏小小虑及“男子往来,可以乘骑,我一个少年女儿,却蹙金莲于何处”,遂叫人打造香车,还填了《临江仙》描摹油壁车的形状,“毡里绿云四壁,幔垂白月当门。雕兰凿桂以为轮,舟行非桨力,马走没蹄痕”。这个小说作者内心或有胆大设想:这个油壁车,天子坐得,苏小小也坐得。
另一个道具——青骢马是指青毛与白毛相间的马。如果说油壁车意味着迎送,那么青骢马则意味着来往。两者关系看似协调,实则紧张之至。后来无数作品都沿用这对堪称经典的道具,让爱情的悲剧彻响着油壁车的轮声,以及青骢马的蹄音。
《苏小小歌》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意象,即“西陵松柏”。西陵泛指西陵桥一带,西陵桥则横架于孤山与苏堤。据周密记载:西陵桥,又名西林桥、西泠桥。苏小小为何选择的恰恰是西陵?陵者,高丘大墓也,指向生命的归宿地。松柏,则以其有森森之态,向来为陵的伴生植物。元人张可久《黄钟·人月圆》有“笙歌苏小楼前路……孤坟梅影,半岭松声”之句,朱彝尊《梅花引·苏小小墓》亦有“小小坟前松柏声”之句,均将坟墓与松柏并置,亦可佐证前述猜想。这套意象,越是细读,越是生出一种诡异的凄凉,潜含着一个相见、相别、相思乃至人鬼殊途的故事。

西湖美景 摄影/东方IC
5
《苏小小歌》的好,见证着苏小小的好。《钱塘异梦》和《西泠韵迹》据此发挥,后者说苏小小“更有一种妙处:又不曾从师受学,谁知天性聪明,信口吐辞,皆成佳句”,前者则叙及苏小小鬼魂吟唱自己填写的半阕《蝶恋花》。
除了才华,后世之发挥,还包括有貌、有情、有识三端。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之二十:“何处春深好,春深伎女家。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兰麝熏行被,金铜钉坐车。杭州苏小小,人道最夭斜。”苏小小眉毛比杨柳叶漂亮,罗裙让石榴花嫉妒,同于张祜《题苏小小墓》句“脸浓花自发,眉恨柳长深”,亦同于徐渭《拟吊苏小小墓》句“绣口花腮烂舞衣”。皆取譬于花木,乃是承袭《诗经》传统。
李贺《苏小小墓》前两句,“幽兰露,如啼眼”,不再是取譬于花木,而是托身于花木,不妨称为《楚辞》传统。后来袁宏道学步李贺,其《西陵桥》有句“莺如衫,燕如钗”:“燕如钗”尚能出新,“莺如衫”已然离奇,远不如李贺来得妥帖传神。
到叙事性重写文本,比如《西泠韵迹》,就有“远望如晓风杨柳,近对如初日芙蓉”、“望影花娇柳媚,闻声玉软香温”、“碎剪名花为貌,细揉嫩柳成腰”之句,均不过是《诗经》传统的不肖之效,而另如“姿容如画”、“色貌绝伦”,与《钱塘异梦》“翠冠珠耳,玉佩罗裙”,早就已经落入俗套。
苏小小之有情,则见于白居易之《杨柳枝词》八首之五之六,“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唐胜馆娃。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白居易对苏小小最深的认知,就是“多情”、“别有情”,——情者,情态情致情调之谓也,并非专指情感。
苏小小之有识,主要体现为怜才,见于小说《西泠韵迹》。鲍仁萧然一身,得遇苏小小,苏小小当即主动搭话,随后如是说来,“今睹先生之丰仪,必大魁天下,欲借先生之功名,为妾一验”。两人投契,苏小小遂邀请鲍仁同返镜阁对饮,鲍仁自恨眉低气短,乃主动请辞,苏小小随后取两封白物送别鲍仁。后鲍仁果得功名,官至滑州刺史,奈何苏小小已奄然而逝。鲍仁常有而苏小小不常有。历代困蹇文人,每因不遇自己的苏小小而心生怅惘,就连迟至郁达夫,也曾写出“苏小委尘红拂死,谁家儿女解怜才”之句。
6
白居易早年耿介,中年风流,晚年安闲,虽然曾贬谪江州,人生种种亦算得如意。这就决定了白居易对待苏小小的态度,只能是湖山之补缀,而绝非心灵之萦牵。《杭州春望》有句,“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余杭形胜》有句,“梦儿亭古传名谢,教伎楼新道姓苏”,不过是将苏小小拉来,凑成一联而已。白居易与李绅生卒同年,他异于李绅处在于,将苏小小当成一位芳邻来写,却从来不涉及苏小小的死与墓。
唐代还有两个参差同时的诗人——韩翃和柳中庸,都生活在大历年间,他们曾分别写下《送王少府归杭州》和《幽院早春》,稍晚杜牧亦写下《悲吴王城》,这三首诗都有牵涉苏小小,但是情况与白居易差不多,代入自身较少。
至于白居易《闻歌伎唱严郎中诗因以绝句寄之》,“但是人家有遗爱,就中苏小感恩多”,以及刘禹锡对白居易《杭州春望》的和诗《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诗有柳色春藏苏小家之句因而戏酬兼寄浙东元相公》,“女伎还闻名小小,使君谁许唤卿卿”,均已将苏小小作为朋友之间的调侃之词:白居易调侃他的前任严维,却又被他的朋友刘禹锡反调侃。这种戏酬无非将苏小小作为代词,与苏小小已无关系。却对后世(特别是元曲)产生了意外的影响,以张可久《中吕·上小楼》、曾瑞《中吕·红绣鞋》为例,无非借来苏小小、张好好、许盼盼之类名目自写其意而已。
7

西湖落日 摄影/图虫创意
张祜《苏小歌》三首用苏小小口吻写来,其一:“车轮不可遮,马足不可绊。长怨十字街,使郎心四散。”其二:“新人千里去,故人千里来。剪刀横眼底,方觉泪难裁。”其三:“登山不愁峻,涉海不愁深。中劈庭前枣,教郎见赤心。”这组小诗,无论具象还是情感,都可视为《苏小小歌》的下游,不避重字重句,设喻古拙,造语朴直,颇有古乐府之风,即便与后者并置为四首,亦无不妥。张祜另有《题苏小小墓》,已是中规中矩的文人诗,字句拘谨,意境平凡,反而不如前三首来得真率。
而最引人瞩目的死亡抒情,仍然是李贺,且看他的千古绝唱《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这首鬼诗意象转个不停,氛围却始终寒峭。乍看无不是写西陵之坞,细读无不是写苏小小。苏小小的泪眼、衣物、用具已经散见于墓畔每一处花木,甚至每一处山水。诗人之心与苏小小之心早已合律,两者之生命相互镶错。
而此种生命与写作的高度同构,则有可能导致诗人之死。据《新唐书》记载,李贺“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每日旦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母亲的担心并非多余,他后来只活到二十六岁,比苏小小仅多七岁。李贺另有《七夕》,写及男女聚散,直呼情人为“苏小小”,则已为后人留下更加宽阔的造梦空间。
比李贺稍晚的李商隐,怀才孤独,其《汴上送李郢之苏州》有句“苏小小坟今在否,紫兰香径与招魂”,就已经潜含人鬼恋情结(complex)。紧接着就到了宋代,以苏小小为女主角的人鬼恋故事忽而大为流行,《钱塘异梦》可视为滥觞。
8
《西泠韵迹》实是三个独立故事的拼盘。小说重点设计了三个男性主角——阮郁、孟浪、鲍仁,分别代表青春、权力、才华。苏小小就像一位冒险家,通过让渡部分女权,试图获得更大的女权。纳兰容若对此感到困惑,《卜算子·新柳》才有“苏小门前长短条,即渐迷行处”的茫然之感。很显然,龚自珍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热衷于“屠狗功名”和“雕龙文章”,所以在《湘月》词里尴尬自嘲,“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苏小小轻易就解除了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支配,对社会强加的性别充满了戒备和怀疑。当然这是对历史人物苏小小的绝对虚构。
若说历史上真有女权主义先驱,袁枚当算一位。他刻一闲印——“钱塘苏小是乡亲”,用的正是韩翃《送王少府归杭州》中的半联。某尚书过访南京,向袁枚索取诗集,后者并未深思,就加盖此印,哪知这个尚书竟对袁枚大加斥责。袁枚开始还道歉,后来难忍絮烦,就正色道:“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 历史完美地兑现了袁枚的预瞻。无数文人参与了对这个女性人格的想象和设计,成全了一种才貌情识并重的十九岁的绝对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