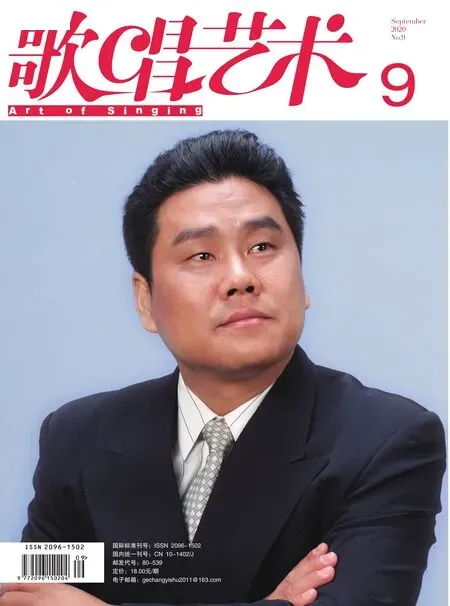一生求索的杨鸿年
2021-01-29阎宝林
阎宝林
一项事业,需要胸怀格局,更需要鼎力实干;一项工程,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通透实施;一位学者,需要思维前瞻,更需要行为始终。杨鸿年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不断求索的学者型指挥家,倾其一生从事合唱与指挥专业的教学、研究与表演,无论是广义的社会教育还是狭义的校园教育,对中国合唱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在合唱教学、合唱指挥、合唱理论和合唱创编等诸多方面的贡献和深入探研,在我们近二十多年频繁的接触中,姑且不论成就之高,仅从生活的细节来看就写满了勤奋、惜时、坚毅……
近一年半来,早知杨先生身患多疾,数次出差赴京欲往探望,而重症监护病房多有不便,只得屡次以电话问询关注病情。特别是2019年8月8日在国家大剧院的“八秒十载”专场演出,我与前来捧场的杨先生之子杨力教授交流,得知病情得到相对控制,欣慰之余,总觉得先生会像以往那样,治疗一段时间就会好转。于是,近来忙于书稿,少有问许。时至2020年7月26日下午,朋友圈里突然传出杨先生仙逝的噩耗,无以言表之痛,直至后背之凉!连日来,脑海中各类往事似过电影般地不断涌现,唯叹逝者已去不能还。纵观杨先生的一生,成功者的成功并非偶然,透过众所周知的许多报道和频繁转发的网络信息,在回忆的点滴中,不难发现这位前辈铸就辉煌的必然。受《歌唱艺术》之邀,将往事细节梳理撰文以表哀思。
善于思考好学的人
杨鸿年先生之所以在合唱指挥、合唱教学、合唱理论和合唱创编等多方面做出杰出的成就,重在始终拥有善于思考、取百家之长、勤于笔耕的秉性。
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从报刊上知道“杨鸿年”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国际上屡获大奖,90年代因一家音乐刊物刊登了一篇我的专访,同期亦有杨先生的介绍,于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曾有电话请教。随着2000—2003年对国内外合唱的比较反思和教学中的排演初探,2004年的德国之行我们终于有了近距离交流的机会。接触中,很快发现杨先生思维敏捷、善于捕捉各种信息为从事的工作服务,即便是聊天、就餐、观景,也少不了与专业的联系和反思,由此亦坚定了我用国际化音乐语言讲民族故事的信念。记得2004年5月间,我们曾就我2000年撰写的论文《从十位作曲家的创作特征认识巴洛克时期的合唱风格》中关于演唱的颗粒状问题交谈了许久。现在查看当时的记录,杨先生认为,“颗粒状的演唱并非是巴洛克时期才形成的音乐特征,而是早期宗教音乐受古希腊语感多为断开的影响,巴洛克时期只是更加明显”。这一特征在西欧传统音乐上继承较准确的是德国、波兰、奥地利三国,法国有些异化,而美国音乐则是欧洲传统音乐的“二手货”,在传统音乐准确的定位上当然有一定的影响。他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反思,也激活了我的课题“合唱在史学、文化交流及视觉艺术中的深层意义”的积极申报!与善思考者接触,一定会启迪思维的活跃和深究的兴趣。
日本音乐教育家斋藤秀雄所著的《指挥法教程》(1995年版)一书是由我的启蒙老师刘大冬与王少军先生合译,曾一度脱销。因研究急需,杨先生请我复印成册寄去,之后因为一个图示、一个和弦,他会叫略通日文的我校对原文。记得有关第67页的指挥图示中“分割”(ぶんかつ)一词,我们进行过深入地讨论。该词作为他动词“ぶんかつする”时,在日语中具有割裂、分离、断开之意,常用于领土不能分割、岔路口路标示等。到了指挥的挥拍技术中,如果机械地理解成“节拍分割”就非常令人费解。与杨先生商讨后,觉得“分割”在本书中应合乎释义,灵活译为“分拍”更准确。一个小小的单词却能发现杨先生研读中的精细,令人着实佩服。
“八秒”合唱团三度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前两次杨先生光临观看,并在演出结束后登台与“八秒”们亲切交谈。2019年8月8日,即使重病在身,昏沉中还叮嘱杨力教授亲临。
2015年与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现北京爱乐合唱团)等联合演出“徐坚强无伴奏合唱作品专场音乐会”,最后由我指挥返场曲目时,深刻体会到“杨团”手下的孩子们对指挥手势的快速反应、扎实的音乐基本功和声音的穿透力,足见其训练的功力。次日的座谈会上,他对“八秒”为微电影《蓝柳》演绎的无伴奏合唱现场配乐赞赏有加,还特别提到《归园田居》第46—56小节的精致处理。杨先生就是这样,赞扬和批评一定是有依据的。正因为他思考后的提示,不仅使人很快就明确该坚持与反思的具体细节,同时面对他的认真与研究,也激发了对方继续探究的学习兴趣。人生难识是自身,在我与杨先生的交流中,明确要保持和放弃的方面,是难得的收获!

十余年来,作者与杨鸿年共同参加国内外专业赛事和学术活动合影
“八秒”早期曾演唱过一首德文作品《群鸟飞翔》(Starenflug),乐谱是2000年一位法国指挥家赠予我的。杨先生偶然听到“八秒”演唱的这首作品,告诉我内声部有个错音,我仔细校对后并未发现。随后,他索要乐谱比对后发现,我俩手头乐谱的版本不同,最终通过素材、和弦的分析与反复推敲,达成统一的定稿。合唱作品中确实会因为一个音就改变和弦性质、调性归属,甚至风格派别,所以不要忽视任何一个声部的任何音。杨先生这种不将就、不凑合的钻研,不仅是一种治学精神,更是一种对职业的敬畏,对我的工作态度和排演作风影响至今。
“八秒”团员们曾每人写一句话呈送杨先生厚厚一本满载着祝福的笔记本。我依然记得其中有一句:“您这把年纪还如此好学,我们岂能不努力?!”杨先生虚心好学、钻研业务的精神,不仅是我辈学习的楷模,更是我教育学生、培养晚辈的很好实例。有时,身教的力量胜过太多空泛地说教!在诸多研讨会、音乐会、讲座课堂上,有意料之中、更多是意外地见到杨先生,而他总会说出那句“我是来学习的”口头禅。先生听课的认真程度和记忆力是少见的。我有几次讲学结束后发现杨先生也在现场时,确实又紧张又高兴。紧张的是,别讲错了什么,误导了学员;高兴的是,有老人家来把脉,又能和他聊业务了。所以,他用行动教会了我等懂得教与学的另一关系,即认真对待每一次授课,就是对自身学习很好的总结。我时常感叹,遇到如此执着的前辈是吾辈之福报,值得庆幸!
一直与时间赛跑的人
熟知杨先生的人一定能感受到他惜时如命的习性,原以为我等尚属努力,看到他的日程安排,深感自愧不如。近三年,每次听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就很不是滋味,他确实一直都在与时间赛跑!
2012年,在宜昌我和杨先生参与了“第六届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比赛”的各项活动后,因为同时要赶回杭州参加“浙江省合唱大赛”的评审工作,途中便由我推着轮椅照顾行动不便的杨先生。背起他的行李,“哎哟,够分量”,原来都是书谱。我问:“干吗这么抓紧?”先生说:“写书查资料最费时间,做一点儿是一点儿嘛。”一路上除了说笑之外,无论候机、转车还是路途中,坐在特殊照顾的座位,我发现老人家总在不停地翻阅、写作。即便是在武汉转车时身处喧闹的候车室,他也专注地在书上画画写写,那种认真刻苦,至今记忆犹新。
其实,杨先生外出带着书稿工作是一种生活常态。2009年,由我主持的“2009中国合唱教育高峰论坛”邀请杨先生参会时,就知道他有熬夜的习惯。送夜宵时,我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书稿,想顺手帮他收拾、腾个吃饭的地方,他马上制止,“别动!顺序别搞乱了,找起来费时间”。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扎在书堆里,有时几天不出门,外面发生的事什么也不知道。也正因如此,杨先生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惜时如命的“工作狂”,在他身上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废寝忘食”。有段时间见他总穿黑短袖衬衫,我问:“大热天怎么也不换衣服呢?”他笑道:“我天天换啊,意大利买的一元一件的处理货,省时,不用洗衣服了,哈哈。”在他看来,洗衣服、买菜、做饭、吃桌餐等都太浪费时间。于是,很多次演出、讲座前,他常常是就餐的早退者;连合唱团开声,他都智慧地利用小曲目预热,并逐渐升调,既达到了科学开声的目的,又节省了时间,同时还掌握、复习了多首返场小曲,可谓一举三得。
记得最后几次通话时,我对先生说,希望他不要太辛苦。他总说,我没时间了,不抓紧怎么行?有次采访时,他说:“童声是人声中最明净、空灵的音色,在人的一生中,拥有这种声音的阶段实在短暂。用正统“美声”方法训练的童声合唱,音域更宽阔、声部更和谐,音质和旋律的高度统一能达到一种辉煌和美妙的境界,这也是我们这些人所苦苦追求和探索的。”今年以来,问候的电话几乎都是由唐重庆老师(杨先生夫人)转告,据说在病床上清醒时,他还惦记着许多书稿和创作的事情没时间完成……杨先生用尽一生、分秒必争地投入合唱事业,正可谓生命不息,求索不止!
外柔内刚坚毅的人
杨先生的外柔,从二十多年前初识时,见他拄着拐杖就已经定格。见其虚弱,身体时好时坏,每次会晤均不由自主地搀扶他前行。杨先生的外柔还表现在说话慢声细语,令人深感亲近。在我接触他的几十年间,几乎没见到他与任何人红过脸,即使身处尴尬事态时,他依然温文尔雅地坦然处之。
我也深晓杨先生内刚且坚毅的性格,虚弱的身体一旦进入作品排演,其精神状态瞬间判若两人。每次聆听先生慢条斯理的言语,细细品味,总会发现他明确的旨意,坚定的态度。有时,在研讨会上,他回眸神态的刚毅,立刻就知其态度如何!他有他自身特有的表达方式,也有笑看人生的潇洒与执着。仅从他勤于笔耕、置身于教学第一线的人生足迹,操持北京爱乐合唱团三十七年的坚定不移,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坚毅和韧劲!
他的坚毅表现在业务追求上,可谓“一根筋”地钻研。有时,几个月前电话里谈论过的问题,下次见面他依然会说起并提出新发现,辩证地说明同意与反对的认可比值,依然固守着他认为正确的方方面面。有些观点在其著作中能感受到贯穿数十年的求索足迹,那种始终不渝的较真儿令人折服,他不成功都不可能!
他的坚毅表现在生活细节上。身患糖尿病多年的他并非严于律己,遇上喜欢的甜食或新花样的菜肴,他一定要尝尝。如同他对任何一首合唱佳作,无论出自何人之手,都会饶有兴趣地阅读分析,足见其“猎奇”的童心犹存。但杨先生不贪食,一旦品尝后,再美味的佳肴也不再入口,有时克制力的体现并非从不触及,而恰恰是触及后却能抗拒诱惑,更突显其具有的自律性。
他的坚毅表现在乐观心态上。晚年的杨先生讲学时、生活中,常爱说一句顺口溜:“活着,干!死了,算!”有一次,他身体不适,主办方请我陪同,以便在先生难以支撑时补充讲完。课间,他用的耳麦突然不响了,我赶紧上台帮他调整挂在腰间的接收器。让他试声时,谁料他说:“你怎么一上来就脱我的裤子?”出其不意的幽默惹得全场哄堂大笑,他的乐观使身体和上课的氛围轻松了许多。在我的记忆中,和杨先生通话几乎都在晚上,有时甚至是午夜零时。我太太一听我和先生通话,一定去忙别的事,因为她知道,这是少则半小时、多则数小时的等待。其实,在先生烦闷时给他讲讲笑话,听他谆谆教导,难得的放松聊天亦是“加油”的良策。正因为乐观的心态,使多疾缠身的杨先生坚毅地挺过了一次又一次与病魔的搏战。
在辛辛那提的“世界合唱锦标赛”上“八秒”获得冠军,杨先生第一个登台与我们共享升国旗、奏国歌的待遇;在春城昆明因“八秒”在“金钟奖”赛场摘金夺银,我们在颁奖仪式上相拥庆祝。无论是200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排演我的习作《畲族情歌》时的鼓舞,还是“八秒”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举办专场音乐会后的登台赞赏;无论在讲学中和我彼此范举实例的肯定和剖析,还是“G20峰会”大型实景音乐会上“八秒”参演后的电话关怀,杨先生的举止对我们都是莫大的鞭策!他用一生的求索告诫我们艺海无涯,勇于开创。
对于杨先生和他的合唱团,以及指导过的团队,不乏轰轰烈烈的报道,获得大奖的风光,充满智慧的范本和情趣盎然的授课,那些都是艰苦付出后的必然。过于注重结果,就会不自觉地忽略许多过程,而决定成功的关键,恰恰取决于过程中的各种细节。所以,我在撰文时,总想透过光鲜与大家一起走近我所了解的杨先生,通过善于学习、惜时如金、外柔内刚的一生求索,以不经意的细节说说他必然成功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