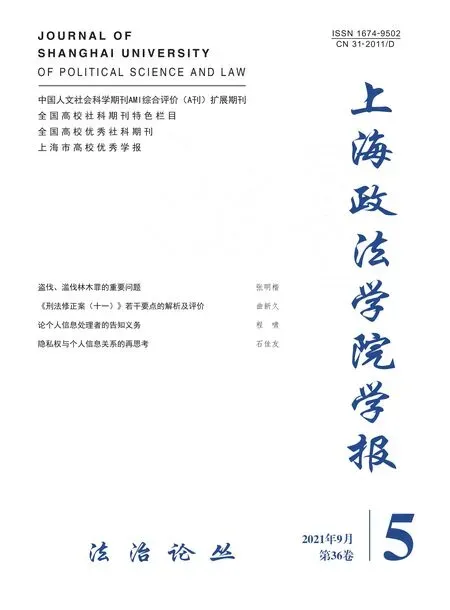盗伐、滥伐林木罪的重要问题
2021-01-28张明楷
张明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45条第1款与第2款分别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解释将上述两款规定的犯罪分别确定为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在司法实践中,两罪的发案率都比较高,但存在不少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两罪的保护法益是否相同,各自的构成要件究竟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二者是什么关系,如何处理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关系等,都是刑法理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盗伐、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
少数观点认为,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相同。例如,有的论著指出,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侵犯的客体都是“国家对林业资源的管理制度”。①参见周道鸾、张军:《刑法罪名精释》(下)(第4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886页、第888页。然而,如后所述,由于两罪的行为对象并不相同,作为行为对象的具体物是法益的物质表现②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9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589-590页。,故应认为二者的保护法益并不相同。如果认为二者的保护法益相同,也难以说明法定刑的差异。或许有人认为,由于盗伐林木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滥伐林木罪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前者的主观不法更为严重,因而法定刑更重。可是,非法占有目的对于“国家对林业资源的管理制度”这一保护法益的侵害程度不产生任何影响。
多数观点认为,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有相同之处,但不完全相同。亦即,盗伐林木罪侵犯的是双重法益,而滥伐林木罪侵犯的是单一法益:如果说滥伐林木罪侵犯的是A法益(单一法益),则盗伐林木罪侵犯的是A法益+B法益(双重法益)。其中的B法益,刑法理论均认为是国家、集体或公民个人对林木的所有权,至于A法益是什么,则有不同表述。例如,有的教科书指出:“盗伐林木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保护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和国家、集体或公民个人对林木的所有权”;“滥伐林木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林木资源的保护制度”③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第5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0页、第1431页。相同表述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9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589-590页;李希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1页、第544页。。前者的“管理制度”与后者的“保护制度”似乎没有明显区别,只是用语不同而已。再如,有的论著指出,盗伐林木罪的“客体要件即国家管理林业资源的法律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所有权”;“滥伐林木罪的客体要件是国家管理林业资源的法律秩序”④牛忠志、朱建华:《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第347页。。显然,上述观点都认为,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是单一法益,即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或者管理秩序。但在本文看来,这样的表述并不理想。
首先,上述观点没有进一步解释“管理制度”“管理秩序”的具体内容,如此抽象的表述不可能揭示刑法分则规定滥伐林木罪的目的,不能说明滥伐林木罪的实质。实现法益保护目的是刑法将某类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正当化根据所在。反过来说,只有确定了某类行为的有害性才可能确立某种制度与制裁措施。例如,“打算以维护一般市民的健康为目的,以某种药物对健康产生恶的影响为根据禁止、处罚对该药物的贩卖等行为时,设置刑罚法规的前提是确认该药物的真实有害具有一定的盖然性”⑤[日] 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第2版),有斐阁2018年版,第27页。。行为的实质危险与法条的保护目的具有对应关系。一方面,任何管理制度都是为保护法益服务的,维护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说一种规范的目的在于保护另一种规范,等于什么也没有说。⑥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对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检视》,陈璇译,《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如果说行为的有害性只是侵犯管理制度,而没有侵犯其他法益,废止该管理制度即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国家设立林木采伐等管理制度,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刑法规定滥伐林木罪不可能是为了保护林木采伐等管理制度本身。另一方面,“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或者管理秩序”充其量只是意味着成立滥伐林木罪以行为违反森林法的规定为前提,但这只不过说明了构成要件的部分内容,而不能说明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与实质违法性。
其次,将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或者管理秩序作为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不能对滥伐林木罪的构成要件解释起到指导作用,因而导致处罚范围不明确。国家对森林的管理制度包括诸多内容,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确定的森林保护和林木采伐制度外,还有部门规章也确定了相关管理制度。但难以认定,凡是违反林木管理制度的行为均成立滥伐林木罪。例如,1989年林业部的《关于切实加强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的通知》(已废止)指出,“各地因特殊需要必须超限额采伐的,除因紧急抢险需要,可先采伐、后报批外,其他情况(包括清理因火灾及各种自然灾害损失林木资源等)都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报林业部批准后实施,否则要追究当地林业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责任”①2003年国家林业局《关于未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火烧枯死木”行为定性的复函》指出:“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外,凡采伐林木,包括采伐‘火烧枯死木’等因自然灾害毁损的林木,都必须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一种观点据此认为,滥伐枯死林木的行为,“由于破坏了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制度”,也构成滥伐林木罪。②参见真少萍、吴孔宝:《关于枯死木是否列入盗伐滥伐林木犯罪对象的问题探讨》,《林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1期。实践中也有这样的判例。但这样的观点与做法难言妥当。例如,被告人韦某(女)在某坡地种植了杉木林。2011年5月,韦某的儿子覃某为筹集资金建房,计划砍伐韦某种植的杉木林,并对活立木进行剥皮。同年7月,覃某因病死亡,被剥皮的林木尚未得到处理,至同年11月,该片林木已经枯死。韦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请村民砍伐该片杉木林(无证采伐的林地面积10.8亩,立木储蓄量为51.2514立方米)。法院认为,韦某未经林业部门批准颁发采伐许可证,擅自采伐林木,构成滥伐林木罪。③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3)金刑初字第228号刑事判决书。诚然,覃某的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但韦某对此并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可以认为韦某是覃某滥伐林木罪的被害人。然而,在林木已经枯死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取得采伐许可证而予以采伐的,也没有破坏林木资源。主张韦某的行为构成犯罪的观点,只是以行政法律、规章为根据,完全没有从刑法规定滥伐林木罪的目的进行独立判断,或者牵强地认为枯死树木具有经济价值或者水土保持价值。然而,林木资源的保护,需要“及时清除枯立木、风折木、衰弱木和虫源木。这是防止蛀干害虫的有效措施”④吴利平等:《建德松树枯死原因剖析及治理》,《浙江林业科技》2001年第4期。。例如,“及时清理山上死亡松树不仅可以缓解松林内树种间的竞争,促进植物群落演替,还可以减少松材线虫病传媒松褐天牛的虫源,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⑤刘金燕等:《松材线虫病防治中及时清理死亡松树和诱杀松褐天牛的必要性研究》,《现代农业科技》2011年第1期。。既然如此,就不得将未取得采伐许可证而滥伐枯死树木的行为认定为滥伐林木罪。⑥参见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
最后,将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或者管理秩序作为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可能导致对滥伐林木既遂的认定过于提前。从逻辑上说,只要是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禁止的行为,都必然已经违反了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于是,任何违反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的行为,都是本罪的既遂。例如,行为人着手滥伐林木时,其行为就违反了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因而构成既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其实,行为违反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前置法),只是成立滥伐林木罪的前提。虽然前置法的目的也可能成为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但前置法及其确立的各种制度本身不可能成为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森林法》第1条规定:“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保障森林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定本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森林、林木的保护、培育、利用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活动,适用本法。”显而易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就是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第1条规定:“为合理采伐森林,及时更新采伐迹地,恢复和扩大森林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第3条规定:“全民、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个人所有的林木采伐更新,必须遵守本办法。”不难看出,合理采伐森林,也是国家对森林资源进行管理的目的;个人所有的林木是国家森林资源的组成部分。滥伐林木的行为,破坏了森林资源,妨害了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反过来说,刑法规定滥伐林木罪,就是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即使是个人所有的林木,如果没有经过批准而滥伐,也侵害了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因而具有可罚性。
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所谓“人的生活利益”,不仅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而且包括建立在保护个人的利益基础之上因而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刑法将什么作为利益予以保护,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具有宪法根据。我国《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显然,将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作为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宪法依据。诚然,法益保护手段虽然不限于刑法,但事实表明,“在遏止环境污染方面民法是不够的,而刑法应当用来保护生态价值和利益”②[瑞典]汉斯·舍格伦、约兰·斯科格:《经济犯罪的新视角》,陈晓芳、廖志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所以,即使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来说,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也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
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是环境法益、生态法益的一部分。如所周知,关于环境犯罪(不限于狭义的污染环境罪,还包括其他破坏环境的犯罪)的保护法益,国内外刑法理论主要存在纯粹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与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以及折衷说(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之争。
纯粹人类中心的法益论认为,环境自身不是保护法益,只是行为对象;环境刑法的目的与作用在于保护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法益免受被污染的环境的危害,所以,只有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才是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③Vgl.Olaf Hohmann,Von der Konsequenzen einer personalen Rechtgutsbestimmung im Umweltstrafrecht, GA 1992,S.539.只有当环境污染行为具有间接地侵害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的危险时,才能成立环境犯罪;与生命、身体、健康没有关系的环境,即使是一种公共利益,也不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这种学说,也可谓对生命、身体、健康的间接保护说。④参见[日]伊藤司:《環境(刑)法総論:環境利益と刑法的規制》,《法政研究》第59卷(1993年)第3、4合并号,第673页、第700页。根据这种观点,行为人盗伐或者滥伐一些林木,因为不可能给任何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形成任何威胁,故不能作为犯罪处罚。这显然不妥当。
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也称环境中心主义的法益论)认为,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就是生态学的环境本身(水、土壤、空气)以及其他环境利益(动物、植物)。①Vgl.Arzt/Weber,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Lehrbuch,Verlag Ernst und Werner Gieseking, 2000, S.883f;Wessels/Hettinger,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Band I, 26.Aufl., C.F.Müller Verlag , 2001, S.276.问题是如何确定“植物”这种环境利益的范围。例如,能否认为,任何砍伐林木的行为,都侵害了环境利益,因而成立犯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国《森林法》第6条规定:“国家以培育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为目标,对公益林和商品林实行分类经营管理,突出主导功能,发挥多种功能,实现森林资源永续利用。”对森林资源永续利用的主体显然是人,而不是大自然本身。所以,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也有疑问。
通说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亦即,水、空气、土壤、植物、动物作为独立的生态学的法益,应当得到认可,但是,只有当环境作为人的基本的生活基础而发挥机能时,才值得刑法保护。②Vgl.Gramer/Heine, in: Schönke/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 26. Aufl., 2001, S.2480.换言之,只有存在与现存人以及未来人的环境条件的保全相关的利益时,环境才成为独立的保护法益。本文主张的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可以归入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其一,盗伐、滥伐林木,破坏了森林资源。虽然一次盗伐、滥伐行为不会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也不会使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受到明显影响。但盗伐、滥伐林木罪可为累积犯,如果不禁止这种行为,其累积起来就会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进而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其二,人不仅具有生命、身体、健康等方面的权利,而且还具有享有优美环境(包括动物与植物)的权利(环境权)。这种环境权不是一般的环境伦理,而是个别的环境权,即要求清洁的自然环境、优美的自然景观、物种的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存在等权利。③参见[日]町野朔:《環境刑法の展望》,《現代刑事法》第24号(2001年),第82-83页。行为人滥伐林木,也侵犯了人们观赏植物、享受优美环境的权利。其三,如上所述,国家并非仅仅从事森林、林木的保护、培育,而且还要合理利用森林、林木。滥伐林木的行为妨害了国家、集体、他人对林木的合理利用。
如果能够肯定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是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那么,盗伐林木罪的行为也破坏了森林资源,妨害了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换言之,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也是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但是,森林与其他林木具有双重属性,即一方面作为森林资源受到森林法与刑法的保护,另一方面作为财产受到民法与刑法的保护。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331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而林地承包经营权人通常同时对其种植的林木享有所有权。即使森林与其他林木具有作为森林资源保护的价值,也不能否认林木所有权人对之享有的财产权。如果森林与其他林木不再具有作为森林资源保护的价值时,就只能作为财产予以保护。所以,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还包括国家、集体、他人对生长中的林木的财产所有权。正是因为盗伐林木罪侵害了双重法益,所以,其不法程度重于滥伐林木罪,这便是盗伐林木罪的法定刑重于滥伐林木罪的根据所在。
综上所述,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是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是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以及国家、集体、他人对生长中的林木的财产所有权。
二、盗伐、滥伐林木罪的成立条件
从法条表述上看,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的构成要件,只有一字之差,但涉及行为对象与主观要素等多方面的内容。什么样的行为成立盗伐林木罪,什么样的行为成立滥伐林木罪,虽然有司法解释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没有争议。
在本文看来,首先必须肯定的是,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特别关系。如所周知,特别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甲法条(刑罚法规)记载了乙法条的全部特征(或要素),但同时至少还包含一个进一步的特别特征(要素)使之与乙法条相区别。①Vgl.C.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I, C.H.Beck, 2003, S.858.换言之,特别法条规定的行为均完全符合普通法条规定的成立条件。②参见张明楷:《诈骗犯罪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51页以下。根据这一判断标准,应当认为刑法关于滥伐林木罪的规定是普通条款,关于盗伐林木罪的规定则是特别条款。
在根据森林法的规定采伐林木需要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形下,凡是没有取得采伐许可证,或者虽然取得了采伐许可证,但违反许可的地点、数量、种类等要求采伐林木的,都属于滥伐林木。至于行为人所采伐的林木由谁所有,采伐行为是否违反林木所有权人的意志,行为人是否对所砍伐的林木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都不影响滥伐林木罪的成立。可以肯定的是,盗伐林木行为也必然是没有取得采伐许可证,或者虽然取得了采伐许可证,但违反许可的地点等采伐林木的行为。既然如此,盗伐林木罪也符合滥伐林木罪的构成要件,只不过如后所述,盗伐林木罪必须另具备特别要素。但是,滥伐林木行为并不必然符合盗伐林木罪的构成要件。所以,规定滥伐林木罪的条款是普通条款,规定盗伐林木罪的条款是特别条款。③从刑事立法论的角度来说,刑法分则一般应先规定普通条款,后规定特别条款,但我国刑法分则并没有遵循这一规则,而是先规定严重犯罪。例如,各国刑法分则都是先规定了盗窃罪,后规定抢劫罪,但我国刑法分则却是先规定抢劫罪,后规定盗窃罪。但这种规定方式并不影响刑法理论对特别关系的判断。
诚然,从法条表述上看,滥伐林木罪需要“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而盗伐林木罪则没有这一要求。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区别,并无本质的不同。其一,没有取得采伐许可证的采伐行为,可能并没有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故不一定构成犯罪。所以,需要强调滥伐行为必须“违反森林法的规定”。例如,《森林法》第56条规定,“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采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但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第57条第3款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林地上的林木,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核发采伐许可证。”显然,并不是任何没有取得采伐许可证的采伐行为均构成滥伐林木罪。换言之,《刑法》第345条第2款中的“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其实就是指在必须取得采伐许可证的场合没有取得采伐许可证,以及虽然取得采伐许可证,但没有按许可的地点、数量、种类等要求砍伐林木。其二,任何盗伐作为国家森林资源一部分的林木的行为,均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所以,盗伐林木罪不需要作出这一规定。如果行为人盗伐农村居民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则仅构成盗窃罪,而不构成盗伐林木罪。概言之,如果行为人所盗伐的林木并没有被森林法列入森林资源的保护范围,该盗伐行为就并不构成盗伐林木罪。反过来说,行为人所采伐的林木是否属于“国家森林资源的一部分”,原本也需要根据森林法的规定进行判断。在此意义上说,盗伐林木罪也必须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因而也可以将“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视为盗伐林木罪的不成文要素。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数量较大的,依照刑法第345条第2款的规定,以滥伐林木罪定罪处罚:(一)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二)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林木权属争议一方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擅自砍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以滥伐林木罪论处。”
据此,下列情形成立滥伐林木罪:⑴未取得采伐许可证采伐自己所有的林木的。这种行为显然没有侵犯他人对林木的所有权,只是侵犯了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⑵虽然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任意采伐自己所有的林木。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3月26日《关于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以外,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1款第(一)项“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情形,数量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45条第2款的规定,以滥伐林木罪定罪处罚。这种行为也没有侵犯他人对林木的所有权,只是侵犯了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⑶未取得采伐许可证,擅自采伐可能属于自己所有的林木的。严格地说,这种行为可能侵犯他人对林木的所有权,《解释》之所以规定以滥伐林木罪论处,大体是因为行为人以为是自己所有的林木而采伐,因而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故不成立盗伐林木罪。②当然,也可以认为司法解释贯彻了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⑷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但在本文看来,这一情形值得研究。虽然这一行为也构成滥伐林木罪,但由于该行为不仅侵犯了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而且侵害了他人对林木的所有权,故如后所述,对该行为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论处。
《解释》第5条关于滥伐林木罪的上述规定,在行为对象方面,没有完全排除滥伐他人所有林木的情形。如果从法条关系以及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方式的角度来说,既然滥伐自己所有的林木可以成立滥伐林木罪,那么,滥伐他人所有的林木,当然成立滥伐林木罪。因为《刑法》第345条第2款并没有对作为行为对象的林木本身作出任何限定。这样理解,可以肯定上述第⑶种情形的合理性。这样理解,也可以肯定上述第⑷种情形作为中间结论的成立,但不能肯定其作为最终结论的成立。
那么,作为特别条款的盗伐林木罪需要具备什么特别要素呢?《解释》第3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数量较大的,依照刑法第345条第1款的规定,以盗伐林木罪定罪处罚:(一)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二)擅自砍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三)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虽然《解释》并不一定基于特别关系规定盗伐、滥伐林木罪,而是试图明确区分二者,但我们依然可以根据上述规定,发现盗伐林木罪有两个特别要素:一是特别的主观要素,即非法占有目的;二是特别的客观要素,即行为人擅自采伐的是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的林木。①他人承包经营的林木,一般也是承包经营者所有的林木。问题也同时出现在上述主客观两个方面。其一,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伐林木罪的主观要素是否合适?对于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伐他人林木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这是《解释》同时采用两个标准区分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所形成的困境。其二,就特别的客观要素而言,《解释》的规定既不彻底,也不全面。亦即,超过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的(以下简称“超过数量”),成立滥伐林木罪;超出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的(以下简称“超出地点”),成立盗伐林木罪。至于超出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树种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的(以下简称“超出树种”),《解释》并无明文规定。②单纯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方式采伐林木的,一般仅构成滥伐林木罪,在此不予展开讨论。由此形成的问题是,在客观方面区分“超过数量”与“超出地点”是否合适?对于“超出树种”的应当如何处理?
在本文看来,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盗伐林木罪的特别要素,只要行为人擅自采伐并非自己所有的林木,就构成盗伐林木罪。
如前所述,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是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也包括这一内容,所以,二者均可能表现为没有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超出地点”与“超过数量”采伐林木。二者的法定刑之所以存在区别,就是因为盗伐林木罪是擅自采伐国家、集体或者他人所有而非行为人所有的林木,进而同时侵犯了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财产,而滥伐林木罪则是擅自采伐行为人所有的林木,没有同时侵害他人的财产。然而,并非只有出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才能侵犯他人对林木的所有权。例如,在财产罪中,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但后两罪的成立并不以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前提。同样,行为人违反他人意志擅自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就侵犯了他人对林木的所有权(如同故意毁坏财物罪或者破坏生产经营罪)。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要求盗伐林木罪出于非法占有目的。
林木所有权具有不同于普通有体物所有权的特点。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虽然包括他人对林木的所有权,但这是指他人对生长中的林木的所有权,而不是指对已被采伐后的木材所有权。盗伐林木罪的法益侵害性就表现为将他人生长中的林木采伐为木材,而所谓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针对生长中的林木的非法占有,而是对采伐的木材的非法占有。③参见董玉庭:《盗伐林木相关犯罪的司法认定研究——以对<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评析为切入点》,《人民检察》2008年第16期。行为人采伐他人生长中的林木后,即使并不运走其所砍伐的木材,其行为也侵害了他人对生长中的林木的所有权。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伐林木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另一方面,只要行为人明知是他人所有的林木而采伐,就具备了盗伐林木罪的故意。即使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同样说明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重于滥伐林木罪的非难可能性。所以,没有必要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伐林木罪的主观责任要素。
《解释》规定盗伐林木罪必须出于非法占有目的,可能是由于将盗伐林木罪视为盗窃罪的特别法条,而盗窃罪需要出于非法占有目的,故盗伐林木罪也需要出于非法占有目的。然而,如后所述,特别关系以侵犯同一法益以及不法的包容性为前提,但盗伐林木罪的不法并不能完全包容盗窃罪的不法,不能将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视为法条竞合中的特别关系。
《解释》规定盗伐林木罪必须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也许是由于重视了《刑法》第345条中的“盗”字。诚然,一般来说,“盗”就是窃取,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者占有。①参见[日]西田典之著、桥爪隆补订:《刑法各論》,弘文堂2018年第7版,第160页。但“盗伐”中的“盗”是限定“伐”的,“伐”才是构成要件行为,“盗伐”只是意味着违反被害人意志擅自采伐②如同1979年《刑法》第173条规定的“盗运珍贵文物出口”中的“盗”不是指“窃取”一样。,而擅自采伐并不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前提。例如,行为人为了使私家车进出森林,而擅自采伐国有林木的,即使其对采伐的林木并不具有占有目的,也应认定为盗伐林木罪。
《解释》规定盗伐林木罪必须出于非法占有目的,或许是基于社会生活事实,亦即,在现实生活中,盗伐林木的行为人一般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是,任何人对事实的观察都不可能没有遗漏,任何人也不可能对将来的事实有全面预见。所以,任何人都不应将熟悉的当作必须的,不能将自己所观察到的有限事实强加于规范。“刑法学是规范学而不是事实学,什么样的因素是构成要件要素,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来确定,而不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确定,也不能根据所谓的人之常情来确定。”③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将非法占有目的规定为盗伐林木罪的主观要素,不利于司法机关合理认定盗伐、滥伐林木罪。例如,2016年3月开始,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张某某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且未经许可,共同在权属为国家所有的某村石树顶山开荒种植沉香,经专业机构现场调查,林木被砍伐面积约18亩,蓄积量为98立方米。被告人与现场勘查可以证明,被砍伐的林木并没有被杨某某、张某某挪作他用,而是遗留在原地(“种植沉香采伐案”)。公诉机关认为,两被告人“无视国家法律,违反森林法及相关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私自采伐国家所有的林木,破坏森林资源,数量较大,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也认为两被告人的行为成立滥伐林木罪,但法院判决指出,“虽然控辩双方均认为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3条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数量较大,构成盗伐林木罪。该《解释》第5条规定,未取得核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规定的时间、数量等,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等行为,则构成滥伐林木罪。经查,涉案林木权属为国家,两被告人为在涉案地块种植沉香谋取非法利益,擅自砍伐国家所有的林木,并已实际非法占有,其是否出售牟利并不影响非法占有的认定,故两被告人的行为应构成盗伐林木罪”①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刑初236号刑事判决书。。
公诉机关显然是按照《解释》规定起诉的,亦即,由于杨、张二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认定为盗伐林木罪,故只能认定为滥伐林木罪。按照本文前述观点,杨、张二人的行为也的确符合滥伐林木罪的成立条件(但不符合《解释》第5条的规定),因为没有取得采伐许可证而采伐林木的行为,都属于滥伐林木。但是,其一,如果将杨、张二人的行为仅认定为滥伐林木罪,就没有评价其行为侵害了国家对林木的所有权这一不法内容,因而评价不全面。其二,倘若因为杨、张二人的行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符合《解释》第5条的规定,便仅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则仅评价了行为对国家财产的侵害,并没有评价行为对森林资源的侵害。其三,只有以盗伐林木罪论处,才能全面评价本案事实,实现罪刑的合理化。而要评价为盗伐林木罪,就不能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本罪的主观要素。上述一审判决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非法占有目的包括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②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56页以下。,杨、张二人显然没有利用意思。
反之,在滥伐林木案件中,行为人也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因为,所谓非法占有目的只是意味着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采伐后的木材的目的,而不是指非法占有生长中的林木的目的;“非法”则既包括违反实体法的情形,也包括违反程序法的情形。行为人没有取得采伐许可证而采伐自己所有的林木时,其对所采伐的林木的占有,虽然不是违法所得,但由于其滥伐行为违反了森林法关于必须取得采伐许可证的规定,因而其目的本身也具有非法性。所以,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伐林木罪的主观要素,就可能导致下级司法机关将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滥伐林木行为也不当地认定为盗伐林木罪。
综上所述,根据盗伐、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从行为人所砍伐的林木由谁所有以及是否具有采伐许可证这两点,就可以合理决定对行为是以盗伐林木罪论处还是以滥伐林木罪论处。
第一,由于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是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以及国家、集体、他人对生长中的林木的所有权,所以,即使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是出于毁坏目的采伐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林木的,也应以盗伐林木罪论处。“例如发生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林区的一个盗伐案例,行为人为了采松仔方便砍伐了几十棵松树。对于这样的案件,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砍倒林木的目的,如按《解释》则无法认定盗伐林木罪,但这种盗伐与有非法占有目的盗伐有什么区别呢?对这样的盗伐行为不认定为盗伐林木罪显然是不恰当的。”③董玉庭:《盗伐林木相关犯罪的司法认定研究——以对<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评析为切入点》,《人民检察》2008年第16期。前述种植沉香采伐案也是如此。当然,如果采伐行为得到了林木所有权人的同意,则只能认定为滥伐林木罪。
第二,如前所述,《解释》第5条规定,“超过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的,成立滥伐林木罪;“超出地点”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的,成立盗伐林木罪。然而,就超出或超过的部分而言,上述两种情形都是没有得到许可的采伐,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不能认为“超出地点”的采伐行为就必然侵犯他人的林木所有权,也不能认为“超过数量”的采伐行为就不可能侵犯他人的林木所有权。《解释》或许考虑到“超出数量”的期待可能性减少,故作出上述规定。然而,期待可能性减少虽然可能影响量刑,却不应当影响定罪。况且,超出许可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期待可能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可能有所增加。所以,本文认为,对于“超出地点”与“超过数量”的采伐行为,需要区分两种情形:“超出地点”或者“超过数量”采伐自己所有的林木的,由于没有侵犯他人的林木所有权,只能认定为滥伐林木罪;反之,“超出地点”或者“超过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的,因为侵犯了他人的林木所有权,虽然也符合滥伐林木罪的构成要件,但由于具备了盗伐林木罪的特别要素,应以盗伐林木罪论处。概言之,就“超出地点”与“超过数量”的采伐行为而言,只能根据行为是否侵害了他人对林木的所有权,来决定最终对行为以何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解释》规定了“超出树种”任意采伐自己所有林木的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但没有规定“超出树种”任意采伐他人所有林木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按照本文的观点,由于“超出树种”采伐他人所有林木的行为同时侵犯了他人对林木的所有权,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论处。例如,甲承包村集体山林种植油松,承包协议明确确定,山上的阔杂树仍由集体所有。甲取得采伐油松的许可证后,同时采伐了油松与集体所有的阔杂树。甲采伐阔杂树的行为仍然成立盗伐林木罪。
综上所述,对于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而采伐他人所有的属于国家森林资源一部分的林木的,不管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均应以盗伐林木罪论处;对于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的,也应以盗伐林木罪论处。没有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自己所有的属于国家森林资源一部分的林木的,仅成立滥伐林木罪;虽然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采伐自己所有的林木的,也成立滥伐林木罪。
或许有人认为,本文上述观点实际上使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形成了对立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本文认为,所有的盗伐林木均符合滥伐林木罪的成立条件,盗伐林木罪的特别要素只是行为对象必须是他人所有的生长中的林木。由于二者不是对立关系,所以,在林木所有权存在争议的场合,即使采伐行为不成立盗伐林木罪,也能成立滥伐林木罪;在行为人对林木的所有权产生认识错误的场合,按法定符合说,只能以滥伐林木罪论处。①如果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就难以处理这种抽象的事实错误的情形。
三、盗伐、滥伐林木罪的相关问题
以上讨论了盗伐、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与成立条件两个重要问题。接下来有必要就几个相关问题予以说明。
(一)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关系
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关系,一直是刑法理论界争论的问题。笔者曾经从不法的包容性的角度说明,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不是绝对的特别关系,而是可能成立想象竞合。这是因为,“罪数论·竞合论是在实体法上经过了对某一行为的违法、责任的判断阶段后,为量刑提供基础的领域的讨论。”①[日]只木诚:《罪数論·竞合論》,载[日]山口厚、甲斐克则编:《21世纪日中刑事法の重要課題》,成文堂2014年版,第73页。量刑的基准是责任,或者说是有责的不法。②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页以下。如果A法条的不法内容(程度)完全能够包容B法条的不法内容(程度),那么,就只需要适用A法条,而无需同时适用B法条。如果A法条的不法内容不能包容B法条的不法内容,当甲的行为同时存在A法条的不法内容与B法条的不法内容时,适用其中任何一个法条,都不能对甲的行为的不法内容进行充分评价。在这种场合,就必须认定为想象竞合。换言之,“一个行为(犯罪事实)的不法内容,只要适用一个刑罚法规就能够穷尽全部评价时,便是法条竞合;在有必要适用数个刑罚法规进行评价时,就是想象竞合(观念的竞合)”③[日]只木诚:《観念的競合における明示機能》,《研修》2011年4月号(总第754号),第6页。。所以,“特别关系的确定,也并不一定总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必须通过对被排除适用一方的构成要件的不法程度进行目的论的考量予以补充的现象并不罕见”④C.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I, C.H.Beck, 2003, S. 850.。即使人们坚持认为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是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⑤从法益的同一性来看,将二者确定为想象竞合才是合适的。,那么,按照不法的包容性的实质标准,这种特别关系仅限于盗伐林木的财物价值(不法程度)没有超出15年有期徒刑程度的情形。换言之,当盗伐林木所造成的财产侵害程度需要判处无期徒刑时,其与盗窃罪之间便是想象竞合。这是因为,如果仅认定为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就没有对重大财产侵害这一不法内容进行充分评价,而仅认定为盗窃罪就没有评价对森林资源的侵害内容。只有认定为想象竞合,才有充分评价行为的不法性质与不法内容。
详言之,由于《解释》与通说认为盗伐林木罪以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前提,又由于林木也是财物,于是,与盗窃罪相比,盗伐林木罪多出了一个特别要素——行为对象为生长中的林木。所以,盗伐林木罪必然符合盗窃罪的成立条件,盗伐林木罪就成为特别法条。但是,《刑法》第264条所规定的普通盗窃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刑法》第345条对盗伐林木罪所规定的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如果认为规定盗伐林木罪的法条是特别法条,就意味着盗伐林木罪是减轻构成要件。可是,不能不追问的是,刑法规定减轻构成要件的根据何在?既然盗窃罪的保护法益只是财产,而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是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以及他人的财产,就没有理由认为盗伐林木罪的不法轻于盗窃罪的不法。相反,在财产价值相同的情况下,盗伐林木罪的不法程度重于盗窃罪的不法程度。所以,如若认为盗伐林木罪是盗窃罪的特别减轻法条,就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会导致处罚不公平。例如,《解释》第15条规定,“非法实施采种、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等行为,牟取经济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显然,倘若行为人剥下100棵树皮的盗窃行为,财产价值数额达到200万元而应判处无期徒刑,那么,行为人盗伐了相同的100棵树,价值远远超过200万元时,不可能因为其行为符合了盗伐林木罪的构成要件,就认为(或者声称立法者认为)其不法程度低于盗窃罪,也不可能认为仅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合适的。再如,甲等人为了种植某种植物将大量的国有林木锯倒后堆放在一边,乙等人事后盗走该林木(数额特别巨大)。如果仅认定甲等人的行为成立盗伐林木罪,而不认为同时触犯盗窃罪,就会导致对甲等人的处罚反而轻于对乙等人的处罚。这明显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正确的刑罚裁量终究是整个竞合理论的目的。”①[德]Ingeborg Puppe:《基于构成要件结果同一性所形成不同构成要件实现之想象竞合》,陈志辉译,《东吴法律学报》2006年第3期。离开竞合理论的目的确定特别关系,缺乏实质的合理性。在上述情形下,只有承认甲等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的想象竞合,才能妥当地解决定罪与量刑问题。②参见张明楷:《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按照本文的观点,非法占有目的不是盗伐林木罪的主观要素,所以,盗伐林木罪的行为不一定符合盗窃罪的成立条件,于是,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就不是法条竞合中的特别关系。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则仅取决于案件事实。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伐他人所有的林木时,由于行为同时符合盗窃罪的成立条件,故构成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想象竞合;行为人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伐他人所有的林木的,则不成立盗窃罪,仅以盗伐林木罪论处,二者既不是法条竞合也不是想象竞合,只是中立关系。
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既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特别关系,故不能以主观目的或动机区分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一方面,盗伐林木罪的成立虽然不要求非法占有目的,但不排除行为人事实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一方面,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内容,也不能成为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区分标准。
例如,某判决书认定以下三起事实:⑴2014年11月1日至11月2日,被告人任某某雇佣程某某等人,在屯留县张店镇吴而村屯留国营老爷山林场林地内,盗挖油松43棵。11月2日晚21时左右,任某某将油松装车准备运走时,被屯留县林业执法人员在吴而村当场查扣。被盗43棵油松树经屯留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估价为15 050元。⑵2016年4月26日,任某某雇佣朱某、牛某某和秦某等3人,在屯留县张店镇寨上村屯留县国营老爷山林场圪岭洼林地内,盗挖油松一棵,当天下午15时左右,由王某某(刑拘在逃)带领闫某某驾驶挖机进入现场,用挖机将挖好的油松装上任某某的三轮车准备运走时,被寨上村村干部和屯留县林业执法人员现场查扣。经屯留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被盗1棵油松价格为2 500元。⑶2017年5月初,方某某(在逃)、王某某(在逃)与被告人任某某共谋实施盗挖油松。5月7、8二日,被告人任某某雇佣朱某某、刘某某、刘某某等8人在与屯留县吴而村交界的安泽县宋店村将军沟盗挖油松3棵,在准备用挖机将油松装车运走时,被接到报案的安泽县公安局森林派出所民警当场抓获。经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任某某等人盗窃的3棵油松价格为人民币130 000元。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任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雇佣多人盗挖油松,涉案总价值达人民币147 55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③山西省安泽县人民法院(2017)晋1026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任某某提出的上诉理由之一是,原判定性错误,应以盗伐林木罪对其定罪处罚,而非盗窃罪。二审法院则认为,“任某某组织他人盗挖油松后出售,以达到获利的目的,其主观上追求的和盗挖行为最终实现的都是活体油松的经济价值,而非木材的经济价值,侵害的是该油松所有权人的财产所有权,应以盗窃罪予以定罪处罚”,并认定该三起事实为盗窃罪未遂。①参见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刑终45号刑事判决书。
但在本文看来,这一判决存在疑问。其一,不管行为人是为了实现活木油松的经济价值,还是为了实现木材的经济价值,只要行为人擅自采伐了作为国家森林资源一部分的林木,就理所当然成立盗伐林木罪。其二,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不只是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而且包括他人对生长中的树木的所有权。本案行为人所盗伐的并不是村民房前屋后的树木,而是林场林地内他人所有的林木,既然如此,就不能否认行为成立盗伐林木罪。诚然,行为人的行为也的确成立盗窃罪。但是,不能因此否认盗伐林木罪的成立,只能按想象竞合处理。
总之,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不是特别关系。由于“盗伐”是指违反林木所有权人的意志,擅自采伐他人所有的生长中的林木的行为,故所有的盗伐林木行为都毁坏了他人财物。据此,可以认为,盗伐林木罪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特别法条。行为人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伐他人所有的林木时,由于行为并不符合盗窃罪的成立条件,故属于盗伐林木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法条竞合。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伐他人林木的,也必然触犯故意毁坏财物罪,二者同样形成法条竞合中的特别关系。
(二)盗伐林木罪的既遂标准
大体没有争议的是,行为人滥伐林木的,只要采伐了林木,亦即导致生长中的林木不能继续生长,就构成滥伐林木罪的既遂。关于盗伐林木罪的既遂时点,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判断标准。
有的法院将盗窃罪的既遂标准运用于盗伐林木罪中。例如,2014年8月7日晚,被告人何某甲、何某乙、何某丙携带大刀锯、卷尺等工具,来到婺源县大鄣山乡古坦村委会张溪村“破亭”(又名“高山碑”)山场盗伐属于该村委会村民洪某丁所有的杉木,并将盗伐的杉木堆放在便于装车的山塝上。次日凌晨,何某甲通知何某丁到山场运树,何某丁到山场后发现警车,便告知何某甲等3人逃跑。经勘验,现场遗留背包、大刀锯、手机、杉原木等物品。经检量,被告人何某甲、何某乙、何某丙3人在“破亭”山场盗伐杉木原木材积3.505立方米(“破亭案”)。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某甲、何某乙、何某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伐属于他人所有的林木,数量较大,三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盗伐林木罪。……被告人何某甲、何某乙、何某丙在盗伐婺源县大鄣山乡古坦村委会张溪村‘破亭’山场杉木时,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②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 (2015)婺刑初字第58号刑事判决书。本案中,被告人已经采伐了林木,并且将所采伐的林木放在便于装车的山塝上。法院认定为盗伐林木罪未遂,只是因为行为人还没有将盗伐的林木运走。显然,这一判决将行为人运走所采伐的林木作为盗伐林木罪的既遂标准。
有的法院认为,只要行为人已经采伐了林木(如已伐倒、已盗挖等),就成立盗伐林木罪的既遂。例如,2015年4月26日、27日,被告人张某某与张发明(已判刑)相互邀约,雇佣龙某等2人到富民县罗免镇马房村后山、秧田村小庙丫口山盗挖野生马樱花树,4月27日富民县森林公安局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被告人张某某与张发明将盗挖好的马樱花树49株,作案使用的皮卡车及锄头、铁锹等作案工具丢弃在现场后逃窜。经云南云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盗挖的49株马樱花树活立木材积(蓄积)共计6.7189立方米,价值人民币150 820元(“马樱花树案”)。张某某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某某系盗伐林木罪未遂,但法院认定张某某构成犯罪既遂。①参见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7)云0181刑初203号刑事判决书。还有判决明确指出:“盗伐林木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林木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制度,被告人黄凤牙实施了盗伐行为把树伐倒,且达到一定数量,就使国家的森林资源和环境资源以及国家对此的管理制度遭到破坏,属犯罪既遂。”②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20)赣0502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两上诉人虽然未将已砍伐的树木运离砍伐现场,但其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林木所有权,亦主要侵犯了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制度,只要两上诉人实施了砍伐行为,且达到一定的数量,即属于犯罪既遂。”③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池刑终字第00077号刑事裁定书。
本文赞成后一类判决的判断标准。一方面,如前所述,规定盗伐林木罪的条款并不是盗窃罪的特别条款,只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特别条款。盗伐林木罪虽然也侵犯了他人财产,但该财产是指生长中的林木,而不是任何木材。盗伐行为则是擅自采伐他人所有的生长中的林木的行为。所以,只要行为人擅自采伐了他人所有的生长中的林木,就不仅侵害了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而且侵害了他人对生长中的林木的所有权,应当认定为盗伐林木罪的既遂。换言之,盗伐林木罪的行为对象是他人所有的生长中的作为国家森林资源一部分的林木,构成要件结果是生长中的林木不能在原地继续生长。反过来说,不能将被害人所有的生长中的林木等同于普通木材,也不能将盗伐林木罪的构成要件结果理解为转移了被害人占有的林木。另一方面,盗伐林木罪的法定刑原本重于滥伐林木罪。如果对滥伐林木罪采取伐倒的标准,而对盗伐林木罪采取运走的标准,就可能导致在相同情形下,对二者的处罚不协调。亦即,在同样是将林木伐倒的案件中,如果是滥伐林木便认定为既遂,如若是盗伐林木便仅认定为未遂,就可能导致对盗伐林木罪的处罚可能反而轻于滥伐林木罪,这显然不合适。所以,上述“破亭案”的判决存在疑问。
当然,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虽然是盗伐林木,但如果由于没有达到盗伐林木罪的数量较大标准,因而被认定为盗窃罪时,则应按盗窃罪的既未遂区分标准予以认定。例如,2018年12月17日5时许,被告人柴某、王某驾驶吉利牌金刚轿车到阳城县町店镇崦山自然保护区,王某负责望风,柴某用事先购买的油锯盗伐林区内柏树5棵计蓄积1.353立方米,未转运后返回县城。当日林区管护员在巡查中发现被盗伐林木即安排人员蹲点守候。次日5时许,柴某、王某再次驾车来到崦山自然保护区,将所盗伐柏树抬至林区路边计划择日转移。7时许,二人驾车返回时被林场工作人员查获。经鉴定,被盗伐林木价值9 00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柴某、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盗窃罪。法院也认为,被告人柴某、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伐自然保护区内的林木,数额较大,其行为均构成盗窃罪,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属犯罪未遂。④参见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522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书。在本案中,被告人采伐的林木没有达到2立方米,不符合盗伐林木罪的数量较大条件,但由于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成立要件,故法院认定为盗窃罪是完全合适的。但在认定为盗窃罪的情形下,就只能将行为人或第三者实际占有了所盗伐的林木作为既遂标准。⑤如果行为人“将所盗伐柏树抬至林区路边”的事实,可以被评价为已经转移了对林木的占有,则本案构成盗窃罪的既遂。
(三)滥伐林木罪的违法所得
1993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滥伐自己所有权的林木其林木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的批复》指出:“属于个人所有的林木,也是国家森林资源的一部分。被告人滥伐属于自己所有权的林木,构成滥伐林木罪的,其行为已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规,破坏了国家的森林资源,所滥伐的林木即不再是个人的合法财产,而应当作为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依照刑法规定予以追缴。”这一批复虽然仍有效力,但由于其合理性存在疑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例如,被告人杨某甲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自家自留山林木83株,立木蓄积18.333立方米,并全部用于修建羊圈。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只是在判决中表述“另查明,被告人杨某甲所采伐的林木已用于修建羊圈”,而并未对赃物进行折价等其他处理。①参见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15)黔法刑初字第00027号刑事判决书。
再如,2016年7月17日至19日,徐某某、姜某某、赵某某等11人,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胡某某、赵某某雇佣多人一同砍伐徐某某、姜某某承包的树木,后胡某某、赵某某将这批树木卖予张某某,获取37 500元。经测算,现场伐根共75个,林木总蓄积量为47.6426立方米。2016年7月18日、19日,张某某在胡某某、赵某某未提供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仍以37 500元的价格收购其树木并卖予他人。一审法院认定徐某某、姜某某、赵某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但没有判决追缴被告人所滥伐的林木。②参见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17)苏0981刑初166号刑事判决书。一审宣判后,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被告人滥伐自己所有的林木,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规,破坏了国家的森林资源,所滥伐的林木不再是个人合法财产,应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原审判决未依法追缴,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抗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首先,《刑法》第64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是指行为人因实施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而取得的全部财物及其孳息,其重要的特征是该财物的来源必须违反刑事法律。在确定违法所得的范围时,应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的界限,注意保护不法行为人的合法财产。其次,依据《刑法》第64条规定,不得因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法所得而导致行为人双重受罚。对行为人尚未实施违反刑事法律行为即已依法取得的财物,不能界定为违法所得而进行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最后,刑法所规定的滥伐林木罪,与相近的盗伐林木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国家、集体所有或者他人依法所有的林木有着明显的区别。森林法中对盗伐林木案件规定了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而没有作出没收滥伐林木或者变卖所得的规定。本案滥伐林木罪中的林木,不是行为人实施违反刑事法律行为而取得的财物,不能界定为违法所得。③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9刑终307号刑事裁定书。
本文赞成上述判决的观点与理由。如前所述,《民法典》第331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森林法》第17条也规定:“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林地(以下简称集体林地)实行承包经营的,承包方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承包林地上的林木所有权,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承包方可以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转让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承包经营林地的行为人在没有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采伐自己所有的林木,虽然是滥伐林木的行为,但该行为只是侵害了森林资源,而没有侵害他人财产。换言之,行为人只是以违法的方式转让了自己的林木,而不是违法地取得了他人财产,故其林木并非违法所得。①参见寇建东:《滥伐林木罪中的林木未必是违法所得》,《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0期。如果对滥伐林木罪中的林木进行追缴,则侵犯了林木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不符合《民法典》与《森林法》的规定。这是因为,个人所有的林木虽然是国家森林资源的一部分,但行为人滥伐后的树木已经不再是国家森林资源的一部分,而是其个人所有的财产。换言之,滥伐行为只是侵害了国家森林资源,而非侵害国家财产,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只是使国家森林资源遭受破坏,而不是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故不能认为其所滥伐的林木属于违法所得。既然如此,就不应当追缴滥伐的林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