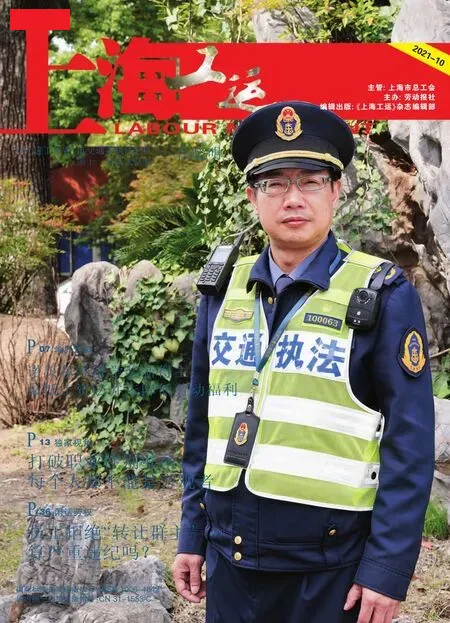结缘市宫第一期工人诗歌创作组
2021-01-28金洪远
◎金洪远
每当走过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时,我都会情不自禁驻足观望这座风采犹存的古典欧罗巴建筑。1950 年,老市长陈毅为市宫亲笔题书横匾——“工人的学校和乐园”。市宫这座建筑就像一座闪烁的灯塔,迎接一批批各行各业的工人来这里学习、休闲和娱乐。40 多年前,我曾荣幸与化工局诗友李士平、俞文达参加第一期上海工人诗歌创作组活动。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青春时光,诗友间赤诚相见、掏心掏肺,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不称老师唤“师傅”
第一次走进工人文化宫时,听见来自市里各工业局的诗友自豪地说,“我们是诗歌‘黄埔’第一期”,那抑制不住的喜悦难以表述。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一个仅发了几首小诗的小青工,怎么会被文化宫诗歌创作组选中,是不是撞了大运了。
犹记得在市宫负责创作组的吴士余第一次热情洋溢的讲话,记得当时在《解放日报》副刊的张鸿喜是创作组的召集人,他们的年龄约在30 岁左右,却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文艺评论和诗歌。第一次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对于我们在诗歌小道上艰难跋涉的爱好者来说,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告诫自己:珍惜这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
我不会忘记,当毛炳甫、居有松、陈晏等工人诗人出现在会议室时,我和一干诗友齐刷刷投去尊崇的目光。他们的诗篇激情讴歌生活、讴歌时代、讴歌火热工厂,对我们这些每天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青工来说,当然是感觉分外亲切和熟稔。工人诗人诗作里热辣辣的工厂气息,笔尖下汩汩流淌着的诗意从铁锤、船台、纺织机前传来,常常让我们捧读一遍又一遍,不能自已。我们都唤他们为“师傅”,因为他们朴素的面容、朴素的言语就像厂里朝夕相处的师傅一样,让人产生可以信赖的信任感。
我很荣幸,被分配在朱金晨为组长的“第一小组”。虽然我和金晨是第一次相识,但对他的作品早有耳闻,他刊发在沪上报刊上,描述建筑工人的诗作总会令我“眼前一亮”,我不禁发自内心喝一声“好诗”!那日,《解放日报》副刊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金晨的作品“建设者的窗口”,建筑工人艰辛劳作的场景,被金晨写得荡气回肠,如此诗情画意,令人击节赞叹、心生敬意。
我还记得,金晨向毛炳甫介绍我,操着一口宁波话的毛师傅拉着我的手亲热地说:“小金啊,知道,知道。”时光易逝,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毛师傅头上一顶鸭舌帽,鼻梁上一副大圈套小圈深度的近视眼镜的形象依旧清晰如昨,那随和可亲的目光从眼镜里折射出来,让人是很难拒绝叫上一声“毛师傅”的。
两年后,我赴金山参加工程建设,但在市宫结识的工人诗人依旧没有中断联系。我成家后,郑成义、居有松和陈晏结伴来我家小住,还带来了毛师傅对我的问候。工人诗人“不薄新朋爱旧友”的市宫情结让我又一次感动。虽然居有松、毛炳甫和陈晏师傅先后作古,但他们生前对学诗者的鼓励和提携,至今让我心怀感恩。
掏心掏肺诗友情
诗歌创作组的诗友来自各工业系统,大家文化程度高低不同,性格也各异,但长期工厂生活的锤炼,让他们坦荡无私、乐于助人。在我的脑海里,他们都一样的可敬可亲。
毛炳甫当时是有名头的工人诗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代表上海工人作者参加过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但他为人谦和低调,没有一点架子。唯一高调的是他戏话连篇,走到哪个小组,笑声就从哪里飞出。就像在车间里喜好搞笑的师傅,总是受到工友们欢迎和追捧。
记得有一位年轻的业余作者有点内向,毛炳甫不是一本正经地开导,而是自嘲自个儿是“扫盲班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仔”,旁人被他寻自己开心逗得忍俊不禁,他却一本正经地肃着面孔,很有冷面滑稽的范儿。我一直想,他怎么不改行去讲独角戏!
居有松是沪东造船厂出来的工人诗人,一口“刮啦松脆”的苏北话很有特点,诗友递上诗稿请他指教,他往往是用苏北话抑扬顿挫朗读起来,然后逐句点评。看来他是很讲究诗歌的“上口”,我至今还记得他写造船工人的诗作的豪迈气概。“千山万水站起来看,看咱徒弟闹竞赛,擂台对着江和海,你们要船这里来”。将造船工人火热的心怀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有韵有味。
陈晏的热心在诗友中是有口皆碑的。他才思敏捷,论诗改诗很见功底。
活动中间休息的时候,时不时有诗友递上习作请他指点,这当儿,他总是习惯点上一支烟,在袅袅的烟雾中就诗稿的立意、构思一一点评。他客观中立的评诗风格,让一干诗友连连点头、心悦诚服。陈师傅评语非常精彩和独到,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做人要老实,但写诗不能太老实,诗要有诗意,如果没有诗意,就成了标语和口号”。更多时候,他用笔在初稿上勾勾划划,为诗友淬炼诗句,你还别说,经他妙笔生花这么一改,稚嫩的习作立马像十八岁的姑娘变得“弹眼落睛”,像模像样。
虽然创作组活动规定晚上九点结束,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如饥似渴,总嫌时光过得太快。散场前,我们总喜欢一齐到张鸿喜周围,听他传经送宝。有一次张师傅问我:“小金,你是怎么写诗的?”“怎么写诗的?我是想到就写的”我回答道。他笑了,竖起三个手指告诉我,他构思一首诗,无论是长诗还是短诗,都要酝酿从不同角度写三首,从中精心挑选其中最佳的角度进行反复打磨,直到满意后才投给报刊。
原来一首好诗是这样练成的,作为初学者的我们醍醐灌顶。现在回想起来,他后来改写歌词,如人们耳熟能详如电影《日出》、电视剧《家·春·秋》的优秀词作,深得曹禺和巴金的赞叹,确实难能可贵。而风靡一时电视剧《济公》的主题歌“鞋儿破、帽儿破”能直抵人心,广为传唱,是不是他当年虔诚的诗心,从“三首”里“磨”出来的呢?
印象深刻的讲座
我至今感恩市宫为我们第一期诗歌创作组举办了多场诗歌讲座。当时主事者是吴士余,善解人意的他不辞辛劳请来了多位沪上名编辑、名师、知名诗人为我们解疑答惑,这对在诗歌上尚“一穷二白”的我们绝对是“给力”。传授者在台上讲,我们屏息静听,那笔尖在工作手册上滑动的沙沙声,像极了蠕动的春蚕在桑叶上贪婪地、细细地咀嚼桑叶发出的细响。
令我印象最深有三位演讲者。
第一位庄稼。他当时是《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清俊的面容,修长的身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口不疾不徐的浙江官话。他把副刊选稿的标准一一道来,从业余作者来稿中常见的“不足”之处一一开列。到底是资深老编辑,一下子抓住了我们投稿中“多发病”,就像给摸黑前行我们,齐刷刷地亮起了指路明灯。散场后,一干诗友评价说:“老庄的讲座简明扼要,没有一丁点官话和套话,全是实打实的干货,太受用了!”顺便提及一下,当时不流行叫“老师”,即使有人叫了,庄稼总会和颜悦色地相告:“叫我老庄亲切。”
第二位是王宁宇。宁宇是沪上著名的诗人,在我家中书橱里就有他的诗作,选登在国内名家荟萃的“朗诵诗选”里。无可置疑,他我们心中敬仰的大咖。宁宇讲座的特点是现身说法,他从自己的学诗写诗的历程娓娓道来,时不时自嘲和开涮自个儿是个“笨鸟”,不时引发会场一阵阵笑声。
看得出,诗人宁宇有备而来,事前一定有人“通风报信”告知他,有部分诗友因基础差、底子薄而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诗人宁宇这把钥匙打开了诗友的心结,有不少自认为不少写诗料的诗友坦言:“虽然我不可能达到宁宇的‘高度’,但只要用心、上心,再加上一点点悟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获。”
第三位是吴欢章。吴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的教师,经常在报刊上刊登诗歌的评论文章,这次目睹其风采,让初出茅庐的我们领教到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口才。吴老师旁征博引了不少经典诗作,告诉我们,诗要“写自己熟悉的工厂生活”,诗要“真情实感,只有自己动情了,才能打动编辑和读者”。
我记得吴老师当时还对参会诗友一首歌颂“苏州河”的小诗进行了即兴点评,诗中有一句“苏州河水作明镜”,他首先肯定了这居住在苏州河旁作者的“热情”,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吴老师说,苏州河“墨墨黑”上海人都知道,怎么能作“明镜”?这是违背生活常识的,不如改为“誓将河水作明镜”来得更为生动和确切。当时我们在讨论这首小诗时,对“苏州河水作明镜”赞誉有加,认为颇有诗情画意,经吴老师一番点拨,茅塞顿开,原来诗要高于生活,但不能违背生活,违背生活是要闹大笑话的。这首经吴老师点评和经作者修改的诗,不日即刊登在文汇报副刊上。
梦想起航的地方
当年参加市宫第一期诗歌创作组时,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如今是一脸沧桑“奔七”人了。每当我路过西藏中路,总会驻足,对她深情凝望,在别人眼里,文化宫只是一栋七层的始建于1929 年的古典欧罗巴建筑,但在我的眼里,她是我永远怀恋的地方。
我在这里学习,起步,感受车间师傅们为我圆诗歌梦默默无闻地辛勤付出;深感实收诗友掏心掏肺,为对方喝彩的氛围,感受工人诗人真诚,坦率和豪爽。就像不久前刚去世的老诗人王森在化工局曾在诗友聚会上所言:“市宫是工人业余作者的摇篮和园地。
“我的那首‘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的初稿就是在市宫的图书阅览室里草就的,是市宫目送着这首短短的民歌插着音乐的翅膀飞出上海,飞向神州大地。
“八十岁那年,我的歌词作品研讨会也在市宫举行,市宫培养、哺育了我,我对他怀有深深的难以割舍的情愫。”
这座曾为旅店的建筑,曾经展开她温暖的手臂,将一批批工人业余作者揽入她宽厚的胸怀,让他们在人生的驿站歇脚、充电,让他们积攒了能量去奋力远航。在市宫结识的吴士余和朱金晨等人成了沪上新闻出版和诗坛上的知名人士,更多的成了各行业的业务骨干。
抚今思昔,我想对当年参加市宫第一期诗歌创作组的诗友深情地问一声:你们好吗?还记得市宫诗友间相互欣赏热情交融的场面吗?还记得提携我们、传帮带的工人诗人和讲座的老师吗?还记得当年的我们对诗歌一往情深的向往和憧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