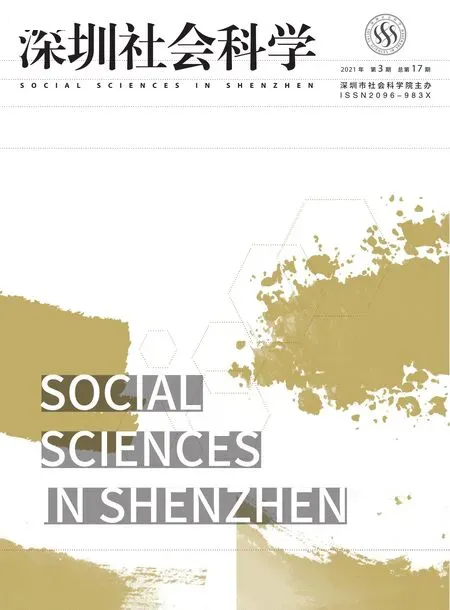批评何为?*
——雅斯贝斯论莱辛的诗学思想
2021-01-28孙秀昌
孙秀昌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①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汉译卡尔·雅斯贝斯、卡尔·雅斯贝尔斯、雅斯培等。本文正文统一使用雅斯贝斯,简称雅氏;在尾注所列参考文献中,笔者尊重原译者译名。的思想版图中,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是一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与“唤醒者”。他总是不断地搅动那些怠惰、固执、傲慢的“世俗实存”(mundane existence,意指“常人”、“大众”)诉诸主客分立的“一般意识”(consciousness at large)所建构的静态化、封闭化、独断化的观念体系,期待他们从一劳永逸地掌握或占有实体化真理的迷梦中苏醒过来,呼唤他们要敢于在世界之中断然地立足于本真、灵动、温煦的“生存意识”(consciousness of Existenz)与诚实、公正、开放的批判理性采取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行动,进而永不休歇地行进在通往整全的真理的途中。鉴于此,雅氏把莱辛看成是伟大的哲学家,在《大哲学家》(Die Großen Philosophen)第一卷的“导论”中,他将莱辛列入其构拟中的四卷本《大哲学家》的第二卷(第二大组)名录,并将其与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一并称为“伟大的信仰复兴主义者”[1](P20)。令人欣慰的是,雅氏在生前已经完成了第二卷的大部分文稿,这些文稿经萨尼尔(Hans Saner)编辑后已被完好地收入《大哲学家》(遗稿1-2卷)中,其中就包括雅氏列专章阐说莱辛的文字。[2](P346-415)1995年,伊迪丝·埃利希(Edith Ehrlich)、伦纳德·H.埃利希(Leonard H.Ehrlich)将其中关涉笛卡尔、帕斯卡尔、莱辛、克尔凯郭尔、尼采、爱因斯坦、马克斯·韦伯、马克思的部分译成英文出版,并将“伟大的信仰复兴主义者”(Die groben Erwecker)译成“伟大的唤醒者”(The great awakeners)。就第二卷中关涉莱辛的文字来看,雅氏重点阐说了莱辛的生平与作品、文学成就与诗学思想、哲学思想、神学思想以及他在德国古典时代与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影响等话题,可以说这些文字已是一部相对完整的莱辛专论。
莱辛在我们的印象中首先是一位诗人、艺术评论家,不过,他留给后世的那些彪炳千秋的文学作品、艺术评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影响并未局限于文艺界;我们同时知道,雅斯贝斯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固然不会轻忽莱辛的文学作品与艺术评论著作的地位,不过他终究不会像某些专业化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那样对莱辛的这些文字从文艺本身的角度作出更多的诠解。作为哲学家,雅氏一以贯之的态度就是他在《哲学》第三卷中所说的“在艺术中思考,而不是思考艺术”[3](P168);进而言之,他所思考的并不是艺术本身的幽趣,而是涵淹于艺术中的那种唤醒生存意识的独特力量。正是在这里,艺术成为哲学的器官,艺术家论遂成为其哲学家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此前已对这个话题作过探讨[4](P205-208),这里只强调如下一点:也正是基于其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的视域,雅氏才会在更为根本的基源处——“生存”(Existenz)是艺术与哲学共有的基源——与莱辛相遇,并对莱辛的作品作出了别具意趣的品评:“在文学史上,莱辛作为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占有一席之地。在将他视为哲学家中的‘唤醒者’来解读方面,我认为他的伟大之处主要并不在于那些虚构的作品。不过,莱辛作品中诗作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须得提请人们牢记于心的。”[5](P13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雅氏从未小觑过莱辛作品中诗作的地位,不过须得注意的是,既然要将莱辛解读成一位哲学家中的“唤醒者”,雅氏自然会把涵淹于莱辛作品中的“唤醒”力量作为其品评的重心。鉴于此,雅氏在专论莱辛的文字中颇为看重“批评”之于莱辛诗学思想的核心地位,具体说来,他是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品评的:其一,作为诗人的自我理解;其二,批评与诗意的想象;其三,批评与启蒙精神。
一、作为诗人的自我理解
莱辛是一位颇富理性精神的诗人,这种理性精神不仅表现在对他人的批判性审查上,而且表现在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的批判性反思上。雅氏就此指出:“我们拥有莱辛在人生的各个时期对自己的文学活动所作的评价。这些评价全都关涉他的作品中反思与诗歌之间的关系。反思与诗歌是密不可分的,不过反思性的思想则居于首要的地位。”[5](P135)所谓“反思性”,指的是自我质疑、自我抗辩、自我扬弃。纵观莱辛一生的文学活动,他正是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审查、自我理解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的。鉴于此,雅氏辐辏于“反思与诗歌之间的关系”,就莱辛分别在《论寓言的本质》、《汉堡剧评》中进行的自我理解作了深入的阐发。
(一)莱辛在《论寓言的本质》中进行的自我理解
雅氏看到,莱辛一生酷爱寓言,他不仅喜欢阅读、使用寓言,而且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寓言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审查与深刻的自我理解。雅氏特意谈及莱辛1759年出版的《论寓言的本质》一书,格外强调了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对自己发表过的作品所作的批评:“在表达‘最初的不悦’时,莱辛写道,‘通过持续追寻更加美好的事物,我现在可以为年轻时所写的那些轻率之作赎罪了,或许到最后,我会将它们弃于脑后甚至全部遗忘’。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他很想抛弃早期的全部作品。然而,他紧接着又考虑到那些‘怀有好感的读者’。难道他应该将这一看法——他们的赞许乃是浪费在了完全无价值的东西之上——曝之于众吗?‘你们宽容地鼓励着我,希望我通过在作品中加入足够多的富含真正价值的内容,并且这些作品的表述是极其恰切的,足可表明它们已意识到了内在的承诺,借此来努力证明你们的判断乃是正确的。因此,我决定尽可能地采取改善的态度,而不是随顺最初的冲动去抛弃那些早期的作品’。”[5](P135)雅氏在这里以其惯常使用的“理解-描述”的方法真实地呈现了莱辛当时的心路历程,从中可以看出,莱辛之所以会对过去的作品大为“不悦”甚至产生了“赎罪”之感,乃是因为他要持续地追寻更加美好的事物。在更加美好的事物的吸引下,莱辛起初很想抛弃那些早期的作品,不过考虑到那些“怀有好感的读者”的宽容与策励,他准备为作品“加入足够多的富含真正价值的内容”进而实现其“内在的承诺”。我们知道,莱辛的心灵始终是向公众开放的,这种基于爱与真诚而进行的生存交往让善于自我审查的莱辛能够健朗地行进在祈向纯然真理的途中。于是,他最后决定采取“改善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抛弃过去,而是扬弃过去。正是通过这种扬弃的态度,莱辛终于在不断尝试与探索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超越。
越是自己所酷爱的东西,就越要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这是莱辛一以贯之的立场。那么,莱辛为什么如此酷爱寓言呢?他撰写《论寓言的本质》一书的心曲又何在呢?雅氏就此写道:“莱辛从早期的作品中选取了大量的寓言。‘我喜欢处在诗歌与道德所共有的那个边界上的寓言’。他读过全部古代的寓言和新近的寓言,并对寓言理论进行过思考,这‘引导着他撰写了目前这部作品’。他起笔就奚落‘人们要么因着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而像搞研究一样做笔记,要么并不注重表达的精确性而仅仅满足于思索那些思想,要么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尝试着记下那些梗概’。在现阶段,‘对于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书来说,仍缺少很多的东西’ 。然后,莱辛告示读者这部作品最终会是怎么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它将作为一部寓言集而面世,书中另附有关于寓言的若干篇论文。”[5](P135-136)这里需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莱辛之所以喜欢寓言这种文体,乃是因为它“处在诗歌与道德所共有的那个边界上”。莱辛从来就不是那种“为诗而诗”意义上的诗人,他写诗的目的是教育人类,其最终的归趣在于使人成为人。于是,“处在诗歌与道德所共有的那个边界上”的寓言便成为他自觉选择的一种用于启蒙大众的文体。由此可见,寓言在莱辛的心目中是与其启蒙大众的职志紧密相连的,尽管国内已有少数学者(如李淑[6])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整体来看人们通常还是把寓言仅仅当成是一种有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文体。就此而言,我们重温雅氏当年所作的提醒,仍是大有裨益的。其二,莱辛之所以要撰写《论寓言的本质》一书,乃是为了反拨当时的种种弊端,以便能够写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书”。莱辛在此反拨的时弊主要是那种脱离作品实际的知识化、抽象化、实用化的做法,他所期待的那部“真正意义上的书”理应实现寓言作品与对寓言实质之理解的内在统一。鉴于此,“莱辛要求他的读者,‘莫要脱开这些论文来评判那些寓言,其中的原委在于,即使我并没有为了增进对寓言的理解而撰写这些论文,也没有为了增进对论文的理解而创作那些寓言,但是二者——就像那些齐头并进而同时到来的事物一样——之间的相互借鉴程度是非常大的,并不能保持彼此独立与隔绝的状态而不受对方的影响’”[5](P136)。在莱辛看来,一位诗人对寓言实质的理解与他创作的寓言作品之间不能彼此独立、彼此隔绝,而是应该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成全的。进而言之,一位诗人在创作寓言的过程中,理应深刻理解寓言这种文体的本质,以便能够依循自己的理解进行创作,这样一来,他所创作的作品也就体现了寓言的本质。
由此可见,正如《论寓言的本质》一书的书名所标示的,莱辛所关心的乃是寓言创作中的根本性的东西。那么,对莱辛颇为看重的寓言创作来说,什么是根本性的东西呢?难道就是作家们通常所总结出的某些“规则”吗?雅氏敏锐地发现,莱辛并不是这样看待的:“莱辛郑重声明,如果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我谈论的这些规则并不总是与那些作品相符’的话,那么他就愿意毫不犹豫地抛弃那些寓言。他就此断言,读者理应‘晓得,天才总是倔强而执拗的,他们很少会有意地遵循规则来创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规则意在修剪那些过度的部分,并不会抑制作家的天赋。因此,就请读者在那些寓言中鉴察自己的品味,并在这些论文中检验我的论证吧’。”[5](P136)莱辛是一位颇富创造力且影响深远的天才诗人,他所创作的那些寓言并未有意地遵循任何一种外在化、抽象化、教条化的“规则”,说到底,他是根据自己对寓言之实质的理解进行创作的。如果说经由天才诗人切己的理解所提出的某些看法也算是规则的话,那么“这些规则意在修剪那些过度的部分,并不会抑制作家的天赋”,而且这样的规则可以鉴察出读者的品味并经得起读者的一再检验。莱辛就此肯定了他对自己创作过的寓言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自我理解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而打算把这种做法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推广开来:“莱辛打算把他处理寓言时所使用的这种方法同样运用于其他类型的作品。他想重新考虑、调整与补订迄今所创作的以及未来将要创作的作品。他曾对自己行之有效的经验作过如下描述:‘只要行家里手计划非难、搜集、挑选、整理这些想法,并且将它们划分成若干个话题,他就会为自己孕生出多种有益的构想而感到欣喜若狂。不过,他一旦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着手将自己的创意变成文字,那种分娩的阵痛就出现了,而他并不乐意在没有鼓励的情形下去忍受这种阵痛。’”[5](P136)莱辛重新考虑、调整与补订自己创作的各种作品的过程,也正是他通过自我审查“非难、搜集、挑选、整理”自己的各种想法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深化着对作品的理解,同时“孕生出多种有益的构想”。这些有益的构想乃是诗人借助于自我理解而在心灵中新结胎的创意。当然,若想把这些创意变成新的作品,其间尚需经过“分娩的阵痛”,而读者建立在生存交往基础上的鼓励则可以使诗人把这种阵痛降低到可以忍受的程度。由此可见,无论是旨在审查自我的理解还是意在审查他人的理解,它们在创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是不可小觑的。对莱辛来说,这种批判性理解的地位甚至可与作品创作平分秋色。
(二)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进行的自我理解
雅氏认为,《汉堡剧评》是莱辛将他在《论寓言的本质》中使用的自我审查、自我理解的方法从寓言领域推扩到戏剧领域的典范之作。于是,雅氏对此作了专门的阐说:“莱辛在《汉堡剧评》(1769)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先谈谈我自己吧’:‘我既不是演员,也不是诗人’。他只是试着写些戏剧。‘最初尝试着写那些剧本,是把表现乐趣和愉快当作天才的目标。我充分地意识到,最近创作的任何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我只将其归功于批评。我觉得那眼流淌于心的活泉并不是靠着自身的力量喷涌向上的,也不是靠着自身的力量喷射出如此丰富、如此新鲜、如此纯净的水柱的:我须得用力地挤压我自己,以便把这种压力输送进条条喷射水柱的管道。假如不是勉力学会了谦恭地借用他人的珍宝,借助他人的火堆来温暖自己的身子,我就会沦为一个极其贫乏、冷漠、短见的人了’。”[5](P136)莱辛的《汉堡剧评》迄今仍饮誉文艺批评界,然而它的魅力究竟何在呢?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内有的学人(如刘鸿庥[7])看重其对古典主义的批判,有的学人(如钦文[8])更看重其对英法戏剧的批判与接受,有的学人(如冯钢[9])则把目光聚焦于《汉堡剧评》的表演艺术观……诸如此类的看法仍拘囿于某一具体的批评对象或学域。相较之下,雅氏的评说显然更为彻底,他在此给出的解释是,《汉堡剧评》的魅力恰恰在于莱辛对“批评”的重要功能的强调与运用。莱辛所说的“批评”不仅是指向他人的,更是指向批评者自身的,这里所谓的“我既不是演员,也不是诗人”就是典型的自我批评。正是通过自我质疑与自我理解,莱辛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位戏剧家的职分所在,进而对自己最初撰写的那些剧本进行了自我扬弃、自我净化与自我提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莱辛认为自己最近创作的任何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其成功的秘密只在于“批评”所发挥的作用,如此鲜明地标举批评的独立地位的态度在整个文学艺术史与文艺批评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这种态度在批评与创作各行其道、彼此睥睨的当下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了。对莱辛来说,个体生存中既有的创造天赋宛如一眼活泉,仅靠天才诗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喷涌向上”的,更遑论“喷射出如此丰富、如此新鲜、如此纯净的水柱”了;进而言之,天赋的灿然喷射需要莱辛这样的天才诗人“用力地挤压我自己,以便把这种压力输送进条条喷射水柱的管道”。莱辛用以挤压自己的力量,说到底就是“批评”所具有的唤醒力与澄明力。莱辛就此彰显了批评本身的独特力量,并向这种独具魅力的“批评”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莱辛对批评的作用心存感激,这种意识令他在读到或听到有人指控批评会抑制天才时就‘大为光火’。‘我自己是一个蹩脚之人,因此,对我所依靠的拐杖的抨击并不可能启发我的思考’。”[5](P136)莱辛在这里把自己比作“蹩脚之人”,把“批评”比作自己“所依靠的拐杖”,其实这个比喻的旨趣仍在于提示批评的重要作用:具有创造力的个体生存只有依靠批评的澄明力,他才能把自己既有的天赋唤醒出来,进而使自己始终行进在奔赴纯然真理的正途中。按照莱辛的理解,这样的批评从来都不会抑制天才,因而他才会对那种武断的指控“大为光火”。
《汉堡剧评》不仅是戏剧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且是整个文艺批评史上的典范之作,它的地位堪与《歌德谈话录》《芬奇论绘画》《罗丹艺术论》等相媲美。莱辛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与批评实践,使创作与批评实现了内在的统一,这种做法迄今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更为关键的是,莱辛格外强调了批评的独特力量与不可轻忽的地位,从而使批评这种文体形式在自己身上实现了自觉。莱辛的批评自觉在其全部的艺术评论著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评论中,莱辛通过从原则上区分相关的范畴来阐释文学与艺术作品,并借助于对这些特定作品的阐释让问题变得明晰起来。”[5](P133)莱辛的艺术评论别具一格,一般人难以品出个中的滋味来。拿他的《拉奥孔》来说,迄今仍有不少学人(如王为群[10]、张辉[11]、徐玫[12]等)将这部著作的重心归结为诗与画的关系及其具体区别,甚至为莱辛谈及的某些具体观点争论不休。按照雅氏的看法,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中提出的某些具体观点,而在于其使用的方法,亦即从原则上作出“区分”,这种区分的方法让那些探讨的问题最终“变得明晰起来”。可以说,莱辛的“区分”方法同样是其批评自觉的具体体现,它以其理性精神所特有的澄明力量为后世的艺术批评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动力与活力。
二、批评与诗意的想象
由于对“批评”这种文体形式的格外看重,雅氏又辐辏于“批评与诗意的想象”这一话题对批评在莱辛这里的独特韵致与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莱辛看来,批评就其自身而言就是至高无上的形式。‘我自认为是从密切接近天才的东西那里获得了批评这种才能的’。这让他慢工出细活,让他持续不断地进行旨在激励自我超越的批判性反思(‘毫无疑问,我最初的那些想法比起其他每个人来一点儿也不强,不过脑子里灌满别人想法的人最好还是待在家里’),这种批判性反思本身就有其不可轻忽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他撰写那些文学批评的目的,乃是为了给批评赋予一种更加成熟与有益的角色。后来,这些篇目都收进了《汉堡剧评》一书里。”[5](P136-137)莱辛所谓的“批评”,指的是凭借公开运用理性的权利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种批判性的反思“旨在激励自我超越”,它通过辨析对象、厘定界限、敞开空间、觅得基源,进而为诗人拓辟出一条通向纯然真理的道路来,因此,“批评就其自身而言就是至高无上的形式”。这样一来,莱辛便立足于批判性反思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为批评赋予了更加成熟与有益的角色,这也正是他撰写《汉堡剧评》的指归所在。基于上述考虑,莱辛对批评的作用同样给予了颇高的评价:“莱辛就批评的这种作用宣称道:‘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勤奋努力而感到骄傲:可以说,我已仔细检验了剧本创作这门艺术……我也通过充分的实践让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享有了发言的权利……就我无力去做的那些事情而言,我仍然能够判断自己能否去做。’”[5](P137)如果说这里所谓的“检验”指的是批判性反思,那么这里所谓的“实践”指的就是在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同时而进行的戏剧创作。正是通过批判性反思与戏剧创作的内在结合,莱辛在戏剧艺术问题上“享有了发言的权利”,这种发言的权利说到底是一种诉诸自我理解、自我审查、自我调整、自我引导的判断力,莱辛凭借这种判断力不仅意识到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意识到不能够做什么,进而提醒自己在探索戏剧艺术的道路上切莫误入歧途。
回溯莱辛戏剧探索的历程,雅氏发现他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汲取了避免误入歧途的智慧:“确保莱辛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研究而并未误入歧途的秘密是:‘我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从活跃于希腊舞台上的无数杰作中抽取出来的那些观念完全一致……,特别是我考虑到自己能够(就悲剧问题)无可置疑地证明,如果不想稍许偏离完美之境,那么悲剧就寸步也不能脱开亚里士多德的引导。’”[5](P137)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是建立在古希腊悲剧创作实践基础之上的,他从无数杰作中抽取出来的那些“观念”本来就不是任何一种僵化的教条,正因为如此,莱辛认为这些观念仍旧能够引导后世的悲剧创作;也正是基于自己对悲剧问题所作的理解与评价,他敏锐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洞见给后世带来的各种最极端的后果:“与‘我们的感觉’背道而驰的是,法国悲剧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规则所建构起来的那些先入之见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些英国戏剧唤醒了沉睡中的我们’。”[5](P137)后世在接受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影响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极端:其中的一端是法国悲剧(指的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它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规则化约成“三一律”之类的教条,莱辛对种种出于“先入之见”的教条颇为反感,认为它们并不能够指导现实的戏剧创作;另一端则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戏剧,这种戏剧并没有什么先入之见,而是以其诗意的想象“唤醒了沉睡中的我们”。有意味的是,这种缺乏确定规则的戏剧反而得到了莱辛的赞许:“被这束突如其来的真理之光刺得睁不开眼睛,我们反而又被弹回另一个深渊的边缘。英国戏剧缺乏……确定的规则……,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即使没有这些规则,我们也能实现悲剧所要达到的目的。……可是,人们一旦从这些规则入手,就会把所有的规则都弄乱套了,进而会因食古不化——天才应被告知什么必须要做以及什么不需要做——而遭受谴责。”[5](P137)事实上,莱辛在这里的看法与康德提出的“天才就是那天赋的才能,它给艺术制定法规”[13](P152)不谋而合。对莎士比亚一类的天才诗人来说,即便没有规则,他们也能凭借自己的天赋才能“实现悲剧所要达到的目的”;相较之下,从先定的规则入手的“法国悲剧”却因其“食古不化”而遭到了莱辛的批评。在莱辛看来,“法国人”(指的是那些泥守“三一律”之类教条的人)的岐误在于,他们从主客分立的“一般意识”出发,割裂了悲剧理论与悲剧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严重误解了古代戏剧的法则”,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戏剧作法的理论中的一些外部特征视为戏剧的本质,这反而削弱了那些至关重要的部分”[5](P137)。人们诉诸一般意识只能认知现象性的东西,而无从把握戏剧的本质。若想把握戏剧的本质,只能诉诸超越主客分立的“生存意识”与“诗意的想象”,并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对其进行唤醒与澄明。然而颇为遗憾的是,法国人却以那些教条化了的“规则”翦杀了亚里士多德理论中活的精神,诸如此类的规则只会以寡头化、独断化的姿态阻抑诗人发挥自身的天赋才能。
当然,莱辛并没有一概而论地否弃戏剧规则。雅氏就此指出,“规则确实是存在的”,莱辛所认可的那些戏剧规则乃源自于“天才自身所富有的创造力”。从根底处看,它们“并不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而是从天才富有的创造力本身所产生的规则那里汲取来的”,鉴于此,“莱辛认为自己就有能力来改进伟大的剧作家高乃依所写的每一部戏”。[5](P137-138)尽管高乃依也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但是若将这位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奠基人与更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相比,无论在提出问题与处理问题的方式上,还是在性格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上,抑或在视野的开阔与自由度上,他的作品因缺乏诗意的想象仍是颇显促狭的。基于上述评判,“莱辛把法国悲剧从它一直享有无上权威的宝座上推了下来。他就此发现了莎士比亚”[5](P138)。其实,莱辛在学生时代也曾受到过法国戏剧的影响,不过随着批判性反思的不断深入,他终于唤醒了自己的创造天赋,进而在沿着属于自己的道路勇毅前行的过程中扬弃了法国戏剧。
三、批评与启蒙精神
莱辛的作品(艺术评论著作)以及弥漫于其中的“理性的气氛”是其时代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雅氏看来,莱辛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迫切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时代,在这个光明与黑暗剧烈较量的时代里,一种使德国人真正成为其自身的德国精神正在一批呼唤纯粹人性与个体自由的伟大思想家的艰辛孕育下渐愈形成。“这乃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德国古典文学培壅着地基的一种文化,凭借着这种文化,德国人真正地成为了其自身。今天,我们仍然凭借我们的古典文化遗产继续做着真正的德国人。”[5](P187)雅氏认为,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如果说歌德乃是“打开真正的解放与自由之门的第一人”,那么莱辛则是推动德国文化转型的“先驱者、开拓者与拯救者”:“在德国古典主义时期,歌德是打开真正的解放与自由之门的第一人,正是他透过众多的西方观念而使那解放与自由之门得以洞然敞开。莱辛作为一位先驱者、开拓者与拯救者,他尚未进入由他自己所筹划的那块领地。但是,根据历史的观点并在此引导下,将莱辛视为推动德国文化转型的先驱,这对于所有的时代以及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在古典领域取得了一流成就的人们)来说都是恰当的。”[5](P187)如果说歌德是以其提出的“世界文学”的观念最终奠定了他在德国古典时代不可撼动的地位的话,那么莱辛则是以其清澈澄明的理性气氛、批判性反思的生命智慧最终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先驱者、开拓者与拯救者”的。莱辛的一生固然没有歌德那么幸运,他固然“尚未进入由他自己所筹划的那块领地”,不过这位一直行进在通向纯然真理之路上的探索者始终为自己留住了一个不可摇夺的信念:“生活在每个时代的每位个体其实都是‘与上帝比邻而居的’存在,他们就活在当下,并为着最好的自己而生活。”[5](P187)作为“与上帝比邻而居”的生存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理应真诚相待、真心相爱,为的是祈向一个纯粹的人性涵淹于其中的精神共同体,正是基于内心涌动的这个不可摇夺的信念,莱辛对经验世界中一切可能独断化、教条化的事物不断地审查着、扬弃着。正是在这里,雅氏发现了莱辛的伟大之处:“莱辛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倦地努力着,并树立了一个恒在的范本,或许对今天的人们仍具有特殊的意义。”[5](P187)应该说,这里的“或许”(perhaps)一词完全可以去掉。
莱辛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迫切需要启蒙并且涌现出了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的时代,渴望在世生存的莱辛以其真诚、公正、开放的理性精神介入了这个伟大的时代,于是,这位坚持不懈的思想开拓者为解决时代难题付出的种种努力便具有了另一重意义:“莱辛的世界属于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这是一场发生在欧洲上层社会的智力运动,随着民族气质和状况的不同而不断得到改进,它最早发生在英国,随后是法国,继而是德国,并越过这些国家而蔓延开去。”[5](P187)相比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启蒙运动的消息来得较迟些。在莱辛之前,诸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荷兰犹太裔哲学家斯宾诺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都已曾试图通过自然宗教、道德与法律来指导人们的生活。从整体性征上看,这一时期的启蒙运动在科学发展的影响下,弘敷进步的观念,强调变革的意志,思想家们主要致力于一种旨在开启民智、改造社会、争取更多自由与权利的“智力的启蒙”。这种“智力的启蒙”固然在没有读写能力的大众阶层中收效甚微,不过对受过教育的各个阶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意味的是,当莱辛受到前辈思想的激发而独自踏上启蒙之路后,他却与当时趋于思想的单义性、确定性的主流启蒙思想家们渐行渐远了:“莱辛远离了启蒙运动的单义性及其寓于精确明晰的思考中的那种单纯的确定性,在他看来,追求思想的单义性与确定性正是启蒙运动犯下的根本性的错误。”[5](P162)思想的单义性、确定性是有悖于理性的批判性、澄明性的,这种倾向虽然得到了科技理性与实证方法的支持,其经过确定性的思考得出的那些单义性的结论也容易为大众阶层所接受,但是它却从根底处丧失了理性启蒙的活力,因而遭到了莱辛的批判与审查。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莱辛的思想世界固然属于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不过他那弥漫着“理性的气氛”的思想世界从一开始就与主流启蒙思想家们保持着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距离,从而在启蒙运动内部开辟了别有意趣的另一种面向。就此而言,在德国古典时代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只有康德能够与莱辛——“德意志民族的这个伟大的儿子”[14](P214)——相媲美。
莱辛的作品对中国文学界来说并不陌生,不过这些作品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美国学者维塞尔(Leonard P.wessel)在《启蒙运动的内在问题——莱辛思想再释》一书中将弥漫于莱辛作品中的“理性的气氛”(批判性思维)比作“思考酵母”,可以说这个比喻是颇为恰切的。至于“如何认识莱辛‘思考酵母’之确定内容”,研究者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无不感到颇为棘手。“也正是由这一点开始,研究者们分道而行了。在莱辛思想探索方面,研究者们得出各种具体的结论,所依据的,是自己对莱辛的思考酵母、思想方法或莱辛关于真理概念构成要素所做的分析。”[15](P4)就此而言,雅斯贝斯依据其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对莱辛所作的诠释,无疑为莱辛研究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域与范式——生存哲学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