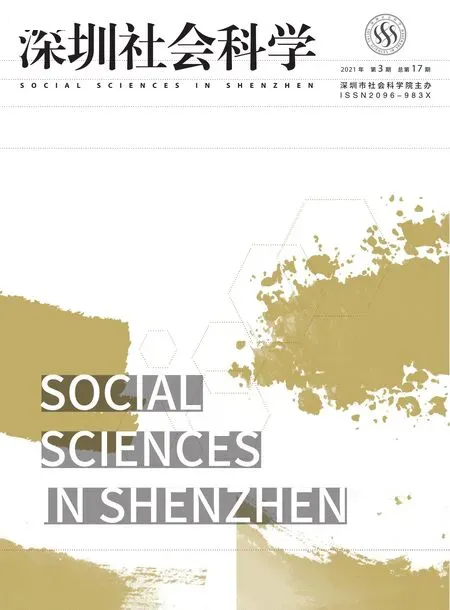中西印哲学中的“出世”与“入世”观念比较
2021-01-28姚卫群
姚卫群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
“出世”与“入世”问题是东西方哲学中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在发展中面临的两条需要抉择的道路。所谓“出世”主要指企图摆脱世俗生活,远离现实中的种种不完美,以期进入一种完美的状态。所谓“入世”主要指努力深入现实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获得完美的人生。在东西方哲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出世”与“入世”观念。本文拟对中西印三大文明发展区域的“出世”与“入世”观念进行梳理,并加以比较分析。
一、古代印度的“出世”与“入世”观念
古代印度是一个极为关注“出世”与“入世”问题的国度。印度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婆罗门教和后来的印度教对于一个人的理想人生是有一些基本看法的。这主要体现在所谓人生“四行期”上。
按照古代印度的一些所谓“法典”等的说法,一个人(非贱民类最低种姓)的一生应该经历四个行期。第一行期是“梵行期”。这一行期的人主要是指未成年之人,他要到一个老师家学习宗教知识和仪轨。这个时期生活的目的是求“法”[1](P15-39)。第二行期是“家居期”。这一行期的人从老师那里学成回家,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尽世俗义务。这一行期的生活目的是求“欲”和求“财”(世俗工作和结婚)[1](P40-89)。第三行期是“林居期”。这一行期之人年纪渐大,开始隐居山林,从事各种修行活动,为最终解脱作准备[1](P106-108)。第四行期是“遁世期”。这一行期的人自己单独进行苦行,禁欲限食,磨炼意志,准备进入最后解脱[1](P109-104)。四行期中的后两期要求取得的目的就是“解脱”。
在这四个行期中,第一行期主要是年幼时到老师那里学习宗教圣典和有关思想,但不是过一般的世俗家庭生活,可以说是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阶段。第二行期则属于入世。第三和四行期基本上属于出世。因而可以说,在古印度,既有出世的观念,也有入世的观念。人并不是只能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有入世的时期,也可以有出世的时期。不同时期的追求是可以有不同的。古印度的不同宗教,在“出世”与“入世”问题上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在同一个宗教中,也会根据具体场合有不同的说法。
在印度佛教中,就有不同的说法。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前对人生现象做了细致考察,在这种考察中,他发现世间事物的无常和人生充满痛苦,并认识到痛苦与人的欲望关系密切,认识到不应执著于世间的享乐,应放弃人的种种欲望。这些思想就有了出世的色彩。在创立佛教后,他逐渐形成了对世俗社会和世间事物的更系统的看法,决心摆脱世俗社会一般都追求的欲乐。他父亲派给他的五个侍从成了佛教最初的比丘(五比丘)。此后,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释迦牟尼建立了佛教的僧团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戒律戒规。这些戒律戒规对教徒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作了规定,许多一般民众可以做的事情佛教徒是不许可做的。释迦牟尼还为此创立了其他一些配套的理论。他创立这些戒律戒规及相应理论的根本目标是要摆脱痛苦。佛教认为,一般人对世间的本质不能认识,有所谓“无明”,无明之人在世俗生活中充满了欲望,这与痛苦的形成有直接关系。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提出了根本教义“四谛”。四谛说就是对人世间状况的一种分析及应对理论。四谛说谈及了苦的现象(苦谛)、苦的原因(集谛)、灭苦的必要性及要达到的目标(灭谛)、灭苦的方式或道路(道谛)。此说实际也为佛教的出世观念做了重要论证。佛教最初的出世观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出来的。
若客观地分析,应当说,印度的初期佛教或所谓小乘佛教在发展中,明显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即认为世俗社会中充满痛苦。因而,他们多认为应出家。也就是说,这时的佛教还是明显表现出“出世”的倾向。初期佛教在论及最高目标“涅槃”时,通常认为它是一种摆脱了世间种种烦恼等的境界,如《杂阿含经》卷第十八说:“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槃。”[2](P126)
在初期佛教看来,贪欲、瞋恚、愚痴、烦恼这些现象是世间中存在的,而摆脱了它们就能脱离痛苦,达到最高境界。早期佛教经常谈到一般的世间环境不适合佛教圣贤求得真理,如《长阿含经》卷第一中说:“人间愦闹,此非我宜。何时当得离此群众,闲静之处以求道真!”[3](P7)这类论述显示,在初期或小乘佛教中,“出世”观念还是佛教较为强调的。
大乘佛教中也有涉及出世的说法。如大乘般若类经典很明显地突出“空”的思想。《金刚经》中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4](P752)这里将有造作变化的世界比喻为“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也就是要表明事物是“空”的。而“空”的思想起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贬低世俗世界的意义。
虽然无论是早期佛教还是大乘佛教中都有贬低世俗生活意义的出世言论,但并不是佛教都持这种立场。实际上,在早期佛教和大乘佛教中,都同样有重视世俗生活,要求入世的言论。
在早期佛教中,阿含类经典就有这种论述。如《长阿含经》卷第一中说:“佛出于世间,转无上法轮。”[3](P9)此话意为,佛不能离开世俗世界,而是要在世俗世界中传法。因此,可以说,早期佛教中就有明显将佛或佛法与世间紧密关联起来的言论。只是比较而言,这一时期更强调世间中的痛苦以及产生痛苦的烦恼,力图摆脱这些烦恼。后来的小乘佛教多强调佛教追求的境界与世俗世界不同,强调在涅槃境界没有世俗世界的那些愚昧无知和贪欲等,不大突出佛典中说的佛或佛法离不开世间的内容。
大乘佛教虽然有很多论述事物“性空”的言论,但是相对早期和小乘佛教来说,大乘佛教中也明显强调重视世俗社会。大乘对世间的解释或看法明显与先前的早期或小乘佛教的看法有差别。大乘佛教更为突出慈悲利他,认为佛教的涅槃不是脱离人们生存的世间才达到的,而是就在世间之中。与小乘佛教通常主要追求“自利”不同,大乘佛教则还要追求“利他”,即要使其他人也摆脱痛苦。大乘佛教认为,即便是达到了涅槃,也不能离开世间,还要在世间中弘扬佛法,救度众生。较早的大乘经在这方面就有表述,强调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的论述更多一些。
如《妙法莲华经》卷第五中说:“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槃,而实不灭度。”[5](P43)这句经文的主要意思是说:佛为了使众生脱离苦难,即便自己涅槃了也不会离开世间,这就是所谓“方便现涅槃”。因为佛教认为这样才能救度处在世间中的众生。不少大乘佛典还直接论述了“世间”和“涅槃”的密切关系。《维摩诘经》卷中说:“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乐涅槃不乐世间为二,若不乐涅槃不厌世间则无有二。”[6](P549-550)这里明确表明,“涅槃”并非是一个脱离“世间”的另一个世界。
大乘佛教的一些论典也有这方面的论述。如中观派代表人物龙树在《中论》卷第四中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7](P36)龙树在此处明显是用一种重复表述的手法来强调涅槃与世间的关系紧密,表明二者的不可分离性。中观派在这里表明,所谓“世间”的本来面目就是佛教强调的“涅槃”要认识的样子,二者并无绝对化的区别。若像小乘那样把二者作绝对化的区分,实际就是还有“执著”或有“分别”,未能认识世间的本来面目。若按中观等大乘佛教的思路,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实际即能达到佛教的最高认识境界,这也就是“涅槃”。
佛教的“二谛”理论中也涉及出世和入世观念。二谛即“真谛”和“俗谛”。真谛侧重讲事物“性空”,俗谛侧重讲事物“假有”。大乘佛教认为二谛都是佛所说的。佛针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情况,有时讲真谛,有时讲俗谛。尽管二谛中有俗谛,讲假有,但真谛的内涵是佛教主要强调的观念,而俗谛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表明真谛的手法。中观派认为,“二谛”多少还是有本旨及为明本旨所用手段之区分的。如龙树在《中论》卷第四中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7](P33)这里表明,直接导致涅槃的是真谛。而要表明真谛又要依靠俗谛。因为真谛若不使用言语这种俗谛是不能让世间民众明了的。因此,应当说二谛理论既强调了“性空”这种直接涉及“出世”的成分,也兼顾了“假有”这种照顾“入世”观念的成分。讲俗谛就是要佛教徒深入社会生活。
就印度佛教的总体来说,尽管在初期或小乘中有一定程度上的将涅槃与世间严格区分的情况,但在此教后来的演化过程中还是突出强调佛法或佛教的发展不能离开世间。即便是在初期或小乘佛教的经论中,也还是有要求信徒深入世间方面的内容的。因为作为一种宗教,它必定要有“超凡脱俗”的内容,必须要有一种民众能感受到的神圣感,这样才能吸引信众。但任何一种宗教形态,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里,都要根植于民众之中。离开了民众的信仰,离开了社会环境,任何一种宗教都无法生存。因此,虽然宗教一般都有“出世”的要求,但并不能真的不食人间烟火,最终还是要以某种方式“入世”。
总之,印度佛教文献中既有强调“出世”的思想,也有认为“入世”必要的论述,这对后来的佛教的不同发展方向都提供了经典依据。因此在佛教传出印度之后,不同的佛教宗派或分支,有的强调“出世”,有的强调“入世”。这些说法都与古印度的佛教原典有关联。
二、古代中国的“出世”与“入世”观念
古代中国的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没有古代印度的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大。但中国古代也有“出世”和“入世”方面的思想。古代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说有三大文化体系,即所谓儒、释、道。这之中的“儒”是中国本土影响最大的文化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释”为佛教,最初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后来逐渐在中国扩大影响,吸收了原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体系。“道”是中国本土的思想流派,后来在道家的基础上演化出道教,也在中国本土有重要影响。
在这三大文化体系中,儒家基本上是属于讲“入世”的。道家和道教中“出世”的成分较多,但“入世”成分也有。佛教从印度传来,是一种宗教,出世的色彩很浓厚,但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入世”的主张,而且影响还很大。
儒家的创立者主要是孔子和孟子等。孔孟的学说主要是讲人们的处世之道,讲社会生活中人们应有的人伦道德,力求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真理。他们把这种寻求与对宇宙的根本实在的认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努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真理。
儒家的创立者孔子就极为关注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8](P27)孔子还强调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8](P26),并且大力宣传他的“仁”的理论,认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8](P25)不难看出,孔子十分重视人们在社会中的关系,要求人都能按照某种适当的行为规范来行事,追求建立一个人们能克制自己,合乎所谓礼的好(仁)的社会。
孟子也极为关注社会问题,认为社会中的人各有其作用。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还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8](P98)孟子参与社会事务的兴趣一点也不比孔子小。孟子还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表明了孟子对待社会的基本态度,其本质还是愿意“出世”干一番事业的。
汉代著名儒家代表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还总结和发展了先前的儒家思想,提出了不少有关伦理纲常方面的思想。他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说:“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耻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而有博。”[8](P298)这里,董仲舒将其看重的人的社会伦理道德等观念加上天命的光环,实际是要树立儒家伦理思想的权威性。这种“入世”思想与其天命观是融为一体的。
唐代的儒家思想家继承了前代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如韩愈就反对佛教与道教的出世观念。韩愈曾指责道教“不信常道而务鬼怪”[9](P387)。韩愈排斥佛教和道教当然有其提升或保护儒家在社会中影响力的因素,但佛道所具有的某种程度的“出世”倾向也应说是引起他反感的重要原因。韩愈本人是积极“入世”的。
宋代的程朱理学基本都是强调“入世”的。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学说中的“天理”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观念,而是实际上与其社会伦理思想结合在一起的。程颢说:“天者,理也。”[10](P34)程颢还说:“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10](P72)程颐说:“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10](P72)他在这里说的“理”,是包括社会生活及人伦原则等的道理在内的。朱熹(1130-1200)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10](P105)朱熹的“理”也是被作为人的生活准则或道德标准的基础的。
道教产生时的理论基础是在它之前的道家思想。道家强调“无为”,如老子的《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中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8](P82)“无为”是一种处世态度,实际是既包括对待欲望的态度,也包括人在处理世间事务时的一种不过度干涉的主张。“我无欲”多少有些出世的色彩,而“我无事”则有些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展的态度。只是最后的结果“民自富”、“民自正”、“民自朴”实际是道家所期待的无为之后出现的结果。这种期待又多少有些“入世”的意味,并不是对世事完全漠不关心。
道教作为一个宗教当然有出世的言行,此教极为强调要清修,道教信徒一般把求取个人成仙作为修持的目标。这严格来说属“自利”行为。然而此教并非只是追求自利,它的教义中也有强调“利他”的内容。道教认为,若要长生,就必须积善立功,慈心于物,乐善好施。在此教中,“自利”和“利他”紧密相关,“利他”是“自利”(如长生)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若不利他,则个人长生或成仙的目的就难以达到。这利他,通常也是社会行为。也就是说,道教的一些教义虽有“出世”色彩,但其所期待的目标往往实际要“入世”才能达到。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最初在中国社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应当说是它的“出世”方面的理论,中国人最初遇到外来的佛教时借用本土的黄老等思想的一些概念来理解认识它,后来则大量建立佛教的寺院庙宇,以方便信众出家。许多中国民众都把信奉或皈依佛视为 “踏入空门”,属于“看破红尘”后的“了却尘事”。
印度佛教在中国最初是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大致同时传入,相差时间并不长。较早传入中国的是印度小乘佛教中的静坐冥观,追求弃绝有关外部事物杂念的修持方式,但印度大乘佛教中关于“入世”的思想也很快在中国产生了影响。而且,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思想对佛教的发展也形成影响。因而,在中国佛教中,重视“入世”的佛教宗派由此也逐渐成为各宗派中势力最大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禅宗,尤其是禅宗里的“南宗”系统。
禅宗虽属佛教,然而它在佛教的宗派或分支中却是相对不是很重视佛教传统经教的派别;它虽然称禅宗,然而却也不大注重传统佛教传统中一般说的“禅定”。在较早的中国禅思想中,如达摩所弘扬的禅思想中,“出世”的思想较为突出。在慧能的《坛经》中,也有一些论及“出世”的思想,但在慧能之后,禅宗实际真正重视的是如何在世俗社会中认识佛教真理,悟出人的真正本性。南宗禅十分强调不能离开世间而成佛。他们提出的重要口号就是“佛法在世间”思想。《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11](P351)慧能等在此处明确强调认为要在世间中去寻求所谓“佛法”,强调佛法并不是离开人们生活的世界中的其他世界的产物。这与印度大乘佛教中实际已提出的不能将世间与出世间作绝对区分思想是一致的。因而可以说,禅宗虽在形式上还有不少重视“出世”的表述,但实际上努力倡导的是要让信众广泛深入社会,行走世间,成为一个特别大力强调“入世”的佛教宗派。
在慧能之后的南宗禅里,不少僧人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们公开反对遵循传统佛教的一些修行方法,力图在破除这些方法的过程中获得真理。这在一些禅宗的语录中就有体现。如《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中记述说:“王常侍一日访师,同师于僧堂前看,乃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师云:不看经。侍云:还学禅么?师云:不学禅。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师云:总教伊成佛作祖去。”[12](P503)这段材料表明:一些禅师实际认识到,获得佛教的根本真理或成佛,并不能单单依靠传统佛教中倡导的读经学禅可达到,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下工夫,把日常生活都当作修行来对待,即要在日常生活中参禅悟道。客观地说,中国禅宗在发展中,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实际比一般的宗教派别要紧密。禅宗要求信众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来体悟佛教的道理,最终真正达到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
禅宗里的一些禅师十分重视在日常劳作中进行禅宗的修持。如百丈怀海禅师等就提出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12](P1018)的主张。这和传统佛教中的僧人专心修行,一般不参与常人之劳作的观念有很大不同。尽管禅宗中不少祖师或僧人实际也不反对参加生产劳动,但像百丈禅师这样作出明确规定,要求信徒与一般民众同样劳作,同样做工种田,而且将这一做法制度化,这是有创新的。此种做法在印度佛教中不曾见到,在中国佛教中也不同以往。[13](P342-351)
在中国形成的佛教诸宗中,禅宗的影响最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此宗重视“入世”有紧密的关联。中国儒家思想等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完善自己,重视对人的一般行为准则的探讨,把对人伦或道德规范问题的思考与对宇宙本质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或寻求真理。禅宗看到了这种中国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它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将印度佛典中本来就存在的“入世”观念加以凝练,并对中国原有文化中的“入世”思想进行改造,而且在理论中仍保持印度佛教中原有的“出世”思想,把这些成分融在一起,大力弘扬其中的“入世”观念,并将其推向极致,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因此,可以说,禅宗较好地处理了本宗的“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作出了明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不仅决定了本宗的基本走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到了近现代,佛教界几乎都认同“人间佛教”的主张,它成为聚集广大中国佛教信众的一面旗帜,得到教内外民众的广泛赞誉。
三、古代欧洲的“出世”与“入世”观念
古代欧洲哲学在中世纪之前对于“出世”与“入世”问题不是很关注。古希腊哲学中虽然也讨论“神”的问题,但对于一般人来说,神的世界并未被普遍设定为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人们的世俗生活也很少与神圣的世界的生活对举或相比较。斯多葛派的一些思想家则是较早论及这方面问题的人。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在《论老年》XXI中说:“灵魂本是天上的东西。……上天之所以驱使灵魂入于肉体,正是要有人料理这个尘世,同时再以天上的风光贯彻到人生里来。”“灵魂既是永久活动,并且是自动,所以灵魂也永远没有终止,因为灵魂不会抛弃其本身。”[14](P187)他在《论老年》XXII中说:“我从来不相信灵魂在躯壳里便是活的,离开躯壳便是死的;我也不相信灵魂离开那本不能思想的尸体便不能思想,我以为灵魂脱离肉体之后,便更光明。”[14](P188)西塞罗在《论友谊》IV中说:“灵魂离开了躯壳便可以归到天府,如果灵魂是有美德而公正的,便可一直地顺利升天。”[14](P188)
西塞罗在这里确认灵魂不灭,实际上将灵魂生存的世界分为附在肉体中的地上的世界和灵魂升入天府有天上风光的世界。在肉体中灵魂的世界是受束缚的,劳苦的,不合乎于其神圣本性的,而脱离肉体的天府世界中的灵魂是神圣的、智慧的、光明的、自由的。这些思想有禁欲主义的倾向[15](P128),明显有一种贬低世间和向往出世的思想倾向。
新柏拉图派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论述。此派的代表人物柏罗丁(公元205-270年)在《九章集》VI.9,9中说:“灵魂很自然地对神有一种爱。……不知道这种天上的爱的人,也可以从地上的爱获知天上的爱的某种概念,以及拥有最喜爱的东西是多么愉快。且让他回想到他所爱的这些对象是凡俗的、变灭的,他的爱所攫取的只是一些泡影,很快地对事物发生厌恶。”“看到过这种爱的对象的人,是知道我所说的话的真理的,他知道灵魂如何在走向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赶快脱离这个世界上的事事物物,痛恨把我们缚在这些事物上的锁链,最后以我们的整个灵魂拥抱爱的对象,不让我们有一部分不与神接触。”[14](P217-218)
柏罗丁在这里也是明显有贬低世俗生活的倾向。他将世俗世界说成是“变灭的”、“泡影”、使人“厌恶”。他认为应该追求“更高的世界”。这些叙述实际就表明了他的“出世”与“入世”的观念。世俗世界是“挂着血肉的”,是“我们缚在这些事物上的锁链”;而“更高的世界”则是“走向这个真理,接近并分享这个真理”、“与神接触”的世界。
基督教产生后,在古代欧洲逐渐产生较大的影响。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人们生活的世界,甚至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神造的。欧洲古代的神学家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是较早对神造世有论述的人。
奥古斯丁在《教义手册》9中说:“宇宙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即‘父’,由父而生的‘子’,从父出来的‘圣灵’,这圣灵就是父与子之灵。”[14](P219)在《教义手册》10中,奥古斯丁说:“一切事物都是由那具有至上、同等、永不改变之善的三位一体的神所造成的。”[14](P219)
奥古斯丁这种论述将一切都纳入了上帝或神的光环之中。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事物是与神无关的。
那么,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罪恶又如何解释呢?人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切呢?意大利神学家,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谟(1033-1109)在其《宣讲》中说:“但愿我能仰望着你(上帝)的光,不论是站在远处望到或者是在深处望到。当我寻找你的时候,盼望你指示我,把你自己向我启示,……圣主啊,我承认并感激你,你在我身上创造出你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已经被恶习所毁损和消灭,……我的理解力,决不能和你的崇高相比拟,但我却切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你的那个为我所信仰所爱的真理。”[14](P240)
在这里,安瑟尔谟实际把人们生活的世界加以贬低,认为神创造的形象“被恶习所毁损和消灭”。而人们应该仰望上帝之光,盼望上帝的启示,感激、想念、热爱上帝,理解上帝所给予的真理。这些说法实际也表现出一种寻求“出世”的愿望。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欧洲13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经院哲学家。他在《神学大全》中说:“神学所探究的,主要是超于人类理性等的优美至上的东西,而其他学科则只注意人的理性所能把握的东西。……神学的目的,就其实践方面说,则在于永恒的幸福,而这种永恒的幸福则是一切世间科学作为最后目的而趋向的目的。所以说:神学高于其他科学。”[14](P260-261)
托马斯·阿奎那的这种观点将世俗世界一般科学的地位置于神学之下,认为追求神圣的宗教神学目标是至高无上的。
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使得许多人开始关注宗教的负面影响,开始重视世俗生活和科学。这之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荷兰思想家爱拉斯谟[14](P1469-1536)。
爱拉斯谟在《愚神颂》中说:“撇开神学家不谈,也许是明智的。这群脾气急躁、目空一切的家伙……把自己估计的至高无上;他们的一举一动如同登了天堂一样,他们用怜悯的眼光把别人看成一群蛆虫一般。他们用堂皇的定义、结论、系论以及明确与含蓄的命题筑成围墙,来保护自己。”[14](P312)他在《愚神颂》中还说:“与教皇同等可嘉的,是一些普通神父的虔诚的力量。就其圣洁的情形而论,他们并不亚于他们的领袖。他们以真正的军事姿态,用投枪、石头和武器来为什一税而战斗。他们的目光是多么敏锐,能从古代著作中找出他们需要的东西去恫吓人们,使人们相信自己对教会所负的债比什一税还要多。当然,他们忽视自己的工作才真正是对人民负了债。他们剃光的头顶并没有提醒他们应当摆脱种种世俗的私欲,应当默想天国的事。这批好人们却相反地认为,如果他们已经低声诵读那些短小的祈祷文,他们的工作就已经做得很好。”[14](P314-315)
爱拉斯谟在这里用犀利的语言嘲讽了教会神父们的可笑与愚昧,表明祈祷和天堂等的说教的虚伪。他这方面的言论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民众对现实生活的重视和对宗教活动的蔑视。
18世纪的法国出现了不少无神论思想家。他们对于有神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反对种种宗教行为,否定宗教追求目标的价值,大力肯定人们现实生活的意义。霍尔巴赫(1723-1789)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德国血统的法国人,著有《自然体系》《社会体系》《神圣的瘟疫》等著作。
霍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中说:“社会对于人的幸福是有益的和必须的;人不能独自使自己幸福;一个软弱而又充满各种需要的生物,在任何时刻都需要它自己所不能提供的援助。只有靠它的同类的帮助,它才能抵御命运的打击,才能补偿它不得不尝到的肉体的苦难。”[16](P230)
霍尔巴赫在《自然体系》中说:“很多人承认迷信所造成的种种胡作非为是非常现实的灾难;很多人抱怨宗教的流弊,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见到这些流弊和灾难是整个宗教的基本原则的必然后果,而宗教本身是只能建立在人们被迫由神形成的那些令人不快的概念上面的。”[16](P232)
霍尔巴赫肯定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反对迷信和一些宗教所宣扬的那些超越现实社会生活所追求的目标。
四、比较分析
“出世”与“入世”问题在中西印哲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三地的不同派别或思想分支在这方面的主张与其所处的思想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与各自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倾向有着重要的关联。在这个问题上,三地哲人有共同处,也有差别点。
共同处主要表现
第一,三地哲人在发展中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超越他们社会生活的一种理想的思想境界或超凡脱俗的状态。如古印度的人生四行期追求的是最后的解脱;佛教徒追求的是最终的涅槃境界。古代中国的道家追求一种“无为”的境界。道教追求个人长生或成仙的目的。中国佛教追求成佛或觉悟的境界。古代欧洲的神学家追求灵魂与神接触以及得到神的启示的状态。
第二,三地哲人无论如何追求“出世”的至善境界,在发展中最终都要给世俗社会留有空间。他们都不可能真的跳出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最终的发展必定是在“入世”的过程中实现的。如古印度的大乘佛教虽然追求涅槃,但又认为即便涅槃了也不能离开世间。古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入世”思想。中国儒家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佛教中的禅宗强调“不离世间觉”。欧洲的西塞罗认为上天会驱使灵魂入于肉体,要有人料理这个尘世,同时再以天上的风光贯彻到人生里来。这也是把其最终着眼点放在尘世。
第三,三地的宗教色彩浓厚的派别最初一般都较强调“出世”的观念。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和后来的印度教、佛教在最初创教时期,都有鲜明的强调“出世”的色彩。中国的道教产生时也有明显的“出世”目标。古代欧洲的神学家们也把与神接触,得到神的启示、摆脱尘世的罪恶作为目标。
差别点主要表现
第一,古印度哲学中对“出世”与“入世”问题的探索基本上贯穿各主要派别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各主要哲学派别普遍关注的问题。古代中国哲学相对古代印度哲学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没有古印度那么大。中国佛教较为重视,但这里面有印度佛教影响的成分。其他中国哲学派别在这个问题上论述有限。古代欧洲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如古代印度哲学。古希腊哲学在这方面就很少涉及。中世纪之后,欧洲基督教的影响变大,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开始多起来,但总体上说,这一问题不是欧洲哲学关注的重点。
第二,古印度的思想文化,从古至今,虽也有“入世”的主张,但“出世”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古印度的几大主要宗教派别中都是如此。而古代中国,“入世”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儒家的主导思想是如此,道教和佛教中的“入世”思想后来也很突出。在古代欧洲,“入世”的观念没有古代中国的影响大;“出世”的观念则没有古代印度的影响大。
第三,古代中国文化中对“出世”与“入世”观念的处理较为恰当,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明显。古代印度中虽也讨论这一组概念,但相对来说“出世”的观念较为突出,这虽然对于抑制人的贪欲有一定作用,但缺乏鼓励民众积极进取,所以也有一些负面作用。古代欧洲哲学关注“出世”与“入世”问题相对少些。欧洲近代的科学和社会民主较为发达,是明显鼓励民众积极参与社会进步与发展活动的。
总体上说,“出世”与“入世”观念是中西印哲学中涉及的重要问题。三地哲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展示了他们理论的重要特色。各思想流派或不同哲人在这方面的观念与他们的基本理论倾向有较大关联。梳理和分析这方面的内容,对我们了解东西方哲学的主要思想特征和基本发展脉络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