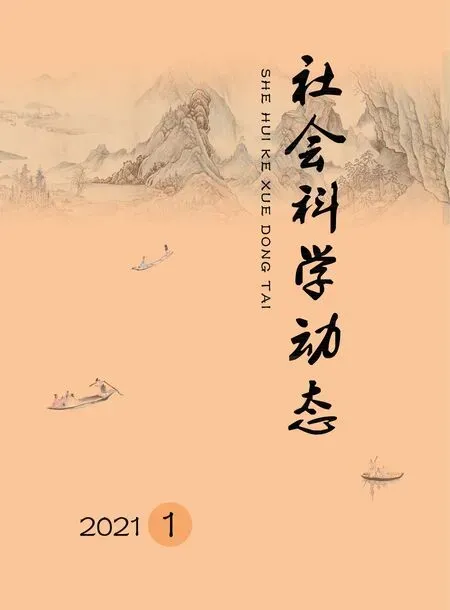鄂南秋收暴动失败原因探析
2021-01-27叶美燕
叶美燕
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其时中共中央尚在武汉,故而中共湖北省委能够率先响应中央号召。8 月3 日中共中央制定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革命的社会势力需要新的聚集和训练”,要进行“工农革命军”旗帜的秋收起义运动。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准了罗亦农制定的湖北暴动大纲,并规定湖北省委可依据该暴动大纲作出具体的计划。①8 月5 日,《鄂南农民暴动计划》便率先全国出台。8 月7 日,八七会议作出了详细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举行秋收起义成为当前摆在首位的任务。②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派省委委员符向一率领40 余名工作人员到鄂南组织起义,鄂南各县纷纷成立了暴动委员会,改编农民自卫军为农民革命军。8 月中旬,省委又派吴德峰及黄赤光等来到鄂南,成立了中共鄂南特委,全权负责指挥鄂南区的武装起义。鉴于鄂南重要的地理位置,且革命形势较好,8 月29 日,中共中央又制定通过《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决议案》,以实现湘鄂两省秋收起义的互相配合。9 月上旬,中共长江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亲赴鄂南进行起义部署。9 月8 日,以“中伙铺劫车”为标志,鄂南秋收暴动正式爆发。③但是,仅两天后“新店事变”突发,鄂南秋收暴动(以下简称鄂南秋暴)旋即节节败退,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暴动很快便跌入低谷。鄂南秋暴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进行了“军事投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然而暴动失败存在各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军事投机”错误。④
一、“军事投机” 说
“军事投机”导致鄂南秋暴失败,是事后湖北省委的一致观点。通过考察分析有关鄂南秋暴的相关报告,最常见的就是对依靠农民武装的强调和对地方犯“军事投机”错误的批评。在总结鄂南秋暴时,中共湖北省委就多次反复申明鄂南秋暴犯了严重的“军事投机”错误。他们认为:“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实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群众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完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的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暴动,暴动毫无疑义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⑤忽视群众工作、没有深入发动群众成为暴动失败的一个最常见的批评口径。中共湖北省委的这种观点是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中共中央要求暴动中不能依赖军事力量而要依靠群众力量。这并不是说中共中央忽视军事力量,相反地,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得中共中央认识到拥有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在中共中央的认知当中,以军事为主的暴动会使农民认识不到自己拥有的力量,从而过度依赖军队。因为暴动不仅是一场军事运动,更是一场政治运动,暴动要通过农民的亲身参与来提高其政治觉悟,坚定其参加革命的决心,农村便可得到新的集训和训练。在暴动的过程中,可以组织农军而编成工农革命军,中共中央认为工农革命军才是真正的武装力量。显然,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军事投机”的说法,是遵从了中共中央的逻辑思维。
中共湖北省委对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和贯彻较为彻底。秋收暴动失败后,在总结其失败原因时,有人指出八七会议决议“可惜未达入群众中,武汉之下级党部尚听到一些,但外县党部竟一点都不知”⑥。值得注意的是,但凡革命失败,一般都首先强调没有正确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大大小小的暴动失败原因进行考察分析,不难发现都是采用的这种固定话语和解释问题的方式。当时的文件报告大多遵循着这种言语逻辑,这有时是地方党组织为与中央保持一致观点所造成的,其实他们本身并不一定理解了这些词的含义,所以“军事投机主义错误”“工农反抗情绪已达于极点”等词往往在报告中随口而来。事实上,中共湖北省委对于八七会议的传达是结合革命形势而有选择性的,大革命失败后的九、十月份,是以将八七会议精神与组织秋收暴动结合起来为重心,至于八七会议体现的其他精神内容,在实际行动中根本无法立即实施起来。从开展秋收起义的层面来讲,八七会议精神像春风一样吹遍了鄂东南地区。⑦在八七会议后,鄂南紧锣密鼓的组织农民暴动就是有力的证明。
那么,鄂南秋暴多大程度上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 “军事投机”是不是导致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有无“军事投机”涉及暴动失败的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鄂南秋暴失败,地方和省委都在互相归咎责任。组织地方暴动的人常常抱怨缺乏军事协助,认为省委给的枪支弹药极少,农民暴动起来自然会走向失败,因而“这一次的失败,省委是要负相当责任的”⑧。针对这一说法,中共湖北省委则强烈谴责地方犯了忽视民众自身力量而偏依赖军队的“军事投机”的错误,因为暴动“根本上是建筑在广大的农民群众的身上”,而“不该建筑在几十枝盒子炮身上”⑨,“各区同志均各行其是,完全不执行省委决定的策略,甚至与此策略背道而驰”⑩。实际上,为了避免上级“军事投机”的批评,地方暴动以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作为暴动的标准,暴动的主观性大大增强。各地听从政策而不顾实际的纷纷举行暴动,不暴动就会受到“军事投机”批评,暴动后失败则由中共湖北省委来承担责任。鄂南暴动开始之日,原计划先攻取蒲圻、咸宁二城,但咸宁只能集中农民800 人,县委书记杨其祥,特委书记吴德峰都不主张攻城,只有符向一力主攻城,“但也不是相信民众的力量,是怕省委的骂,就是失败,由省委负责”⑪。综上所述,以中共对“军事投机”的定义来看,鄂南秋暴多少存在这方面的错误,但不能简单的把“军事投机”认定为鄂南秋暴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综合因素” 说及其分析
“军事投机”说是鄂南秋暴失败后党内的一致观点,是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认知。鄂南秋暴的失败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以下所分析的几点原因,不可能囊括所有,而是最为关键性的若干方面。
( 一) 中共党组织的问题
第一,忽视暴动的客观条件,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中央的暴动策略是“相互响应”,但实际情况因各地环境的差异及中共在各地的发展状况而有很大的差别,“相互响应”的策略有意无意地无视了这些。就鄂南秋暴而言,原计划鄂南暴动开始后,鄂中鄂西亟需暴动与鄂南联络,但在具体实践中,革命指挥者很快发现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湖北各地区的暴动都存在着实践差,“鄂南暴动以后,鄂西一时不能行动,鄂东鄂中仍无把握,鄂东后虽有一个勇敢同志的暴动,亦无济于事。”⑫在暴动的举行和攻城问题上,很明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由省委派去的指挥暴动工作的同志会坚决的贯彻省委的计划,即使他们认识到有些地方攻城的条件并不成熟或根本没有这种能力。而当地工作的同志在基于调查了解地方情况后,并不都赞成立即暴动和攻打城市。这种矛盾难以调和,但最终下级要服从于上级的指导,否则就要受到胆怯、不敢斗争之类的批评。其实,对于暴动的举行及其后果,我们不能简单的判定对错,这是一个战略与战术的问题,中央认为暴动纵然失败,在战略上仍然是成功的。再者,党内同志意见存在分歧在所难免,毕竟想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是,即使他们明知可能失败,也还是要依中央和省委计划而举行暴动。因为不举行是鄂南地方上的责任,未暴动地区将受到中共湖北省委的严厉批评。同样,地方后来也谴责中共湖北省委指挥不当而导致暴动失败。加之,当时党内存在联系机制不通畅的问题,暴动并未“互相响应”。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国民党仍多是占据着中心城市,且对中共形成包围和封锁,不能想当然的以为暴动的“互相响应”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无论是纵向的上下级之间,还是横向的同等级之间,中共难以形成畅通的信息管道,互相之间往往消息不通,鄂南秋暴没有按照预期举行,暴动的时间一变再变,使得各地对暴动出现不明所以的现象。
第二,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关系认识不够。暴动期间,注重武装斗争的暴动实践,“这新时期中,我们的主要政策是组织民众暴动,赞助民众暴动”⑬而忽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中央和地方的文件中都着重陈述农民阶级的痛苦及其对地主阶级的愤恨,因而认为“全国的革命潮流,表面上虽似一时的低落,实际却是继续往上涨”⑭。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中共认为农民会主动积极地参加秋收暴动,农民暴动会到处爆发,中共湖北省委也认为农民只要有一个人,一把梭镖,一根火柴都可以行动,在他们的情感认知中,动员农民起来革命似乎十分简单。一般地,只需要准备诸多标语口号,到处张贴宣传,土地革命的意识自然会印在民众的脑海里,从而引着他们向暴动的路上前进。可见,在急于暴动的心态下,中共对于农民的革命情绪进行了乐观的估计,着重强调的是如何组织暴动,这种思想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动员农民起来革命的过程中忽视对土地革命的切实开展,“分配土地,为切要工作,鄂南亦未切实注意此项问题。通山在我们手中的时间很长,对于此项工作,亦未积极注意。”⑮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在很多地方成为了一种口号。这当然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民众武装暴动和开展土地革命毕竟是两件事情,虽是互相贯通,但也难免有所侧重,最重要的目标还是在于希冀暴动夺取数省的政权。李维汉回忆中也指出:“当时的农民暴动,并不都是‘自发的’,其中大都是党组织领导的”,“其中有的还带有强迫命令的性质”⑯。在整个鄂南暴动中,虽然强调要开展“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运动,但在实际行动中,“以城市为中心”的急于攻占城市的迹象十分突出。其没收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的土地,更多的是为了准备乡村间极普遍的大暴动,也就是说只注重把土地夺过来,而缺乏公平公正的分配土地之策略与技术。当然,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既是当地革命党人工作上的错误,更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共关于土地革命的方针策略是步步形成起来,甚至在一定时期可能出现倒退。在实际情况下,党进入乡村是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党的乡村动员和组织工作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易于成功。⑰
( 二) 农民武装的缺陷
第一,从农民参与革命的动机来看农民武装的缺陷。农民是现实的,共产主义的远大前程他们并不能如何理解。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⑱。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也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⑲纵观有关鄂南秋暴的报告及叙述,不难发现“利益”因素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农民参与革命的最直接原因往往是可以获得钱财和物资,这一革命动机在鄂南秋暴中十分明显。中伙铺劫车后,参与战斗的农民都得到一定的物资分配,中共在领导农民“打土豪”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将夺得的东西分给四乡农民,这一点对于物资缺乏的农民来说极具诱惑力。中共将土豪劣绅和农民放在完全对立的两个面上,对土豪劣绅举起屠刀,普遍开展“四抗”斗争,农民尝到了拥有钱财和土地的滋味,便更要拿起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暴动中往往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当然,在农民杀土豪劣绅的时候,地主并不是任由其宰割,亦杀死不少农民,双方都在不断地进行报复,在鄂南暴动的口号中,就有“为死难农友复仇”⑳这么一条。鄂南农民参与革命的动机决定了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水平,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为革命信仰而战。
第二,从实际作战中的表现来看农民武装的缺陷。中共十分注重农民武装,没有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农民革命军存在极大的缺陷,军事战争中没有军事技能和战斗经验的军队是不可想象的。农民的性格特质,决定其在武装暴动中的革命信念具有动摇性。以中伙铺劫车为例,黄赤光开枪发出信号之后,“两旁农民亦畏惧不敢动,再呼始上车”,“后农民上车,乱杀一场,内中误杀了一个同志”。㉑在后来的“失马桥”一战之中,农民“忽闻枪声,土枪队即四散,仅存十支快枪,是时所遇敌人约一连,系分三路来攻,刘镇一当令散开御敌,且战且退,敌人则冲锋前进。退至马桥时,仅余镇一一人。”㉒敌人枪声一响,农军组织的土枪队立即溃散,经过组织建立的农民军队尚且如此,不难想象一般性的农民暴动队伍在战斗中是怎样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中共革命的特殊性,中央并不是不知道农民军队的局限性,但在革命的湍流之下,对农民的训练与改造并非短时期内能奏效。从这方面来说,中共认识到农民革命很有可能归于失败,但广大农村在暴动中已得到新的聚集和训练,从这一点上而言,民众的觉醒或许是更为深刻的战略意义上的胜利。
( 三) 敌我力量的悬殊
在中共的文件报告中,我们随处可见对农民革命武装的赞扬与信心。但是,在全国“反共” “清乡”的大环境下,国民党并非毫无实力与作为。武装力量的对比上,国共存在相当的差距。中共武装情况:咸宁有快枪、驳壳、九子连,共计54 支;蒲圻有快枪38 支,却未能完全受指挥;嘉鱼有快枪、手枪、驳壳,共计53 支;通城机关枪及炮弹子弹及50 余枪,但是队长非同志;通山有快枪、手枪驳壳,共计30 支;崇阳有快枪25 支,也未能受指挥。国民党驻军情况:国民党在咸宁和嘉鱼驻有警卫团,在蒲圻、通城等县驻军一个团。㉓据此可知,中共在人数、武器掌握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实际作战中,农民军队劣势明显。通城起义中,通崇农军通过智力夺取了县城,但是得知国民党第13 军即将派军来镇压的消息后,中共通城县委违背了“中共鄂南特委要求通崇农军仍按9 月9日参加鄂南秋收起义”㉔的要求,迅速撤退转移至江西修水。可见,地区上在敌我力量的估计上还是比较保守的,国民党援兵一来随即寻找退路。通山县攻城农军有一首鼓动农民参与革命的《暴动歌》,其中就有一句“拿起长矛和大刀,扛起锄头和土枪”。㉕在暴动中,农民“除少数有快抢、机关枪、大炮外,大半皆持土枪、梭镖等”㉖,依靠落后装备的战斗自然是肉体的搏斗与鲜血的流淌,我们要知道,革命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更何况散在各县乡镇的武器,大多“都没有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上,是在地方上二流子、游手好闲的恶棍手上,这些人与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乡保甲长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㉗从力量对比上来看,中共领导的这场农民运动存在着技术与装备上的落后性。
三、鄂南秋暴失败的根本原因
“左”倾思想在地方上的实践,是鄂南秋暴失败的根本原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低潮,主张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盲目要求部分地区进行武装起义,党内“左”倾情绪不断滋长起来。“‘八七’会议制订的总暴动计划,既不考虑地点的不同,也不顾及情况的各异,一味地要求各地一律暴动,一律进攻。”㉘鄂南秋暴作为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秋收起义之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是以中央所主张的“民众武装暴动”和“夺取城市”为指导思想的。所谓“民众武装暴动”,即不能是纯粹的军事行动,其所依靠的军事力量要是从民众中组织起来的农军势力,“民众”主要就是指农民。中共对于革命形势是乐观估计的,认为只要民众的革命情绪和革命行动得到动员,“则我们枪支虽少不难扑灭有数倍枪支的敌军”㉙。从暴动中农民的实际行为和战斗效果来看,这种暴动思想存在极大的缺陷。因为忽视暴动的客观条件,依靠鼓动和号召而集结起来的农民武装,往往是松散的组织,并不能形成坚固的战斗力量,这一局限在鄂南秋暴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一定的体现。而“夺取城市”是组织“民众武装暴动”的目标所在,暴动的整个过程都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1927年8 月开始的秋收起义,在湖北是以鄂南为中心。㉚鄂南秋暴计划中则明确规定暴动开始后,重点在于夺取蒲析、咸宁县城,“在暴动方面开始,首先亟需征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区的中心城市”㉛,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鄂南为中心是从敌我形势出发的策略,是增加暴动的成功率的方法,其最终目标还是在于夺取更为重要的中心城市。
“左”倾思想在暴动中,往往表现为“过火”现象的产生。在农村,土豪劣绅被当做农民的死敌,二者置身于你死我亡的对立面,农民不杀死土豪劣绅,便是土豪劣绅杀死农民。查阅相关文件报告,没有记录主张鄂南秋暴“过火”的言论,相反地,在批评党在机会主义策略之下,对杀死土豪劣绅的工作“不给以切实指导”,“而跟着一般人说农运过火”㉜。在经历大革命时期的教训之后,持农民运动“过火”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因此,无论是地方省委的报告中,还是亲历者的回忆录中,都高度地与中央的观点保持一致,不承认鄂南秋暴有“过火”的行为,因此就很少有记载和描述。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暴动必须杀尽豪绅与反动的大地主,烧杀和掠夺成为激发农民革命情绪的一种有效办法,打土豪意味着大肆的烧杀,这在当时几乎是普遍现象。这些现象从侧面反映出,农民武装在仇恨和利益的鼓动下,显示出一定的无序性和狭隘性。在整个鄂南秋暴的过程中,杀戮土豪劣绅、政府官吏本就是暴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想要夺取乡村及县城的政权,这一行径不可避免。但是普遍的“红色恐怖”,甚至会导致朋友变成敌人。鄂南秋暴的后期,就发生过通山书记李良材卷枪逃走的事件。据当事人记载,通山县被捉之县长及征收局长9 人中,有8 人是李良材的同乡,李良材有意保护他们免遭屠戮。在这一问题上,领导干部们形成两派意见。一方以李德峰为代表,主张不杀他们,原因在于他们是好官,将来可用作书记。一方以刘镇一为代表,力主将他们就地正法。但是,最终特委命令将9 人全部枪毙。这一做法,引起了李良材对于自身安危的恐慌,所以卷枪出逃。㉝单一性的斗争手段,导致内部力量发生分裂,其时正值鄂南秋暴遭受打击,在亟需团结力量的时候,因为死守革命原则,而致使革命队伍的力量受损失的做法并不明智。
综上所述,历史具有复杂性,不能将鄂南秋暴失败简单地归因于犯了“军事投机”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湖北省委的“军事投机”说,更多的体现了官方解释问题的一种方式,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身处的时代背景与政治逻辑,具有鲜明的话语体系特色。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缺乏军事力量支撑,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群众暴动的力量,必须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即使不断提升对军队重要性的认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力量始终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并逐渐形成了“群众路线”。解剖历史后不难发现,鄂南暴动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当时,中央至地方上的中共党组织,在“左”的情绪领导下,充分强调革命的主观能动性,普遍存在忽略客观条件的倾向,既对农民武装的认识不够彻底,也对自身处境认识不够清晰。大革命失败后,形成了“无动不暴”、“无处不暴”的局面。与高度强调暴动相比,八七会议制定的土地革命方针执行上相对滞后,这是对农民革命与土地革命关系认识不够成熟的表现。尽管暴动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本质上却是中央“左”倾错误路线在地方实践的必然结果,路线错误导致了革命行动出现偏差,也决定了鄂南秋暴的失败走向。
如何看待鄂南秋暴的失败,涉及对鄂南秋暴的评价问题。从目前相关研究现状来看,关于鄂南秋暴的评价主要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忽视,由于对鄂南秋暴知之甚少,故而只字不提。另一种是全面肯定,因为情感立场或研究重心,所以存在过度评价倾向。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共自身也在不断地成长过程中,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其间难免存在不足与错误,从对鄂南秋暴失败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讲话中说:“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㉞这话对于我们理解鄂南秋暴具有同样的借鉴意义。走近鄂南秋暴就要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不能简单地以“旁观者”的视角加以评判,应当时刻立足于当时的时间、地点与条件。我们要明白,革命的道路是前人一步步走出来的,鄂南秋暴的失败结局由历史条件所决定,具有必然性。当时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许多问题是突然出现的,中共往往要在没有预先的准备的情况下做出反应。更何况历史运动趋势是力的综合作用,其发展前景本就包含着某些未知与偶然,在当时谁也不能对做出的决策和行动打包票。在当时形势下,要立刻做出判断和抉择本就不易,我们后世者看起来十分清晰的道路,在当时却是云山雾里,甚至有可能走向错误。因此,要多角度分析鄂南秋暴的失败原因,同时给予鄂南秋暴客观评价。
注释:
①⑬⑭⑲㉙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397、216、373、373页。
②八七会议原计划于7 月28 日召开,会议相关内容亦早已确定,但由于时局等原因延期至8 月7 日。《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实际是在八七会议精神之下而制定。《鄂南农民暴动计划》则是对四省秋收暴动大纲的全面贯彻和深入拓展。
③以李城外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主张鄂南秋暴从8 月14 日崇阳“洪下暴动”宣告开始,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是将鄂南秋暴广义化。定义鄂南秋暴,最好还是要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当时中共中央及中共湖北省委所说的鄂南秋收暴动明确有所指,是以蒲圻暴动为开始点。至于在这之前的崇阳、通城、通山等地暴动,当时有文件称之为“骚动” 时期,笔者认为“骚动”和“暴动”存在一定区别,前者通常带有自发性和偶然性,鄂南秋暴有明确的组织性和规模性。
④鄂南秋暴研究中以李城外较为突出,他的文章《鄂南系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研究》 (《江汉论坛》2017年第9期)论证了鄂南秋暴期间通城和通山红色政权的地位;《鄂南暴动与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学习月刊》2017年第1期)论述了鄂南暴动之于几大革命根据地创立的意义;《鄂南秋收暴动研究》 (《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4期)强调了鄂南秋暴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这些文章论述了鄂南秋暴的经过、地位和意义等,但是没有论及鄂南秋暴的失败原因。
⑤⑧⑨⑩1⑪⑫⑮⑳㉑㉒㉓㉛㉜㉝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1 辑,内部编印,1987年,第46、57、57、131、60—61、49、66、43、60、46、52—53、49、38、65页。
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3),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3年版,第370页。
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⑯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⑰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中共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1927—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㉔㉕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512、521页。
㉖《鄂南暴动之经过》,《中国青年》1927年第8卷第3期。
㉘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㉚在湖北,1927年8 月至12 月,为响应“八七”会议精神,组织了以鄂南为中心的秋收起义。1928年1月至8 月,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发起了全省的年关暴动。1928年9 月至1930年6 月,在“六大”精神指导下,发动了一系列起义。1930年7 月至1931年10 月,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继续发动武装起义。湖北地区从1927年8 月起至1931年10 月止,由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大小小有数百次,这些起义暴动大多以失败告终。
㉞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 月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