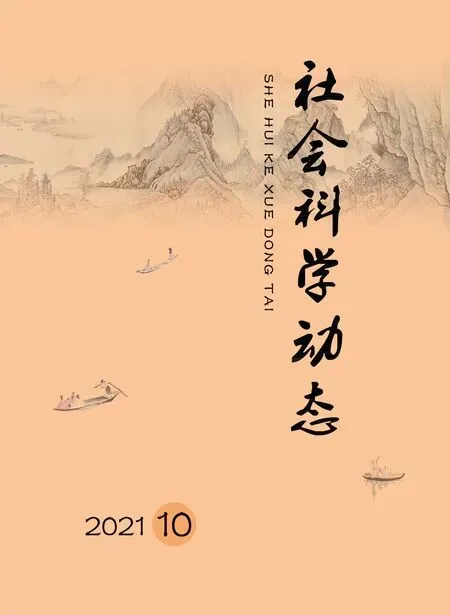《会见日》:当代中国县城日常生活的智慧书
2021-01-27梅兰
梅 兰
《会见日》是一部以吸毒者为对象的惊艳之作,书名波澜不惊,像是报告文学,每一篇却精雕细刻,叙事风格和意义指向极为丰富,说它是曹军庆的代表作并不为过。作为中国当代县城最耐心而果断的观察与书写者,曹军庆在《会见日》里使得这一题材小说既凝重严肃又扑朔迷离,他越来越跳脱单纯的现实世界框架,频频穿行于县城小镇人的犯罪行为与精神世界,像个小镇通灵师。吸毒/戒毒透射出县城小镇居民比普通人更为险峻的精神生活,这让这部小说更类似一部县城人生存状况之精神调查报告——他们真实的心灵状况,宛如新城开发中不断推进的城乡结合带一样荒凉而混乱,像极了某种灾难经过后的废墟。在《会见日》里,曹军庆选择了逆向而行,从戒毒者的心灵症状追溯还原他们生活的县城村镇,并藉此打开当代中国县城日常生活层层包裹的艰辛、寄托、痛苦、惘然与安慰。
一、日常思维异质性与底层生存策略
《会见日》共有20篇短篇小说,几乎全以戒毒所的学员为主角。开头一篇题名《会见日》:写一对农村夫妇骑着摩托车来探视正在戒毒所强制戒毒的儿子,妻子怀着二胎这几天正待产,见儿子的过程毫无喜悦或安慰,他们按照指示找到戒毒所领导澄清儿子没有精神病,得到了“需要观察”的标准答案,在要回去时发现车胎被人扎破了,又在修理厂补好胎后,准备回尖山村,但路上孕妇疼痛要生产,摩托车只好折回幸福县,路人帮忙把两人用绳索绑在一起,就这样孕妇到了医院并顺利生产。这个结尾其实是小说最具安慰的一幕,在失去一个儿子后,他们迎来了另一个孩子,完成了另一种“补胎”。小说集以《会见日》开篇似乎意味着:读者可以从这里进入到戒毒所和他们的故事,后面展开的所有故事都是戒毒者的悲欢离合;同时会见日也是一个出生和死亡的时刻,这对夫妇之所以再要一个孩子的前提是,他们已经假定吸毒的儿子死去,提前接受了这个结局,所以会见的时刻也是抛弃的过程,这也是后面那些吸毒/戒毒者的遭遇——他们大部分是一群被社会和家人抛弃的人。
惨烈或者悲剧命运并不是曹军庆小说最让人难忘的地方, 《会见日》在叙事过程中穿插进来的那些孕妇口吻的碎碎念补叙,才是小说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 “大约十个月前,关秀英果真怀孕了。可是她不愿意把孩子再生在方岗村。如果孩子长大了又吸上毒怎么办?是啊谁能保证他不吸毒?没人能保证。关秀英于是想不如移民吧,移民到一个没有吸毒的地方去。可是能移民到哪里去呢?移民是他们最为迫切的愿望,想来想去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移民的地方。最后还是关秀英想到了尖山村”①。尖山村是关秀英出生的那个村落,现在已没人居住。在这样的叙述中,读者不能不注意到曹军庆独特的幽默感,他不是把幽默强加于一位村镇孕妇,而是对关秀英的所思所想保持着足够的尊重和耐心,并且相信她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确信也并非源于作家的想象或沉思,而来自他对中国底层社会长期的观察和理解。
众所周知,从新写实主义以来,当代中国小说才真正开始从比较低的或者说平等的角度观察和书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也可以说当代中国小说里才出现了满足或挣扎于琐碎日常生活的普通人。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当代作家,比如刘震云。刘震云的小说擅长在日常生活中描述农民等社会底层人的遭遇和抗争,后者渐趋传奇化比如《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等,在类似题材小说中很具特色。在建国后前30年农村苦难遭遇的描绘力度方面,50后作家几乎是难以超越的,痛苦荒诞到极致的描绘也让这些作品中的底层人形象相当固化——他们总是被动地被驱使着欺骗和戕害,无力抗争那些人祸天灾,除了无限轮回或逃离苦难,小说几乎设想不出其他的出路。而刘震云的小说常常有着农民立场的对公权力的质疑和出色应对,这使得他的作品独树一格。但问题也可能是,由于太突出农民的聪明才智,小说情节就显得过于灵活伶俐以至于游戏化,有时候这让小说没有足够的反思空间,更缺乏诚恳的严肃性。刘震云的小说有着看透社会规则的成功者的自信,却也在游戏规则中失去了失败者的那份纯朴无争,或者说是简化浅化了社会底层世界的生存策略,而真正的底层社会要复杂得多,很难用一种二元对立立场去概括。
《会见日》的最后一篇名为《天上的街市》,看起来和其他小说距离甚远,这篇小说的主角不是戒毒者而是作家本人。 “我”结束了在戒毒所会见日的采访,想找个地方静一静,于是来到白龙山。“我”从白龙山下来时迷了路,夜晚误闯响堂村,住进了罗爷的家,这个村子恰好是“我”在山上看到的那个漂亮得宛如天上人间的村落。罗爷告诉“我”,响堂村尽管有着一栋栋漂亮楼房,村里却几乎没有人。罗爷说村子原来很穷,他自残一条腿多年以乞讨为生,后来在孙叔伟的带领下,全村富裕起来盖了新楼房,他才不再乞讨。第二天,在被确定了不是公安局的人之后, “我”才得知公安局从村子里先后抓走了700多人,全村青壮年都在蹲监狱,这就是村子空心的真相。唯一令村人欣慰的是带头人孙叔伟还没被抓住。孙叔伟带领全村人以电信诈骗致富,他设计了整个村子的建筑街道甚至垃圾箱,还修建了村灵堂,村里没人会背叛他。“我”回到山下的飞沙镇,发现孙叔伟已名扬乡里。小说在罗爷对孙叔伟的期盼和“我”的惶惑离开中结束。 《天上的街市》描绘了一个无视道德的罪恶之地,它同时又是一个共同致富的拯救之地,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村人敬仰和闻名乡里的能人,也是异乡人眼中的头号罪犯。小说中的“我”先是被如此荒凉的崇山峻岭中忽然出现的美丽村庄所吸引,然后就踏入了这漆黑一片的法外之地,好像走进了一个完全颠倒了世俗价值的陌生世界。可以说, 《天上的街市》是底层社会的一个角度独特的镜像,是底层人对自己的自救活动和英雄的描述,这里没有对公权力的抗议或嘲弄,只有丧失价值标准、不择手段的剥夺抢劫他人,而他们的心安理得就像每家每户在墙壁上安装的假窗帘一样令人费解,他们对犯罪事业的忠诚自豪也几乎只有现代艺术家才能与之媲美。
人们常常低估日常生活的创造力,它看起来重复而世俗,没有理论或主义指导下的那种丰沛的精神力量,但是正如理论家阿格妮丝·赫勒所发现的,日常生活所孕育的思维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日常思维是异质的:非拟人化的和拟人化的世界观以及思想动机,在日常思维框架中以未分化的形式自由地混合”②。日常思维可以同时是从日常生活经验类推出来,也可以不是,它们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为了解决现实难题,汶川地震的幸存者把自己和死者绑扎在一起骑车回乡的故事,启发了《会见日》的主人公简方明,他让路人把自己和正失血待产的妻子绑在一起,以尽快抵达医院。而农村孕妇关秀英,会认真考虑用移民来摆脱下一代可能继续吸毒的厄运,尽管她的移民目的地只有20多公里之外的尖山村可供选择。关秀英和诈骗犯孙叔伟一样,都不得不重新构思并找到生活困境的出路。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任何方式都在备选之列,包括日常经验之外的犯罪。一个靠电信诈骗致富而摆脱了贫穷的村庄,就是孙叔伟从受害经验逆推出来的犯罪奇迹,它就像天上的街市一样美丽而虚幻,伫立在谎言、欺骗和掠夺之上。但正如小说里的罗爷所质问的,在村庄所犯下的罪恶与它所遭受的悲惨之间,人们无法进行简单的衡量比较,也无法否认村人要过上正常生活的要求的合理性。
《天上的街市》其实是这本小说集的一个总结:不管是掠夺他人还是自我伤害,贫穷山村的电信诈骗和蔓延在城乡间的吸毒者一样,某种程度上是一些孤立无援者的变态自救反应。底层的日常生活藏污纳垢又事出有因,那些罪恶之人和其他人其实血脉相连,但人们却往往把他们推向陌生和对立的位置。这就如同人们对精神病人、癌症病人、传染病人等人群的另眼相看,似乎精神、生理疾病是他们被所谓正常人排斥的原因。福柯关注的愚人、精神病人、性少数群体和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就指向这些边缘人群。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告诉人们,区隔排斥可以用来维持传统社会的所谓正常秩序,让其他人以为从此就保证了正常人的安全,但事实上来自社会的隔离、歧视、不公,只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新的罪恶,直到败坏掉所有人的道德水准和生存环境。所有这些被排斥遗忘的人和普通人并无二致,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在日常生活里苦寻出路,他们以各种病态、变态甚至死亡传达出这个社会本身的结构性暴力问题,包括吸毒在内的各种病态变态并非仅出于个体原因,而是某些社会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症状。在这个意义上, 《会见日》并不仅仅揭开了普通人遗忘的吸毒者的暗流生活,而是正视当下社会的日常生活本身,它伴随着高度同质化结构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些吸毒戒毒者的审视下,忽然之间充满了谎言、欺骗和暴力,这即是当代小说能够带来的独特智慧。
二、城镇文化生态的悖反与日常生活的仿真性
曹军庆的小说通常具有反日常逻辑的特质,或者说展现了日常生活中相互支撑又互相拆解的复杂层面, 《会见日》堪称其中短篇小说里是难度最大的一部。 《会见日》聚焦于一些戒毒者、他们的亲属朋友以及管教者,但却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戒毒/吸毒者的故事集,在折叠的故事和复杂情感之下,小说讲述的实际上是一些正常生活边界上的危险之人,吸毒者对于家庭、朋友、社会来说显然是一种病痛,除了危害家庭和社会,他们也在自我伤害甚至走向死亡。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是戒毒者所打开的不同生活面向或时空维度,吸毒者类似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不可思议的骨刺,不断刺激着周围的正常秩序,探测出当代城镇文化生态的复杂与悖反。 《会见日》将吸毒等犯罪变成了打开县城日常生活的问题域的契机,读者从那里看到了不同的底层生存现状和法则,在分裂、狂躁、混乱中触摸到当代中国县城日常生活的仿真性。它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部当代城镇文化生态小说,从吸毒者戒毒者的视域,揭开了县城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悖反生态及仿真规则。
《卧底》将优秀缉毒警察郭一伟的残存日记徐徐展开,他从缉毒警察到吸毒者再到卧底英雄的身份轨迹,编织出松山镇警匪之间复杂的互动地图。《木头镇曙光肉联厂》里梦想当城管队员的古布从小痴迷秩序爱好执法,虽然进不了县城管大队,但进了曙光肉联厂的稽查队,他卖力焚烧私货猪肉的癫狂终结于一次尿检,从执法者以及秩序爱好者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个讽刺的自反性结尾。 《大同小异的故事》里的民营企业家王大同与孪生哥哥幸福县水利局副局长王小异完全是两种人,他们从小因为性格等差异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实际上却互相羡慕对方的道路。当王小异陷入赌博不能自拔时,还是王大同来为他还赌债和解围,在受人尊重的仕途与神秘凶险的黑道之间,王大同、王小异一模一样的外表和悬殊身份常常令人感到恍兮惚兮。《小镇兄弟》也一样,镇上的吸毒流浪汉冻死在垃圾桶旁后,却迎来了一场豪华葬礼,镇上名流云集的一次饭局,在一次警方缉毒活动之后就面目全非,一时间政治形势疑云重重。 《会见日》用人物、身份的重叠翻转,逻辑的自反,勾勒出县城政治中执法者与犯法者或明或暗的往来与互动,甚至犯法者即是执法者的悖反生态。其中,二者在话语系统中的相逢可能最富有喜剧色彩。
《吹牛者》里的安尔恕出了戒毒所却越来越怀念在里面的生活,他曾经因为演讲成功担任了班长,管理其他学员并享受了一定的权力,可是当他因怀念之前的生活再次吸毒进来后,却再没人相信他。其实安尔恕才是真正被改造了灵魂的学员,当他参加戒毒所国庆节演讲时,那些词语让他激动到晕眩, “他告诉魏志坚那些话语里隐含着‘奇异的力量’。他从里面出来后还坚持看书,坚持读报纸,坚持看《新闻联播》,就是为了不抛弃那些语言,也不被那些语言所抛弃”③。这就成了另一种瘾。换句话说,安尔恕在话语转换过程中染上了权力之瘾,这肯定不是戒毒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会见日》并不是作者第一次描述县城文化生态,在曹军庆笔下,县城的政治和艺术完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通甚至一体的,日常生活本身将二者融为一体。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都包含艺术的虚构手法和微妙调整,县城政治生活可能是对此最近距离的观察点,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哪一样又少得了对权力的熟谙呢。曹军庆的小说总是能在县城及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些戏剧性的瞬间,展现出日常生活的艺术创造力。 《什么时候去武汉》描述了县城里人们疑窦丛生、各执一词的婚姻生活。 《和平之夜》记录下整个县城的民众是如何一起编织所谓黑社会的风云故事。 《风水宝地》揭櫫休闲钓鱼活动与县城政治生态的隐秘对应关系,以及钓鱼活动本身的表演性质。 《纸上的父亲》里,为了儿子的健康成长,林美芬将正在戒毒的丈夫余世冰塑造为见义勇为的英雄。而《天上的街市》里,一个村庄都生活在犯罪和谎言中,只要诈骗能产生财富。和曹军庆之前描述的常常由权力和资本带来的仿真艺术相比较, 《会见日》不仅将仿真性推向了犯罪等方面,而且推到了一个最易忽视的方面,日常生活本身。
仿真的前提是真实的现实, 《会见日》的一些篇什可以说掀翻了这个前提,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应有之义》中。 《应有之义》采用第二人称讲述一个有一定家庭背景的县城公务员的一生,不管是上学、参军还是就业结婚, “你”过着一种被安排的体面的同质化生活, “你总是自动接受那些强加给你的东西。你永远活在道理里面……可怕的地方在于你没有自己的道理,你的道理全是别人给你的东西”④。作为药品稽查队队长, “你”像顺从父母的人生安排一样,收取了药店老板们竭力奉上的红包,也听从了他们的吸毒教唆。 “你”确实一直听话且温和,除了在父亲亲自探望的那个会见日,竟不合时宜地发作了癫痫。 《应有之义》中,日常生活的规则经验才是这篇小说的主角,而小说所呈现的“你”的空心化和失控,无疑是对日常生活法则的巨大嘲讽。
对于正常生活秩序来说,吸毒肯定是一种破坏,需要及时制止并挽救。 《会见日》描述了一些面对日常生活规训的吸毒者,比如《耳鸣症》以第一人称“我”叙述家人对“我”的帮扶过程及失败。妻子方艳红“现在就像是我读书时的辅导员,像我小时候的班主任。或者像我未成年时的母亲……她就是我的神父。我们频繁谈心,没有时间限制。白天谈,晚上也谈。一对一,就像我是她的帮扶对象。她在对我精准扶贫。她说: ‘我是在扶你的精神之贫。’” “我的精神已经荒芜,如何拯救我,忏悔仍然是重中之重”⑤。正是在妻子反复规劝和演讲中, “我”的耳朵里出现了各种噪音,就在又一次的谈话或者说上课中,不堪其扰的轰鸣声迫使“我”不仅把方艳红绑在椅子上,而且拿水果刀割破了她的嘴唇。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失败的挽救例子,小说里的耳鸣症患者就像是不堪忍受精神说教的一个精准隐喻,日常生活的规训实际上总是充满权力的说教,对某些个体来说这种折磨或伤害不可忍受,可能会产生更暴虐的后果。
很多情况下,人们以为用隔离的方式能够保证正常的生活不被那些堕落的人污染,但结果常常不如人意。 《去往济南的路上》开头一派祥和,孙正耀开车带着祖母和女友,准备去济南的监狱接病危的父亲保外就医。孙正是耀被祖母和伯父一家养育大,祖母有道德洁癖且竭力想把孙子培养成一个成功者……鄂北高速出口处的一次例行缉毒检查打断了温馨的家庭回忆,因为涉毒,孙正耀不得不中断旅程进了戒毒所,错过了和父亲的最后一面。小说设置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正常的社会生活厌弃罪人就像祖母想彻底抹去那个标志着家族耻辱的儿子一样,但是禁忌的东西总是会返回并重现,正如从小精心培养的孙子也会成为一名嗑药的瘾君子。
《会见日》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是所谓特殊人群的故事,人们可能一开始是抱着一睹罪恶暗流的心态步入会见大厅的,不幸的是,我们总是从那些最边缘最黯淡的人群身上,辨认出每一个个体共通的伤痛和日常生活里熟悉的百转千回,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亲切真实牢固的现实也在一瞬间变得陌生、虚假而且可笑。
三、异质性生命体验与爱
戒毒者处于社会日常生活宁愿忘掉的那些暗面,把吸毒者送进戒毒所似乎就是家庭和社会所能尽到的最大职责,或者说把这些人强制隔离出来,以免危害正常的社会生活。但这些被抛弃的戒毒者正是正常社会的一个个内窥镜,那些隐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虚伪、残酷往往以各种形式烙印在他们身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即是社会生活的真实面相和沉淀物,因为吸毒的缘起、过程、结局中,无不映射出整个社会的症状和病灶。对此, 《会见日》的做法是,让戒毒者自己讲话,作家像一个聆听者,极少参与对吸毒讲述的干扰,有些篇章干脆是第一人称的戒毒者自述,这种叙事方式的难度其实更大,因为吸毒者的思维和表达异于常人,幻觉和跳跃很多,但也因此带来了叙事上的极大自由,从吸毒者的视角重新观察和审视所谓的正常社会生活,也为这本小说打开了一种异质性的生命体验。
在吸毒者那里,生命的状态无疑是矛盾的,它与一种加速走向毁灭同时也是让人逃避痛苦的毒瘾纠缠在一起,诱惑与死亡来源于同一种欲望,生命成为自我反对和毁灭的欲望机器。 《会见日》里的吸毒/戒毒者很难用一种身份去概括,他们的身上会发生很多令人惊异的变化和意外,这让很多人物成了身份流动和叠加的人,或者说难以定义的人。比如说《读词典的人》里,瘦小的李应该自愿教高大的郝龙彪学习《现代汉语词典》,没人知道的是,李应该曾是网络著名写手,正在撰写一部巨著,为了写作他亲自体验了毒品,没有到达想象的自由之境,却进了戒毒所。 《外科手术》里,为了探索根治毒瘾的方法,善于思考的网络主播吴得夫自学成才拿起了手术刀,在网上直播为邱家声剔除那根毒品神经的开颅手术。 《线人》里吸毒濒死者魏志坚睡在了一块等待出售的空白墓碑上,他还拨打了上面的电话号码,为自己预订了一块墓碑,并留下了碑文“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在生者与死者、天才与病态、医生与病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烂人与英雄、缉毒者与吸毒者、义人与诈骗犯等等之间, 《会见日》模糊了身份界限,突出了人生的偶然性,它看起来既像是当代的醒世恒言,又像一部当代社会生活的亵渎书。
从生命状态来说, 《会见日》的戒毒者处于各种可能性的边界上,在正常生活与死亡之间暂停,事实上他们也一直处于自由与失去自由、清醒与幻觉等边界上,吸毒者可能是最难以定义的人群,他们能打破人类社会既有的一切界限,他们的身体成了快感与死亡、真实与幻觉、爱与禁忌、秩序与疯狂、人性与非人性的实验场。自甘堕落的吸毒者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群游离了所有家庭束缚、社会监控的逃亡者,他们失去了正常生活里的所有身份,他们就是德勒兹所描述的解域流或逃逸线,对他们周边的家人家庭、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社会秩序进行了解码或逃逸,揭开了一般人难以窥视的社会结构性暴力、规训路径和仿真现实,也在各种难以想象的人生困境中重新获得安慰与爱的能力。
戒毒者丧失了家人朋友的关心照料,也意外地得到了一些新的连接方式。 《会见日》描绘了某种让人陌生的社会关系,它不同于血缘、地域、阶层、性别等一般的家庭与社会关系,完全是在一些陌生人之间形成的关联,流浪汉、捡破烂的、吸毒者、农村妇女、癌症病人、心理病人、打工仔、医院保安、网友、毒贩、失职警察、戒毒所所长、快退休的老干警……他们的关系无法定义,没有世俗的利益驱动,更找不到道理和原因,只能说,就是一种剥离掉一切后的安慰与爱。巴迪欧说,爱“是一个生存命题:以一种非中心化的观点来建构一个世界,而不是仅仅为了我的生命冲动或者我的利益”⑥。在巴迪欧看来,爱是在世界之中发生的一个事件,无法预计或计算,也无法还原,但充满惊喜和戏剧性。只要读过《读词典的人》 《在美容院楼上》 《假发套》 《猜忌》 《一封没有寄送地址的信》 《线人》 《前妻之间》 《本命年》,人们会惊讶于那些发生在底层世界的安慰与爱,那些近乎一无所有的人在一种怎样的人生绝境却能互相给予安慰和希望。
从正常人的眼光来看,爱与安慰只能是正常人赋予吸毒者的珍贵馈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奉献。《会见日》其实推翻了这番假定,那些来自家人的所谓关心和爱,毋宁说是猜疑和监视, 《耳鸣症》里“我”在妻子的思想帮扶和全家的监视下,陷入越来越难以容忍的耳鸣症中,并最终割伤了妻子的嘴唇。 《纸上的父亲》里的余世冰进了戒毒所后,成了妻儿创作的素材,妻子将有缺陷的丈夫包装成见义勇为的英雄,儿子则把这个父亲写进作文,赢得了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羡慕,但余世冰从戒毒所出来时才发现,妻儿早已离他而去,虚构瘾君子为英雄的动机及过程,和爱毫无关系,只是对戒毒者最后的利用及剥夺。
对吸毒者的抛弃或者伤害并不是《会见日》关注的重点,相反,小说相当多的篇什写到戒毒者的爱与安慰,对爱的描述让人异常感动。比如戒毒者对家人的爱与依恋,这常常被人们忽略甚至漠视。《假发套》里19岁的秦继伟在戒毒所疯狂吞食刀片、铁钉、钥匙、书籍、塑料牙刷等异物,只是为了能够到外面住院,母亲可能会来看自己。 《一封没有寄送地址的信》是以“我”的口吻写的一封给爱人的信, “我”回顾俩人相识相恋成婚生子的经历,一直到爱人忽然失踪,真正令“我”心碎的是发现爱人可能已和战友私奔,失去爱的绝望让“我”染上毒品。 《猜忌》里,戒毒学员宋军民在分享会上讲述了自己原来的心理幻觉,他因吸毒后处处怀疑猜忌、毁物撞车被送进了强制戒毒所,可是他的妻子却随之开始猜忌以往的事情,疑心丈夫的所作所为和家产缩水都另有原因,各种证据在妻子的收集下一一到位,甚至弄到了所谓外遇的照片和悔罪书。这是一个家庭悲剧从吸毒向四周的延展扩张,猜忌对妻子精神的伤害一点不比吸毒对丈夫的伤害小。小说结尾处,宋军民“我一定要救我老婆”的喃喃自语,从戒毒者的角度颠倒了某种公认的正常/不正常等级,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着难言的脆弱性。
《在美容院楼上》有着一种自然流露的舞台剧意味,小说开篇对新城区的一段描述和雨果《巴黎圣母院》对教堂的描述具有同样的隐喻功能。某种程度上,新城区的美容院就是现代城市的巴黎圣母院,它前面门脸房的繁华光鲜供奉着人们的欲望和信仰,它后面那架简陋狭窄的楼梯通向的才是真实的生活场景:一屋子下岗职工和一个吸毒的弟弟,还有两位老人。焦光忠因吸毒时逃捕,摔断了一条腿,不得不回家养伤,但全家并不欢迎他,他也只和楼下捡破烂的老袁处得来。老袁其实也不叫老袁,袁克隆这个名字和那些破烂儿一样,也是他随便捡回来的。这两个人就是社会底层的底层,谁也不关心的那些人。因为开美容院的妹妹放在客厅的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焦光忠不得不面对妹妹的问询和怀疑,待到焦虑的他找出顺走电脑的毒友,对方已经卖掉换了毒品。为了筹集赎回电脑的一千块,焦光忠两天后想到了捡破烂的老袁, “他掀开床铺……他的嗅觉没有欺骗他。破烂的袜子、袖管、手套、内裤、破布条、烂手帕。总之,所有那些能够缠裹钞票的东西,那些能够盛装的器物,里面都零零碎碎地塞着些钞票。有零票子,也有整票子,还有钢镚儿。它们混在垃圾中,也像是垃圾,无法清理。焦光忠将拿到手的钱拢在一起……这一小堆金钱,共计一千三百二十多块钱”⑦。焦光忠拿了一千块,同时留下一张欠条。在攀登后楼梯的过程中,他打电话给毒友,想告知她事情已处理妥当,却得知她已去世的消息,就这样,他摔断了另一条腿,但最终将赎回的电脑还给了焦美丽。可以说,美容院的电脑危机最终是依靠捡破烂老袁的一生积蓄才得以化解。美容院的楼上与楼下的依附与被依附、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关系,在这场危机中以颠倒的方式呈现出来,小说因此用一个吸毒者的行动在冷淡虚假的主流社会中勾勒出社会暗影里那个有情有义的底层空间。
《会见日》实践了朗西埃所说的 “文学的职责”,即通过感性的重新分配让不可见变得可见,这不仅是说以戒毒者作为书写对象,而是从戒毒者的生命体验出发,重新感受、审视、表达周遭的一切,现实世界因此变成了戒毒者的镜像,有着难以言传的诡异构形。吸毒者的感官、情感、身份、社会关系、遭遇、命运的戏剧性变化,使得这部关于他们的小说——《会见日》成为一部富有挑战性的,展现当代县城日常生活的亵渎与安慰的智慧书。
注释:
①③④⑤⑦曹军庆: 《会见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07、140、43、78—79页。
②[匈]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⑥[法]巴迪欧: 《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