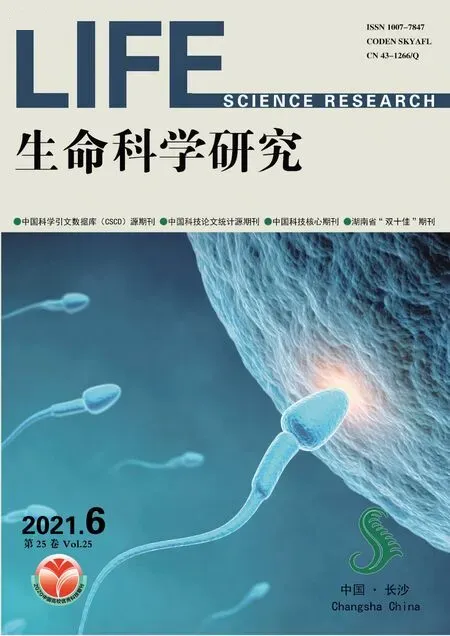环状RNA在抑郁症中的研究进展
2021-01-26谭桂凤肖颂华冯文辉刘中霖
谭桂凤,肖颂华,张 涵,冯文辉,刘中霖
(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科,中国广东 广州 510120)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一类以显著而持久的兴趣减退或是情感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情感障碍,并伴有认知、行为、生物学紊乱和躯体症状,其共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的概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1~3],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自杀率的特点,不仅给护理人员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同时也给社会和患者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估计,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致残性疾病,到2030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将跃居首位,成为全球亟需解决的精神障碍[4]。但目前为止,尚无肯定的生物学标记物用于抑郁症的诊断,其治疗主要针对临床症状,因此积极探索有效且简便可靠的生物学标记物对抑郁症的诊疗及预防至关重要。
抑郁症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们普遍认为其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疾病,但抑郁症的具体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神经病理学研究提示,大脑功能受损和突触可塑性改变可能导致抑郁症发生[5]。但单一的机制无法解释抑郁症的发病机理。近年来分子遗传学研究认为,环境因素和不良成长历程可能导致抑郁症患者某些特定的基因发生表观遗传改变,并相互作用导致神经元功能异常和突触可塑性改变等[6]。此外,有许多研究发现了抑郁症的表观遗传生物标记,如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微 RNA(microRNA,miRNA)和 DNA甲基化[7~9]。近几年,环状 RNA(circular RNA,circ-RNA)在抑郁症中的作用备受关注,抑郁症模型动物研究及临床研究结果表明:circRNA在抑郁症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能成为抑郁症的表观遗传生物标记或药物治疗靶点[10]。本文主要就circRNA的生物学特征和功能及其在抑郁症研究中的进展进行综述。
1 circRNA简述
circRNA是一类通过非经典方式反向剪接形成的,以共价键形成环形结构的内源性非编码RNA分子,分布广泛且种类丰富,具有高度保守性[11]和组织发育阶段特异性[12]。同时,circRNA是闭合环状分子,没有5'端帽结构和3'端多聚腺苷尾巴,因此可以抵抗RNA外切酶和分支酶降解,较其他线性RNA更加稳定,半衰期大约是信使RNA(message RNA,mRNA)的 5倍。circRNA作为一类广泛表达的非编码RNA,其生物学功能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1)对miRNA的海绵吸附作用。miRNA是一类非编码线性RNA分子,可通过碱基互补配对方式负性调节靶基因mRNA表达。通常,每个circRNA包含多个miRNA结合位点,可以作为竞争性内源RNA海绵吸附miRNA,从而影响miRNA对靶基因mRNA的调控。例如:circDYM通过吸附miR-9调节小胶质细胞活性并改善小鼠的抑郁样行为[13];2)与RNA结合蛋白(RNA-binding protein,RBP)相互作用。circRNA与RBP结合形成circRNA-RBP复合物,进而发挥调控底物功能。例如:circHomer1a通过与HuD相互作用影响突触基因表达和认知功能,从而参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展[14];3)翻译功能。传统观点认为circRNA为非编码RNA,但近年也有研究指出circRNA可以通过与核糖体结合促进开环表达,从而翻译成具有生物活性的多肽或蛋白质[15]。circ-RNA独特的生物学特征及丰富的生物学功能使其从众多非编码RNA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2 circRNA与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类涉及大脑发育及突触可塑性异常的情感性精神障碍,而circRNA在哺乳动物大脑中表达丰富且相对保守,具有发育阶段特异性[12]。此外,circRNA在神经元形成、发育、增殖、分化以及突触可塑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表达失调与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16]。因此,circ-RNA可能通过表观遗传修饰参与抑郁症的发生发展,这为诊断和治疗抑郁症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方向,有望作为抑郁症诊断、疗效评估和预后的生物标记物,且可能成为抗抑郁药物治疗的新靶点。
2.1 动物水平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神经胶质细胞异常激活及功能障碍与抑郁症病生理改变有关。在动物水平研究中,通过慢性不可预测应激(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CUS)或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抑郁症模型小鼠,Zhang等[13]发现circDYM可以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从而显著改善抑郁样症状,其机制可能是circDYM通过海绵吸附作用抑制miR-9活性,促使下游分子HECT结构域E3泛素蛋白连接酶1(HECT domain E3 ubiquitin protein ligase 1,HECTD1)表达增加,随之导致热休克蛋白90(heat shock protein 90,HSP90)泛素化增加、HSP90水平减少,从而减少小胶质细胞活化。此外,在CUS诱导的抑郁症模型小鼠中,Huang等[17]发现circSTAG1可以通过与N6-甲基腺苷(N6-methyladenosine,m6A)去甲基酶ALKBH5结合,减少ALKBH5向细胞核的移位,随后促使脂肪酰胺水解酶(fatty acid amide hydrolase,FAAH)mRNA的m6A甲基化增加和FAAH水平减少,从而改善星形胶质细胞功能,缓解CUS诱导小鼠的抑郁样症状。
另外,诸多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菌群在维持宿主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其通过微生物-肠-脑轴不仅可影响神经系统发育和功能,还可调节5-羟色胺、γ-氨基丁酸、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以及乙酰胆碱等神经递质,从而参与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生发展[18]。近年来,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和抑郁症模型小鼠的肠道微生物菌群紊乱[19~21],而抑郁症患者肠道微生物菌群被移植到无菌小鼠后可导致抑郁样行为,且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家族3(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 3,NLRP3)基因敲除小鼠的粪便微生物菌群被移植到受体小鼠后,可以显著改善CUS诱导的受体小鼠的抑郁样行为[22]。Zhang等[22]在CUS诱导的抑郁症模型小鼠中发现,circHIPK2水平显著增加;NLRP3基因敲除小鼠的粪便微生物菌群可能通过抑制circHIPK2表达,减少CUS对受体小鼠星形胶质细胞功能的损害及随后出现的抑郁样症状,其中部分代谢产物可能参与了circHIPK2介导的星形胶质细胞功能调节。该研究首次探索了在CUS诱导的抑郁症模型小鼠中微生物菌群与circHIPK2水平的相关性,揭示了宿主-微生物菌群-circRNA相互作用的新机制。
目前,药物治疗仍是抑郁症治疗的主要方法,探讨抗抑郁药物的分子网络机制有利于疾病的精准有效治疗。氯胺酮是一种新型抗抑郁药物,亚麻醉剂量的氯胺酮可以在抑郁症患者和抑郁症动物模型中快速产生疗效且效果持久,对传统抗抑郁药物耐药的患者也具有治疗效果[23~25]。在氯胺酮处理的大鼠中,Mao等[26]采用微阵列芯片筛查和实时定量PCR验证发现,海马区rno_circRNA_014900的水平增加而rno_circRNA_005442的水平减少。rno_circRNA_014900和rno_circRNA_005442有多个miRNA结合位点,部分miRNAs与抑郁症发病密切相关。同时,这两个circRNAs与神经发育形成、树突棘生长有关,并参与Wnt、PI3K-Akt、多巴胺能突触及轴突导向等信号通路,其中部分信号通路已被证实与抑郁症发生相关,例如:Wnt信号通路在抑郁样行为以及抗抑郁治疗中起重要作用[27~29];PI3K-Akt信号通路与抑郁症发生发展及某些药物的快速抗抑郁样作用有关[30~31]。此外,从药用植物中提取的活性成分在改善轻型抑郁症方面也具有潜在作用。例如:Zhang等[32]发现三七叶总皂苷可以缓解轻度慢性不可预测应激(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CUMS)诱导的抑郁症模型小鼠的抑郁样行为,其机制可能是三七叶总皂苷上调mmu_circ_0001223水平,促使与抑郁症相关的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c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1,CREB1)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水平升高。由于抑郁症发病机制复杂,新型抗抑郁药物的药理机制应涉及多个基因和通路。miRNA和circRNA在抑郁症病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circRNA可以吸附多个mi-RNAs,调控多个靶基因。因此,人工构建circRNA药物可能是抗抑郁疗法的新方向。
2.2 临床水平研究
目前,临床上诊断抑郁症主要依靠临床病史采集,缺乏客观诊断依据,易造成漏诊、误诊。近年来,在临床水平研究中,孔令明等[33]选取5名抑郁症患者和5名健康个体行基因芯片筛查,确定了10个差异表达的circRNAs,随后通过实时定量PCR验证circRNA水平,并采用24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items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评估抑郁症状,结果显示:circRNA_100679水平对抑郁症严重程度有较好的预测价值,而circRNA_002143和circRNA_103636水平与患者的抑郁症状有密切关系。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孔令明等[34]发现,抑郁症患者存在认知功能障碍,而circRNA_103636、circRNA_100679和 circRNA_104953水平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有一定预测作用,提示部分circRNA可能通过损害个体的认知功能调控抑郁症病生理过程。Cui等[10]在100例未服药的抑郁症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中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抑郁组有4个显著差异表达的circRNAs(hsa_circRNA_002143、hsa_circRNA_10-3636、hsa_circRNA_100679 和 hsa_circRNA_1049);随机挑选30例抑郁症患者,使用抗抑郁药物(包括西酞普兰/舍曲林/氟伏沙明分别联合米氮平)治疗4周和8周后复查circRNA水平,发现仅有表达下调的hsa_circRNA_103636在使用抗抑郁药物之后显著上调;进一步采用ROC曲线评价hsa_circRNA_103636的诊断价值,结果表明hsa_circ-RNA_103636的曲线下面积为0.632(95%CI:0.533~0.688),敏感性为0.73,特异性为0.65。因此,PBMCs中的hsa_circRNA_103636可能作为抑郁症的诊断和预后指标。
此外,抑郁症能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促进2型糖尿病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并发症,如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等;糖尿病也可以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且2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对个体影响极大,相比单纯的2型糖尿病或是抑郁症,其死亡风险更高[35~36]。这种联系提示两种疾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An等[37]发现全血中的circ-RNA-TFRC(transferrin receptor,TFRC)和circ-RNA-TNIK(Traf2-and Nck-interacting kinase,TNIK)水平在糖尿病共病抑郁症患者中较单纯的糖尿病患者显著增加。TFRC与胰岛素抵抗相关,是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因素[38~39]。而TNIK是一种脑内高表达的丝氨酸/苏氨酸激酶,通过调节突触组成和活性密度,对树突发育和突触传递具有良好作用,其表达缺少可导致智力障碍[40~41]。Jiang等[42]将研究对象分为糖尿病共病抑郁症组和单纯的糖尿病对照组,通过微阵列芯片检测出差异表达的circRNAs共247个,其中183个circ-RNAs上调,64个circRNAs下调;挑选4个显著差异表达的circRNAs(hsa_circRNA_005019、hsa_circRNA_015115、hsa_circRNA_003251和hsa_circ-RNA_100918)进行实时定量PCR验证,检测结果与测序结果一致;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4个circ-RNAs与18个miRNAs和529个mRNAs相互作用,其中 hsa_circRNA_015115和 hsa_circRNA_003251竞争性结合has_miR_761发挥海绵吸附作用,调控has_miR_761水平。相关研究表明,has_miR_761可以调节线粒体网络及促进学习和记忆[43],而has_miR_761高表达能抑制p38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p38 MAPK)信号通路[44]。因此,hsa_circRNA_015115和 hsa_circRNA_003251可能通过调节has_miR_761参与抑郁症发病,但是其确切的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同时,Jiang等[42]通过KEGG通路分析发现,hsa-circRNA_003251、hsa-circ-RNA_015115、hsa-circRNA_100918 和 hsa_circ-RNA_001520与甲状腺激素、Wnt、ErbB、MAPK 信号通路紧密联系。此外,针对糖尿病共病抑郁症患者使用八段锦运动疗法治疗前后的mRNA、lncRNA和circRNA水平,An等[45]首次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糖尿病共病抑郁症患者行八段锦运动疗法治疗12周后,有610种mRNAs、207种lncRNAs和266种circRNAs的表达水平存在差异,而血糖水平、抑郁症指数和患者健康问卷量表-9分数显著降低,提示八段锦运动疗法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通过调节lnc-RNA、mRNA和circRNA有效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和血糖水平,该研究为探讨八段锦运动疗法抗糖尿病共病抑郁症的潜在机制奠定了基础。
3 展望
表观遗传机制如miRNA已被认为在调节基因表达和抑郁症易感性方面发挥重要生物学功能[46],因此miRNA可能成为诊断抑郁症的生物标记物及治疗靶点。circRNA不仅可以通过海绵样吸附结合多个miRNAs,调控多个mRNAs表达,还可以通过与RBP结合影响基因表达,因此circRNA是研究抑郁症的新方向。虽然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但生物信息学、分子遗传学及转化医学等的发展为实现circRNA用于抑郁症诊断、治疗与疗效评估提供了可能性。未来,相关工作需进一步探讨circRNA在抑郁症发生发展中的分子机制,人工构建circRNA新型抗抑郁药物,监测circRNA在临床诊疗中的动态变化,这有望为抑郁症的诊断、治疗提供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