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者到画家
2021-01-25夏晓虹
一

夏晓虹
9月23日外出一天,晚上十点才回到家里。将近十点半,我的手机微信中忽然跳出三行字:“张京媛美国时间昨天半夜12点15分安祥地离世。我是京媛的姐姐。”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骤然从京媛自己的微信中,看到通知她本人过世的消息,无论如何都让我难以置信。于是立刻回复:“这不是开玩笑吧!京媛得了什么病?”
不愿或者不肯相信京媛的远逝,是因为今年我们还有过联系。1月27日,大年初三,京媛发来微信,用一连串的询问代替了每年例行的吉言:“晓虹,国内新冠肺炎流行,你们还都好吧?过节不聚餐了吧?天气冷,在家猫着也挺舒服的,是吧?”那时,她在为我们担心,尽可能地宽慰我们。
到了4月初,局面翻转,纽约、华盛顿疫情严重,成为重灾区,又轮到我写信去问候。京媛的回信语气少有地沮丧:
我们这里几乎全停止了,大家躲在家里,连门都不出。学校早就开始网上授课了,学校关门,学生都让回家去了。我这个学期是休假,所以不用学习网上授课。所有的社会活动都终止了,教堂和瑜伽所也关门了。我的朋友也不来画画了,很郁闷……樱花节城里空空荡荡,花都白开了。
对于是否需要口罩的问题,京媛也径直以“我连门都不出,所以不需要”回答。其中那种令人寒心的低落、悲观,我虽有感知,当时也只当作病毒肆虐造成的精神损伤,于是试图套用她的说法安慰她:“宅在家里,还是可以继续画画,这对调整心理状态有好处。”此言又引出她的感叹:“画画好呀,就怕看新闻。”并顺手发给我一张画作,说明:“这是最后一次去张明明家画的写生。我们现在都各自宅在家里,苟延残喘。”尽管京媛使用了“最后一次”这样带有终结意味的说法,我那时却毫不在意。没想到,这竟成为京媛最后写给我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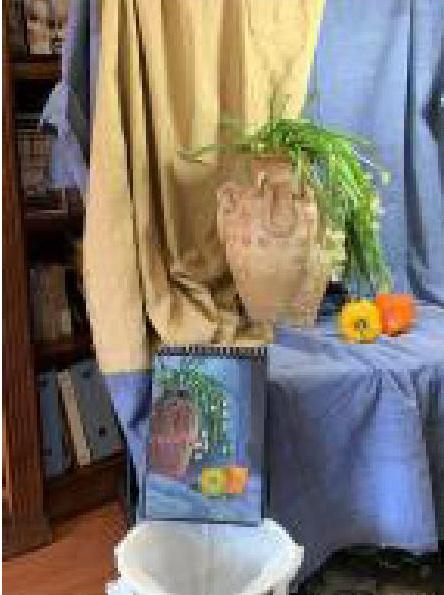
在张明明家中静物写生
接下来,7月11日,我发去一个在手背作画“太逼真了”的视频,京媛没有回应。9月17日,我又转发了一则“微信美国用户被封已经开始”的讯息,另外加上两句我对在美友人共同的担忧:“真的开始了吗?以后还能用微信联系吗?”这次京媛还是没有作答。不过,我仍然没有感觉到异常,照样归因于京媛的心情不好。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京媛一直是健康强壮的,我绝对想不到她已病势沉重。
二
和京媛成為同事而相识,是从她到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任职开始的。1989年初,经过乐黛云老师的努力,京媛从美国归来。我们此前一年刚刚搬进畅春园55楼的一层,京媛住在三层。相对于本楼住户的以家庭为单位,京媛的一人一间,已经属于特别的照顾。不过,一人独居,附近又没有食堂,做饭也会成为负担。所以,不知何时起,京媛成了我们家的常客,进而留饭也很顺理成章。起初可能还有些拘谨,菜会做得讲究一些,但很快就变成了我们有什么,她就吃什么,不再刻意准备。京媛于是也时常得意地向人介绍说,她是我们家著名的食客。其实,那时还真没有什么好食材,买条鲢鱼做一锅鱼粥,已经算是很拿得出手的美味了。可即便如此简陋,我们和京媛的终生友谊确是自此结下。
京媛赴美国读书多年,在康奈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才回来。依照我当时的认知,除了每天起床后必须喝咖啡外,京媛和我们这些“土鳖”生活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在房间里安装了一个窗式空调。那个年代,空调还属于奢侈品,我也是第一次在京媛那里见识了窗式空调机。我本来怕热,于是也不时去她那里“蹭凉”。而由于空调占据了窗户很大的一部分,京媛的屋里显得比较幽暗,白天也常会开着灯,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让我真正领略京媛这位留洋博士学术风采的,还是首次听到她的会议发言。1989年12月,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系为此举办了专门的研讨会。此会的一大新意是开始尝试采用国际通行的发表模式,一位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副教授魏纶(Philip F. Williams)的论文,即是由京媛担任评议人。不知别人如何看待,我当时尚未走出国门,所以非常想知道外面是怎样开会的,故而对京媛的讲评充满期待。京媛果然也不负众望,表现精彩。尽管已不记得她批评的具体内容,但其言辞之犀利酣畅,风度之从容不迫,在让我大开眼界的同时,也大为佩服。我还记得,京媛对自己的“表演”似乎也有点小得意,下来时,还对我们吐了吐舌头。
由于有了这份交情,1990年春,陈平原在家里组织一个小型读书会时,邀约参加的朋友中也包括了京媛。由于话题偏向国学,我猜想京媛未必有兴趣。不过,即使很少发言,她还是会到场,以表示对朋友的支持。1991年,平原与王守常、汪晖主编的《学人》创刊,设立了“学术史笔谈”专栏,京媛也在第二辑发表过《国内女性文学(史)研究的现状》。
现在看来,京媛在北大的那几年,是她意气风发、出成果最多的时候。那时的比较文学研究所还在初创期,所长乐黛云老师慧眼识人,组建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副所长严绍璗出身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熟悉日文典籍;孟华在巴黎四大获得博士学位,专长中法文学比较;从电影学院挖来的戴锦华,先已与孟悦合作出版过《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成名作,对大众文化更有持续关注。在这样的布局中,京媛显然需要撑起英语世界比较文学与文化这根大梁。
京媛也确实以出色的业绩证明了她的实力。最简单的做法是列举一下在北大五年由她主持编译的书目: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文学批评术语》,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除《文学批评术语》在香港出版,内地尚不多见,其他三本列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著作,俨然已成为那个年代的新经典。包括我在内的同代学人都会对张京媛怀抱感激,甚至把她看作是中国学术新风尚的引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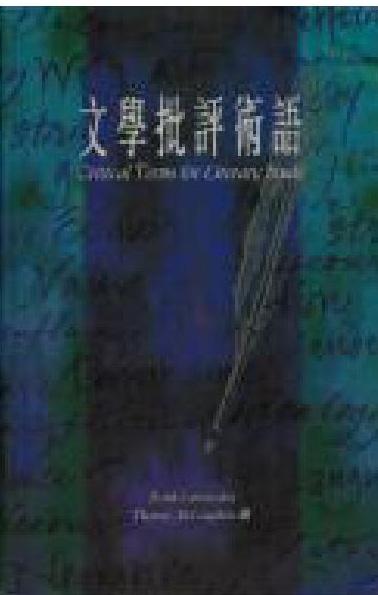
《文学批评术语》
而更让我欣慰的是,在上述诸书中,我对促成《文学批评术语》的翻译成书曾小有贡献。重读该书的《译后记》,我惊喜地发现了一段久已忘却的往事。京媛在其中提到,这本译文集是她1992至1993年春季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开设“理论翻译”选修课的成果。她说,在授课之前,自己对于“如何教授理论翻译以及如何设立预期的标准”,心里并没有把握:
一日在好友夏晓虹家聊天谈及此事,晓虹提问为何不选一本有价值的英文理论书籍,一边讲解一边与学生一道翻译,这样可以达到教学目的又能为学术界作出些贡献。教授理论翻译的最好方式应该是翻译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经验,即“译文/学书”。朋友之间的商谈往往要比一个人的苦思冥想更有启发,于是我采纳了晓虹的建议,初步订下授课计划。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排版的失误,上引文字中加粗的部分在原书中遗漏了,京媛特意打印、剪贴给我,包括“文学”中间的那个斜杠,都属于我的“独得之秘”。虽然翻阅全书,只有《绪论》的译者为京媛自署,其他均出以学生姓名。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课程结束后,京媛埋首在一大叠译稿中,一边抱怨,一边奋笔修改的情形。而我在1994年11月,也迅速得到了由她题签的“谨以此书献给晓虹”的厚重译著。这就是京媛当时的工作效率。
学术之外,我们之间当然还有很多日常的交往。其中值得一述的是1991年平原的香港之行。那年的1月到5月,平原得到李达三捐赠基金的资助,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研究四个月。京媛也在那里,只是早到早走一个月,大半时间二人重合。当时还有一位洪子诚老师的博士生陈顺馨,本是香港人,寒假回家,也常在一起聚。尤其是当年的除夕夜,三人在维多利亚港湾漫步,观赏灯饰。临近午夜,平原居然还找到一个公用电话,在嘈杂的人声中与我通话。这段难得的经历被京媛概称为“三匹马聚首香江过年”,因为他们三人同岁,都属马。
而我经常听平原说到的在港期间京媛的一则趣事,则与其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身份有关。某次,二人一起外出购物,平原出于照顾女性的习惯,有意帮京媛提袋子,结果受到不客气的训斥,因而学乖了。待京媛要携带巨大的箱子回京时,尽管她反复表示箱子太重,平原一直不吭声。最后還是忍不住,才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可不可以帮你拿?”京媛大喜,但仍责怪他:“你怎么不早说?”平原回称“怕挨骂”,京媛又教育他:“你应该有眼力见儿。小的、轻的东西就不要帮忙了,大的、重的应该抢着上。”虽然这个故事当着京媛的面讲过几次,并顺带嘲笑一下她的不坚定的女权立场,京媛却也不恼,还在一旁得意地笑。而我倒是从中窥见了她不为僵硬的理论所拘限的可爱的一面。
5月中旬,平原从香港归来。到家的次日,我们出去看一位朋友。傍晚回来,在楼下见到袁行霈老师,被告知家中遭窃,警察正在等候。幸好我们临走前突然想到,有人提醒过,顶楼易被盗,因此特意把平原带回的一袋港币塞入暖气片上的杂纸堆中,才得以逃过一劫。这其中就有京媛托带的机票款。
而最妙的是,就在盗贼光顾的那段时间,大约午后四点多钟,京媛晃过来看我们。她后来描述说:“你们家的两道门都大敞着,我进来后没有人,还以为你们有事临时出去一会儿。”因为当时我们已搬到畅春园51楼住,这个单元的结构比较特别,和东边的独门独户不同,我们这边是两家另有一个共用的大门。京媛于是悠闲地坐在我们的转椅上,翘着二郎腿,顺手拿起一本《读书》杂志看起来。这中间,她听到过脚步声,于是大声问:“你们回来啦?”见没人答应,又等了一会儿,她才怏怏离去,门也没关。我们问:“我家被翻得乱七八糟,你都没有任何怀疑吗?”她眼珠一转,理直气壮地回答:“你们家本来就那么乱!”这真是天知道,当时小偷可是把我们所有的抽屉都打开翻了个底朝天。事后还原现场,我们还得感谢京媛。她进来时,小偷很可能躲进了靠门口的厕所,她后来听到的脚步声,应该就是此贼溜出去下楼的响动。京媛的到来吓走了盗贼,反过来,我们倒该为她的安全担心了。
三
过从既密,我们也逐渐得知京媛在美国有男朋友,并且还曾经和这位中文名叫“韩思”的美国男士见过面。韩思的专业是哲学,人显得比较腼腆,当然,在语言沟通出现困难的时候,这种状态很常见。京媛起初也在设法为韩思在中国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不过,那时外国人在华,多半是做外教,不会进入专业。应该是不愿让韩思过于委屈,京媛最终放弃了她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安稳的职位,毅然到美国和韩思一起生活。
京媛是在1993年10月离开了北大。27日,她到我家吃了“最后的晚餐”,那时平原已到东京。记得赴美后,京媛先在中部一所大学落脚,随后才转到乔治城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任教。我听她讲过为了省钱,她和韩思租了一辆大卡车,轮流开车,长途搬家的壮举。应该说,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毕竟最先为她提供了大展才华的舞台,看得出来,她对比较文学研究所也充满感情。离去的最初几年,她每年回来,必定到比较文学研究所报到,为学生们做一次讲座。而我们也总会相约见面,吃饭聊天。
1997年春,平原和我有机会一起到美国访学四个多月,其间主要住在纽约,也借机走访了哈佛和加州大学多个校区。由于京媛的大学位于华盛顿,对于初次来美的我们,此乃必游之地。因此,从费城出来后,我们即投奔京媛而去。使用“投奔”一词,是由于京媛直接把我们安顿在她和韩思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里。说起来,华府和弗州是两个行政区划,感觉应该相距很远。京媛解释道,其实从她的住处到华盛顿,中间只隔了一条河,而弗吉尼亚的物价要便宜许多,所以,在华盛顿工作的人,多半会选择在此居住。
如同到其他几处一样,我们的游览必须要有学术活动开道。京媛为此也联络了乔治城大学东亚系主任,专门为平原安排了一场讲座。而全程中英、英中两边的翻译,都由她一力承担。尽管在我看来,京媛应付此事应是游刃有余。但她自觉到该系时间未久,生怕有点滴差错,力求完美,结果把自己搞得很累,这让我们十分过意不去。
尽管课务繁忙,京媛还是抽空陪我们参观了阿灵顿国家公墓与美国国家大教堂。更多的时候是她为我们准备好三明治作为午餐,然后开车送我们到某个博物馆,自己则赶去上课。等傍晚工作结束,再在约定的博物馆门前捎上我们,一起回家。实际上,华盛顿之行中,最让我们满足的就是参观博物馆。这里的博物馆是一个庞大的群落,一家连着一家。并且,区别于别处的需购门票,华府所有的博物馆都实行免费开放。我们于是尽兴地出入其间,虽只能走马观花,已觉快乐无比。并且,当时台湾故宫精华展“中华瑰宝”正在国家美术馆举办,由于其中含有从未露面的特级珍贵文物,其安全性曾在台引发舆论质疑。而我们适逢其时,赶上了这场盛宴,得以大饱眼福,幸何如之!这也成为由京媛安排的此行中最出彩的一章。
2005年秋,我们又一起到哈佛。这次平原逗留了两个月,我只有二十天。临近我归国前,京媛特意赶来见面,陪我们游览了两天。第一天在波士顿,主要活动是坐观光车看老城。第二天由她开车,带我们去罗德岛新港,参观美国著名的听涛山庄,此乃运输大王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家族于十九世纪末建造的夏季别墅。由于京媛很少来这里,路不熟,往返都多花了时间。我们晚上八点多才回到哈佛,和准备送行的学生吃晚餐。可以想见,一直在开车找路的京媛有多辛苦,但她显然把在地导游看作是对朋友应尽的义务,心甘情愿地耗时费力。
虽然京媛赴美后,从空间上说是距离遥远,但在情感方面,我们总觉得一如既往,毫无变化。比如,凡是需要用英文处理的事,我们最先想到可以帮忙的人一定是她。小到个人简历,大到会议论文,我们都会随时开口,请京媛出手相助。也因此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编辑的会议论文集《Paths toward Modernity》中,收入了一篇京媛帮我翻译的《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英文版,为我们的友情留下了物证。类似的打扰终止于京媛为我翻译巴黎会议论文提要之后,当我得寸进尺,再问她是否可以帮忙翻译全文时,京媛终于说她“撑不住了”,因为她也有一篇论文要修改提交,还有一篇约稿须在限期内完成。在说出“你是不是能找别人帮你翻译成英文”的提议后,她还满怀歉意地加上“谢谢啦”(2013年11月23日信),似乎不是我给她找麻烦,而是她亏欠了我。这也让我憬悟,京媛已不再年轻,精力有限。
依照我的观察,京媛在美国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对朋友,她总是慷慨大方。也不知从何时起,她开始承包我们的保健药。最初常用的是多维与鱼油,后来又增加了葡萄糖胺软骨素。每次她回国探亲,都会带好几大瓶这类保健品相送,并且要求我们,需要什么药一定告诉她,说:“我不存钱买棺材的。能在有生之年给朋友们做点事就是我的心愿。”(2008年5月17日信)
最让我感动的是2013年7月我们一起在巴黎开会的经历。出发前一周,京媛即写信给我,询问“有什么让我带的”。她也果然按照我的嘱托,买好了大瓶的多维和膝关节药。一天半的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旅游,其中有一整天在一起。那天的活动排得很满:上午参观莫奈博物馆;下午到奥赛博物馆,五点半闭馆出来;然后沿着塞纳河,走到亚历山大三世桥;经过大、小皇宫,转入香榭丽舍大道,一路步行至凯旋门,登顶拍照。由于一整天几乎都在不停地走路,与我们同行的年轻二三十岁的学生已经明显体力不支,登上凯旋门后,即瘫坐在椅子上,毫无留影的兴致。而直到吃晚饭时,京媛才从书包里掏出她送我的三大瓶药,正式移交。没想到她背着走了一天的药足足有三四斤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让我很觉不安。京媛却故作轻松地说:“这不算什么,外出写生也要带很多装备。”当然,这是在宽慰我。
最后一次和京媛见面,应该就是2015年平原到访华盛顿。她仍然一如既往地提前去仓储商店购买了大瓶的多维、鱼油等药,只是这一次,平原坚持自己付了款。
四
去國以后,京媛的研究状况我们其实不够了解,知道她仍然在编译写作,但数量明显减少。按她的说法是:“我实在太不多产了,不过有朋友多产就行了。”(2009年2月12日信)其中,她用力最多的应该是《中国精神分析学史料》。这本书也是她的博士论文副产品,对于她显然具有特殊意义。作为《编者序》的《重溯中国精神分析学的历史轨迹》一文,曾在平原主编的《现代中国》第八辑(2007年1月)发表。同年,此书由台湾的唐山出版社印行。鉴于“在当代中国,研究精神分析学与文学的关联有一些专著和文章,但是精神分析学在其他领域的作用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京媛此文及其所编史料集“就是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景观,使读者了解二十世纪前半叶精神分析学在中国各界的影响”。所说“各界”,包含了临床治疗、心理学、教育学、社会与文化评论以及文学批评,京媛的概述与选文对这段学说传播史的展现确实相当精准。记得当时京媛已感觉到她的中文表达在退化,所以请我帮忙修饰文字,我自然是义不容辞。
2009年,为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前一年接手系主任工作的平原操办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京媛本来很想参会,2008年底已在设想题目,3月份更是提交了《此心非彼心:重议五四时期关于“心”的科玄论争》的论题。不过,最终她还是缺席了。原因已记不清,可以知道的是,报题目时,她已一再说:“我的论文还没写好(差很远呢)”,“四月份咱们可以在北京见,希望届时我的论文会写好。我现在做事没有一点效率,很丧气”;“看来这次到北大开会的人很多,到北大班门弄斧有点害怕。我现在连斧子也举不起来,更别提‘弄了。让别人宰吧。”(2009年3月2日两信)
表面看来,京媛的逐渐淡出学术,与美国高校教师拿到终身职后,即可不再写论文情况相似,但其实还另有隐情。一个原因应该是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失望。京媛发来过一篇前耶鲁大学校长批评中国大学现状的短文,虽表同感,又马上话锋一转:“不过那位教授应该知道美国大学的现状也不怎么样:大学成了加工厂,学生学习就是为了分数,挺没意思。我反正是看透了,教书只是一份工作,有了这份不太费力的工作糊口,我可以做其他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事。”(2010年6月24日信)而她真心想做的事就是画画。

《华府樱花节》

张京媛在参展画作前留影

《操劳的一对儿》

《十全十美》
记不清从哪年开始,京媛迷上了绘画。因为是本校教员,她可以免费听艺术系的课,这使她的画越来越专业。2009年上半年她休假,本有来北大开会之议,但2月写信来说,她其实很忙,除写文章外,重头戏是“修四门美术课”(2009年2月12日信)。看来她的勤勉学习,绝不输于专业学生,而其水平的迅速提高,也足令我们惊讶。
至少从2009年起,对应我们每年寄送的旅游集锦贺年卡,京媛开始回赠她的画作照片。而且,每年秋天,她都会画一张色彩绚烂的秋叶图。至于華盛顿春天最美的风景,当然就是盛开的樱花了。下面是她2010年4月4日信中所写:
华府的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开始了,城里满是游客。昨天我和张明明(张恨水的女儿)去杰弗逊纪念堂湖边去画写生,张明明是职业画家,现在退休在家。她的水粉画十分棒,她画完当场就被人用150 美金买下了。我不愿卖我的水彩画,自己留着。给你寄去一阅。

《魔方映真》
我对这张画的评价是“很棒,画出了樱花的轻盈如雪,随风飘落”。信中提到的张明明,经常出现在京媛口中笔下,实为其交往最密切的画友。二人一起外出画画,甚至2018年初夏还结伴去了希腊,临写雅典和爱琴岛如画的美景。直到2019年2月,京媛还在兴致勃勃地筹划5月与张明明一同去西班牙和葡萄牙写生。而我所看到的京媛最后一幅画作,也是新冠疫情尚不严重时,她在张家所绘静物。

《水中石》
应该说,京媛对绘画的痴迷与对学术的疏离恰是此长彼消,前者日渐取代了后者的专业地位。这不只表现在为了写生而出国旅游,而且,融汇中西也已成为她追求的理想境界。2010年6、7月间,京媛要到北京住一个月,她很早就在筹划找老师,以期“全力以赴学国画”。她自陈:“我以后不会以国画为主,但学习不同的画法对发展我自己的绘画风格有好处。我目前和将来绘画的侧重点还是西洋画,因为我喜欢绚烂的色彩。(当然国画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书法和诗词,那得需要一辈子的功夫和修养,所以我也不敢高攀。)”(2010年2月6日信)此外,观摩画展也成了京媛的常课。2011年,她专门去科罗拉多的丹佛美术馆看过徐悲鸿画展;当我们到纽约时,她也强力推荐我们去参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并发来了谷歌名画网上的相关链接。2013年相聚巴黎时,她更是当仁不让地做了莫奈与奥赛两所艺术博物馆的专业导游,为我们指点图像中的精妙所在。
令人兴奋的是,京媛的画作也开始频繁参加各种画展。记录一下我所了解的最初情况:第一次应该是2010年9-10月,在北京798举办的海外画家艺术展,之后有同年12月马里兰州伊斯顿(EASTON)的节日画展,2012年12月厦门美术馆举办的第三届“龙在天涯”美籍华裔艺术家书画展,2013年春节华盛顿的华人春节画展,等等。厦门那次展览,京媛提供了六幅画作,她自嘲是“跟人家专业画家混在一起滥竽充数”(2012年12月17日信),但心里实在是很高兴。
接下来就是作品的接连获奖。第一幅《操劳的一对儿》(A Working Couple)画的是两匹拉车的马,2017年3月在华盛顿当地画展中获奖,京媛还是以半开玩笑的口气报告喜讯:“现在我可以吹嘘地说我是获奖画家了。”(2017年3月9日微信)当年12月,画了六个橘子与四个茄子的《十全十美》(Perfect Ten)又获“荣誉提名”(三等奖),画作被人买走收藏。我祝贺她“成了得奖专业户”,她回复说:“我还得拼命再努力画更好的画。”(2017年12月18日微信)。
我所看到的京媛画作中,最具创意的应该是《魔方映真》。那也是2017年12月的作品,原准备即刻送台湾参展,画展却延期到明年。2016年11月病逝北京的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的头像,被京媛设计在一个白底魔方上,魔方中间一层已向一侧转动,陈映真的脸部因此被分割开来。魔方顶部正中的一小块则被抽离出来,落在旁边,这个透明体中有一只瞪视的眼珠。我曾经给一位专业画家看过此图,他也赞赏不已。但我还是提醒京媛:“新作《魔方映真》构思和寓意都很好,不过,涉及敏感人物,评价可能分歧,且与艺术无关。”我的意思是,这幅画与政治牵连,如果不能得奖,也不一定是艺术原因。京媛解释说:“正因为陈映真是有争议的作家,我才把他构造成魔方,任人拼解,那所谓的第三只眼似乎是中间空挡抽出来的,但其实是无法还原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2017年12月18日微信)这也是我见过的京媛绘画中唯一显露其学术思想的作品,表现方式则是我喜欢的含蓄且智慧。
起意向京媛讨画是在2010年2月,我看到了她发来的秋叶、瓶花与模特三图,觉得她的技法已相当成熟,于是问她7月来北京时能否送我们一张画。京媛没有丝毫为难,一口答应,并且大度地表示:“等我画几张好点的画,让你挑一张。”并问我们想要哪一种介质(水彩、炭笔、丙烯、油画)、什么题材(人物、风景、花卉),我们挑的是水彩风景画。

张京媛为文章作者所绘第一张肖像画
6月7日她写信说:“我正在完成一幅水彩的‘水中石,自己想象出来的石头,没有原型,是半抽象画,看着像石头。(我想画一系列的石头,每一幅的石头都不一样。)这幅自己觉得不错,就先许诺给你吧。”只是,这幅画要先去参加北京798的画展,我们不会立刻拿到。京媛安慰我们说:“反正是天下只有这一幅,你们留着,以后等我90岁成名了,就可以卖大价钱了。哈哈,哈哈。”我当即回信,对她的慷慨相赠,让我们荣幸地收藏她的得意之作表示感谢。
而最终到手的画作却又并非这第一张《水中石》。因为两天后,京媛又有新发现:
今天我步行去附近的野生公园,看见河里的石头,发现自然石头比我画的漂亮多了,也不圆墩墩的。人的想象力哪里比得上大自然造物主呀。于是我又有了新的动力,我得赶快再画一个石头画,争取回北京之前完成。如果下一个石头画比我这幅好,那我就给你最新的。我想我的石头会越画越好。
果不其然,6月11日凌晨两点半,京媛画完了新的《水中石》方才睡觉。十点,她已迫不及待地发信报告:“醒来在自然光线下看看这幅畫觉得还不错,比前一个石头好看。于是就送你这幅吧。这幅跟上幅尺寸一样,但有流水的幻觉,也更潇洒些。”这张画确实有了一种水中光影的亮度,比前一张更灵动。我不由赞叹:“看来你绘画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京媛却并不要求先拿去参展,而是到京后,直接去中国美术馆对面的小店订制了画框,我拿到的已是可以直接挂出的成品。这就是京媛,乐意把最好的作品以最完美的方式留给朋友。
最让我得意的是,京媛还为我画过两张肖像。这应该是缘于平原的提议。他曾经去一位台湾学者的家中做客,看到一幅女主人的画像,据说是绘出了其人青春的美丽与中年的睿智,让平原很是羡慕。京媛于是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接受了这份委托。2013年7月底从巴黎回去后,她就开始酝酿。其间,因为带状疱疹的干扰,直到12月2日,京媛才完成了画作。这张肖像是根据我在巴黎的一张照片画的,她说自己当然改了不少:“今天早上张明明来我家画画,看到照片说:我把你画得年轻了10岁。这就是绘画和摄影的不同。绘画可以创作,摄影就难了。”并说,如果我不喜欢,她就自己留着。我自然要求保存,虽然这张画“确实是把我美化了,年轻不说,还胖了”,总之,时光留下的缺陷,在京媛那里都得到了修复。不过,因为京媛曾说过想画出我的手,手在绘画中很有表现力,可惜没有合适的照片,我于是得陇望蜀,提出要她再画一张有手的肖像。
这一次京媛确实是郑重对待。为了配合我的对襟短袖衣,我们特意去一位共同的朋友家中拍照,因为那里有满堂的中式家具。京媛带来她姐姐非常高档的相机,我也在各种光线下,从多个角度摆拍了很多张照片,作为画像的素材。这是2013年底的事。我不知道京媛是何时开笔的,但这幅油画她应该画了很长时间。平原2015年4月去华盛顿时,京媛本来说,“那张画也画得差不多了,再画几笔就完了”,希望能够让平原把画带回(2015年2月23日信),却由于家里装修,无法作画而搁置。直到2017年5月2日,她才发给我完成的作品,微信中说:
晓虹,这幅画一直没画完,放在那里。这些天我又拾起来,加了未名湖的背景,换了衣服的色彩。就这样了,好不好就是它了。给熟人画肖像,我有精神负担,因为想讨人喜欢,但往往事与愿违。你要不喜欢,我就自己留着,没事儿。
我觉得这张画像的神情更接近本人,当然还是比本人年轻。京媛高兴地说:“我就成心把你画年轻的,皱纹全部去掉了。标题叫‘永远的夏晓虹。”我后来按照她的图示,配了金、棕两色的双色框,装好后拍照给她看,她表示满意。因为前一幅肖像京媛没有寄给我(应该是不愿意把不够满意的画作送出),这幅未名湖背景的肖像画就成为京媛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品。
五
京媛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朋友的很多生活细节,她都会清楚记得。2012年12月17日她来信提起:“明年是蛇年,该是晓虹的本命年了,一定找根红腰带扎上,欢欢喜喜过本命年。”她也一再说到,2014年“就是我和平原的本命年了,我们三头马(加上陈顺馨)一定得聚在一起举杯庆祝!咱们越老活得越皮实,前途无量(亮),得自个打灯笼找乐子了”。虽然筹划了很久,京媛也如约在前一年的12月回到北京,可惜平原那时主要在香港,三匹马的聚会没能实现。我想,京媛会觉得很遗憾。
2008年,京媛迷上了瑜伽,自己练功后,感觉很好,也向我推荐。先是告诉我可以上网买《三天速效瘦身瑜伽》等DVD教材,我回说:“希望我家里能够放下瑜伽垫,据说那也是很占地方的。如今房子里又堆满了书,夺占了我们的活动空间。”京媛当即斥责我的推脱:“书重要还是人重要?不要本末倒置嘛。瑜伽垫可以折叠的,用时展开,不用时就卷起来放到储藏室里,不占地方的。”(2008年9月20日信)过后,她干脆直接刻了盘送给我。她所认定的好东西,总希望能够和朋友分享。
京媛尽管很早出去留学,而且最终选择了在美国生活,但她最牵挂的还是中国这片故土上的人与事。现在读她2008年5月17日信中的一段话,仍然让我动容:
这几天我天天看中文网络视频报道四川地震的消息,常是边看边哭,心都碎了。除了给国际红十字会中国分会捐款,我再不知道能为震区的人们做些什么了。个人的能力太小了。虽说世事无常,但亲眼看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在一瞬之间翻天覆地确实万分震撼。那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将怎样走完剩余的时光,我连想都不敢去想。人们好苦呀!我最感动的是那些反映人性光芒的舍己救人的事例,此时此刻“我们都是中国人”。(911时我可没想过“此时此刻我们都是美国人”,当时和现在一样我是中国人。)祈求上苍保佑芸芸众生,保佑我们的家园。祝你和平原大家都平安!
我知道,京媛是在四川读的大学本科,汶川地震带给她的疼痛才会格外强烈。而此信也让我明了,京媛之所以滞留美国,纯粹是为了她口中的“我家韩思”。
也许与练瑜伽有关,更可能是京媛心中固有的善根,使她的关爱对象甚至超出了人类,而普施于动物世界。也就是说,素食对她不只是一种新的饮食习惯,也已经成为一种深入心灵的信仰。某次,我偶然在信中提到去西北旅行时,牛羊肉没少吃,她立刻发来《当人肉被动物从超市买回来》的微信文档,说是让我们一笑,实则我看到这些反向思维的画面时,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
可以认为,善待自然作为一项根本的生命原则,已浸润在京媛的日常生活中。2017年11月,当我告诉她平原手术的情况,她立即给出的建议是:“吃素,吃 G-BOMS (greens, beans, onions, mushrooms, seeds) 蔬菜,豆类,洋葱类,蘑菇类,种子类。少油少盐少糖。”并极力推荐“自然疗法之父”葛森(Charlotte Garson)的《救命圣经:葛森疗法the Garson Therapy》(2017年11月26日、2018年1月23日微信)。联系此前几年我接受点穴治疗时,她对我说:“西医就知道动手术,殊不知切掉了器官也除不了病根,尤其是内分泌之类的病。还是中医好,点穴按摩针灸激发身体自愈能力,而且不伤身。”(2010年12月5日信)据此,我推测京媛在确诊癌症后,大概并没有动手术,而是希望依靠素食、瑜伽以及绘画等自身的修心养性控制住病情。
按照她姐姐所说,“京媛是癌症晚期4B,坚持了三年多”,那么,她的发病还在平原之先了。不过,京媛不仅从未对我们提到她的病症,而且照样关注着朋友的健康。她叮嘱我“一定每年按时做体检”,同时询问“需要什么药,只要不是处方药,我可以买来给你们寄去”(11月26、29日微信)。我们也太相信京媛身体的健壮,并一直记得她对自己的期许——“等我画到90岁”(2011年11月30日信),以致完全忽略了来信中透露的点滴资讯。2019年4月我们到哈佛访学,写信向她报到,她回复说:“知道你和老平原来波士顿了,很高兴。一直没有跟你联系是因为近来我的身体不大好,蛰居在家,无法像过去一样邀请你们来DC玩,实在无奈。”(2019年4月16日微信)我那时只想到,她刚卸任系主任,需要好好休息,不要去打扰她,却完全没有料到她已重病在身。
京媛邮寄我的肖像画时,正好得知平原生病,于是多寄来一张夏天画的荷花,说:“荷花讨吉利,祝他早日康复。”(2017年11月26日微信)她看了平原病中自娱所写的字,也要“求一幅260字的《心经》,不要太大幅的,我的墙壁面积有限”。虽然我表示平原没写过这么多字的书法作品,要有耐心等,她也肯定地回答:“没问题,我有足够的耐心。”可她既没有如其所说“明年回国再取”(2018年10月17、20日微信),平原也没有料到留给京媛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这份欠债于是成了一件无法弥补的终生憾事。
重温京媛过去写给我们的那些文字,2018年4月7日的一段记述最见其惦念至情与我们之间的深厚交谊:
晓虹、老平原好吗?前天晚上做梦,见到老平原坐在高背椅子上,桌上堆满了书和报纸文章,说是给我的。你坐对面。你们俩都笑嘻嘻的,后来他站起来走了,说是一会儿就回来。你我对视着,然后我就醒了。坐起惆怅半时。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如今剧情反转,此情此景,今夕何年?
六
最近几年,京媛每年都会说到“回来”这个话题。2017年1月23日的信中预告:“我争取今年回国看看你们,今年老平原该退休了吧?我来祝贺老平原的荣休。”2018年4月8日再次订约:“我9月底去上海开个会,然后争取回北京看看。到时一定跟你们联系。”回国看看的念头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年。可以想象,这边有她的亲人和朋友,她实在放不下。然而,所有的期盼最终都未能如愿。2020年9月23日,京媛在美国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
初闻噩耗,我的第一反应是,京媛如果留在国内,或许可以躲过此劫。但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不断与书信中的京媛对话,我的想法已有所改变。如果始终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工作,京媛多半只能成为一位好学者,她归国后的出色表现已足以证实这一点。美国生活却为她在学术之外,打开了生命中的另一扇大门。在绘画的世界里,京媛自信自得,享受着充分的快乐与自由。作画虽然也很辛苦,但在京媛那里永远是其乐无穷。她经常说:“我画画完全是因为爱好,做的是‘无用功,心里充满欢乐。”(2010年6月24日信)如此毫无功利打算,心无旁骛,她的画技与画境才能突飞猛进,迅速达到专业水准。2012年12月,得知她参加了厦门画展时,我对她说过这样的话:
和专业画家比肩“厮混”,可见你是大器晚成,确有绘画天赋。只是没有早一点展现,有点可惜。当然,如果你更早以画家成名,我们可能也就无缘聚首了。因此,你还是现在这样——越画越精彩更好。
京媛对自己的未来其实也很看好,虽则期之以“90岁成名”,而她的现时状态又总是以“拼命”来形容。計日程功,其作为画家的前景正是未可限量。偏偏天不假年,刚刚65岁的京媛竟提前谢幕了……
京媛的遗愿是骨灰撒入大海。在去世一个月后,她的两个姐姐与韩思已经为之完成了海葬,连韩思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也坚持上船出海,送京媛最后一程。我听到消息,心中萦绕不去的只有“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句诗。
(责任编辑:马倩)
